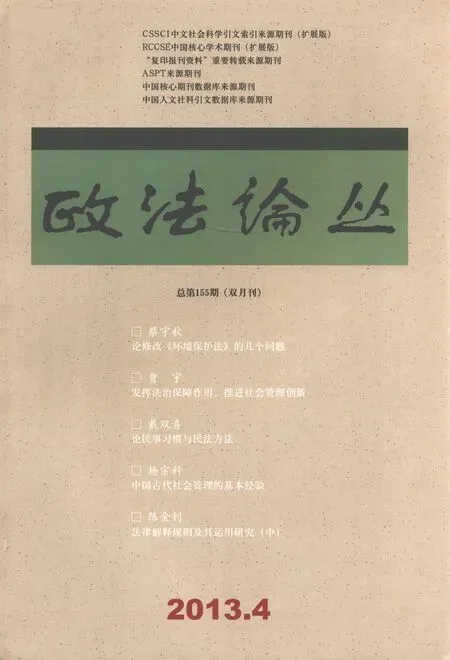亲属间死亡赔偿请求权研究
——兼论亲属间伤害赔偿
石春玲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上海 201701)
亲属间死亡赔偿请求权研究
——兼论亲属间伤害赔偿
石春玲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上海 201701)
亲属间一方导致另一方伤害或者死亡,受害者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损害赔偿权利与侵权法的价值并不契合,所以对亲属间的死亡赔偿请求权应予以适当限制。赔偿权利人只限于死者一亲等亲属,并且赔偿只限于加害人故意的情形下。直系血亲间一方致另一方死亡,死者近亲属不得提起赔偿请求。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还应注意赔偿与相关当事人的权利、责任的冲突问题并予以适当协调。
亲属 死亡赔偿 正义价值 限制
近些年,亲属间人身伤害案件呈上升趋势,①相互间请求伤害和死亡赔偿的案件越来越多,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转型期各种矛盾和冲突也大量发生在有亲缘关系的人之间,殺亲案时有发生,轰动一时的北京大兴灭门案即是此类案件的典型,私人汽车的大量拥有也使一些车祸受害人往往是乘坐肇事者车辆的肇事者亲属;另一方面,受害者法律意识和个体意识逐渐觉醒,萌生了较强的求偿欲望。本文旨在探讨亲属间的死亡赔偿请求权,对亲属间伤害赔偿以及侵权法在亲属间的作用也有所涉及。
一、亲属间死亡赔偿正当性分析
(一)从侵权法的正义价值看
侵权法的正义价值在于,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侵害了另一个人的人身、财产或名誉,那么他就造成了损失,并且根据正义原则他必须赔偿受害人从而消除这种损失。[1]P91、102有学者进一步阐述认为,无视道德并利用自己的力量伤害他人的强者被判定打乱了由道德所确认的平衡或平等秩序,由此正义要求尽可能由做错事的人去恢复道德上的平衡状态,在简单的盗窃案件中,正义仅仅要求返还被窃物,而损害赔偿则是这个原始观念的延伸。[2]P162亲属间一人致另一人受伤或者死亡,按照侵权法正义价值的一般要求,致害人应给予受害人相应赔偿。那么在亲属间是否存在或者需要这种正义?
某种意义上,亲属间因为血缘与婚姻联系,构成一个密切的共同体。任何共同体必须是基于众所周知的条件而共同生活的一群人,这些条件界定了其成员的身份,并使每一个成员知道他应该为其他成员提供什么以及其他成员应该为他提供什么。有一件事是任何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所必需做的,这就是对所有伙伴成员的福利的实际关心。如果一些成员遭受苦难,他们的伙伴成员就有义务采取各种实际步骤去解除他们的痛苦。[3]P42-49家庭成员之间,较之一般共同体成员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在亲情上,可以说不分彼此,水乳交融,在法律上有相互扶养、相互继承以及共同共有的财产关系。“家族的身份这种我们现代最多地叫作‘身份’的东西被保留下来并按照现代人的平等观念分解为血亲和姻亲等身份”。[4]P53亲属、家庭历来是各国受法律保护的单位,意大利最高法院甚至将使丧失子女看作是对为宪法所保护的家庭之完整和统一的侵害。家庭成员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给另一人或者数人造成伤害或者死亡,是给其造成了苦难,对方或者另外的一人或者数人对加害人通过法律的手段进行追究,也断不能认为是解除家庭成员的痛苦。“诉讼具有负价值。尽管个别的原告能获得损害赔偿和其他救济,但全面地看,诉讼纯粹是一种损失。因此从社会的立场或从潜在的原告或被告的立场来看,应避免打官司。法律体系和程序存在的理由在于它是一种较轻的邪恶,用法律来解决争执胜于血亲复仇、野蛮的犯罪与暴力等”。[5]P37由此看来,家庭成员之间,无论采取违法的、暴力的还是合法的、诉讼的方式,一方加重另一方的损害或者是痛苦都与家庭共同体的伦理和福利相悖,侵权法的正义价值不应在家庭中得到彰显。不仅如此,我们多年前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中所忧虑的人格商品化,在直系血亲间就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了。当这种因为生命的丧失而使亲人间在财产上锱铢必较的时候,我们已经看不到他们之间的伦理亲情和对家庭的维护,而只能沁到商品的气息了。
但是,生命和身体乃是个体的最后载体,当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发生伤害乃至致死的事故,家庭这一共同体是否可以完全包容而不需按照一般的正义要求予以补偿?有学者认为:近代法律否认侵害生命本身为近亲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由,是缘于法律的个人主义立场。[6]P639这一观点是针对发生在一般人之间的生命损害,依照这种观点, 基于法律的个人主义立场,每个人的生命专属于个人,个人死亡,其近亲属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没有正当性,从而近代法律否认对于生命损害的赔偿。那么进而推之,发生在亲属之间的生命损害,其他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更属不当。
然而,亲属与家庭都是一定范围的,但是又相互迁延的。发生在亲属之间的生命损害,损害在死者的近亲属之间漫延,死者的近亲属与加害人之间可能并无亲密的亲缘关系,这时,家庭或者家族的共同体效用削减,其财产的诉求就加大了。当一个共同体对它的所有成员来说,庞大到使他们无法保持一种亲密或经常的联系时,就产生了区别乃至分离。中国老百姓称“人大分家,树大分叉”,人和财是家的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二者只要结合为一个共同体就可以称之为家,学界一般称之为“同居共财”。[7]P69-72从经济的角度,中国家庭的属性在于共财就说明为什么家庭只存在于一定范围的亲属,这样,超出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的赔偿请求就具有了一定正当性。
(二)从侵权法的功能价值看
学者普遍认为侵权法具有惩罚、教育、预防、补偿等功能,但侵权损害赔偿如若存在于近亲属之间,那么这些功能则难以实现。现代社会中,惩罚、教育以及遏制、预防这些功能在通常的侵权责任中已经有所弱化,在亲属间更是难以发挥作用。在亲属间故意发生的伤害甚至杀戮这种极端案件,加害人完全罔顾人伦亲情,即使剥夺其财产给予受害人,也难以通过由此引发的利益机制、道德心理机制和舆论机制对本人或者社会产生惩罚、教育以及预防作用。而在过失造成的亲人间损害,相信对加害人来说,更是一种意外的事故,亲情的作用已经促使其尽到足够的注意,亲情的发生的机制作用也远大于利益、道德和舆论机制。
与其他法律的救济功能相比较,补偿功能,即用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来补偿受害人所受到的物质或者精神损失的功能为侵权法所特有。对家庭成员个体的人身伤害救济最终仍以财产来表达,而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财产关系又常常是共同的,或者是有不可分割联系的,例如丈夫导致的子女死亡,妻子作为求偿权利人的情形,再如未成年的哥哥打伤了弟弟,两人的父母要作为哥哥的监护人对弟弟进行赔偿,要作为弟弟的监护人代理诉讼并接受和管理获赔的财产,这样侵权法的补偿功能就几乎没有价值。我们承认某些家庭成员有自己的特有财产,但因为共同生活和消费以及共有的关系使这部分特有财产的独立性大大减弱,尤其是通过侵权诉讼而享有的这部分财产所牺牲的其他成本要远远大于所得补偿本身。
从侵权法的实施成本看,众所周知,侵权制度有着高昂的成本,在英国,支付受害人1美元的纯利益时,就将花费85美分,美国的研究表明了更高的运作成本,在汽车事故中为1.07美元,而在产品责任中为1.25 美元,这些高额的交易成本是侵权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主要原因是权利人和赔偿来源之间的对立关系,赔偿依赖于因果关系和过错的认定,而这又要求进行证据调查,并且经常发生争议。[8]P139在亲属间的诉讼中,因为两造双方是亲属关系,除国家承担的司法成本以外,大部分成本都是由同一家庭成员承担,所以其诉讼的投入产出更加得不偿失。另外,侵权法因为举证和审理程序的限制,其时间成本也较大。如果说一般人之间的侵权诉讼尚有正效益的个案,那么在亲属间的这种诉讼就几乎没有正效益了。
(三)从有关法律的发展历史看
我们注意到,早期的普通法对于夫妻之间的侵权诉讼予以豁免。从很大程度上讲,这种豁免是在普通法不合理地赋予已婚妇女的地位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已婚妇女的丈夫具有行使妻子权利的法定资格,所以,如果一妇女打算对其丈夫提起诉讼,则须由丈夫来提起,任何的义务均指向他自身,所以丈夫可以放弃这一诉权。如果丈夫打算起诉妻子,也准用同一方式。与此相关的父母——孩子之间的豁免形成于美国,与夫妻间的豁免类似,支持该豁免的理由在于保持家庭和睦,而且不干涉亲权。[5]P308现代侵权法废除了原来规定的夫妇之间不得相互起诉以及子女不得起诉父母的免责规定,从一些被豁免的案件来看,这种废除是完全正当的,例如子女起诉其父母的理由中有被非法囚禁于精神病院中、有被父亲强奸、有被异常虐待。但是仍应看到,因废除上述豁免,则人们或许会认为侵权法会成为反家庭暴力的重要工具,至少在非穷人家庭会如此。但是,虽然这种诉讼有时也有人提起,但仍然极少,[9]P1268相反,管束令、离婚法、警界援助、刑事自诉(有时是公诉)、对儿童的保护性服务和看护以及特别家庭暴力法案等,却成为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求助的主要法律工具。[10]P333在我国,婚姻法对家庭暴力规定了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其所在单位予以劝阻、调解,由公安机关予以制止,构成犯罪的通过提起自诉或公诉追究刑事责任、以及离婚损害赔偿等救济措施。唯一的损害赔偿救济措施只适用于离婚夫妻间,这说明我国法律不肯定侵权损害赔偿在家庭中的适用。
还有一种中西法律暗合的现象值得本文加以思考,这就是亲属间人身侵犯,罪重于非亲属间人身侵犯;亲属间的财产侵犯,罪轻于非亲属之间的财产侵犯。[11]P51古希腊人认为侵害亲属不仅伤害人伦,亦伤害了“神伦”,因而以特重刑罚惩之。在古罗马,杀害近亲属为“弑亲罪”,设置了“弑亲审问官”专审此种案件。[12]P216并对于这种最可怕的罪行,处以特异的刑罚。这一观念在现代欧洲法律中仍得显著体现,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前保加利亚、前罗马尼亚刑法也有杀伤亲属加重处刑的规定。与侵害人身不同的是,亲属间的财产侵犯,在无论中外的古今法律都采取了比一般人间的财产侵犯更加宽厚的态度。自唐到明清,“亲属相盗”专条成为封建伦理法律化的典型体现之一,整个古代法的原则是:本着“同居共财”、“亲属不分财”之伦理,规定亲属间财产侵害之罪责轻于常人间的财产侵犯,通常是减免刑罚。以上观念不仅为中国法律,也为众多外国法律所共持。这充分说明,亲属间的人身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应该以更大代价保护的,亲属间的人身侵害,犯罪恶性更重,社会危害更大,因而刑罚予以严惩。而亲属间的个人财产利益则是弱化和模糊的,“亲属分财”不利于亲属间关系的凝聚,因而对亲属间财产犯罪从轻处置。死亡赔偿是亲属间的人身伤害以财产表达,是“亲属分财”的典型表现,无疑是对于亲属关系的双重损害。
(四)从死亡赔偿自身特点看
死亡赔偿与伤害赔偿有着显著的区别,这就是请求权人的转换。伤害赔偿的权利人是受害者本人,而死亡赔偿的权利人已经转化为死者近亲属,这就可能出现以下几种伤害赔偿所没有的情形:其一:侵权人本身也具有请求权人资格,例如丈夫导致妻子死亡,丈夫作为配偶也是第一顺序请求权人,未成年的子女导致父亲或者母亲死亡,其本人是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有请求必要的生活费资格,这样权利与义务同归于一人;其二:亲属间的伤害赔偿,因为相互交织的血缘和婚姻关系,就可能出现请求权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关系远于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关系。例如丈夫致妻子死亡,妻子的近亲属只有二亲等的兄弟姐妹,请求赔偿的人,其与受害人的关系较之加害人更远,其三:部分请求权人与加害人之间已经不具有近亲属关系。例如夫妻间一方导致另一方死亡,请求权人包括加害人的岳父母、死者的兄弟姐妹等,这些与加害人之间作为姻亲关系,已经不属于近亲属。其四:损害赔偿与共同财产分割以及继承关系、扶养关系相互交织,当事人身份重叠与冲突,财产的功能与利益重叠与冲突。
基于亲属间死亡赔偿的上述特点,我们认为亲属中的一部分人因为其另两个亲属的加害和受害而得到赔偿,于伦理上值得商榷;由死者较近的近亲属赔偿较远的近亲属,似乎有违公正;曾经的姻亲关系亲属或者与加害人处在较远亲缘关系的亲属,其请求赔偿有一定的正当性;在各种身份和权益交织的情形下,要完全厘清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似有难度。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亲属间的死亡赔偿,既应承认其一定的正当性,又要看到其侵权法价值与功能的大大削弱,以及与亲属家庭价值的极大冲突,因而在承认亲属间的死亡赔偿请求权的前提下,应对其有所限制。
二、亲属间死亡赔偿请求权适当限制之我见
(一)请求权人限制
1. 直系血亲间一方致另一方死亡,其近亲属不得提起赔偿请求
直系血亲是生育自己和自己所生的上下各代亲属,直系血亲一方致另一方死亡的情形,发生在父母子女间或者祖孙间。直系血亲无论是一亲等还是二亲等,其所包含的生命传承、情感依赖、生活互助、伦纲礼常价值无与伦比,这些价值远大于侵权法的矫正正义价值。“血缘关系在亲子之爱方面产生了心灵所能发生的最强的关系,关系减弱,这种感情的程度也就减弱”,[13]P389就生命现象本身而言,直系血亲对于生命是施与授的关系,相互间的血缘成为生命传承的纽带,从而成为永不消亡的天然联系,正是这种天然联系使亲属关系无法因为个人主义而消亡。因此,在一方致另一方死亡的情况下,受害人的近亲属不得提起损害赔偿。
以父或者母致子女死亡的情形为例,依现行法,第一顺序请求权人包括受害人配偶(加害人儿媳或者女婿)、子女(加害人孙子女)、父母(包括加害人),这一顺序请求权人和受害人的关系以及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关系都是同等远近的一亲等亲属关系。第二顺序请求权人包括受害人兄弟姐妹(加害人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加害人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加害人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这些请求权人与受害人的关系,常常远于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关系,如一个母亲致儿子死亡,其另一子请求赔偿,则请求人和受害人的关系比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关系为远。如果致害是发生在祖孙间,则请求权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较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关系相同或者更近。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上述请求权人除晚辈死者的配偶以外,都与加害人有非常紧密的血亲关系,并且大多数是直系血亲关系。一方面,直系血亲之间天然的紧密联系足以排斥任何其他人的关系以及利益,这种人身关系即使受到了损害,也远非其他任何利益可以弥补;另一方面,至亲之间,一组血亲成为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关系,另一组血亲因为前一组血亲的加害与被害,获得经济上的利益,有悖伦理。
从情感上说,如果加害人的行为是无心之过,有谁比加害人受到的伤害更重?除了遭受丧亲之痛,还有内疚与悔恨;如果加害人的行为是有意为之,严厉的刑事处罚和殺亲所引发的背天理、失伦常都足以使加害人付出足够的代价。此外,还有直系血亲致害的加害人、受害人、请求权人之间交织着密不可分的扶养关系、继承关系、共同财产关系以及赔偿关系,这些关系的厘清都使死亡赔偿的价值和功能大打折扣。
2.请求权人只限于一亲等
我国法律目前承认一、二亲等亲属的赔偿请求权,在没有一亲等亲属的情况下,二亲等亲属得请求损害赔偿,并且对一亲等和二亲等亲属在赔偿数额上没有差异。近亲属之间的死亡赔偿,二亲等亲属作为请求权人,加害人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加害人是一亲等亲属,其与受害人的关系较之请求权人更近,例如丈夫杀害妻子,妻子的兄弟姐妹作为请求权人请求赔偿。另一种情形是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是二亲等亲属,两者与死者关系同样远近,例如哥哥致弟弟死亡,两者的其他兄弟姐妹请求赔偿。两种情形下,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加害人都应属于有请求权资格的人之列。
基于损害转移理论,人身伤害乃至死亡损害具有扩张性或者转移性,随着伤害的进行性加重,各种损害逐渐向近亲属扩张和转移。如果极其轻微的伤害,人身和财产损失还仅限于本人承受,随着损害加重,受害人不仅不能履行作为亲人的照顾和扶助责任,自己尚需人员护理,及至残疾,对被扶养人不能尽扶养义务,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为人配偶,不能履行角色职责,加重亲属的财产和劳务负担,个人痛苦向亲属蔓延,最终不能承受生命之重,亲属忍受丧亲之痛,亲属身份和结构破坏,所有的人身和财产负担由亲属承受,全部的损害转嫁到近亲属身上,近亲属的生存状态恶化。所以在近亲属间,丧亲之痛无以言表,亲人之间常会产生恨不得代替亲人承受痛苦和死亡的情感。死亡的损害转移给近亲属以另外的方式承受着。[14 ]P93不仅如此,死亡损害转移的程度随着亲属之间的亲疏不同而逐渐减弱。受害人的死亡,除了其本人生命损失外,对一亲等亲属造成的损害最甚,对于其二亲等来说影响较小,也就是转移的损害更小,至于更远的亲属,这种损害逐渐消逝。如果说一般人之间的死亡损害,我们尚没有足够的理由否定死者二亲等亲属的赔偿请求权,那么在亲属之间的死亡损害,二亲等亲属的赔偿请求权应予以完全否定,而让位于家庭的统一和稳定以及亲情和伦理的价值。
(二)主观过错的限制——以故意为限
尽管侵权是发生在不特定人之间的行为,侵权关系是发生在不特定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侵权人和被侵权人之间总是因某种必然和偶然的原因而处在同一时空或者发生某种先前联系的,如果当事人之间具有紧密的生活联系,交往越密切,侵权发生的概率越大。亲属之间,尤其近亲属之间是人们交往最密集的社会关系,也是最大概率处在相同时空的人际互动。同时,调查表明,亲属之间,婚丧嫁娶、婆媳矛盾、妯娌纷争、继承、赡养纠纷、分家析产不均等都能引发矛盾,而且较之一般邻里纠纷更不容易和解,相互间的期待更强,失望更甚,矛盾愈烈。侵权法,就其最原始而且最简单的形式而言,这种侵权法律制度必须具有的核心内容,可以这样简洁地加以表达——“让开”(keep off)。[15]P5-7可见,基于亲属交往的这些特点,规范一般社会交往关系的侵权法规则与归责原则如适用于亲属之间的伤害纠纷,则与这些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并不契合。
事实上,如果简单套用上述侵权发生概率的一般认知,似乎亲属之间要常常笼罩在纠纷和流血的阴影之中,但现实并非如此,因为适应亲属之间交往规则的亲情关系、伦理规范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美国学者克廷的解释,当事人是具有风险的社会交往模式的参与者,也是可能的加害人和受害人。但是,那些可能的加害人和受害人,他们同样都是自由和有道德的人,力图确定追求他们主张的符合善的观念的社会条件。[15]piv置身某种特定社会关系的当事人,比之法律更能选择适合其人际交往的规则。亲属关系中,亲属成员们谨小慎微、不计回报地关注和呵护着彼此和家族的共同利益,法律在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在婚姻家庭中,法律的缺陷似乎可以暴露无遗。法律的重心在于,按照普通的、合理的人的行为标准,对具体行为进行判断;而道德上的判断更加注重每个人的主观与心智状况——更加强调那些故意或者蓄意损害他人行为的可责罚性。
如前所述,既然亲属之间是用亲情和伦理在维系和调解彼此的关系,法律在其中就无法发挥准确的纠纷处理作用。例如,某祖母看护孙女,因一时疏忽,孩子从高处跌落死亡,孩子的父母起诉要求孩子的祖母赔偿。如果说孩子的祖父母违反了谨慎看护的义务,那么这种义务又源于哪里?孩子的祖母与邻居、朋友等不同,后者假如以语言或者行为承诺对孩子进行看护,那么其对孩子就有一种特定义务,这种义务的产生是源于其本人完全自愿的意志或者先前看护孩子的行为。对孩子进行照管是父母的法定义务,祖父母并无这一义务,但孩子的祖母对孩子的看护,虽无法律或者合同上的义务,却有道义或者亲情或者复杂的人际关系方面的责任,对非法律义务的违反,要承担法律责任似乎对加害人有失公允。
还有很多情况下,家庭伤害的发生,往往是加害人和受害人共同过错作用的结果。例如生活中发生的很多家庭车祸,往往是作为乘客的家人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妻子乘坐丈夫酒后驾驶的汽车,哥哥为了赶时间不断督促开车的弟弟超速;再如有些伤害行为的发生,受害方的出轨、言语刺激、家庭暴力等等都是对方行为发生的诱因;有些精神病人实施的伤害行为,受害亲属往往就是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总之,亲属之间因为密切的人际交往,对于损害的造成,加害人和受害人相互间的过错相互交融,不分彼此。
综上,笔者意欲表达的是,近亲属之间的伤害和死亡赔偿纠纷,法律只应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发挥其作用。即加害人只有在故意行为导致的损害中进行干预,支持受害人的赔偿请求,而在加害人过失的情形下,不应支持受害人的赔偿请求。
三、亲属间死亡赔偿请求权行使的几个问题
(一)责权能否相抵
如前所述,导致亲属死亡的加害人,常常是对其亲属的死亡享有赔偿请求权资格的人。实际情形有四种:一种是加害人是同一顺序中唯一的请求权人,死者的其他亲属都是第二顺序请求权人,例如儿子导致母亲死亡,儿子是母亲唯一的一亲等亲属,但除此之外,母亲还有其兄弟姐妹等二亲等亲属;一种情形是加害人与另一受害人为同一顺序请求权人,例如年轻的母亲产下一畸形婴儿,婴儿的父亲独自将婴儿杀死掩埋;第三种情形是加害人是第一和第二顺序中唯一有请求权资格的人,例如弟弟将孤寡的哥哥加害致死,这种情形没有研究的价值,因权利人和义务人完全混合。“尽管人们对权利的理解各自保留着独立性,但权利产生的主体基础必须是多方的,自己对自己主张权利,或者自己对自己的权利侵害,在法学研究领域的价值是不大的。”[16]P17;第四种情形是加害人是第二顺序请求权人,但尚有第一顺序请求权人,例如哥哥对弟弟加害致死,但弟弟有配偶和子女或其他第一顺序亲属,这种情况下,第一顺序权利人的存在完全排斥了第二顺序人的权利,也不存在加害人的权利和责任冲突问题。我们需要研究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形下,加害人的权利和责任能否相抵的问题。
第一种情形,即加害人是受害人唯一的第一顺序请求权人,是其请求权与赔偿义务相抵,请求权消灭,还是由第二顺序请求权人顺位向加害人行使赔偿请求权?如前所述,在一般死亡赔偿案件中,我们尚且认为死者的二亲等亲属,其赔偿请求的数额应当相应减少,而在近亲属损害赔偿中,我们对于第二顺序权利人的请求权持完全否定态度,至于加害人为唯一的第一顺序请求权人,同样的理由我们否定第二顺序请求权人的顺位,而主张加害人的责权相抵。传统侵权法从侵权人角度,探究其侵犯了受害人的什么权利,犯了什么错,现代从受害人角度,关注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关注损害或者利益的成本,亦即赔偿不是因为有权利、有过错,而是因为有损害。[17]P352某人死亡,除其本人权益受损外,客观上,其近亲属利益受到损害,一亲等亲属所受损害最甚,所受损害远远大于二亲等亲属,即使该一亲等近亲属本人是加害人。至于该加害人是否获益?如其行为为过失,则不能有任何获益,如其为故意,则可能有犯罪的快意所得,[18]P113这种快意并非所谓民法上的利益所得。此时,如果无视加害人的损失,而转由其受损害更轻二亲等亲属,接受加害人的赔偿,则是对加害人的多重惩罚。在同一亲等关系中,加害人是一亲等请求权人之一,则其应享有份额应当免除,否则其他受害人则获得了不正当利益。
在侵权法上,有所谓损益相抵、与有过失等原则,基于与这些原则相似的法律精神,我们赞成亲属间死亡赔偿的权责相抵,以达致亲属间的利益公平。同时,在责权相抵的情况下,某些亲属间的死亡赔偿诉讼无法启动,则可以减少交易和评估非财产损失的成本,减少诉讼,淡化家庭纠纷。
(二)请求权行使当事人的牵连性
发生在甘肃的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后常某,将妻子段某杀死,经鉴定,常某患有精神病,段某的家属在得知无法追究常某刑事责任的消息后,随即向安宁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赔偿,段某的家属认为,常某的行为给其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于是,段某的父母作为原告将常某及其法定监护人常某的父母告上法庭,要求3被告赔偿其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失等共计22万余元。该案起诉后,法院认为并没有穷尽本案利害关系人,遂要求将常某的1岁儿子追加为原告,共同参加诉讼。在非亲属间的死亡赔偿中,一般不存在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当事人的牵连问题,例如甲致乙死亡,乙的近亲属作为共同原告,基于共同的利益,自然会向甲共同提起诉讼,而在亲属间的损害赔偿,交织的亲情与多重身份利益会发生只有死者的部分亲属主张请求权的问题。案中常某的儿子因年幼以及监护问题,在解决技术问题后追加为共同原告似乎不是问题,而大量的此类案件中,部分有请求权的人则是基于与加害人的亲情关系而放弃权利。这样,我们须探讨如下问题:
第一:部分权利人放弃权利,是否对其他权利人的权利构成影响?或者说,只有部分权利人主张权利能否启动诉讼程序?从实体法角度,某人因侵权导致死亡后,其多个近亲属作为权利人,尽管相互间有牵连性,但每个人均是独立的权利实体,而且较之一般伤害的共同诉讼当事人,其利益的共同体弱化,例如前述案件中,如果段某的死亡是由其他人造成,则段某的父母与段某的儿子甚至配偶常某,则是密切的权利共同体,而在对常某的诉讼请求中,当事人的各方则利益完全对立或者疏离,利益的差异非常突出,某人对权利的行使不应对其他人构成影响。从诉讼法角度,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一人放弃权利也不应对其他人的诉讼启动构成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4条第2款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放弃诉讼权利的,应当允许,并记录在案。
第二,如何认定权利人对权利的放弃?对于未提起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有人认为应通知其作为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参加诉讼,如其没有表示放弃,则应将其列为民事诉讼原告人;如其明确表示放弃诉讼权利,则视其放弃权利,可不列为民事诉讼原告人。我们认为亲属间的死亡赔偿,权利的放弃既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默示,也就是说权利的主张必须是明示。但是在共同诉讼中,应给予其充分的意思表示机会,而不是如通常的共同诉讼,如不明示放弃权利则将其作为共同诉讼的原告。
第三,部分权利人放弃权利,是否影响其他权利人的赔偿份额?亦即部分权利人放弃权利,其权利份额是由其他权利人享有还是在份额内免除侵权人的责任?这里涉及到对于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认定问题,如其作为权利人因近亲属死亡所受损害的赔偿,则各个近亲属的请求权内容是分离的,近亲属死亡,每个人基于自身所因此受到的损害获得相应赔偿,各自行使各自的赔偿权利获得各自的赔偿份额,尽管通常是一揽子做出赔偿,并且对各个亲属的所受的不同损害加以区分很难。如果作为生命损害的补偿,也就是命价,则其赔偿是一种定额赔偿,不因为权利人的多少以及是否有权利人放弃而有差别,部分权利人放弃权利,其份额由其他权利人承受。如果将死亡赔偿金认定为近亲属继承来源也就是死者收入来源的损失,则各个继承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0条规定:继承诉讼开始后,如继承人、受遗赠人中有既不愿参加诉讼,又不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应追加为共同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不再列为当事人。这样,部分近亲属放弃权利,其放弃份额也是由其他权利人承受。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主流观点原持收入来源丧失说,从现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看,我们认为更接近于“命价”补偿。但是在亲属间损害赔偿中,各自的利益又超越了统一的“命价”,基于各自的损害产生了各自的权利。这样,部分请求权人放弃索赔,则应认为其豁免了侵权人的相应义务,而不能将其应得的补偿额转由其他权利人承受。
(三)权利冲突的协调
1.侵权赔偿义务与法定扶养义务冲突,扶养义务优先
侵权赔偿与法定扶养义务的冲突历来存在,例如侵权人导致受害人死亡或者重伤,侵权人有限的财产如何平衡受害人极其近亲属的赔偿权利以及加害人的被扶养人的受扶养权的确值得商榷。在亲属间损害赔偿中,此类冲突更加复杂化。还以常某杀妻案为例,案中既有加害人常某和受害人段某共同负有扶养义务的未成年儿子,有受害人段某负有扶养义务的父母,还有加害人常某负有扶养义务的父母。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侵权赔偿与法定扶养义务冲突的情况下,应以法定扶养义务优先,加害人的财产优先支付加害人或者受害人负有扶养义务者的扶养费。在上述三种享有扶养权的人中,三者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同等的,由法官考量各自的具体情况,如有无其他收入、有无其他扶养人等而优先保证最弱势者的利益。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加害人的被扶养人,其生存利益的保障同样重要。具有相同精神的立法规定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1条规定,继承人中有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即使遗产不足清偿债务,也应为其保留适当遗产,然后再按继承法第33条和民事诉讼法第180条的规定清偿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5条也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所必须的生活费用及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须的物品不得查封,也就是说在执行时当履行赔偿义务与生存权存有冲突时,应以生存权为先。
2.侵权赔偿与继承冲突,侵权赔偿优先
亲属间的损害赔偿,在进行赔偿时,应将死者财产与加害人财产区分,将加害人的财产与其他亲属的财产区分,死者财产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处理。加害人的财产用于满足赔偿要求、具有法定扶养义务人的扶养权利要求。有些加害人因严重的犯罪行为导致加害人死亡,因而自身被判处死刑,这样其自身财产也面临赔偿、扶养与继承问题。前文论述扶养与赔偿冲突,扶养优先,在赔偿与继承的冲突中,则应是赔偿优先,即优先满足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有剩余财产才由其继承人继承。
综上,近亲属间的死亡赔偿,其侵权法的价值受到了亲情伦理等诸多制约,而应予以适当限制,笔者承认以上探讨仍欠成熟和全面,亲属间的侵权责任体系的建立和探讨迄今几乎空白,谨以此文抛砖引玉。
注释:
① 山东省平邑县法院2006年统计近三年受理的近亲属间人身伤害赔偿案件逐年递增,分别占所有伤害赔偿案件的15.73%、22.88%和26.47%。参见李培前:《试论近亲属间人身伤害案件增多的特点原因及对策》,http://old.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606/08/207705.shtml2012-11-28。
[1] Jules Coleman & Arther Ripstein,Mischief and Misfortune,41 McGill L.j.91,102(1995).
[2]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
[3] [英] 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M].夏勇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
[4] 徐国栋.人身关系流变考[J].法学,2002,7.
[5] [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
[6] 杨立新.侵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7]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M].张建国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8] [美]约翰 G·弗莱米.关于侵权行为法发展的思考:侵权行为法有未来吗[A].私法研究(第3卷)[C].吕琳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9] Ira Mark Ellman & Stephen D. Sugarman , Spousal Emotional Abuse as a Tort, 55 Md.L. Rev.1268(1996).
[10] [美]斯蒂芬D·舒格曼.20世纪美国人身伤害法的演变[A].侵权行为法比较研究[C].王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1] 范忠信.“亲亲尊尊”与亲属相犯:中西刑法的暗合[J].法学研究,1997,3.
[12] [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3] [英]休谟.人性论[M].关天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4] 石春玲.死亡补偿费研究[J].法学论坛,2007,1.
[15] [美]格瑞尔德·J·波斯特马.哲学与侵权行为法[M].陈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6] 朱兴文.权利冲突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17] 张民安.法国侵权责任根据研究[A].私法研究(第3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8] [法]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ResearchonDeathCompensationClaimbetweenRelatives——And Damage Compensation between Relatives
ShiChun-ling
(Law Schoo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701)
When one party of relatives caused damage or death to the other party, the rights of damage compensation of the victims themselves or their close relatives aren’t fit into the value of tort law, so proper restriction should be exerted on compensation claim between relatives. So the person of having the right of claim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first degree of kinship, and only the compensation is possible when the inflictor is in the case of intentionally. Between the direct lineal descendants, when one party caused in injury to the other party , close relatives of the dead should not have the right of claim. When dealing with such cases,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flict of compensation between the right of relevant parties, the conflic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given appropriate coordination.
relatives; death compensation; justice value; restriction
DF526
A
(责任编辑:张保芬)
石春玲(1964-),女,山东文登人,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人格权法、侵权法。
1002—6274(2013)04—1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