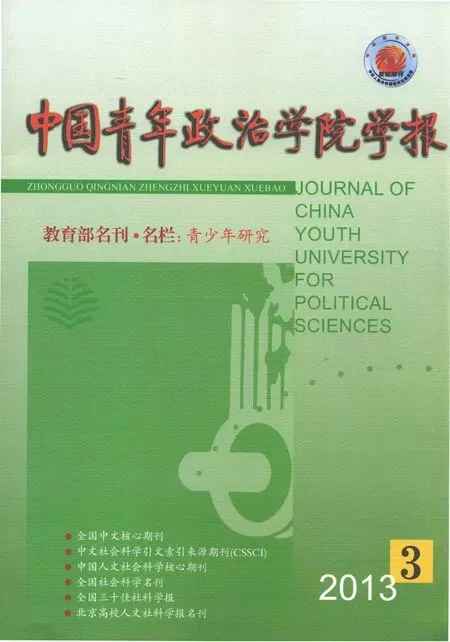未成年人作证规则之检讨——以刑事证据法为视角
程 捷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北京 100089)
相较于成年证人,未成年人证言往往具有很高的可暗示性而容易影响其陈述内容。在某些案件(性犯罪、虐待罪)中未成年人往往是直接受害人或唯一目击者,是最了解案情的人,如何评价其陈述的价值以及专业地引导其参与刑事诉讼,向来是各国刑事证据立法以及理论中一项极受瞩目的议题。应以怎样的标准与程序去审查未成年人的辨别与表达能力?如果未成年人具有辨别与表达能力,且案发时并无其他人证在场,其证明力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完成补强?当辩方提出异议时,又应该以何种情境下的何种方式予以质证才能符合未成年人心理、思维与语言特质,最大限度地保证未成年人证言的可信度?以上疑问无法从立法中找到直接具体的答案,而我国未成年人作证规则的学理研究也一直处于单薄状态。本文拟围绕上述问题聊叙鄙见,以俾未来相关实务与理论之跟进。
一、未成年人作证规则的中国图景
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围绕未成年人证言的特别规定比较笼统,总体上可以分为作证能力规则、证明力规则以及质证规则三类。
(一)模棱两可的作证能力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有观点认为,既然任何了解案情的人只要具备“辨别是非”、“正确表达”的能力即有作证的义务,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证人资格有任何额外要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年幼”与“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在法条文义解释下具有特殊关联关系,一定年龄以下的未成年人感知事物的能力脆弱,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询问时的心理素质不稳,不宜作为证人。这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响应[1]。2012年12月修改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69条第3款在引用《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基础上,补充解释道“对于证人能否辨别是非,能否正确表达,必要时可以进行审查或者鉴别。”但年龄在审查与鉴别中究竟起到决定因素、参考因素抑或根本不予考量,仍旧捉摸不定。
(二)治丝益棼的证明力规则
现代证据法理论认为,证明力应委由法官自由心证,属于经验操作领域,立法对其不应予以过多干涉。但基于我国法官独立审判机制的欠缺以及客观真实至上的司法理念,2013年1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称《解释》)依旧用心良苦地为未成年人证言证明力设计了“超法规补强规则”。《解释》第109条规定“下列证据应当慎重使用,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表达存在一定困难,但尚未丧失正确认知、表达能力的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所作的陈述、证言和供述。”这种“孤证不能定案”的思想等于直接否定了“一对一”犯罪案件中未成年人证人的证明力。相互印证性的证明思维或许能够在特定案件中满足上级或社会大众的外部检验之需,但长远来看,也将导致许多犯罪事实因为“历史的碎片”不足而无法追究。
(三)挂一漏万的质证规则
为了保证未成年人证人接受办案机关以及对方当事人询问时不受到引诱和干扰,也为了强化对未成年人证人的权利保障,避免其沦为追究犯罪的工具,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办案机关在询问未成年人证人时,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代表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组织的合适成年人到场。相较于前述证明力规则,对法院评价证据证明力起到担保作用的质证规则显然更为重要,关系到未成年人证言究竟是“真实的谎言”还是“诱导的想象”。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配套司法解释显得“为德不卒”,既没有规定法庭质证中询问人员的特殊心理学专业要求,也没有对法庭质证方式做出不同于成年证人的特殊安排。
二、未成年人的作证能力及其判断标准
如前所述,在未成年人是否有作证能力的议题上,既有主张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即没有作证能力的观点,也有主张对于未成年人证人“法律不因年龄或生理原因剥夺其资格”的观点,至于未成年人证人的表达能力以及可信度都应该交由法官在审查判断证明力的环节判断,而不受作证能力制度的宰制[2]。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一)作证能力的制度定位
笔者认为,作证能力既不同于民事行为能力,也不同于诉讼能力,而有自身独立的规范目的。民事行为能力乃以自己的行为依法行使权利与承担义务的资格,要求行为人必须认识自身行为的内容并意识到相应的法律后果。诉讼能力则指能以当事人名义单独且有效地实施或承受诉讼行为所必需的资格。由于诉讼上的行为要远远复杂于民法上的交易行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往往无法洞察诉讼行为的意义,因此多数国家都统一地做出“未成年人一概不具有诉讼能力”的规定。但是,诉讼能力是针对当事人设计的制度,不应准用于完全不同于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证人,对于某人是否可以成为证人的判断,并不适用诉讼能力的有关规则。由于证人提供证言属于事实查明的事项,即便不具有诉讼能力的当事人也可以接受询问[3]。
作证能力主要考量的因素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确保证人具有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所谓感知能力就是将特定信息加以处理与组合的能力,这里又包括具体感知能力和抽象感知能力,前者如对颜色、气味、形状的认知;而后者即理解何人对何人做了什么。显然未成年人基于智力程度的不同,不同个体对于抽象感知能力明显存在差别。所谓记忆能力,即将组合整理的信息在大脑中做永久记录的能力;而表达能力就是将储存的信息从大脑中提取、以回应一些暗示与事件的能力。二是确保证人能够理解真实作证的意义。理解真实作证意义的能力并非要求证人清楚拒绝作证或作伪证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但至少要求证人能够承诺说实话,并且能够对提问予以沟通了解。
(二)未成年人作证能力判断标准的比较法考察
主张放弃未成年人证人作证能力限制的另一个重要论据在于“国际上证人资格的一个总体趋势是限制逐渐被消减,各国都倾向于不对证人资格做出限制”[4]。这显然曲解了各国立法的现实。
1.国际上几种主要的立法例
世界各国或地区关于未成年人作证能力的规定,主要有四种立法例:(1)抽象标准——这种立法例以美国、英国、日本为代表,即不以年龄因素作为有无作证能力的标准,但要求必须具有“心智能力与理解真实作证的能力”。(2)具体标准——即以一个固定的最低年龄为标准,如智利(规定为7岁)、阿根廷(规定为10岁)、罗马尼亚(规定为14岁)、波兰(规定为13岁)、俄罗斯(规定为15岁)等。(3)混合标准——以上述两种方法相结合为标准。例如,美国部分州规定以10岁为分界点,10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一律具有作证能力,未满10周岁者,经法院调查并确认能完整地认知外在事实的经过、被询问内容以及真实作证的义务时,也具有作证能力。
2.分析与评价
以上三种作证能力的立法例在实质精神上都是一致的,都以未成年人的感知、记忆表达以及对于如实作证的理解能力为标准。只不过一些国家或地区为了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基于自身国情以及司法水平,人为地用年龄加以界定作证能力。比较起来,抽象标准与具体标准各有优缺点。抽象标准能够符合具体证人的个别情况,也与作证能力制度的理论基础相吻合。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逐一个案审查,徒生繁琐,影响裁判结果的社会接受程度以及法律适用的统一。以一个固定的最低年龄为标准的立法例,显然由于其标准的明确性而使其便于适用,但此种固定的标准不一定符合因人而异的具体情况,有时其适用的结果甚至与立法宗旨相悖。
(三)二阶段审查法:我国未成年人作证能力的标准选择
结合《刑事诉讼法》与相关司法解释的文本,笔者在此主张二阶段审查法,其标准与顺位如下:
一方面,10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一律具有作证能力。首先,文义解释是一切法律解释的逻辑起点,《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二款明确将“年幼”作为作证能力的考虑情形。至于如何判断“年幼”的年龄标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少年”指人10岁到十五六岁的阶段,据此将“幼年”定义10岁以前的年龄阶段符合一般人的认知。其次,早在《唐律疏议·断狱》就有“基于律得相容者,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的规定。这说明我国10周岁以上的自然人在生理上具备完整的感知、记忆与表达能力符合悠久的历史经验。最后,虽然作证能力既不完全等同于民事行为能力、诉讼能力,但是作证能力中的“识别与理解提问”的能力与限制行为能力所要求的“意思能力”并非全无交集,未必不能适当参考。
另一方面,1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经法院依职权调查,如果能够识别外在事实的经过、被询问的问题内容以及真实陈述的义务,则具备作证能力。由于年龄仅仅是作证能力的外在参考条件,因此《刑事诉讼法》第60条中的“年幼”与“不能辨别是非、正确表达”之间应属于递进补充关系,而非并列选择关系。部分观点认为,未成年人能否辨别案情以及表达程度应该交由法官在证明力层次判断。笔者认为,这里的“辨别表达”能力并非指未成年人在具体个案中的辨别表达程度,而是指未成年人是否具备最基本的感知、记忆与理解沟通能力。例如10岁以下未成年人往往对于“贿赂”、“集资”此类抽象事项是无法感知与理解的,应该否定其对此类事实的作证资格;再比如四岁的儿童虽然只会使用“水水”、“车车”这类幼稚的语言,但只要能够对待证事实做到具体描述,并且对于日常提问能够及时回应,则依旧具有证人能力。
三、未成年人证言补强规则及其合理解脱
与未成年人作证能力的议题不同,各国对于未成年人证言证明力罕有立法干涉,而是完全委由事实认定者通过经验、良心和理性予以自由判断。与之相反的是,我国司法实践却极其重视未成年人证明力规则,几乎所有涉及证据的司法解释和地方性证据规定都能找到未成年人证言必须补强的依据。
(一)我国未成年人证言补强规则的困境
必须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补强证据规则,极大地拘束了未成年人证言的证明力,在信息有限的案件中,尤其是在性侵犯、家庭暴力这种“一对一案件”中,可能无法突破证明困境导致追诉犯罪功亏一篑。下面,笔者以一个典型案例来加以说明:李某系某小学教师兼班主任,2012年2月在监督自习课期间萌生猥亵念头,借口让被害人小美(一年级女生,当时未满8周岁)协助监督同学们上自习,让小美陪自己坐在讲台上,并借助讲台遮掩,抚摸小美的屁股与阴部,甚至拉开裤链,强制小美用手抚摸他的外生殖器以满足淫欲。小美当日回家后被父母发现精神恍惚而导致案发。小美向公安机关陈述了被告人李某实施猥亵行为的经过,其陈述与被告人李某的供述基本一致,但在时隔四个月后的一审法院开庭时,被告人李某突然翻供,否认其有猥亵行为,而被害人小美的当庭陈述也与之前的侦查笔录记载在事实细节上存在差异。
假设在该案中因为被告人李某的庭前口供当庭翻供而被排除,目前只剩以下四项证据:(1)被害人小美的当庭证言;(2)案发当天做出的小美被侵犯部位的伤痕病例;(3)小美同班同学提供证言,证明小美当天的确被安排在讲台与李某坐在一起;(4)李某以前曾窥探女厕所而被学校处分的记录。结合本文前面所引《解释》中的证明力补强规则,首先,小美的当庭证言是本案中唯一的直接证据,但兼具有利害冲突的被害人以及未成年人的双重原因,必须要找到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由于伤痕病例是间接证据,最多只能印证小美当天被猥亵,却不能印证猥亵系李某所为。至于同学的证言只能证明李某有作案时间与机会而已,更何况小美的同学因为也是未成年人,其证言也需要补强。至于李某的处分记录是品格证据,往往只能用于量刑,不能用于定罪。综上,四项证据印证性不足,法院只能宣告李某无罪释放。
本案在未强行设置证明力规则的其他国家能否定罪呢?笔者认为是有可能的,试想小美被安排坐在一个有性变态经验的老师的同一天就留下被猥亵的伤痕,而且能对被告人作为进行清晰的指认,即便因为案发当时与开庭时间的间隔,导致部分细节描述不一致,但仍可合理解释为未成年人记忆能力的必然误差,未必影响陪审团或法官达成被告人有罪的内心确信。
(二)未成年人证言补强规则的成因
那么为什么实务中偏好未成年人证言补强规则呢?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因素:(1)“孤证不得定案”的司法经验。我国刑事证明模式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客观主义认识论的支点上,必然要求证言证明力的判断不能仅凭法官的个人感受,还必须经得起一般经验的考验而具有普遍接受性。“孤证不能定案”的司法经验一直被扩大化和绝对化地理解,哪怕是“一对一”的案件,未成年人证言也只有在得到其他证据印证之后,才可具备证明力。(2)“黄口孺子不可信”的社会文化。在稳定压倒一切背景下,社会大众对于判决认可度和接受度深刻地影响着裁判的生成方式。“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黄口小儿不足为信”的民众思维方式使得未成年人证言补强法则找到传统参照与道德支撑。(3)“聊胜于无”的未成年人证人出庭率。长期以来,从着眼于保护未成年被害人以及证人的考虑,未成年人证人在实践中几乎一律不出庭,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未成年人证人可以不出庭。在法庭质证程序以及言辞审理原则被空洞化的前提下,法官对侦查卷宗中未成年人证言的审查只能退而求其次,求助于补强证据规则。
(三)未成年人证言补强规则的运用限度
尽管我们可以对未成年人证言补强规则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与同情,却不应置部分案件的证明困境于不顾。笔者主张,对部分仍然缺乏印证的未成年人证言不应一概否定其证明力,而应借助于质证程序的完善,交由法官自由判断。
1.未成年人证言补强规则的运用要旨
补强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能力,但是否用以补强的证据必须是直接证据则在所不问。值得注意的是,只有该未成年人证人证言以外的证据才可以补强该证言,无论是用该未成年人庭前的陈述去补强庭审中的陈述,或是用未成年人证言所形成的传来证言去补强原始证言都无任何意义。
补强证据规则并不需对被补强的证据内容具有完全的证明力,只需要补强证据的综合判断能让法官对未成年人证言证明力产生确信即可。即在坚持未成年人证言需要补强的原则下,为法官的自由判断留出更多的空间。庆幸的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将“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崭新标准,为以上观点扫清了障碍。
2.未成年人证言质证程序的配套完善
某些情形下的未成年人证言或许没有足够的证据加以补强或印证,此时应该传唤有重要争议的未成年人证人到庭,由法官当庭借助于言辞质证把握证明力的大小。法官在自由判断证明力时,还是应该结合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注意以下事项:第一,通过行使诉讼指挥权,尽可能采取开放性问题提问,避免选择性或诱导性问题。心理实验表明,未成年人自发的回忆往往是正确的,而经过特定问题的提示、反复询问会迫使未成年人去想象事件并信以为真,在陈述时加入某种幻想。第二,针对不满10周岁未成年人的询问,尽可能地由熟悉儿童心理的法庭辅助人员代为提问,尽可能符合年幼证人语汇使用以及思维方式的特殊性。第三,确保未成年人证人有其熟悉的、合适的成年人到场,必要时可以借助于视频询问的方式,以减少作证心理负担的不利影响。
[1]田平安:《证人证言初论》,载《诉讼法论丛》(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2]姚 莉吴丹红:《证人资格问题重述》,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5期。
[3]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161页。
[4]董 墚:《被忽视的证言——浅析儿童的证人资格》,载《中国公证》,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