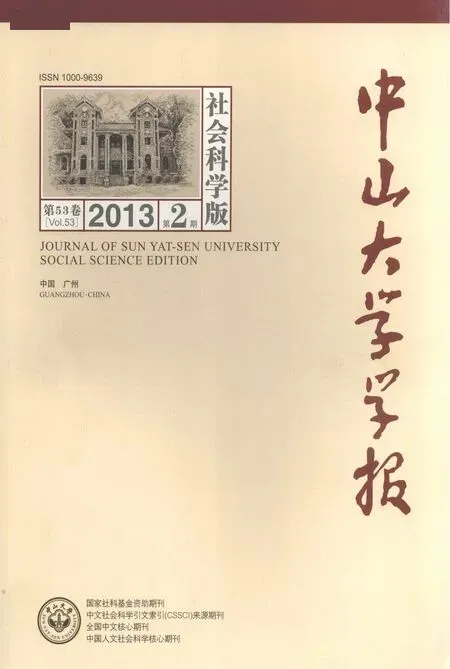正直的界限:《论语》中政治和习俗的分野*
刘 伟
一、解题并释“直”字义
本文说的“正直”,确切地说,应该是“直”,因为从本源义说,“正”和“直”是有区别的。《左传》襄公七年曾引《诗经·小明》“靖共尔位,好是正直”,并释之云“正直为正,正曲为直”①[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52—853页。,则“正”与“直”之区别可见。本文题中所云“正直”对应的是“直”,只是为了遵从现代汉语用法,易“直”为“正直”。故在笔者的行文中,正直皆指“直”。
首先我们来追问一下“直”字的本义。《说文》云:
直,正见也。从乚从十从目。
乚,匿也,象……隐蔽形,凡乚之属皆从乚,读若隐。
清人王筠以为,乚、隐为古今字,乚为古字,于六书为指事,故其体简;隐为后起之今字,为形声,故其体繁②[清]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507页。。按《说文》“读若”之例,或以为通其音,或以为音义并通,莫衷一是。王筠的看法颇为折中,按《说文释例》云,读若者,“有第明其音者,有兼明假借者,不可一概论也”③[清]王筠:《说文释例》,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第499页。。然此处所说乚、隐二字为音义并通者无疑。《说文》云,隐者蔽也,从阜得形;而声旁之字训为有所据依。按段玉裁之说法,隐字得声之旁与隐音同义近,隐行而后其字废④[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34页。。由斯可见,隐从左右二形得义,其右为依据,且为隐之声旁,阜为大山,故隐之义便是躲入大山,诚如段玉裁所言,隐从阜取遮蔽之义⑤[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34页。。由此便可证王氏之说,隐为形声字,乃晚起字,其古字为乚。如上文所引,乚亦有藏匿之义。不止如此,乚尚有弯曲之义,然此义与本文关系不甚大,故不赘。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断定,乚之义有二:其一为隐蔽,其二为弯曲。晚起之“隐”,只承袭了乚“隐蔽”一义。而在今天,无论是隐藏还是弯曲,其反义词都可以表述为“直”。
按《说文》,直从十目乚,乃会意字,意谓将“乚”置于十目所视的场域之中,比如将自己藏在心里不为人知的一面公开出来,就是直。很显然,“十目”之“目”是他者的目光。《大学》曾引曾子的话证明诚意以及慎独的必要性,其文云“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又有“人之视己,犹见其肺肝然”。“十目所视”表征的是“我”之外的他者审视“我”,或者说将“我”置于他者的目光中。在古代,“十”是数之全,所以这里的“十目”所指代的“他者的目光”中的“他者”是复数,就如同《大学》中“人之视己”的“人”指称的是复数一样。所以,“直”不是一个个体性的范畴,它必须置于个体与他者的关系中,才能得到恰切的理解。
如此一来,我们可作如下界定:直,是将自身隐藏的东西置于他者的视域中。“他者”是个复数概念,至于它到底对应何种可经验的状态,后文有具体说明。
二、《论语》中的“直”与“不直”
(一)正直
《论语》云: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
这是一条在后世历史中产生巨大影响的经典语录。从文本本身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和叶公在讨论正直这一概念。问题是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开始的:叶公说,在他生活的“乡党”中,有一个正直的人,父亲偷了或者确切地说是非法占有了他人的羊,这时候这个所谓正直的人站出来证实自己父亲的偷窃行为。在叶公看来,这个“证父”的人没有隐瞒这一行为,而是出来证实,这个证实显然是向他人揭露自己的父亲。如前文所云,正直的本义就是不隐,那么证父者这一揭露行为显然符合正直的本义。可是,在叶公眼里,这个“直躬”者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正直的典型,是因为他“证”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
面对叶公略带挑衅性的表述,孔子的回答针锋相对:在我生活的“乡党”中,正直的人和你所谓“直躬”者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表现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孔子所否定的不是叶公所说的“直”,而是叶公所说的“直躬者”的具体行为。对话是一个交互行为,双方的言说必须建立在对方可理解的前提之上,这意味着在这一则讨论“直”的对话中,无论孔子还是叶公都得承认存在一个双方都能理解并认可的“直”的规定。在叶公所举的案例中,对“直”的本质规定和父子关系无关,而是和向他人“证”这一行为有关,只是父子这一特殊关系使“直”变得更加突出而已。换句话说,如果“直躬”者所“证”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其他人,仍然是正直的表现。正是因为如此,孔子不可能彻底否定叶公对“直”的理解,而是否定“直躬”者证父这一具体行为。只有在父子这一特殊的关系之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中的“隐”这一行为才是正当的。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孔子认为一个正直的人应该为父“隐”,却没有说为父“隐”就是正直。“直”与“隐”是一组完全相反的范畴,它们的相悖只有在父子这一特殊的关系中才能被消解。在文本中,孔子使用的是“直在其中”这一微妙的表述方式,一般说来以“X在其中”作为结论时,“X”所指向的一定是与自身的规定相反的内容。比如在《述而》篇中,孔子曾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很显然,一般人认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并不是一个值得“乐”的状态,故孔子才说“乐在其中”。同样,一般说来,“隐”并不是“直”,只是因为是父子,所以才“直在其中”。孔子并没有否定叶公对“直”的理解,也没有对“直”进行重新规定,不隐藏依然是“直”的本质规定。
明确了孔子本人仍然承认不隐是对“直”的本质规定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则对话的某些细节问题。首先,这一事件发生在“吾党”,即孔子和叶公各自生活于其中的“乡党”。其次,孔子和叶公对直躬证父这一行为的不同理解,根源于各自不同的生活经验。这与个人的境界没关系,并非因为孔子是一个有极高境界的人才会“父为子隐”,而是生活在孔子所在的“乡党”之中的人对于“直”的理解皆如此,否则如果其他人都觉得子证父是一种道德行为,只有孔子一人认为这是不道德的,那么孔子就没法在这个乡党中生活。所以,在同一个乡党中生活着的人,并非只是在地理空间上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指向的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和相对同一的价值观。最后,涉及正直与否的事件是一个与法律(政治)相关的事情——“攘羊”。虽然在现实中大多数盗窃事件可能不会进入司法程序,但从后世“亲亲相隐”成为司法原则这一事实,说明我们不能绝对肯定这是一件处在政治之外的事件,它总存在着引入政治干预的可能。所以,我们也不能排除“父为子隐”和“子为父隐”存在不欲让自己的至亲之人受到政治惩罚的可能。
总而言之,“直躬证父”是一个发生在“乡党”中的事件,孔子和叶公的分歧在于一般意义上的“直”是否适用于父子之间,而并不是“直”本身,他们都必须承认“直”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德行。又《论语》云: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
这里孔子所说的史鱼和蘧伯玉都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从文本本身看,孔子把史鱼视为一个正直的人,无论邦有道还是无道,都如射出的箭一般正直。这可与直的另外一层含义直接对应——不弯曲,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史鱼的正直是因为不刻意隐藏真实的自己。关于史鱼的事件,《韩诗外传》有相关的记载,可视为《论语》此文的注脚。按《论语正义》引《韩诗外传》云:
昔者卫大夫史鱼病且死,谓其子曰:“我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为人臣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死不当治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卫君问其故,子以父言对。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贵之,而退弥子瑕,徙殡于正堂,成礼而后去。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谓直矣。①[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17—618页。
文中将史鱼“生以身谏,死以尸谏”视为“直”,意为史鱼并没有因为对方是君主而隐藏对于蘧伯玉、弥子瑕贤与不肖的看法,不论生还是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则语录中孔子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人——蘧伯玉。在孔子看来,蘧伯玉是真正的君子,理由是蘧伯玉能够做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无论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还是后代,“学而优则仕”都被视为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邦有道则仕”可能是一个默认的想像,即使不存在一个“有道”的生存环境,也可以设想一个士人应该在“邦有道”的时候出仕。可是,如果蘧伯玉没有在“邦无道”的情况下“卷而怀之”的经验,孔子绝不会说出上文那一番话。按《左传》襄公十四年曾记载,孙林父逐其君衎,蘧伯玉“从近关出”;又襄公二十六年,宁喜弑其君剽,蘧伯玉身遭其变,近关再出②[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第923、1032页。。所谓“近关再出”,说明蘧伯玉在政治动乱(“邦无道”)的情况下选择回避是一种常态,并非偶然。
《论语》此处将史鱼和蘧伯玉并提,且称蘧伯玉为“君子”,有贬低史鱼之“直”的意味,至少把史鱼之“直”看成是不完满的。故朱子《集注》引杨氏:
史鱼之直,未尽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后可免于乱世。若史鱼之如矢,则虽欲卷而怀之,有不可得也。③[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3页。
如果前文所引孔子对史鱼和蘧伯玉的评价为独立的两章,那么我们便无法得出孔子将史鱼之“直”视为不完满这一看法。当然,这也可能是孔子在两个不同场景中的言论,后被《论语》的编纂者编在一起,至少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说明在编纂者看来,蘧伯玉与史鱼相比拥有更完满的德行。事实上,孔子更欣赏能够在乱世中自保的人,这从孔子对公冶长和南容的评价中可见,详后。不止如此,从《论语》的习惯表述来看,孔子更倾向于区分“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所以在原宪问耻的时候孔子说“邦有道,榖;邦无道,榖,耻也”(《宪问》),评价南容则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公冶长》)。如果是这样的话,史鱼在“邦有道”和“邦无道”的情况下皆“如矢”,即便没有蘧伯玉的对比,我们似也可断定孔子对史鱼之“直”并非毫无保留地赞赏。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对这一条经典略作分疏:第一,孔子对史鱼之“直”并非毫无保留地赞赏,相比之下,他更欣赏蘧伯玉在“邦无道”的情况下“卷而怀之”;第二,从身份上来说,史鱼和蘧伯玉都是政治人物,孔子评价的内容都和政治相关;第三,政治是理解这则语录的前提,这与上文以“乡党”为背景评价“直躬者”不同。可以说在孔子看来,在政治生活中“直”并非绝对正确的德行。
(二)不直
《论语》有云: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公冶长》)从夫子“孰谓微生高直”这一反问可知,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微生高是一个正直的人。也正是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微生高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孔子才举“乞醯”这个例子来说明微生高的“不直”。故朱子注此章云:
微生姓,高名,鲁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来乞时,其家无有,故乞诸邻家以与之。夫子言此,讥其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不得为直也。①[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2页。
所谓“素有直名”便可说明在大家看来,微生高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朱子在注释中引入“人来乞时,其家无有”这一前提,十分精到。设想一下,邻人来“乞醯”,如果微生高有而“乞诸其邻”,就不止是“不直”,还将包括吝啬、虚伪,这显然比单纯的“不直”更恶劣。
在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孔子之所以认为微生高不直,乃是因为他隐瞒了“其家无有”这一真实情况,因此有朱子所谓“掠美市恩”的嫌疑;第二,如果微生高在“其家无有”的情况下,向“乞醯”者坦白,那么在这件事上他就不再是“不直”,因为不可能在同一件事上怎么做都是错;第三,更关键的是,这件事发生在邻里之间,微生高“乞诸邻家”,可以想像“乞醯”者也必定是微生高之邻人,所以这是一件“乡党”中的寻常事,与政治无涉。
又《论语》云: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縲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冶长》)
《公冶长》整篇大都是孔子对他人的评价。这一章与“史鱼”章类似,评价的对象是公冶长和南容。孔子对公冶长的评价是,他虽然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过错。不是公冶长的过错,就一定是统治者的错,让一个好人坐牢显然是一件不义的事情,所以孔子这一评价本身就暗含着“邦无道”这一基本前提。孔子对南容的评价看上去像是事实的描述,但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南容的肯定。如果加上“以其兄之子妻之”这一事实,就完全可以肯定,孔子对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十分欣赏。事实上,“以其子妻之”、“以其兄之子妻之”并非孔子的话,而是《论语》编纂者为孔子的两个评价所加的注脚。这两个注脚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比较公冶长和南容境界的高低。就如同“史鱼”章一样,孔子这里的两个评价极有可能是在两个不同场合的评价,而夫子以其子妻公冶长和以兄之子妻南容虽然是事实,但却未必和这两个评价存在直接的逻辑关系,或许与年龄或其他的遭遇相关亦未可知。可如笔者前文所说,孔子更欣赏能够在“邦无道”的情况下自保其身,所以即便这两条并非同一场景下的有意对比,我们也能推出:在“邦无道”的情况下,身陷囹圄显然不如“免于刑戮”。
如此,我们便可对这一则语录略作总结:第一,相比于“虽在縲绁之中,非其罪也”,孔子可能更推崇“邦无道,免于刑戮”。第二,在孔子看来,公冶长和南容都生活在乱世,或曾经生活在乱世之中,因为如果南容没有“邦无道,免于刑戮”的亲身经历,孔子很难预测南容在乱世中会免于刑戮。第三,在一个乱世中,公冶长无罪而入狱,是不能明哲保身,但这至少说明公冶长是一个正直的人。孔子曾经说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危者高也。孙通逊,为卑顺。朱子《集注》引尹氏之言以为“君子之持身不可变也,至于言则有时而不敢尽,以避祸也”。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不敢尽言视为“隐”,与之相反的便是“直”。所以,在“缧绁之中”的公冶长肯定比“免于刑戮”的南容更接近于“直”。第四,亦如“史鱼”章一样,公冶长和南容的经历,都和政治有关。
三、隐者之“隐”
既然与“直”本义相对的是“隐”,我们不妨再讨论一下《论语》中与“隐”相关的问题。《论语》中有类特殊的人,他们是隐士。如前文所云,“隐”乃是处于众人的视野之外。如此,所谓隐者,按理说,应该处于人们的言说之外。可是,既然《论语》编纂者让隐者进入“论”语之中,并且与孔子直接照面,这意味着编纂者(言说者)有意在探讨孔子与隐士之间的关系。
《论语·微子》记有两则故事: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第一则故事的内容无太多疑义,讲的是孔子和子路迷失津渡,孔子让子路向两个隐者——长沮和桀溺——问路。两位隐者得知子路和孔子的身份之后,态度并不友好,其中叫桀溺的人表明了他(或者还可以代表所有隐者)的立场:与其在乱世中因“辟人”而周流辗转,不如采取“辟世”的态度。子路返回后告知孔子,孔子以“鸟兽不可与同群”为自身辩护,故事至此结束。第二个故事则是子路与孔子失散,向荷蓧丈人打听夫子去向,丈人回答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并于当晚止子路宿,让其二子拜见子路。第二天,子路见到孔子后,告知此事。孔子让子路返见之,至则荷蓧丈人已离去。于是,现有文本记载了子路的一番议论,兹不赘。
从文本次序上看,《微子篇》这两则故事前后相承;从内容上看,这两则故事所指向的意义大体相同;从逻辑上看,后一则故事必须置于前一则背景之下,其意义才能体现出来。首先,第二则对话以“子路从而后”开篇,虽然从后文子路向荷蓧丈人的问话“子见夫子乎”,可以看出子路所从为夫子,但对于一个一般的故事来说,这并不是正常的表述方式,但如果将上文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看,便不存在问题。其次,从文本上看,荷蓧丈人只是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句话只能说明丈人鼓励学习农业种植,绝推不出他是个隐士,更无法推出其废“君臣之义”。第三,从传世文本中子路所说的话来看,如果想建立起其与荷蓧丈人必要的关联极其困难,但如果将这则对话置于“长沮、桀溺”一章的背景之下,便可以做如下理解:荷蓧丈人曾和子路说了与长沮、桀溺类似的话,或表达过相似的立场,只是在文本创作时被省略了而已。文本编纂者将两条放在一起,是有意用前一则故事来弥补后一则故事的“空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故事,我们必须将它们放在一个解释框架中来理解。
关于第二个故事,还存在着一处版本问题。传世本均将“不仕无义”云云归到子路名下,故郑玄注云:“留言以语丈人之二子。”①[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1页。这说明郑玄看到的本子也是“子路曰:‘不仕无义……’”。朱子《集注》则云:“福州有国初时写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85,185,184页。其中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故事结尾“不仕无义”云云是夫子之言还是子路之言。一般说来,《论语》的编纂以孔子之言作结,是最普遍的记述方式,比如“长沮、桀溺”章。可是,这一章的特殊之处在于,子路见到孔子,把自己的遭遇和孔子言明之后,孔子让子路返回再见荷蓧丈人。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下:孔子遣子路返回见丈人,目的为何?因此,如果“不仕无义”这一番话是孔子说的,那么“子路反”这一行为就变得很难理解,因为孔子的言说对象是子路,他完全可以第一次回来时便说这一番话。这样一来,郑注以为,这一番话不是孔子而是子路对荷蓧丈人的两个儿子说的,便颇值得玩味。也就是说,子路这番话本来是要和荷蓧丈人说的,但他没想到会见不到荷蓧丈人③邢昺以为“夫子言,此丈人必贤人之隐者也。使子路反求见之,欲语以己道”。详参[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第252页。。子路所说仍然是依照夫子之意,这便不违背上文所说一般以夫子之言作结的常规记述。故朱子亦云:“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④[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85,185,184页。
既然这两个故事是一个整体,我们首先必须承认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是同一类人,毕竟第二个故事的文本中荷蓧丈人并没有“辟世”的说法。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根据这两个故事中孔子和可以代表孔子的子路的说法,来看一下孔子对于隐士立场的反驳。在第一个故事中,孔子直接说道: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这里,孔子显然将长沮、桀溺这样的隐士视为与鸟兽同群,因为他们隐于山林⑤[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第250页。,而孔子本人则认为应该与人同群⑥[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85,185,184页。。在第二则故事中,孔子借子路之口说道:
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句话的关键是“长幼之节”。从上文之辞气可知,子路已经默认荷蓧丈人遵守“长幼之节”,问题的关键是子路凭什么认为荷蓧丈人有长幼观念。《集解》引孔注以为荷蓧丈人“知父子相养”,所以知“长幼之节”;朱子则以为,荷蓧丈人态度倨傲而子路谦恭,荷蓧丈人因子路之谦恭而“见其二子”,所以荷蓧丈人知“长幼之节”。揣摩文本“子路拱而立”这句话,朱子之说可从。这里子路或者孔子对荷蓧丈人的批评是基于其有“长幼之节”。似乎在子路看来,有了“长幼之节”便应该接受“君臣之义”,恰恰因为荷蓧丈人不接受“君臣之义”,所以为“乱大伦”。
同样是针对“隐者”,在两则故事中,孔子和代表孔子的子路分别采取了不同的修辞策略。在第一则故事中,孔子以人不可与鸟兽同群来批评长沮和桀溺;在第二则故事中,子路则依据荷蓧丈人有长幼观念来批评其不懂“君臣之义”。很显然,“君臣之义”指向的是政治生活,而与鸟兽同群则指向自然(山林)生活。需要注意的是,在两则故事中,孔子和子路的身份都是政治性的,即为政治生活的参与者。既然此处的孔子是作为一个政治生活的参与者进入故事之中的,那么故事本身必然包含着为政治生活辩护的意味。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将第二则故事视为孔子为自身出仕的辩护词,只是这种辩护成立的前提是荷蓧丈人认可“长幼之节”。第二则故事中的荷蓧丈人因子路“拱而立”而“止子路宿”并食之鸡黍、“见其二子”,这样一来让孔子有了在隐者面前为政治生活辩护的可能,也就是说这种辩护依赖于某种特殊的机缘。如果荷蓧丈人压根就不认可“长幼之节”,那是否意味着政治生活的正当性将无法得到论证?显然不是。我们假设荷蓧丈人根本就没有“止子路宿”这一行为,那么后面的情节将不会发生,如此则第二个故事就不会发生,荷蓧丈人和子路的相遇便成了长沮、桀溺和子路相遇的翻版,而孔子仍然会以“鸟兽不可与同群”来反驳自然生活。所以,这两则故事一则为论证政治生活正当,一则为论证自然生活不正当,而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必须将这两个故事视为一个故事。在这一个完整的故事中,自然生活的不正当是绝对的,而政治生活的正当则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取决于出仕这一特殊的经验。选择自然生活一定是不正当的,但不选择政治生活则未必是不正当的,蘧伯玉逃离政治依然是君子。因此,隐者之“隐”,是因其选择自然生活,而不是因其逃避政治生活。在自然和政治之间仍然存在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乡党)生活。从逻辑上说,社会生活要比政治生活优先,这不单单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进入政治生活的机会,更因为人在选择政治生活之前已经选择了社会生活。
综上可知,人的在世生活呈现为三种不同形态——自然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具体说来,与自然生活相对的是社会生活,而政治生活从根本上说仍然是社会生活,只不过它是社会生活的特殊形式而已。
四、政治与习俗
从孔子对长沮和桀溺的回应——“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们知道社会生活就是指和人而非鸟兽生活在一起。在传统社会,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就是生活在乡党中。问题是:乡党生活的意义何在?
我们且看《论语》原文: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述而》)
这句话在句读上便存在问题。梁章钜的《论语集注旁证》以为,邢《疏》引琳公云:“此‘互乡难与言童子见’八字通为一句,言此乡有一童子难与言,是非一乡皆难与言也。”梁玉绳进一步认为此说有理,因为孔子曾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并不是指一乡之人皆难与言①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92页。。梁章钜和梁玉绳之说皆针对《集解》引郑玄注立说,按郑玄云:“互乡,乡名也。其乡人言语自专,不达时宜。”②[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第95页。邢《疏》引琳公之说,似是而非。按此说法,“互乡难与言”这个判断成立的前提是“互乡”每个人都“难与言”。可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就意味着对“互乡”的任何判断都需要建立在对其中每个人判断的前提之上,如此一来,具有模糊性的日常语言便很难对“互乡”作出有效的整体判断。按郑玄的说法,“互乡”人“言语自专”强调的互乡本身有“自专”的习俗。可这个习俗不可能、也没必要落实到每一个人。《周礼·党正》云:
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凡其党之祭祀、丧纪、昏冠、饮酒,教其礼事,掌其戒禁。郑注:郑司农云,“五百家为党”。《论语》曰“孔子于乡党”,又曰“阙党童子”。③[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25—428页。
按经文云,一党之“祭祀、丧纪、昏冠、饮酒”皆由党正教其礼节与禁忌,这意味着一乡一党(应该)有相同的习俗以及价值观念。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郑玄认定“互乡”一个乡都“难与言”,因为即使党正以礼教民,也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能按礼行事。所以,乡党生活意味着人生活在特定的习俗之中。不同的乡党可能存在不同的习俗,所谓“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晏子春秋》),但习俗本身对人的约束和塑造是遁无可逃的④按《说文》,“习”字的本义是“(鸟)数飞”。段《注》引《礼记·月令》“鹰乃学习”,则此“数飞”指鸟成长时学习飞翔的过程。对于人来说,生和长皆在习俗之中。习俗规定和塑造人,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是也。。
让我们再次回到上文讨论“直”时孔子对几人的评价。可以看出,孔子的评价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史鱼、蘧伯玉、公冶长和南容的评价,第二类是对“直躬者”和微生高的评价。
如上文所云,就一般人的常识来看,相比于蘧伯玉和南容,史鱼和公冶长肯定显得更加正直一些。可是,从两下的比较来看,孔子更欣赏显得不太“直”的蘧伯玉和南容,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前文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孔子评价四人的内容都是和现实政治相关的政治行为,而且都是身处“邦无道”的政治环境之中。孔子也承认史鱼是个正直的人,这里的正直符合“直”的本质规定——不隐,而且这种正直的政治行为本身是值得称道的,只是在与蘧伯玉“卷而怀之”的对比中,“直”的积极意义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与“直”本身无关,而是来自行为的政治性,换句话说,是政治性让“直”的积极意义打了折扣。这意味着,在政治生活中,“直”的评判力是不充分的,因为存在着一种“不直”比“直”更值得欣赏。这与直躬证父不一样,我们不能说在父子关系中,“不直”比“直”更值得欣赏,因为在孔子看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隐”本身就是“直”。我们也不能说蘧伯玉在“邦无道”的情况下“卷而怀之”是“直”。“亲亲相隐”本身就是“直”的特殊表现,而在“邦无道”的情境下抽身而退这一行为不是“直”能涵括的。基于此,我们必须承认,政治是“直”的界限,即在政治生活中,正直的积极意义是不充分的。
与政治相对的是乡党之习俗,还是让我们再回到孔子对“直躬者”和微生高的评价上来。从批评和赞扬这一维度上看,孔子对微生高和“直躬”者的态度是一致的,只是批评的内容有很大的区别。孔子批评微生高,是因为他“不直”,这里的不“直”对应的是有所隐瞒;批评“直躬”者,则并非因为其“不直”,而是“直”的方式不对。在孔子看来,“直躬”者应当隐瞒父亲盗窃这一事实,才是真正的“正直”的人,这是由父子关系决定的。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直躬”者能够“子为父隐”,而微生高能够坦白“其家无有”,那么他们便是符合正直这一德目的人,这里的“直”的积极意义是充分的、不打折扣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乡党生活中存在着意义充分的“直”。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生活和乡党生活中间存在着一条正直的界限。在界限一边的乡党生活中,“直”的意义是完满的、充分的。也就是说,在乡党生活中,正直可以得到其本质的规定。
关于在习俗中可以得到正直最本真的规定,我们仍可以在孔子的表述中得到相应的验证。《论语》云: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文中两个“生”字,颇值得注意。可以肯定的是,第二个“生”是指生存,故《集解》引包咸云:“诬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①[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第78,78页。朱子之理解亦大体如此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9,89页。。问题的关键在第一个“生”字,《集解》引马融之说以为:“人所生于世而自终者,以其正直也。”③[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第78,78页。此理解则“生”当训为生存。朱子则引程子之说以为“生理本直”④[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9,89页。,则“生”当训为“性”,二字古通。郑玄以为“始生之性皆正直”⑤[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第235页。,则以人出生时未经濡染的状况视为本性,有告子“生之谓性”的意味。郑玄、朱子之说皆可通,马融之说则过于牵强。马注显然是为了保证两个“生”字在字面意义上的统一,却忽视了文本的内在意义。“罔之生也幸而免”亦是“自终”于世,如此则正直便不是“人所生于世而自终”的必要条件。所以,当从郑玄、朱子之说,将第一个“生”训为性。至于这个“性”是天理之本然还是甫一出生的特性,于此文来说无关宏旨。如此一来,孔子此言便可以理解为:人的本性是正直的,那些不正直的人生存于世仍然可以免于(政治)惩罚是侥幸而已。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免”字。免字的本义是兔子逃逸,但在孔子时代或者孔子本人的用法中,免是指免于政治处罚,即免是和政治相关的。前文曾提到过孔子评价南容是“邦无道,免于刑戮”,免的对象是“刑戮”;又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为政》),此处免的对象是“齐之以刑”的“刑”;孔子曾云“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雍也》),此处免的对象仍然是政治处罚。罔可训为不直,从孔子所说的“幸而免”可知,这种“不直”免于政治惩罚是因为侥幸,所以这里的“罔”所对应的不直显然不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品质。从免于政治惩罚以及人性本直可知,孔子对此文“直”和“罔”的想像不是在政治生活中,而是在一般民众生活中,即乡党生活中。
这句话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孔子对“直”和“罔”的论述并没有限定在任何一个特殊的情景中,从直观上看,这是对“直”和“罔”的普遍看法。第二,“直”和“不直”都是从孔子的立场来看的,比如大多数人认为微生高直而孔子则从“乞醯”看出其“不直”,但在这里“罔”所对应的“不直”是一种绝对的“不直”。微生高的“不直”和这里的“罔”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说这里的“罔之生也”是“幸而免”,但绝不可以说微生高之生是“幸而免”。所以,在这句话中,孔子所探讨的“直”和“罔”都是绝对意义和理念意义上的。相比之下,微生高的“不直”只是现实经验中的“不那么直”而已。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确定,正直这一德目在习俗之中得到其应有的规定。如此说来,“直”所从之“十目”以及曾子所说的“十目所视”之“十目”所指称的复数意义上的他者的目光,便不是他者目光的简单累加,而是一个具有特定习俗和价值取向的共同体,即乡党。不同的人可能生活在不同的习俗中,但习俗本身对于人来说是先验给定的生存世界。
从《论语》所载孔子的相关表述看,正直这一德目彰显了政治和习俗的分野。另外,由“直”和“隐”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说,在孔子的政治哲学中,习俗比政治更加优先。由此可能会引申出一系列问题,比如“政/教”关系、“性相近,习相远”背后的人性论预设、“道德—教化—政治”的逻辑论证等等,当然,这已经超出本文论述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