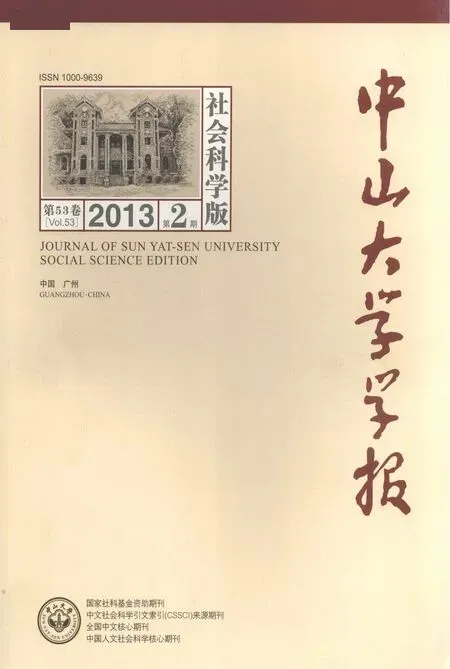清商乐三题*
黎国韬
清商乐又名清乐,是中古最为流行的音乐之一,其曲辞也是中古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清商乐及其曲辞已有很多探讨,但难以解决或尚存争论的问题依然不少。为此,本文拟选择三个具有一定争议的问题展开讨论,包括“侧调”与“瑟调”之关系、清乐表演者之性别、“作女儿子”与戏剧之关系等,故名《三题》。论述过程中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与过往的观点颇存异同,若有不当,万望教正。
一
清代学者凌廷堪《燕乐考源》引用了《梦溪笔谈》中的一段话:“古乐有三调声,谓清调、平调、侧调也。”对这段话,凌氏下按语云:“侧调即《宋书》之‘瑟调’。”①凌廷堪、林谦三、邱琼荪著,任中杰、王延龄校:《燕乐考原》,收入《燕乐三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页。此说一出,近世学者多信从之②如王运熙先生《清乐考略》一文认为:“凌廷堪《燕乐考源》卷一说:‘侧调即《宋书》之瑟调。’案‘侧’、‘瑟’声近;王灼、沈括均解音律,两人谈古乐三调,仅举清平侧,而不提及瑟调。因此,凌氏的话或许是可信的。”(收入《乐府诗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5页)其他从凌氏说者尚有不少,兹不一一摘引。。不过,假如“侧调”真的即“瑟调”,这和历史上关于“清商三调”及“相和五调”的记载就存在不少矛盾,而这些矛盾似乎又无法解释得通。既解释不通,则侧调即瑟调的说法又如何成立呢?以下拟对这些矛盾作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应从乐调数量的方面考虑。据古籍记载,清商乐含平调、清调和瑟调三种主要乐调,合称“清商三调”。而作为清商乐源头的相和曲则含五种乐调,即清商三调加上楚调和侧调,合称“相和五调”。这在《乐府诗集》所录《相和歌辞一》的“解题”中讲述得十分清楚:
《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其后晋荀勖又采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歌诗,即沈约所谓“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书·乐志》曰:“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侧调者,生于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晋书·乐志》曰:“凡乐章古辞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魏晋之世,相承用之。永嘉之乱,五都沦覆,中朝旧音,散落江左。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相和诸曲,亦皆在焉。所谓清商正声,相和五调伎也。①郭茂倩:《乐府诗集》卷26,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76页。
以上引文明明提到,清商三调之外“又有”楚调和侧调,五调合在一起即“所谓清商正声,相和五调伎也”。假如侧调即瑟调的话,岂不成了“相和四调”,何来的五调?这个矛盾是很难解释得通的。郭茂倩所引《唐书·乐志》之文与今本《旧唐书》和《新唐书》略有异同②刘昫等《旧唐书·音乐志二》提到:“《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也。汉世谓之三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3页)而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则提到:“唯琴工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蔡邕五弄、楚调四弄,谓之九弄。”(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4页),但郭氏去唐、五代不远,“相和五调”的说法必有一定依据。
其次,应从乐调产生地域的角度予以考虑。平调、清调、瑟调一向被认为是先秦周世《房中乐》的遗声,可见其渊源于北方的乐调系统,如《通典·乐五》所载可以为证:
《白雪》,周曲也。《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之遗声也。汉代谓之三调。大唐显庆二年,上以琴中雅乐,古人歌之,近代以来,此声顿绝,令所司修习旧曲。③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45,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00页。
而据前引《乐府诗集》“解题”可知,“侧调者,生于楚调”,很显然是渊源于南方的乐调系统,不太可能与北方周人的瑟调混为一谈,这个矛盾也很难解释得通。另据《汉书·礼乐志》记载:
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④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43页。
这也足以说明,《房中乐》的清、平、瑟三调本是周人、秦人的遗声,基本属于北方乐调系统;至汉高祖“乐楚声”,《房中乐》被改为《房中祠乐》,始引入南方的乐调进行创作,由是渐具南乐特点,作为“楚声”的楚调、侧调之兴起大概是在此时,但比周人的瑟调要晚得多。因此,瑟调与侧调的南北分野还是较为明显的。
其三,应从相和曲、清商曲所用乐器的角度予以考虑。有学者认为“瑟”是楚人的代表性乐器,所以瑟调理应出自楚声,故与“生于楚调”的侧调相同。如王小盾先生《论〈宋书·乐志〉所载十五大曲》一文曾指出:
瑟调来自楚声,“艳”和“乱”也来自楚声。逯(钦立)先生已经论证:瑟是楚声的代表乐器,瑟调之命名即因此之故;瑟调和楚调所用乐器一般无二,故云“侧调(即瑟调)生于楚调”……相和歌的歌弦化,主要是依靠瑟调曲实现的……于是我们知道:瑟调曲不仅作为清商三调的一调,参与了相和歌的歌弦化,而且作为楚声的调式,实行了艳、趋、乱的歌弦化。⑤王小盾:《论〈宋书·乐志〉所载十五大曲》,载《中国文化》第3期,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53页。
笔者则以为,凭借一种乐器来确定一种乐调的音乐属性是不够准确的,前辈学者的研究就提出了反例,比如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一书中曾指出:
颇疑清、平、瑟三调即出于秦声,或与秦声有关。此核之三调中之作品及其所用之乐器而略可知也……可注意者,即平、清、瑟三调皆用筝,而相和曲则无之。按前引李斯上书,以弹筝为秦声,应劭《风俗通》亦云:“筝,秦声也,蒙恬所造。”又曹植诗云:“秦筝何慷慨”,是知筝确为秦声独擅之乐器,今三调中皆用之,足证与秦声有密切之关系。楚调曲本为楚声而亦用筝者,当系受秦声之影响而然。①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9—30页。
萧先生举乐器“筝”作为例子,同样也可以说明清、平、瑟三调出于“西方之秦声”。当然,更准确地说,是三调原出周人的《房中乐》,并经秦人修改过,亦即前引《汉书·礼乐志》所说的“至秦名曰《寿人》”。因此,萧涤非先生的观点与王小盾先生的观点颇为矛盾,而且各自使用了一种乐器作为佐证,恐怕大家都难以说服对方。
其四,应从相和曲、清商曲结构的特点予以考虑。有学者认为,《宋书·乐志》所录十五大曲均在瑟调,而瑟调曲有“乱”,与《楚辞》之有“乱辞”在结构上是相同的,因此瑟调的大曲应源于楚曲,故瑟调和生于楚调的侧调相同②比如王运熙先生《清乐考略》一文曾指出:“《宋书·乐志》著录大曲共十五曲,其中四曲有艳有趋,一曲有艳,二曲有趋……《宋志》所录大曲无乱,所载陈思王《鼙舞歌》五篇,二篇有乱。又《乐府诗集》瑟调曲《孤子生行》也有乱。乱与趋性质相同,均在歌曲末尾。乱辞是楚歌结构上的特点之一,是很明显的,《离骚》、《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诸篇和《招魂》均有乱辞。乐府楚调曲《白头吟》原有乱辞,也是一种佐证。大曲的特点是结构比较复杂,其音调则同于瑟调,故‘大曲十五曲,沈约并列于瑟调’(《乐府诗集》卷26)。上面考证瑟调当即是侧调,侧调生于楚调;这样,大曲受楚歌影响较大,是很自然的事情。”(《乐府诗述论》,第206—207页)。然而,这也不是绝对的。《论语·泰伯》记载:“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6页。由此可见,“乱”这种曲式结构并不仅仅限于《楚辞》一类的南方音乐,北方鲁国的音乐亦可有之。由于鲁国的礼乐直接渊源于周人,这说明周人《房中乐》的瑟调曲也不妨有“乱”。换言之,乱声不能作为侧调与瑟调同出于楚声的有力证据。
其五,从相和曲、清商曲演奏的方式考虑。学者一般认为,“相和”这种演奏方式源自于楚声,所以瑟调也出于楚声,与侧调无别④比如王运熙先生《清乐考略》一文提到:“相和一名的涵义,据《宋志》,是由于‘丝竹更相和’而来……我以为相和一名,原当泛指‘一人唱余人和’而言,其用以和者可以是人声,可以是丝竹声,也可以是人声与丝竹声兼有……它的‘一人唱余人和’的方式,在先秦的楚歌中已经如此,宋玉《对楚王问》中说‘国中属而和者’,是人声相和。其后演为乐曲,就配上乐器了。”(《乐府诗述论》,第202页)。然而据史料的记载,“相和”一类的演奏、演唱方式未必就是源出楚声,《通志·乐略一》的引证可以为例:
曰相和歌者,并汉世街陌讴谣之辞,丝竹更相和,令执节者歌之。按《诗·南陔》之三笙以和《鹿鸣》之三雅,《由庚》之三笙以和《鱼丽》之三雅者,相和歌之道也。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部,更递夜宿。始十七曲,魏晋之世,朱生、宋识、列和等复为十三曲。自《短歌行》以下,晋荀勖采撰旧诗施用,以代汉、魏,故其数广焉。⑤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98—899页。
由此可知,“丝竹更相和”这种做法可能从周人演奏《诗》乐时就已经开始,不一定是楚人乐曲专有的特点。而《南陔》、《鹿鸣》、《由庚》和《鱼丽》皆属《小雅》,“雅者夏也”,亦与楚乐无关。再者如前述,清、平、瑟三调出于周世《房中乐》,故瑟调从周人乐中就可以继承“相和”的演奏特点,未必要和“生于楚调”的侧调等同起来。
其六,一般认为清商乐源于相和曲,而琴曲中保留相和旧声最多,所以后世往往把“琴曲”也列入清乐的范畴。如果从琴曲调的角度考察,也会发现“侧调即瑟调说”与史料记载相矛盾。以下先看《韩非子·十过》中的一段记述:
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车而放马,设舍以宿。夜分,而闻鼓新声者而说之,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乃召师涓而告之曰:“有鼓新声者,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其状似鬼神,子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静坐抚琴而写之……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酒酣,灵公起曰:“有新声,愿请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师涓,令坐师旷之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平公问师旷曰:“此所谓何声也?”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①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2—64页。
这大概是最早有关“清商乐”的文献记载,而当时演奏清商“新声”者恰恰使用了“琴”这种乐器,由此可见清乐自始即与琴曲存在密切联系;北魏至隋唐以来,把琴曲划入清乐范畴是不无道理的。而其中有一件事颇值得注意,即北魏后期通过战争掠得南方大批声伎,并总谓之清商乐,且有北朝的学者开始对清商三调乐律进行研究、整理,这在《魏书·乐志》中颇见记载:
先是,有陈仲儒者自江南归国,颇闲乐事,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神龟二年夏,有司问状。仲儒言:……然后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其瑟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角为主。五调各以一声为主,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方如锦绣。②魏收:《魏书》卷109,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33—2836页。
在此,陈仲儒提出了“瑟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角为主”的看法,其理论是“依琴五调调声之法”得出来的,应当比较可靠。而另二调当即楚调和侧调,可见瑟调与侧调是不同的“调声之法”③琴具七弦、备五声,琴家将七弦中的一条或多条放松(慢)或收紧(紧),可以改变弦的音高,从而实现调式的变化,大致就是陈仲儒所讲的“调声之法”。。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史料,见于《宋史·乐志十七》“琴律”所述:
《五弦琴图说》曰:“琴为古乐,所用者皆宫、商、角、徵、羽正音,故以五弦散声配之。其二变之声,惟用古清商,谓之侧弄,不入雅乐。”④脱脱等:《宋史》卷14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42页。
这条史料也提到了琴曲调,还特别提到了“古清商”中的“侧弄不入雅乐”,此侧弄当与相和五调中的侧调有关。如果把《魏书·乐志》的史料和《宋史·乐志》的史料放在一起比较,瑟调与侧调的差别就更能显示出来了。因为“瑟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角为主”,所以清商三调全都是“正音调”⑤陈仲儒对三调的看法,当世学者多认同之,如丘琼荪先生《燕乐探微》一书指出:“平调以角为主,清调以商为主,瑟调以宫为主……是故汉、魏、六朝清乐曲中的平、清、瑟三调,即《晋书·律志》和《宋书·律志》所纪的清角、正声、下徵三调,而汉魏人则称之为平、清、瑟。说得明白些,平调即清角(即角调)调,清调即清商调,瑟调即下徵(以下徵为宫)调。这三种调法,在晋、宋书《律志》中都详细记载……清调曲用商,而此商孔却在宫孔之上,反清于宫,这便是清调又称为‘清商’的原由了……清角即角,晋、宋《志》注云:‘笛体中翕声也……清角之调,乃以为宫,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哨吹即高吹也……汉魏六朝行用下徵,亦以下徵为宫。箜篌引是下徵,所以称之为箜篌宫引,这是合乎事理的。箜篌宫引是下徵之宫,宫引第一是正声之宫,两宫字都不可少,名同而实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8—42页)另如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指出:“《相和歌》中间常常用到三种调式。所谓三调,就是平调、清调和瑟调。平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瑟调以角为主。用现在的说法来说,平调相当于fa调式,清调相当于sol调式,角调相当于la调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8—42页。,古人以宫、商、角、徵、羽为五正音。而“侧弄”使用“二变之声”,属于五正音以外的变声调,所以瑟调、侧调恐难等同起来。
其七,从《乐府诗集》所录《相和歌辞》诸调名的角度考虑。由于《乐府诗集》所录相和五调曲辞中独缺“侧调”,遂有学者据之认为侧调即瑟调,所以不烦另录。窃以为,此说也不尽可靠。据《乐府诗集》所录《相和歌辞十六》的“解题”称: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楚调曲有《白头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东武琵琶吟行》、《怨诗行》。其器有笙、笛弄、节、琴、筝、琵琶、瑟七种。”张永《录》云:“未歌之前,有一部弦,又在弄后,又有但曲七曲:《广陵散》、《黄老弹飞引》、《大胡笳鸣》、《小胡笳鸣》、《鹍鸡游弦》、《流楚》、《窈窕》,并琴、筝、笙、筑之曲,王录所无也。其《广陵散》一曲,今不传。”⑥《乐府诗集》卷41,第599页。
从《乐府诗集》编者引用《古今乐录》、《伎录》等古籍的情况来看,他对“楚调曲”的特点是比较清楚的。另如前述,《乐府诗集》中曾明确指出过侧调“生于楚调”,故编者之所以不录侧调歌辞,更大的可能是由于侧调曲辞可以在楚调中演奏,或者说楚调曲辞实际上已经包括了侧调曲辞在内。这比起前人所说的“侧调即瑟调,故不录侧调”,似乎更加简单直截。
除上述七点以外,关于相和五调还有以下两种说法:第一,谢灵运《会吟行》句云:“六引会清唱,三调伫繁音。”李善注曰:“沈约《宋书》曰:‘……第一平调,第二清调,第三瑟调,第四楚调,第五侧调。’然今三调,盖清、平、侧也。”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2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16—1317页。第二,六臣注《文选》录古乐府《君子行》一首,题注称:“五言平调,(吕)向曰……瑟有三调,平调、清调、侧调,此曲处于平调。”②萧统编,李善、吕延济等注:《六臣注文选》卷27,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11页。第一种说法虽与《梦溪笔谈》“清、平、侧三调”的说法一致,但却恰恰说明了“古清平瑟三调”与“今清平侧三调”并不一样,侧调之取替瑟调成为“今三调”之一,大概另有原因,只是史料阙如,目前暂不能解释清楚而已。第二种说法出于唐人注解,不详其所据典籍。所谓“瑟有调”,当指瑟这种乐器能奏出之调,并不是说瑟调等同于侧调也。
二
接下来拟讨论清乐表演者性别的问题。一般而言,清商乐的发展可以分为两大阶段,“魏晋清商旧乐”是一个阶段,“南朝清商新声”是另一个阶段③有关清乐分段的问题,过往相关著述多有谈及,兹不赘。。在有关清商旧乐及其前身的记载中,这些表演往往与“女乐”联系在一起,如张衡《西京赋》写道:
祕舞更奏,妙材骋伎。妖蛊艳夫夏姬,美声畅于虞氏。始徐进而羸形,似不任乎罗绮。嚼清商而却转,增婵蜎以此豸。④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2《赋甲·京都上》,第78页。
此处的“嚼清商”者显然是女乐。《三国志·齐王芳》注引《魏书》又提到:
太后遭郃阳君丧,帝日在后园,倡优音乐自若,不数往定省。清商丞庞熙谏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忧,水浆不入口,陛下当数往宽慰,不可但在此作乐。”帝言:“我自尔,谁能奈我何?”……每见九亲妇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⑤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0页。
从这则记载看,曹魏时期已有“清商署”这一乐官机构的建制。引文说“九亲妇女有美色”就“留付清商”,可见清商署内所辖均为女性;由此也可推断,早期清商旧乐的表演者主要是女性。此外,《宋书·后妃传》还提到:
清商帅,置人无定数。总章帅,置人无定数。⑥沈约:《宋书》卷4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75页。
总章始于东汉末的女乐⑦有关问题详见黎国韬:《总章考》,《音乐研究》2008年5期。,此处与清商并列,且载入《后妃传》中,说明直至刘宋时期,清乐的表演者仍以女性为主。有鉴于此,王运熙先生在《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一文中遂归纳出以下一个重要观点:
更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即清商曲常由妇女来歌唱。上引张衡《西京赋》“嚼清商”云云,其演唱者为妇女。曹魏清商三调兴盛,遂设有清商专署管理此种女乐……这种制度为后代所沿袭。晋代光禄勋属官仍有清商署。宋齐两代一度并清商于太乐署。但宋代女官中仍设有清商帅一职,见《宋书·后妃传》。到梁陈时代,太乐令下又设清商署丞。六朝吴声、西曲以至江南弄等清商曲辞,绝大部分用女子的口吻来抒发和描写,这样由女伎歌唱,更觉身分贴切,富有真实感……吴声、西曲等继承了过去清商三调的传统,都是以丝竹伴奏的娱乐性乐曲,又都是女乐,由清商乐署掌管,理应称为清商乐。①《乐府诗述论》,第400页。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尚有一些补充的余地。首先,清商乐是一种“部乐”性质的表演,所以《宋书·乐志三》记载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②《宋书》卷21,第603页。另据《隋书·乐志》记载: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调,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及(隋)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其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五人。③魏徵等:《隋书》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76—378页。
这条记载更为清楚,清乐是当时《七部乐》之一;而所谓“部乐”,就是掌管固定乐曲,有固定乐工人数,有固定演唱者或舞蹈者,在固定场合演奏的乐舞组织形式。如果从“部乐”的角度审视清商乐的表演,则一般都有男性乐工的参与,像隋朝的《清乐部》就有乐“工二十五人”,他们作为乐器演奏者,应当不是女性。因此,不宜笼统地说清商乐“都是女乐”,而应该说这一部乐的演唱者和舞蹈者以女性为主。
其次,在宋齐以后,随着清商新声的不断发展壮大,清乐的“演唱者”中也不时有男性的出现,这个时候就更不能简单地用女乐来概括清商乐了。如《通典·乐五》记载:
梁有吴安泰,善歌,后为乐令,精解声律。初改西曲,别[制]《江南[弄]》、《上云乐》,内人王金珠善歌吴声西曲,又制《江南歌》,当时妙绝。令斯宣达选乐府少年好手,进内习学。吴弟,安泰之子,又善歌。次有韩法秀,又能妙歌吴声读曲等,古今独绝。④《通典》卷145,第3700页。笔者案,此段引文有脱误,据许云和先生《乐府推故》观点改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3页。
这位善改西曲的乐令吴安泰显然不会是女性,其子吴弟“善歌”,也不是女子;而斯宣达所选的“乐府少年好手”自然亦非女乐,但他们“进内习学”者却确是列入清商新声范畴的吴声、西曲。另如唐人杜佑撰写的《通典·乐典》“清乐”一条提到:
清乐者,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氏以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调,与魏三祖所作者,皆备于史籍……自长安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转缺,能合于管弦者,唯《明君》、《杨叛》、《骁壶》、《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旧乐章多或数百言,武太后时《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传二十六言,就之讹失,与吴音转远。刘贶以为宜取吴人使之传习。开元中,有歌工李郎子。郎子北人,声调已失,云学于俞才生。才生,江都人也。自郎子亡后,《清乐》之歌阙焉。⑤《通典》卷146,第3716—3718页。
从这则记载看,唐代宫廷专习“《清乐》之歌”的李郎子就是男性,而不是女乐;至于郎子的师傅俞才生,也明显是男性“歌工”。以上材料有力地证明,宋齐以后清商乐的演唱者不少已是男工而非女乐。这一表演者性别的转换,大概即始于萧梁时期选乐府少年好手“进内习学”吴歌、西曲。当然,就现有材料来看,清乐的舞伎似乎极少选用男性。
还有一点可以稍作补充。一般认为,清商乐源出于汉代的“相和曲”;而汉相和之曲也并不限于女乐表演,如《汉书·礼乐志》记载:“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⑥《汉书》卷22,第1045页。由此可见,汉代“相和”之曲也有使用男性“歌儿”表演的。而魏晋清商旧乐的演唱者以女性为主,这在当时大概是一种创新,而这种创新可能始于魏明帝,所以前引《宋书·乐志三》提到:“《相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⑦《宋书》卷21,第603页。既然要“更递夜宿”,于是就改以女乐为宜了。
三
一般而言,南朝清商新声是由魏晋清商三调和南方的吴歌、西曲相结合而生成的,在西曲之中有一首乐曲名叫《女儿子》,据《乐府诗集》卷47《清商曲辞四》所录《西曲歌》之“解题”云:
《古今乐录》曰:“西曲歌有《石城乐》、《乌夜啼》、《莫愁乐》、《估客乐》、《襄阳乐》、《三洲》、《襄阳蹋铜蹄》、《采桑度》、《江陵乐》、《青阳度》、《青骢白马》、《共戏乐》、《安东平》、《女儿子》、《来罗》、《那呵滩》、《孟珠》、《翳乐》、《夜度娘》、《长松标》、《双行缠》、《黄督》、《黄缨》、《平西乐》、《攀杨枝》、《寻阳乐》、《白附鸠》、《拔蒲》、《寿阳乐》、《作蚕丝》、《杨叛儿》、《西乌夜飞》、《月节折杨柳歌》三十四曲。《石城乐》《乌夜啼》、《莫愁乐》、《估客乐》、《襄阳乐》、《三洲》、《襄阳蹋铜蹄》、《采桑度》、《江陵乐》、《青骢白马》、《共戏乐》、《安东平》、《那呵滩》、《孟珠》、《翳乐》、《寿阳乐》并舞曲。《青阳度》、《女儿子》、《来罗》、《夜黄》、《夜度娘》、《长松标》、《双行缠》、《黄督》、《黄缨》、《平西乐》、《攀杨枝》、《寻阳乐》、《白附鸠》、《拔蒲》、《作蚕丝》并倚歌。《孟珠》、《翳乐》亦倚歌。按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①《乐府诗集》卷47,第688—689页。
可见,《女儿子》属于清商新声中《西曲歌》里面的“倚歌”一类。“解题”后录有《女儿子》曲辞二首,其一云:“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另一云:“我欲上蜀蜀水难,蹋蹀珂头腰环环。”②《乐府诗集》卷49,第713页。从内容来看,此二曲有可能是源出于巴东的民歌。从时间来看,它在南齐时已见演出,如《南齐书·东昏侯纪》记载:
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卧未熟。闻兵入,趋出北户,欲还后宫。③萧子显:《南齐书》卷7,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6页。
此事亦见于《南史·东昏侯纪》。对此,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一书中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作《女儿子》”就是戏剧表演中的“妆旦”。任先生还更进一步具体指出:
“作女儿子”,“作”谓演也……“女儿子”应指少女,犹之后世扮小旦、花旦耳……综论我国古代生旦戏发展经过,有七要点:前于此者,曰西汉之胡妲,曹魏之作“辽东妖妇”;后于此者,曰初唐之演合生戏,盛唐之演《踏谣娘》,中唐之有“猥亵之戏”,晚唐之弄假妇人“尤能”。此七点,一线相承,事至明晰……但若遗此两点,尤其东昏侯之作女儿子,则此事之脉络遂断矣。④任半塘:《唐戏弄》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
假如以上所述正确的话,东昏侯之“作《女儿子》”就是南朝时期一出与清商乐有关的戏剧了。然而任先生所述的影响虽然不小,却未能提供有力的证据,他将“作”理解为“戏剧扮演”,将“女儿子”理解为戏剧脚色“旦”,都有一厢情愿之嫌。因为《女儿子》是西曲曲名,与“旦”脚根本没有联系,至于“作”字,也和“演戏剧”无关。
下面不妨就这个“作”字展开探讨,以证明任先生所说不妥。在六朝的时候,歌舞表演往往被称为“作伎”,试举两例以为证:
《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倡此曲,当时特妙。(《宋书·乐志三》)⑤《宋书》卷21,第603页。
世祖于南康郡内作伎,有弦无管,于是空中有篪声,调节相应。(《南齐书·祥瑞志》)⑥《南齐书》卷18,第354页。
不难看出,汉魏时期的“作伎”,仅指歌乐演奏,与戏剧扮演毫无关系。而南齐世祖“有弦无管”的伎乐也只是和清乐演奏方式相近的表演。依据此两例以理解“作《女儿子》”,不过就是“演奏清商新声中的西曲《女儿子》”而已,怎么也联系不到“戏剧妆旦”上面去。另外,王运熙先生在《吴声西曲的产生时代》一文中曾指出:
舞曲与倚歌之别,除有舞无舞外,尚有乐器上的区分。《古今乐录》说:“凡倚歌,悉用铃鼓,无弦有吹。”丝竹是清商曲的主要乐器,倚歌有竹无丝,可说是一特殊的部分……倚歌无弦有吹,倚的应当是竹器。《飞燕外传》说:“帝以文犀簪击玉瓯,令后所爱侍郎冯无方吹笙以倚后歌。”这就和东昏的“吹笙歌作《女儿子》”(《南齐书·东昏纪》)相同了。①《乐府诗述论》,第9页。
王先生根据“倚歌无弦有吹”的特点,将“作《女儿子》”理解为“倚笙而歌”此曲,可谓相当准确,也和“作伎”的意思相近。而任半塘先生之所以把“作《女儿子》”视为“妆旦”戏的一种,关键还是把“作”字错解成“演戏剧”,进而又把曲名“女儿子”错解成“少女”,于是才出现了“妆扮旦脚”以及“生旦戏发展经过有七要点”的误解。换言之,《女儿子》属清商新声《西曲歌》的范畴,与戏剧表演并无关系。
小 结
以上对清商乐中三个具有一定争议的问题作了探讨,并提出了笔者自己的看法。在侧调与瑟调关系的问题上,过往多数学者认为两者是等同的,然而这却和历史文献的诸多记载相矛盾,有的矛盾还很难解释得通。因此,从乐调数量、乐调产生地域、相和曲及清商乐所用乐器、曲式结构特点、乐曲演奏方式、琴曲调名等多个角度来看,侧调都难以等同于瑟调。
在清商乐表演者性别的问题上,不少学者已指出魏晋清商旧乐的表演者多为女乐的事实,这是很有意思的发现。但仍有值得补充之处,特别是宋齐以后,作为南朝清商新声的吴歌、西曲,其演唱者和奏乐者有不少是男性乐工,这在《隋书·乐志》、《通典·乐典》等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大致而言,男性演唱者的不断出现是从南朝萧梁时期开始的。
在“作《女儿子》”的问题上,任半塘先生曾认为这是古代戏剧“妆旦”演出的一种,这一观点与事实不符。因为“作”是“演奏”之义,“女儿子”则是西曲曲名而非指“少女”,“作《女儿子》就是“演奏《女儿子》这首清商曲”,与“演戏剧”并无关系。
以上三个问题都与清商乐有关,其辨明对于中古诗歌史、乐舞史、戏剧史研究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述不当之处,敬祈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