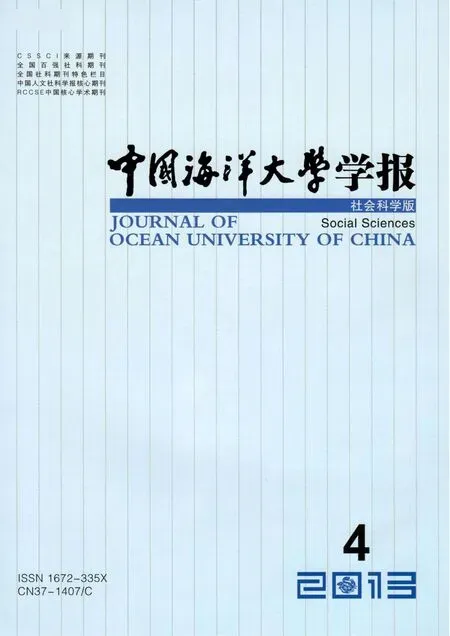论法国学者蒲芳莎(Françoise Bottéro)的《说文》研究*
张大英
(1.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2. 青岛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520)
论法国学者蒲芳莎(Françoise Bottéro)的《说文》研究*
张大英1,2
(1.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2. 青岛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520)
法国学者蒲芳莎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分析方法围绕《说文》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其《说文》研究十分深入,理据充分,角度新颖,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她做《说文》研究视野开阔,重视各国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涵盖了来自中国、日本、欧美相关的资料;通过其《说文》研究,我们还可以感觉到她对中国古代典籍非常熟悉,引用起来得心应手。因此我们认为她是当代西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说文》研究专家。
法国学者; 蒲芳莎;《说文》研究
蒲芳莎(Françoise Bottéro),法国国家科学院东亚语言研究所(CNRS,CRLAO)学者。白谦慎等人的文章《中国书法在西方》提到她“据古代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对汉字分类作了深入研究,这不仅有助于中国书法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也有益于关注汉字形成的学者。”[1]中国学界对外国学者有关《说文》的研究,目前还未见有较系统的介绍和深入探讨,本文不揣冒昧,绍介于此,以飨读者。
蒲芳莎《说文》研究著述有英文的,也有法文的,她围绕《说文》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一、围绕《说文》,涉及面广泛
(一)关于《说文》部首系统
蒲芳莎1994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汉字的语义性及其分类:从“说文解字”到214部系统的汉字分类研究》。1996年蒲芳莎出版了以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汉字的语义性及其分类:从<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以部首整理汉字的系统》。
该书分四章。第一章讨论《说文》基本情况,包括对《说文·叙》的仔细分析。第二章研究以《说文》为本的系列字书。第三章讨论作为《说文》/《玉篇》类型和后来字书类型分类系统重要过渡时期唐代的几部字书:《五经文字》、《新定一切经类音》等。第四章讨论被她称之为“佛道”字典的著作(因为编撰者是和尚或者道士),仔细研究了《龙龛手鉴》和《五音类聚四声篇》。在结语中,她简洁回顾了从《说文》到《四声篇海》以部首对汉字进行分类之系统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部字书构成了这个过程中和革新有关的出发点和终止点,前者确立了语义分类的基本概念,后者确立了用单个笔画作为辅助标准的方案。她认为传统的部首方案有可能限制手写本潜在的“语音主义”(phoneticism)即语音拼字法,字典编纂长期坚持基于语义的汉字分类方案,则有效而长期地保存了汉字书写系统直到现代,尽管在某些方面不合逻辑。
蒲芳莎目的主要在于寻找《说文》部首系统背后的思想和信念。她想表明,通常认为从《说文》540部到梅膺祚《字汇》214部是一条直线发展的道路是严重的误导。这种认识“错过了一千五百多年来所有促成这种发展模式背后的各种各样的动机”。[2](P474)她比较了《玉篇》和《说文》的部首分部情况,为的是“根据二者之间的不同,看能否得出关于每个方案背后思想的什么推论来”。[2](P472)她还把反映通俗口语的、基于词义分类的五个敦煌手写本词表和《说文》分类系统进行了对比,并认为这些词表都是和通俗语言有关,而不是经典的,因此它们“倾向于避开《说文》和《玉篇》高深的正字法分类方案,而更青睐以语言为基础的即基于词汇的分类”。[2](P472)她也分析了唐代作为《说文》字形分类系统和后来字书语义成分分类系统之非常重要过渡时期的原因:一是在唐代《说文》变成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必考科目;二是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异体字的威胁,试图确立正确书写标准的规范性著作开始出现。可见蒲芳莎将《说文》部首研究与东汉及其后来发展的思想史联系起来,也同中国的辞书发展史联系起来。
美国著名汉学家鲍则岳2000年发表文章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说文》分部之选择和顺序背后隐含的理性和逻辑一直都是一个严肃的研究话题,而蒲芳莎的研究是“最新的,也肯定是此类研究中最彻底和最周全者之一”,[2](P471)把她的工作和其他《说文》部首系统研究区别开来的是“她把研究扩展出《说文》之外,调查了从《说文》到《康熙字典》之间受《说文》启发的所有其他重要字书的分部方案”,[2](P471)并且还认为“这部著作非常详细且文献丰富,可被视为对中国辞书发展史语文学严谨精细学识的典范”。[2](P474)
蒲芳莎还曾在《文字统一和辞书编纂》一文“按部首编排的字书”部分中详细讨论了《说文》、与《说文》一脉相承的字书《玉篇》以及后人对《说文》部首概念的改革。[3]她认为汉字的部首系统不仅仅是汉字的一种简单的编排方法,它同时也揭示了人的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形成是和部首的系统产生的思维不可分割的,是对知识归类的一个显著例证。[3]这种归类在拼音文字系统中是难以想象的。她说:“汉字的义符和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某种世界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慎的著述则是对这一关系的揭示。”[3]由此可见她对《说文》部首的研究是独特而又深入的。
(二)关于《说文》六书
1.探讨六书性质
蒲芳莎作为第一作者与挪威汉学家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合作发表的《<说文解字>与中国的人文科学》一文中谈到六书性质。[4](P252-254)关于六书性质传统说法有“造字之本”、“四体二用”等,而该文认为,许慎各种对“书”的描述是动词性的而不是名词性的,把“六书”翻译为“Six (Categories of) Scribal Acts”(六类书写行为范畴),即“创造一个字所涉及的行为类型”,[4](P252)并全部用动词表达式来翻译具体的六书。[4](P252)对许慎六书中如转注、假借描述不清楚的问题,作者认为“在这一点上没有必要去涉及关于六书的争论性细节”,[4](P253)六书从来没有机械地甚或偶然地强加于字典本身,传统所说的假借,许慎在字典主体中完全不关心这些:他所解释的是非借来源的字的本义。
2.讨论六书顺序
蒲芳莎1998年在《东亚语言学报》(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简称CLAO)27卷第2期上发表了《许慎六书表述中的文字观》(La vision de l’écriture de Xu Shen à partir de sa présentationdes liushu)一文,谈到许慎是第一个给出六书定义的人,奇怪的是他的术语被接受,但是他的六书顺序没有被采纳,而班固的顺序成为标准。蒲芳莎在文中对比了许慎、班固和郑众的六书顺序,她认为仔细分析会发现实际上许慎的六书顺序揭示了他的文字发展观,而不是专用于分析汉字。
3.分析六书字例
1996年蒲芳莎在评介鲍则岳《中国文字系统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一书的文章中,分析了《说文》会意字字例之一“信”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公元一世纪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一书中给出的两个例子之一确实有问题,鲍则岳说“信”字形结构中有表音成分是对的。但是根据白一平(Baxter)和裘锡圭的构拟,表音的不是构字成分“言”,而是“人”。
信xin < sinH < *snjins, 'trust'
人ren < nyin < *njin 'man'
言yan < ngjon < *ngjan 'speech'
极有可能在许慎的时代,“信”和“人”之间语音上的亲缘关系已经不再明显,前缀s-给“信”一个清擦音,而在“人”这个情形下则保留了鼻音声母。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许慎把信看成是一个真正的会意字,即由语义构建的字,而不是形声字的原因。[5](P576)
(三)关于《说文》中的“文”与“字”
在2001年首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蒲芳莎提交的论文是《〈说文解字〉中“文”与“字”两个概念的检析》,她“将《说文·叙》中出现的‘文’、‘字’和‘文字’一一检出,并逐个考察它们所表示的意义,从而认为传统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6]2002年蒲芳莎在《远东古物博物馆学报》(BMFEA)上发表《重审“文”与“字”:最大的汉字骗局》一文,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该文分析见解独到深刻,我们将在“钻研深”部分再对此文进行详细讨论。
(四)关于《说文》所述中国文字发明过程
蒲芳莎研究《说文》所述中国文字发明过程主要见其《仓颉和文字发明:对一个传奇阐述的反思》与《中国文字:古代本土视角》两篇文章。二者有些重复的部分,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主要讨论许慎如何理解涉及文字起源的仓颉造字传说,后者则关注许慎如何理解汉字演化过程以及这一认识对其汉字分类与汉字分析的影响。
1.《说文》所述仓颉造字传说
蒲芳莎《仓颉和文字发明:对一个传奇阐述的反思》一文,通过追溯仓颉造字传说的历史,讨论了该传说是如何构建和确立的,以及古代中国学者是怎样认识它的重要性并且如何在自己的思想框架内利用和阐释它的,其中涉及许慎对仓颉造字传说的理解。
《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世本》、《论衡》等众多古籍中都记载了造字的传说,不同的学派把文字发明者归为不同的人:仓颉、史皇、沮诵。许慎只保留了仓颉。蒲芳莎认为,许慎筛选了这些不同的版本,然后选择他想保留的元素,展现出一种合理性。通过重新组织仓颉的传说使它适应汉朝时其他传说的语境,而且也让它更连贯和可信,在整理古文方面,许慎从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一个与刘向和刘歆差不多的角色。通过这种方式他一次性永远地确立和加强了这个传说。在《说文》中,仓颉被确定为黄帝的史官,许慎把他编入一个划分得非常好的历史顺序中。先是伏羲作八卦,然后是神农时代的结绳,接着就是仓颉发明文字。尽管第一段是取自《易经·系辞》,但是许慎用自己的方式来阐释这个故事。在《系辞》中,是包羲发明结绳作网狩猎捕鱼,神农用来统治,是圣人易之以书契。《系辞》中并没有明确是哪一位圣人易之以书契,但是许慎宣称就是仓颉,黄帝的史官,发明了文字。而且许慎接着解释仓颉是如何产生文字观念的:伏羲受鸟兽之文启发而创造八卦,仓颉则是受鸟兽留在地上的踪迹的启发。也就是说,许慎在他的叙中表明仓颉发明文字是效法伏羲,正像八卦和结绳一样,文字是用来统治的。就像对《系辞》中所有发明的变形,文字受到《夬卦》的启发。许慎坚持所有文化重要发明根源在于《易经》的观点,他采取了《系辞》的传统,但是用自己的方式来阐释文字的起源,因为关于这一点《系辞》说得很少。就像《淮南子》、《易经·系辞》或者《汉书》所说的那样,许慎肯定文字让管理变得可能,同时坚持文能宣教明化,以及有助于道德的培养。这表明他对“文”的传递性有很强的信心。
蒲芳莎指出,和前面的学者相比,许慎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更进一步把文字的概念定义为踪迹,包括以前的踪迹和将来的踪迹:“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说文·叙》中描述了“字”的历史发展过程:“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这非常重要的一段文字通常没有被好好地阐释。许慎解释说,在文字记录语言之前,有简单的文字画。也就是说,文字画对现实的描摹要早于文字词对现实的描绘,正是通过把口语中的词和每个形象相联系,文字才开始记录语言。
2.《说文》所述汉字演化历史
在北京大学2007年“早期文字体系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蒲芳莎通过《中国文字:古代本土视角》一文,考察了古代中国人是如何反思自己的文字系统的,其中涉及到对《说文》所述汉字演化历史的认识。
蒲芳莎提出反思中国文字起源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个人的书写行为,二是文字在社会和政府中的作用。所以法家代表人物最早反思中国文字起源绝对不是偶然,后来《说文》作者许慎也发展出文字和政府职能相辅相成的观点。许慎作为公元1世纪汉朝学者在《说文·叙》里对文字演化历史和相关理论进行了反思。先是伏羲受自然启发作八卦,然后是神农结绳而治,再到黄帝史官仓颉初造书契,但是在许慎看来文字的发明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她由此总结出许慎所述之文字产生过程:1八卦发明,代表现实,用来理解世界;2发明描摹自然的图画,即“文”;3把图画与词和发音联系起来,即“字”。
蒲芳莎还对许慎、班固、郑众对汉字六书分类理论做了比较,认为三者顺序不同说明在公元一世纪时人们对文字起源有了不同看法:许慎认为开始于抽象符号,班固和郑众认为始于象形符号。她认为许慎的排列顺序和他《说文·叙》中谈到的文字发明过程相对应。指事与八卦对应,象形与描摹自然对应,形声与给图画加声相对应。许慎与文字发明相对应的六书理论已经认识到字的语音层面,受此影响,在他的字典中分析汉字时率先把字分析成语义成分和语音成分。而在古代文献中,分析字的构成成分从没有提到语音成分,比如《左传》、《史记》中的例子我们看到的都是语义性的。因此与传统的汉字分析法相比,这是一种全新的方法。
(五)关于《说文》的性质与价值
蒲芳莎在《<说文解字>与中国的人文科学》一文中试图重构《说文》成书的历史过程,目标是确立《说文》在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其研究不是解释现成文本,而是解释产生文本的过程,作者打比方说“就像威廉·冯·洪堡特一样,我们不仅对产品(ergon)也对其创造活动(energeia)感兴趣”。[4](P249)文章指出《说文》在科学历史上重要的原因不仅是它自身包含了大量科学知识,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前后一致的规程和透明的分析性术语系统带给我们定义明确的一门重要学科”。[4](P271)科学不仅仅是关于信息,也关于符合逻辑的连贯系统分析。因此,《说文》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史学家重要的资源,它“自身是科学研究的一座丰碑,而且科学的历史不能仅仅简化为自然科学的历史”。[4](P271)该文还认为“《说文》不是一本关于词的基本意义的词典。它是关于字源的词典,并且字源需要和字义分析仔细区分开来。《说文》只提供与用来记词的字形解释有关的意义。同样,《说文》提到字音的范围是它们和字的读音成分解释有关。”[4](P249)作者分析,许慎为所解释的字加另外一个读音或另外一个意义时,它们都被解释为原则上与字形相关。这些从来都不是试图给出词的不同意义全面纵览。许慎注释中所给出的意义经常不是相关词的基本意义,而是他认为最适合解释字形结构的意义。比如,“所”字,《说文》:“伐木声也”,许慎肯定知道这对此字在文章中的理解帮助不大,但他愿意坚持字形得到最好理解的那个意义。作者的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说文解字>与中国的人文科学》一文认为《说文》的每个字条都是根据一定规则来编纂的,在编写字典过程中,许慎继承了中国的注释传统。《说文》中数不胜数的规范的和不规范的引文提供了充足的历史联系。然而,作者认为,许慎的字典是关于字的而不是关于具体上下文中的字的。用现代术语来说:“许慎关心的是语言的系统,而不是具体的言语”。[4](P251)他的兴趣是语言的书写系统,而再也不是如注释传统中的在具体上下文中出现的每一个字。笔者认为这个认识比较恰当地说明了许慎《说文》说解条例的语言学价值。
(六)关于《说文》的翻译
蒲芳莎还比较关注《说文》的翻译问题,她曾在其博士论文中给出带有详细注释的《说文·叙》法语翻译。[2](P471)她在《<说文解字>与中国的人文科学》一文中还就《说文》翻译提出了看法。[4](P270-271)中国典籍文中的句子经常需要在上下文的基础上来消除歧义,而《说文》释义脱离上下文,因此《说文》翻译一直让人不得不在没有充足的上下文的帮助下补充意义,结果就《说文》翻译变得更加证据不足。然而,作者认为有仔细注解的《说文》翻译还是有巨大需要的。
二、见解独特,钻研深入
蒲芳莎的《说文》研究除了涉及面广以外,还钻研比较深入,能够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这里我们仅以她2002年在《远东古物博物馆学报》(BMFEA)上发表《重审“文”与“字”:最大的汉字骗局》一文为例进行分析。
蒲芳莎此文主要目的是要弄清《说文》如何看待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她先破后立,批判了传统认为许慎的“文”与“字”为“独体字”与“合体字”区别的看法,然后提出自己的新解释,最后展示了许慎文字观的独创性。全文结构逻辑清晰,分为四部分:1.《说文》之前的字形解释。讨论《说文》之前某些典籍中对汉字的解释,对比了今文学派的分析和许慎的分析、纬书的字形分析和许慎的字形分析。2.许慎眼中的文、言关系演化。通过分析《说文》中的“文”与“字”来展示许慎对文字和写下来的词之间关系的理解。3.《说文》展示的许慎文字观的独创性。4.结论。认为从来没有证据表明许慎用“文”或者“字”来分别指代“独体字”和“合体字”。许慎作品中“文”和“字”的用法揭示了一个一方面是字形结构、另一方面是书写系统之间的基本区别。
(一)对“文”与“字”之独特理解
《说文·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段玉裁将其概括为:“析言之,独体曰文,合体曰字。”段氏对于《说文·叙》中“文”、“字”之理解,得到中国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也被很多西方学者所接受,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鲍则岳在《剑桥中国先秦史·语言文字》中对《说文》中“文”与“字”的介绍采用的正是段玉裁的注解。[7](P122,Note 82)
但蒲芳莎认为“文”与“字”这个区别对《说文》无效。她认为关于独体字和合体字的区别实际上在《说文》之前,包括叙文在内的整个《说文》标准文本中,东汉其他与此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源里都没有证据。她给出了自己的依据:
1.文=独体字的等式在《说文》之前不存在
蒲芳莎认为在《说文》之前没有显示出“文”与“字”是一个对立的概念,这两个字可能有不同的外延,但所指的都是同一事物即汉字。她给出例子:夫文,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故文,反正为乏。(《左传·宣公十五年》);於文,皿虫为蛊。(《左传·昭公元年》)等,这里武、蛊都不是独体字。
2.《说文》正文对“文”与“字”的说解无此区别
《说文》正文:“文,错画也。象交文。”“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声。”蒲芳莎分析许慎的释义“文”与“字”都没有汉字的意思,更没有谈到“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实际上,“字”确实是一个合体字,“文”是一个独体字,蒲芳莎解释说,她不是要否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之分,她只是要质疑“许慎在整本字典中都是这样定义这两个字,并且用作‘文’与‘字’之间的术语区分的基础”[8](P22)这种假设。她认为,事实证明,《说文》正文中没有这样的区别。
3.《说文·叙》中也无此区别
《说文·叙》中“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一句,蒲芳莎认为其虽表面看来做了“文”与“字”的区别,但实际上,此句说的并不是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而是“仅基于事物之形”的汉字与“形声相益”的汉字之间的区别。如果把“形声相益”理解为像“形声字”里那样在形旁上加声旁,那就意味着只有“形声字”才能算作“字”,在整本《说文》中从来没有说字只是指“形声字”。“形声相益”在许慎的文字发展系谱上意思是给字形赋予读音,而不是给每个字形加上明确的声旁。它是要确立在表形的“文”和汉语口说词之间的一个普遍必须的联系。蒲芳莎认为许慎的定义并不提供任何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而是在于区别是写汉语词还是没有写词。
蒲芳莎还统计出《说文·叙》中“文”出现了10次,(不包括古文和篆文),“字”11次(+1奇字),而“文字”提到了3次,并对这24个相关例子全部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都没有体现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
蒲芳莎根据例子分析总结出:“文”本质上是图画性的,模拟性的,视觉性的,而“字”代表的是词,与语音联系,体现了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二者总体上都可以指“字符”,但角度不同。她提出一个好的表达二者区别的方法就是把字翻译为“character”或“written words”(字符或者书面词),把“文”翻译为“graph”(图),复合词“文字”(writing)则在有口说语言的语境下与“言语”(spoken language, speech, talk)相对。
(二)对许慎文字观之独特分析
蒲芳莎认为:“(《说文》)作为第一部关于书面词的系统著作,含有丰富的关于当时如何看待口说语言以及文字的信息的矿藏。”[8](P15)她注意到《说文》之前典籍所存分析古字的材料大都是对象形字或者会意字的分析,而很少有对形声字的分析,许慎的汉字分析则加入了对声的考虑。许慎把所有汉字分为540部是他的创新,分析了汉字的语音成分也具有同样重要意义。蒲芳莎认为今天不少研究《说文》的人仍旧把自己局限在字形分析中,而没有意识到许慎对文字与所记词之间关系的理解。
蒲芳莎指出中国很多典籍的书名并不是作者所定,而《说文解字》题目由许慎儿子的上书表可以确定就是许慎自己的书名,因此书名中这两个术语在解释他这部著作之目的时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统计,许慎之前的著作没有用这个术语作书名的,《汉书·艺文志》记录了一本《别字》早已亡佚;而在许慎之后,至少有7本书书名含有“文字”,不少于40本含有“字”,许慎对这两个术语使用的影响由此可见。[8](P21)她认为“文”与“字”表达了文字和语言的某种关系,而不受限于字形结构。这对理解文字理论以及文字与语言关系都很重要。
蒲芳莎认为在中国并不是只有一种文字理论,而是有两个互相竞争的阐释文字方式:玄学的符号分析法和语言学分析法。许慎的独创性就是在他的字典中把对文字的两种传统方法联合到一起。一方面,一种古代的方法是把标记视为现实的象征符号,这可以追溯到通过兽骨和龟甲的裂纹来占卜;而另一方面,“语言学”的文字观,这是由文字的记录口语功能加给它的。
蒲芳莎分析了许慎是如何把两种方法融合在一起的。她说,受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似乎有一个悖论:只要记录词的字符,就会自然而然把它看作是记录语言的,而不是对现实的象征。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许慎自然地游走于形声和会意之间,甚至把两者合在一起。比如,“字”,许慎指出其构成成分“子”在“字”中身兼两职,既表意又表声。说它表意,那么“字”就是会意,就是象征现实的符号;说它表声,那么“字”就是形声,自然就跟一个口语词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许慎使字形结构成为形声兼会意,这样就把玄学的符号分析叠加在他的语言学分析上。蒲芳莎认为这也可在许慎《说文·叙》六书排序中得到印证。
蒲芳莎从语言学史角度对许慎进行了高度评价。她认为许慎《说文·叙》中描述了汉字发展历史,并提出“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具有重要意义。她分析:仓颉开始是“依类象形”,在这个阶段他不是在记录语言的词,他只是通过象征符号来表达事物。后来一个新的发展出现:仓颉通过加上语音的维度把他的“形”用于表达口说的词,那么从“文”到“字”的发展,指的就是从描绘现实到记录描绘现实的词。那么许慎就不仅是在重构汉字类型的历史发展,而是在描述文字记录语言过程的创世纪。因此许慎“就不仅仅是汉字的分类者,而是文字起源方面的哲学历史学家”。[8](P24)鉴于许慎的功绩不仅仅是汉字分类,而且对文字起源有杰出看法,因此她提到本论文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公正评价语言学历史上一个伟大知识功绩”。[8](P24)蒲芳莎认为许慎能够通过“文”和“字”做出字形结构和书写系统的区别,这种区别构成了“中国语言学发展基本的一步”。[8](P31)
蒲芳莎最后还指出许慎虽然在理论上对字形结构与文字系统作了重要区分,并在其书名中加以强调,但是他还是持续关注玄学符号分析而不是汉语词汇的语言学方面。因此在许慎的著作中,并没有把语言学与玄学、哲学明显分开。实际上,作为一个语言学和辞书学现代历史的观察者,应该想一想把这些学科专业化地分开是否就真的令人满意呢?蒲芳莎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她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反思。
[1] 白谦慎,邵伟克,劳悟达.中国书法在西方[A].欧阳中石.中国书法艺术[C].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498.
[2] Boltz, William G. “Review: Semantisme et classification dans l'ecriture chinoise: Les systemes de classement des caracteres par cles du Shuowen jiezi au Kangxi zidian”[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20, No. 3 (Jul. - Sep., 2000), pp. 471-474.
[3] (法)蒲芳莎著,方德义译.文字统一和辞书编纂[A].《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法国汉学(第六辑)[C].北京:中华书局,2002.51-67.
[4] Bottéro, Françoise and Harbsmeier, Christoph. “The Shuowen Jiezi Dictionar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in China”[J]. AM (third series) 21.1 (2008). pp.249-271.
[5] Bottéro, Françoise. “Review:TheOriginandEarlyDevelopmentoftheChineseWritingSystemby William G. Boltz” [J].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 Vol. 116, No. 3 (Jul. - Sep., 1996), pp. 574-577.
[6] 黎千驹.中国文字学研究的新进展──首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述评[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4):68-74.
[7] Boltz, William G. “Language and Writing” [A]. Loewe, Michael and Shaughnessy,Edward L. (ed.):TheCambridgehistoryofancientChina:fromtheoriginsofcivilizationto221B.C.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74-123.
[8] Bott ro, Fran oise. "Revisiting the w n and the zì: The Great Chinese Characters Hoax."[J].BMFEA74 (2002), pp.14-33.
OnFrenchScholarFrançoiseBottéro'sShuowenStudies
Zhang Daying1,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2.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Qingdao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Qingdao 266520, China)
Using western linguistic approach, the French scholar Françoise Bottéro has studiedShuowenin many aspects. HerShuowenstudies have unique ideas, and are very deep, reasonable and original. With an open mind in studyingShuowen, she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lated achievements of scholars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etc. Through herShuowenstudies, we can also feel that she is very familiar with Chinese classics, and can quote them with ease. So we think that she is a contemporary westernShuowenexpert who deserves our special attention.
French scholar; Françoise Bottéro;Shuowenstudies
2012-01-1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欧美《说文》学研究”(12YJC740135)
张大英(1978- ),女,山东费县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青岛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语言文字研究。
H02
A
1672-335X(2013)04-0124-05
责任编辑:周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