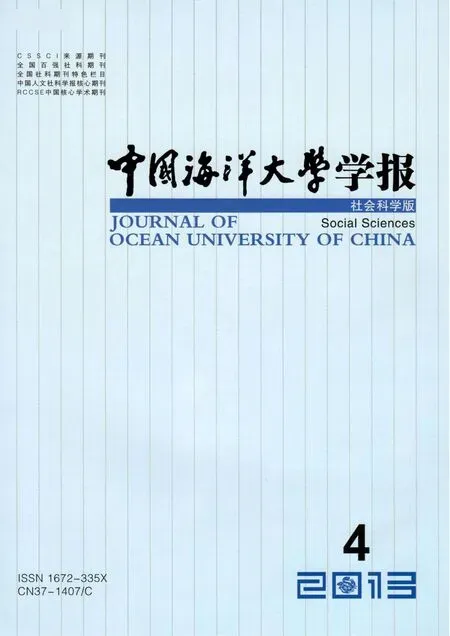论国际逮捕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申世涛
(山东政法学院 刑事司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论国际逮捕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申世涛
(山东政法学院 刑事司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国际逮捕的理论基础主要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两个方面。国际逮捕的正当性主要指国际逮捕权权源的正当性和国际逮捕制度的正当性。国际逮捕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际刑事法庭对犯有严重国际罪行的人,是否有权逮捕的问题,它是和案件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庭对案件具有管辖权和可受理性,也就说明国际刑事法庭具有逮捕权。
国际逮捕;正当性;合法性
国际逮捕是国际刑事诉讼中逮捕制度的简称,而国际刑事诉讼是指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指国际刑事法庭它是指为了起诉和惩罚犯有严重国际罪行的个人而设立的国际性质的司法机构。截止到现在,国际社会先后出现了5个国际刑事法庭,即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本文简称纽伦堡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本文简称远东法庭)、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本文简称前南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本文简称卢旺达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二是国际和国内混合型的法庭(也称为国际化法庭),顾名思义,混合型法庭主要是兼具有国际和国内诉讼程序因素的法庭。目前,国际社会的混合型法庭主要有东帝汶混合法庭、柬埔寨混合法庭等。本文所论述的内容主要是国际刑事法庭,重点是是前南法庭、卢旺达法庭与国际刑事法院的诉讼程序。对犯有严重国际罪行的个人,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诉讼程序。
一、国际逮捕的性质
国际逮捕的性质如何?几乎无学者对此做过解释。在谈到国际逮捕的时候,其笔墨的着力点往往是逮捕的程序和执行,而对于国际逮捕的性质却视而不见。从有关法律的规定看,在国际刑事法庭宪章、规约或规则中,只有《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程序与证据规则》(本文简称《前南规则》)、《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程序与证据规则》(本文简称《卢旺达规则》)对逮捕的性质作出过规定,认为逮捕是根据逮捕令或紧急情况下事先没有签发逮捕令而拘留嫌疑犯或被告的行为。*参见《前南规则》和《卢旺达规则》第2条。本文中有关《前南规则》的条文,参见凌岩:《跨世纪的海牙审判-记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附录一里的中译本及其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网站。有关《卢旺达规则》的条文,参见洪永红:《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附录里的中译本及其联合国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网站。该定义抓住了逮捕的核心要素,认为逮捕是剥夺相对人人身自由的行为;至于对人身自由是临时、短暂性的剥夺,还是长时间的剥夺,并没有直接说明。
笔者认为,从上述定义看,国际逮捕与比较法上通常意义的逮捕,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一种强制到案的方式,是一种暂时、短期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其理由主要有几个方面:其一,从词义上看,逮捕是一种行为,而行为,从法律的角度看,是人的有意识的外部动作,具有时间上的短暂性。其二,从来源看,国际司法起源于国内司法,[1](P29-36)国内司法中的术语、程序、价值等构成国际司法的框架。在国内法中,一般国家都认为逮捕是短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逮捕之后长时间的关押,则转变为另一种强制措施——羁押(detention)。联合国在总结各国逮捕制度的基础上,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中规定,逮捕是指因指控的罪行或根据当局的行动扣押某人的行为*从《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规定的逮捕定义看,它和特设法庭规则规定的非常相似。,而羁押是一种被羁押人的状态。其三,从国际刑事法庭规约、规则的法条看,它规定了逮捕和羁押是两种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如《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本文简称《前南规约》)第29条就把“逮捕或羁押(detention)”并列在一起,《罗马规约》第55条第4款规定,也对此做了基本相同的规定。*《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本文简称《卢旺达规约》)第28条也有相同的规定。在《前南规约》和《卢旺达规约》中,我国学者把detention翻译为“拘留”,笔者认为,为了和比较法上的“羁押”相一致性,翻译为“羁押”较好,《罗马规约》第55条就将该词翻译为“羁押”。本文中《前南规约》和《卢旺达规约》条文,参见赵秉志、王秀梅:《国际刑事审判规章汇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中有关《罗马规约》的条文,参见李世光、刘大群、凌岩:《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评析》(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至于二者的关系,大概也与国内法中的规定一致。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国际逮捕的基本含义是:在国际刑事诉讼中,根据国际刑事法庭规约、规则及其相关法律的规定,对有合理理由相信犯有国际刑事法庭管辖权内罪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
二、国际逮捕的正当性
(一)正当性(legitimacy)的含义-兼论与合法性(legality)区别
正当的基本含义是“在道德意义上述说一个行为”,[2](P80)是对行为的价值判断。正当性是指主体行为或主体之间关系的一种属性。[3](P17)
正当性是来源于西方的一个政治哲学术语,因此,要了解其本质,还要在西方语境中对其做一番考证。从历史的角度看,正当性概念的出现是和自然法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根据韦伯的研究,自然法有三种作用,一是规范作用,也就是为制定法提供一个道德基础,并指导和约束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二是正当化(legitimizing)作用,即为制定法提供一种价值理性的正当性证明;三是革命性作用,即创造新的法律和社会秩序。所以说,Legitimacy所关涉的是社会中权力和权威的基础,以及为实存的法律秩序所提供的正当性证明。因此,Legitimacy意味着对一种政治法律制度的公认,或者说,它是政治法律制度存在的内在基础。[4]
在西方语境中,与正当性相对的另一个概念则是合法性。同样从历史的角度分析,Legality概念的正式出现是在形式主义法学或法实证主义出现以后,在这种理论主导下,强调的是法律秩序的实际存在以及行为者对法律的服从和遵守。在此背景下,Legality表现为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与国家制定颁行的实证法律相对应,合于现行实证法律的行为即具有Legality。[4]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初步得出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关系:正当性是对一种现存政治、法律制度的评价,看其是否符合理性及正义;而合法性则是指行为是否符合当下的实证法的规定,符合规定的则具有合法性,不符合规定则非法。如果把讨论的问题局限于法律制度内,并以实证法为界限的话,那么正当性关注法律之上的问题,即恶法与善法的问题;合法性关注法律之下的问题,即注重行为本身是否符合实证法规定的问题。
正当性既然是一个价值判断,那么其标准是什么呢?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正当性的价值标准处于变化发展中,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及其不同的人对正当性标准的理解是不同的。从亚里斯多德的“正当即善”*在道德哲学里,善和正当(正义)的关系,有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亚里斯多德认为善在后,而苏格拉底则认为正当在后。,到西塞罗的“自然理性”,[5](P60-61)阿奎那的“自然法”,[6](P18)再到韦伯的“形式理性”*韦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法理型统治的扩张,自然法理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微弱,人为制定的形式理性逐渐成为自身的正当性的来源和规范性基础,实证法律不再需要诉诸一种“更高级的法”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参见刘毅:“现代语境下正当性于合法性:一个思想史的考察”,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3-4页。和麦考密克的“从过程到结果的形式标志上看制度的正当性问题”。[6](P18)总的趋势是从人类之外到人类自身,从抽象到具体,从制度之外到制度之内。其次需要注意的是,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来维护正当性的底线。如果要对正当性的标准用一个简单的词汇来概括,那么从没有哪个词比“正义”更适合。因为正当本身就是正义的,上述所谓的“善”,“自然理性”和“自然法”及其“形式理性”等正当性标准无不和正义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哲学家们在论述正当的时候,总是和正义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二者不可偏颇。[7]
然而,正义总“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8](P252)处于变动不居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当然,作为人存在和发展的必需,总有着最低的需求,即生理和心理需求,如果一个制度满足不了这些最低限度的需求的话,那么它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义的。因此,博登海默认为,存在一种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这些要求独立于实在法制定者的意志而存在,并且需要在任何可行的社会秩序中予以承认。这些要求中有一些必须从人的生理构造中寻求,而其他的一些要求则植根于人类所共有的心理特征之中。同样,还有一些要求是从人性的理智部分,亦即是从人的知性能力中派生出来的。这些法律有序化的基本规定的有效性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证实,即它们在所有诞生于最为原始的野蛮状态的社会中都以某种形式得到了承认。[8](P273)
(二)国际逮捕的正当性
循着上述思路,国际逮捕的正当性其实就是国际逮捕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即国际逮捕法律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在论述国际逮捕法律正当性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先行说明,那就是国际逮捕权来源的问题,不解决此问题,谈不上逮捕制度的正当性。
1、国际逮捕权权源的正当性
在国内法中,逮捕权来源于国家权力,似乎是一个不正自明的真理,几乎没有人怀疑刑事诉讼中逮捕权的来源。然而,在国际社会,由于没有国家那样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更没有三权分立制度的存在,因此,国际司法权、逮捕权的来源和根据就成了问题。巴西奥尼试图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进行探讨。“尽管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千差万别,却有着某些共同的历史线索。这种历史同源性可以追溯到大约3500年以前的绝大多数法律制度。默示社会契约的存在表明,个人放弃了自己进行复仇的权利,换得国家对其成员进行保护的义务。如果有侵权行为发生,个人将接受应有的惩罚。”“有组织的社会已将个人的求刑权与民事救济权作了区分,前者从个人转交给国家,后者仍是个人的权利。”“同样,国际刑事司法也在发生这种演变,即国际社会基于默示的社会契约,以互补性观念为基础,通过国家之间合作的制度来分配管辖权。”[9](P586-587)我国学者称巴西奥尼的这种契约论为“国际契约论”,并对此进行了价值分析:*参见宋健强的两本书:《国际刑事法院诉讼详情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58页;《国际刑事司法制度通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1-432页。(1)就社会契约而言,国家社会和国际社会具有相似性,并无大差异;(2)个人是惩罚权的唯一“让渡”主体,国家不是,因此国家也没有保留什么(例如恩赦等)的资格了;(3)不存在国家让渡主权或主权的权力问题,国家是公益名义的代表,是个人的代理人,不是国家刑罚权契约的当事人。由此,巴西奥尼的国际契约论和一般的“国际契约”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国际契约是指国家之间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订立的合约(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实质是“主权国家让渡或限制主权的契约”,[10](P423)相对于巴氏国际契约,一般的国际契约论更容易让国家接受。因为,前者是在个人和国际社会之间直接达成的国际契约,不经过主权国家这个“间接通道”,*按照宋健强教授的说法,巴西奥尼也意识到自己走得太远,在后来的论述中又退回半步,也就是说国际契约应有国家的参与这一环节。不知理解是否正确。参见宋健强:《国际刑事司法制度通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页。对国家主权的影响较大,有排斥国家主权之嫌;后者直接是国家之间的一种协议,是国家自愿让渡部分主权,国家还是国际社会的主体,没有国家也就没有国际契约。
2、国际逮捕制度的正当性
德国法学家施塔姆勒在其《正当法的理论》一书中主张,法律的目标应是实现当时当下的社会理想,这一社会理想就是“意志自由的人们的社会”,为此,他提出正当法的四项原则:(1)个人意志的内容绝不应被迫服从他人的专断的愿望;(2)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不能使被限制的人丧失自我尊重的人格;(3)负有法律义务的人绝不能被专横地排除出法制社会;(4)法所承认的对权力的安排和实施,只有在不使受影响的人丧失自我尊重的人格时才是有效的。前两个原则被他称为“尊重原则”,后两个被称为“参与原则”。[6](P20)当然,上述关于正当法标准的描述是针对国内法而言的,而国内法和国际法有着重要的不同,国际社会没有世界政府,没有议会这样的立法机关。在国际法上,创造法律、遵守或不遵守法律,都是由国家自身来完成的。[11](P5)
正是因为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立法不同,因此,对于两者的正当性标准也应不同。弗兰克教授为我们概括了国际法正当性的四个特征:确定性(或易于识别的具有规范性质的内容或“透明性”)、象征性确认(或权威赞同)、一致性(或连贯性或一般适用)和遵守性(或属于一个有组织的规则等级)。[11](P49)从上述国内法和国际法正当性的标准来看,由于二者固有的差异性,因此导致表面上看来不同的认定标准;但是从其实质意义上看,二者都是把抽象的正当性标准具体化,法律的正当性均内涵于立法过程、立法程序和法律内容之上。因此,国内法正当性标准和国际法正当性标准表象不同,实质一样。
现代社会是法的天下,人人身临其境,处处居于它的枷锁中。人类生活的制度就是由法律所规范的一种规则体系,人们只能在规则体系中行事,而规则和制度往往很难分开。因此,制度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法律的正当性,主要是立法的正当性。[6](P19)具体到国际逮捕法律制度的正当性,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是法律制定过程和程序的正当。这是法律正当性的外部正当。其次是法律内容的正当,即内部正当,表现为是否体现尊重原则、参与原则和法律的确定性和一致性等要素。至于正当性的证明方法,英国的国际法学者马尔科姆·N·肖认为,正当性是可以用实证的方法来证明的,但遵守不仅可以通过观察遵守的国家按照有关原则行动衡量出来,而且还可以通过观察一个违法者即使在违法的情况下实际上对该项原则显出来的顺从程度衡量出来。[11](P49)苏力教授也深有同感,“真正能证明一个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必定是它在诸多具体的社会制约条件下的正常运作,以及因此而来的人们对于这一制度事实上的接受和认可”。[12](P89)
三、国际逮捕的合法性
在论述了国际逮捕的正当性之后,自然就转入合法性的认定过程。关于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含义及关系,上文已经说明。因此,这里的合法性的“法”是指实证法,而非自然法和抽象法。所谓国际逮捕的合法性就是指逮捕行为是否符合相关国际法律的规定,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有无逮捕权的问题,即法律是否规定逮捕权;二是在法律规定逮捕权的情况下,逮捕程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限于篇幅,本文仅论述第一个方面。
关于有无逮捕权问题,实质是和法院的管辖权联系在一起的,在法庭发出逮捕令之前,必须确定案件的管辖权。有管辖权则有逮捕权,无管辖权则逮捕违法。由于前南法庭、卢旺达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建立的基础不同,因此逮捕权合法性的认证也有所差异,分开论述具有合理性。
(一)特设法庭*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合称特设法庭。逮捕的合法性
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规约和规则规定了逮捕制度,只要法庭对嫌疑人、被告人具有管辖权,则在必要的时候自然有权逮捕,逮捕的合法性也不成问题。质疑法庭的管辖权,也是质疑逮捕权的合法性。对法庭管辖权的质疑,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都曾经面临过。由于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建立的基础相同,并且前南法庭成立在前,遇到的挑战也较早,因此,这里的论述以前南法庭为主。前南法庭第一案塔迪奇案,就首先面临了法庭合法性和管辖权问题的质疑,解决了第一案的问题,就为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塔迪奇就前南法庭对其的管辖权的质疑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法庭建立是否非法的问题;法庭的优先管辖权是否适当的问题;法庭属事管辖权(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有无的问题。[13](P34)对于辩护方的质疑,前南法庭审判分庭和上诉分庭都进行了反驳,尽管都驳回了辩护方的质疑,但是反驳理由不同,上诉分庭的反驳理由可能更具有权威性和合理性。
1、法庭建立的合法性问题
法庭建立的合法性问题的焦点是建立刑事法庭是否属于安理会为维护和平与安全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关于这个问题,前南上述法庭论证过程大致如下:前南法庭是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创立的。其第39条(也是第七章第1条)规定了安理会有权判断和平之威胁、安全之威胁或侵略行为是否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建议或抉择依第41条及第42条规定之办法,以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也就是说如果安理会判断存在有威胁和平与安全及其侵略行为,那么它就有权依照第41条和42条规定之办法采取措施,以便恢复和平和安全。
设立国际刑事法庭是否包含于上述第41条和第42条规定的办法之中呢?显然,第42条规定的是武力解决办法,前南法庭应是武力之外的办法。而武力之外的办法也就是第41条所规定的办法。第41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得决定所应采武力以外之办法,以实施其决议,并得促请联合国会员国执行此项办法。此项办法得包括经济关系、铁路、海运、邮电、无线电、及其他交通工具之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关系之断绝。”理解这条的关键是对“可包括”(may include)一词的解释,第41条中所列出的措施,没有提到“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甚至也没有提到“建立司法机构”的可能性。但是,“包括”一词又清楚地表明:这里所列举的措施仅仅是作为例证,它们不是“详尽性的,除了这些措施还存在其他措施。*上述论证和部分语句参见朱文奇:《国际刑事法院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版,第164-165页。进一步说,安理会完全是可以根据宪章第41条设立刑事法庭,设立刑事法庭审判严重违反国际罪行的行为人,是安理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措施之一,具有合法性。
2、法庭的优先管辖权问题
针对被告提出的前南法庭的管辖权不能优于国内法庭,审判庭认为这首先牵连到国家主权问题,被告人个人不具有提起异议的资格,只有相关国家才具有这样的资格。其次是能够被纳入国际法庭管辖的案件,必须具有超出单一国家利益范围的广泛性,而本案具有这种属性。相对于审判庭的理由,上述庭则简洁地认定,前南法庭优于国内法庭的管辖权,即不是依据犯罪的属性,也不是源于惩罚加害人的需要,而是完全根据法律的规定,即《前南规约》的规定。其法理依据如西德华(Rustam S. Sidhwa)法官所说,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4条第1款的规定,联合国成员国在面临宪章第七章所列的情形时,将主权让渡给了联合国安理会,由安理会来决定应对措施。其中让渡的主权内容就包括针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审判权,也包括设立一个国际法庭来执行这一任务。因此,安理会授权前南法庭优先管辖权是合法的,更是合理的。*论述过程和部分语句见王秀梅等:《国际刑事审判案例与学理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3、法庭的属事管辖权问题
被告人认为控诉所援引的《前南规约》第2、3、5条仅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而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国内武装冲突,因此,不属于法庭的管辖范围。审判分庭认为,国际武装冲突的概念不是第2条的管辖权的标准,第3条和第5条对国内和国际武装冲突都适用。因此,无论冲突的性质如何,法庭都有管辖权,它无需确定该冲突是否为国内的或国际的。[14](P509)在上诉时,被告的理由有所变化,认为罪行发生时,该地区根本不存在武装冲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冲突。上诉分庭首先分析了罪行发生时的地区存在武装冲突,然后通过对规约第2条、第3条、第5条的文理解释、目的解释和逻辑、系统解释,认为第2条只适用于国际冲突并且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国际武装冲突,第3条和第5条对国际武装冲突和国内武装冲突都适用。*具体论述过程见凌岩:《跨世纪的海牙审判-记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09-546页。另见the Dusko Tadic case,案件号IT-94-1-T,1995年10月2日关于管辖权上诉庭裁决,详情见前南法庭网站:http://www.icty.org/x/cases/tadic/acdec/en/51002.htm。
(二)国际刑事法院逮捕的合法性
不同于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是安理会附属机构,属于联合国的一部分,国际刑事法院是在协商基础上通过条约建立的。对于法院建立的合法性问题,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异议主要集中于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进行逮捕的合法性问题,如对苏丹现任总统巴希尔和利比亚已故总统卡扎菲发出的国际逮捕令,就遭到了当事国的强烈质疑。本部分以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情势发布逮捕令为例,论述其合法性问题。
根据《罗马规约》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可以对非缔约国行使管辖权:[15]第一,如果犯罪行为是在缔约国境内发生,也就是说,如果苏丹的国民在一缔约国境内实施犯罪,国际刑事法院就可以起诉该苏丹的国民。第二,如果犯罪被告人为一缔约国国民,即如果在苏丹境内实施犯罪行为的被告人为一缔约国国民,法院对此案也具有管辖权。第三,苏丹可以根据《罗马规约》第13条第3款向书记官提交声明,接受该法院对有关犯罪行使管辖权。第四,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向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提交情势,启动法院的管辖权。其中前三种情况都不适合苏丹,只有第四种情况发生时,国际刑事法院才能对苏丹行使管辖权。
对于安理会向国际刑事法院递交非缔约国有关国际犯罪情势的,国际刑事法院需要首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安理会向法院提交非缔约国内发生的国际犯罪情势,能否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基础?也即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管辖权的合法性问题;另一个就是在前一个问题的基础上,根据补充管辖权原则,法官对情势的可受理性问题。二者是递进关系,下面分别论述。
1、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管辖权的合法性
很少有人质疑安理会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非缔约国境内发生的涉嫌国际犯罪的合法性问题。苏丹当然质疑,*卡扎菲当政时期的利比亚也曾质疑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签发逮捕令的合法性问题,质疑的原因和苏丹的质疑基本一样。从苏丹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对其总统巴希尔发布逮捕令的声明看,其异议的主要理由是苏丹不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不受该法庭管辖,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违背国际法准则,它试图强制一个主权国家服从该国没有参与的协议,也没顾忌国家总统豁免的原则。[16]此前,苏丹情势辩护律师沙鲁夫也曾经对管辖权和可受理性提出过异议。
预审分庭没有正面回应上述质疑,而是立足于将《罗马规约》的规定作为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情势管辖权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仅仅根据《罗马规约》第13条第2款的规定,认定国际刑事法院对该情势具有管辖权。[17]
笔者同意预审分庭的结论,进一步补正的理由是: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的管辖权实际上不是来自《罗马规约》的规定,而是来自安理会的权限。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安理会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负有责任,对于和平与安全及其侵略行为具有认定和采取措施的权力。安理会的决议,成员国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第25条),成员国的宪章义务与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义务具有冲突的,宪章义务优先(《联合国宪章》第103条)。既然安理会可以对前南冲突的情势自己建立法庭,来审判国际犯罪者,为什么就不能将情势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呢?
学者们也具有同样的观点:对于联合国作出决议提交而取得管辖权的案件,权力行使的依据并非是《罗马规约》,而是安理会在处理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权威性和终局性。[18]就安理会而言,“安理会提交情势”与“安理会设立特别法庭”,目的都是诉之司法解决,并无实质不同。[19](P424)
对于苏丹政府对现任总统豁免问题的质疑,法庭也没有做出回应。笔者认为这牵连到国际法中的豁免理论,可能会对逮捕令的执行造成法律上是阻碍。毕竟逮捕令的执行还需要国家的合作,在国家合作过程中,有关国家既要遵循《罗马规约》的义务,同时也要遵守其他国际法义务。这就有可能产生义务冲突,从而阻碍逮捕令的执行。
2、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情势的可受理性
对案件有了管辖权之后,并不能保证受理案件,因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是补充性的。也就是说如果有管辖权的国家对案件进行了审理,那么国际刑事法院是不能再次受理的。由此,国际刑事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的情况下,还需要解决可受理性的问题。
国际刑事法院对案件可受理性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正在对该案件进行调查或起诉,除非该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调查和起诉;(2)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已经对该案进行调查,而且该国已决定不起诉,除非作出这项决定是由于该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起诉;(3)有关的人已经由于作为控告理由的行为受到审判,基于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法院不得因同一行为进行审判,除非另一法院的审判程序是为了包庇有关的人,使其免受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刑事责任,或者没有依照国际法承认的正当程序原则,以独立或公正的方式,而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的方式不符合将有关的人绳之以法的目的。(4)案件缺乏足够的严重程度,本法院没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见《罗马规约》第17条、第20条第3款。如果有上述情况之一的,国际刑事法院对案件就不可受理。
就苏丹达尔富尔情势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迫于各种压力(当然安理会的压力是主要的现实压力),苏丹政府对“管辖权异议”的呼声似乎减弱,与此同时,其国内诉讼活动却日益丰富。[19](P412)由此说明,苏丹政府已经放弃对管辖权的抗争,而把重心放在案件的可受理性问题上,以此与国际刑事法院进一步抗争。
在安理会对达尔富尔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不久,苏丹就成立了自己的特别法庭,准备起诉在达尔富尔地区犯有战争罪行的人。然而,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的顾问柯里斯蒂·帕勒玛说,苏丹特别法庭起诉的对象是低级别的犯罪嫌疑人,而国际刑事法院将集中对在达尔富尔地区所犯罪行负有最严重刑事责任的个人进行调查。因此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是对苏丹司法系统的补充。两者并不矛盾, 而是相辅相成的。[15]显而易见,在检察官看来,法院诉讼与苏丹诉讼是在同一情势中针对不同等级的罪行和罪人的“事项”(matter)或“案件”(case)。换言之,同一“情势”包含不同的“事项”或“案件”,只要选定的这种特殊“事项”或“案件”与补充性管辖原则不冲突就可以了。[10] (P382)
[1] 王林彬.国际司法程序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 廖申白.伦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 杨雄.强制措施的正当性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4] 刘毅.合法性与正当性译词辨[EB/OL].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37746.
[5] 张乃跟.西方法哲学史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6] 梁玉霞.论诉讼方式的正当性[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7] 孙培福,黄春燕.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J].齐鲁学刊, 2012,(1):91-100.
[8] (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9] (美)M·谢里夫·巴西奥尼著,赵秉志,王文华等译.国际刑法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0] 宋健强.国际刑事司法制度通论[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11] (英)马尔科姆·N·肖著,白桂梅等译.国际法(第六版)(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2] 苏力.送法下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3] Dominic Mcgoldrick. Criminal Trials Befor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Legality and Legitimacy[C]. In: Dominic Mcgoldrick, Peter Rowe, Errc Donnelly. 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Legal and Policy Issues. Oxford and Portland Oregon, Published, 2004. 34.
[13] 凌岩.跨世纪的海牙审判-记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5] 杨力军.安理会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达尔富尔情势的法律问题[J].环球法律评论,2006,(4):457-468.
[16] 苏丹驻华使馆:坚决犯罪国际刑事法院对苏总统签发逮捕令[EB/OL].http://news.163.com/09/0307/23/53RDC2L7000120GU.html.
[17] 余剑.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情势管辖权的合法性基础质疑[A].载赵秉志,卢建平.国际刑法评论(第五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64.
[18] 杨宇冠.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探究-以利比亚情势为视角[J].北方法学,2012,(2):73-78.
[19] 宋健强.国际刑事法院诉讼详情研究[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AnalysisofLegitimacyandLegalityofInternationalArrest
Shen Shitao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nan 250014, China)
The main theoretical basis of international arrest is its legitimacy and legality.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arrest includes two aspects: the legitimacy of power source of arrest and arrest system. One aspect of legality is whethe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has the right to arrest any person who has committed a serious international crime,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international arrest; legitimacy; legality
2012-06-12
申世涛(1973- ),男,山东菏泽人,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刑法学研究。
D924
A
1672-335X(2013)04-0094-06
责任编辑:周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