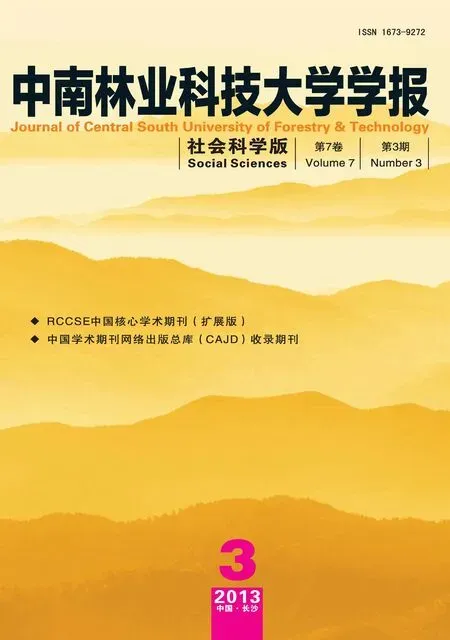《生死疲劳》的欲望与轮回
——试论视野变换下的生命体验
周 妮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长沙 410205)
《生死疲劳》的欲望与轮回
——试论视野变换下的生命体验
周 妮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长沙 410205)
莫言的《生死疲劳》绝不是一部中国农村的田园颂歌,通过借自佛典的名字和轮回,呈现出强烈的魔幻现实主义意味,暗示了这片土地深沉的苦难和深刻的自赎——动物的出场和言述,人转生后的前世记忆和当下体验,“莫言”在文本中的在场和角色扮演,展示了视野变换下历史的种种面相和生命的层层体验。
生死疲劳;欲望;莫言;生命
有人这样评价他:如果说1985年的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的话,那就是出现了莫言。莫言作为我国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都有点邪劲儿” 。[1]以其代表作《生死疲劳》为例,在形式上这部小说借用了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在内容上,它倚着土地,以佛教的生命轮回,家族的变迁传奇论述了中国农村半个世纪的人文和生活景观。文本始终在“故事叙述”与“在场体验”间闪转腾挪,从而产生一种奇妙的视角层差和微妙的存在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这绝不是一部中国农村的田园颂歌,文本的魔幻主义意味呈现的荒诞色彩,充满了是对政治的挪揄,对历史的反讽,对生命的哀叹——文本借自佛典的名字和轮回,强烈的暗示了这片土地深沉的苦难和深刻的自赎,“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类似传统文人对繁华落尽的叹息,却给予了土地以超越的力量,正如《易经》的“地势坤厚德载物”,地上的喧闹归于地下的平寂,地上的人归于地下的土——正如黄互助的头发,连着血脉,抚平创伤。
“六道轮回”是佛教的讲法,说的是有情众生,轮回于六个界别。轮回由欲望始,由欲望终。佛教的终极目标是脱出轮回,而作为《生死疲劳》叙事主角的西门闹,轮回于人、驴、牛、猪、狗、猴,并最终得到人身,并以此肉身回瞰自己的历与劫,历史成为看似宏大却丝丝入扣的掺入人乃至动物的生存经验。往生记忆混杂于当下的体验和感悟,形成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的诠释视角。“莫言”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不仅呈现普通个体的丰富人性、生命意义,而且凸显普通个体生命的悲剧性结局。普通个人的视角取代宏大的叙事,以普通个体感受诠释历史,“零度叙事”昭示着个人在命运生死面前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作为历史叙事的代言人——孱弱睿智的蓝千岁洞悉了台前台后种种的如痴如醉、腾挪跌宕,躲在幕后发出超然会心的微笑。《生死疲劳》正是通过不同的叙述者来强调有必要还原那些消失的历史记忆。
一、“动物(牲畜)话语”的解释学内涵
动物(牲畜)是中国农业社会最为重要的生产力来源,通过动物,可以鲜明的摹画出中国社会农耕文明的样态——这在形式上,使传统得以延续,但是,当人化的“动物”出场,并以“动物化”的人来对世界进行描画和阐述时,这个世界要么是童话,要么是地狱。动物的——正如《生死疲劳》中屡屡提及的——本性往往最为根本的表达出兽性的企求,这里,兽性的满足得到的是天堂,反之,才能有人兽的混绕和人的出场,人的世界充斥混乱、暴力、冲突,“人化”的动物成功的突入人的世界,并在某些时候、某些个体身上显示出极大的心理作用——不管它是轮回的魂灵,还是劳作的帮手,动物与人具备了超伦常的的关系。所以,蓝解放就会有如下的想法:“当时我想,我要是一头没有思想的公牛有多么好啊,当然,现在我知道了,公牛,也是有思想的,不但有思想而且思想还极为复杂,你不但思考人世的事,还要考虑阴间的事,不但考虑今世的事,还要考虑前世和来生。”[2]这个时候,跳出文本给予人的解释学空间,我们会发现“动物(牲畜)”所具有的符号化的图腾意味——佛教要出世,而农民的宗教,则简单、粗粝、原始、生机勃勃、立于当下、辗转生息。动物并不见得比人更低下,因为它可能就是人,但是,人仅仅就是人,因为人对动物的不了解,使得动物可能拥有着许许多多不可知的潜力和记忆,从而比人更高明。西门驴肉搏野狼、大闹队部,对统治者无法无天的反抗让我们热血沸腾;西门牛在集市上披着红旗猛撞乱踹,描绘出文革时的疯狂与荒唐;猪十六在争取民主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力量和智慧令人叹服;西门狗强大的号召力与洞察力也让人望尘莫及;而西门猴眼神的迷蒙正折射出离开土地的人们无根困窘的现状。
“动物话语”是“六道轮回”必然的结果,却可能包含了莫言的种种企图:“文革”乃至之前之后的种种运动,无疑是一场癫狂的、反文明的、切削文化的乱局,“动物话语”无疑是对迷狂的农村社会变迁的一种反讽;对传统农耕文明的暧昧的纠缠不清的挽歌和祭奠,彰显着莫言的深刻的怀旧情绪;一种比写实更有力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从而产生对当下的巨大震撼。潇洒放荡的西门驴,憨直倔强的西门牛,贪婪暴烈的西门猪,忠诚谄媚的西门狗,机警调皮的西门猴,它们充盈着野性的原始生命力。用本能中的直率、顽皮和狡黠始终在高密东北乡这块土地上欢腾,演绎出他们与土地的故事,用它们独特的语言与视角叙说着新中国农村的演变历程。
二、莫言的“莫言”:循环结构下的在场模式
作家以真名进入小说逐渐成为先锋叙事的典型特点。马原在《虚构》、洪峰在《重返家园》、莫言在《酒国》中都做过这种尝试。“在莫言的《生死疲劳》中,作为介绍性叙事者的莫言在第五部结局和开端脱离了蓝千岁和蓝解放的交谈性叙述,使小说的结尾和开头得以衔接,形成一个圆形的循环结构。”[3]
《生死疲劳》中,“莫言”这个艺术形象既是以作家本人为原型的人物,又是故事的参与者与叙说者。“莫言”这个角色虽然不是故事的主人公,但“莫言”作为故事的参与者与叙说者,在整篇小说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正是他拉着蓝解放见证了西门金龙和黄互助的爱情经历,激发了蓝解放的嫉妒之心,最终导致了自己和西门金龙的癫狂;也是他想出了让西门金龙、蓝解放与黄家姐妹结婚的主意歪打正着治好了蓝解放和西门金龙的疯病;还是他20年后将年轻的庞春苗介绍给蓝解放,从而使二人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的忘年恋。最后,又是他为二人日后的生计出谋划策,并为他们提供了私奔后的住处及工作。“莫言”虽然出现的地方不多, 但却在冥冥中成为所有故事的推波助澜者,成为小说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莫言曾说过,“一部小说如果只有一个叙述者势必单调, 必然会出现很多的漏洞。”[4]因此,他的多部小说都会有两个或以上的叙述者从不同视角讲述故事。《生死疲劳》也不例外。小说的前四部主要是通过蓝千岁和蓝解放的视角讲述各自的故事。而“莫言”在蓝千岁和蓝解放的故事中都间或出现,并时不时跳出来就像舞台上串戏的丑角,不断用自己的声音来弥补双重叙事造成的漏洞,起着辅助补充作用。直到小说最后一部,“莫言”的声音才越来越大,由辅助的叙事者成为独立的主要叙述者,用言简意赅的讲述将绵延冗长的故事进行了收梢。“莫言的插入使得整个叙述显得摇曳多姿,一方面丰富了作品的声音,另一方面又使故事更有层次感,呈现出典型的复调性叙事特征。”[5]同时,“莫言”的最后讲述又与开头“莫言”在小说中的叙事首尾呼应,形成了一个圆形的循环结构,这种结构从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生命的往返轮回,印证了小说的题目和题记中的佛家之语,表现了作者独特的生命观和历史观。
三、“历史”叙事:虚弱的记忆
西门闹带着前世记忆闯入高密东北乡民众的生活,这种记忆以仇恨为始,以阎王克意化解仇恨为由,以西门闹的轮回转世为经,以半个世纪农村社会变迁为背景,提供了文本释读的另一个广义的视角:历史及历史叙事下的生活价值和生命意义。
记忆自然将悄悄甄别和慢慢湮灭——西门闹的记忆,集中于:家族及产业、土地及劳作、善良及冤死,等等。历史本身就是记忆,或者说,是记忆的析取和重构。记忆的历史会形成一种独立立场的对当下的读取方式,并限定读取的视角及与当下交流的模式。从文本的设计而言,西门闹始终在意味着一种历史的在场,这段历史充斥着悖谬、癫狂、歇斯底里、荒诞不经,然而人性又始终在试图突围,回护道德法则,坚守心灵净土。从某种意义而言,历史的粗暴与现实的温情在蓝脸身上得以综合——蓝脸甚至没有身份,但是他勇敢、坚持、坚守、独立,没有历史合法性的合法性在于人性的甄别和自我判断——蓝脸的巨大孤独感下偏执狂般的坚守正源于他的朴素的道德勇气和坚韧的生命能量,这种英雄主义的个人气质最终给予了他恰当的历史身份,虽然他仍然是如此的卑微和单薄——但是,这不正是中国农村宏大历史叙事的蓝本吗?中国的传统农村社会的历史印迹,难道不从来都是权力的附庸、英雄的影子、文本的背景、话语的陪衬吗?没有人去追寻她的“出身”,更没有人在乎她的“在场”,但是,她难道不从来都是历史的最神秘的动力、最深刻的背影、最执着的标尺、最孱弱的生灵吗?历史沿用着一种卑微的口述模式,在神话与神化间将脆弱的生命晾干,做成标本,这是个没有名字的标本,或者说,是个可以随意更名的标本,在这个标本里,我们可能甚少看到“人”的要素,因为人都被神化为英雄或者恶魔。——现实深刻的创造着历史,但是,历史却不经意的甚至率性的虢夺着生命的尊严和一元性,我们能看到的,甚至是个不经的故事,一个“莫言”的谰言。诡诘的历史下众生的喧哗和叹息,变成了一场无比脆弱的挣扎和毫无意义的游戏。
这是对记忆的颠覆。的确,西门闹慢慢的、隐然的消退了。从驴时代的刻骨铭心到牛、猪、狗、猴,西门闹越来越不是西门闹了,而纯然成为一个优秀的动物——按阎王的意图,仇恨渐渐消除——然而记忆又在蓝千岁那里历历在目,记忆恢复了,历史不同时也回来了吗?然而,蓝千岁毕竟不是西门闹,就算是西门闹,他对历史的叙事也更平和,甚少偏颇与执见,他娓娓道来,然而肉身孱弱;他看似老道,然实少不更事。历史祛除了强价值观时代,然而孱弱、弱势、虚弱,看似超脱而完全没有承受力,渐渐脱去公共的价值提供者的角色,困于一隅,喃喃自话,变成一场单纯智力的游戏。
这是否依然意味着:蓝脸的个人修行式的执着变成一种魔咒,对这个家族、这个民族,我们缺乏集体信念、大众信仰,我们的民族缺乏集体认知,没有对真正英雄的集体膜拜。——历史只能依托于人性的坚执前行,并留下虚弱的、凌乱的记忆。
四、结语
“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从佛理上讲,耽于此岸的苦楚而追求彼岸的涅槃,祛欲随性,往生极乐是摆脱生死疲劳的法门。从语源上说,生死疲劳的源于佛典,与文本作者的魔幻现实主义旨趣的相去泾渭,自然就有了解释甚至过度解释的意味——至少,它并非朝向佛教信仰的诠释,虽然它借用了佛教的地狱、轮回,虽然甚至在某种印象上,欲望主导的生活充满了错误、暴力、苦痛、变态、死亡,但是,我们不也同样可以看到相对的存在——一味的逃避、批判、否定现实,自然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欲望——一种纯粹生命的、旷达的、直白的欲望写在大地之上,不是也能剔除人性的伪饰,让人赤裸裸面朝大地,展示人性的健硕和伟岸吗。
莫言在佛理与生理、畜与人、历史与当下、权力与沉默间离析和折冲,并给予了文本巨大的解释空间和想象空间。视野变换下的生命体验使小说呈现出别样的韵味。宏大叙事被作家的个性化历史,甚至是不同生命形态的牲畜感知所解构,将扭曲的人性放在特定的情势下观照,并几乎以一种吊诡的、戏谑的方式,对“生死疲劳”这一出处佛教的教条,进行了根本的颠覆——“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几乎可以转换为:生死疲劳由土地起,苍茫大地,身心俱在,从而回归了文本的现实主义旨趣。
[1] 朱向前.莫言小说“写意”散论[J].当代作家评论,1986,4:12-19.
[2] 莫 言.生死疲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3] 刘 伟.“轮回”叙述中的历史“魅影”——论莫言《生死疲劳》的文本策略[J].文艺评论,2007,1:57-61.
[4] 石一龙.写作时我是一个皇帝——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访谈录.延安文学,2007,3:81-109.
[5] 李明刚.论《生死疲劳》轮回视角下的佛性拯救[J].文化研究,2009,8:234.
Desire and Reincaration in Fatigue of Life and Death ——The View of Transformation of Life Experience
ZHOU Ni
(Hu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f Profession of Commerce, Changsha 410205, Hunan, China)
Mo Yan’s Fatigue of Life and Death is not a Chinese rural pastoral ode by name borrowed from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reincarnation. It shows a strong magic realism sense, suggesting that this piece of land deep suffering and profound self-redemption——the animal’s appearance and inarticulate human reincarnation past life memories and present experience. “Mo Yan’s” presence and role play in the text shows various historical faces and life experience amidst the vision transform.
Fatigue of Life and Death; desire; Mo Yan; life
I207.425
A
1673-9272(2013)03-0152-03
2013-02-06
周 妮(1980-),女,回族,湖南常德人,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编校:罗 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