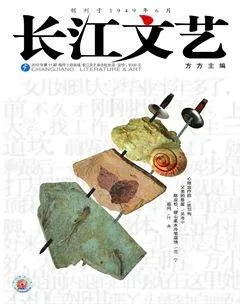复制与内疚
最近一条发人深省同时振奋人心的新闻是:击毙劫匪周克华的地方,正在成为重庆旅游热点,一些人甚至倒地模仿劫匪最后的姿态,并留影。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条简单的新闻,而是摹仿,是复制,是身体的表演。这难道不是艺术最原始的动机,以及最原始的符号?是的,我们将有幸再次目睹文学艺术的伟大复兴……
作家、编剧及导演诺拉·埃芙恩(Nora Ephron)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复制。我们生活在复制之中。人们在大街上成年累月跳交谊舞,学生和老师在电脑上不知疲倦地复制粘贴各类表格论文,社会新闻每天都在播报各种各样的结婚离婚吵架分手虐待强奸杀人碎尸抛尸逃亡悬赏围捕判刑处死,等等。注释①:强奸主要分为官员(包括警察)强奸少女及其它强奸,最近几年的强奸绝大部分是前者;注释②:年龄差距到达一定规模的婚姻,基本也被归入潜在犯罪行列,同时以生物变异现象视之……如果一个外星球的生物,花上一个月时间阅读这些社会新闻,他只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地球上到底住了些什么只会不停复制结婚离婚吵架分手虐待强奸杀人碎尸抛尸逃亡悬赏围捕判刑处死的家伙呢?
实事求是地讲,这是人的本能,就像地球上的一切可怜的生物所能做到的一样,它们只能、只会不停生长复制出一样的细胞。从显微镜下的植物细胞到人类的胚胎,他们的毛病一模一样,生长就是复制,然后再复制。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演变到现在,这种本能没有萎缩反而大大加强了,从制度、机构、建筑到人的外形、语言等等,一切都在更加快速的复制中。受本能的左右,复制不仅在人的肉体上显现本领,而且也延伸到了艺术活动中,正如很多人已经注意到的,我们的电视作品,正在力求完美地复制美剧、韩剧里的人物、情节、故事、台词甚至道具。除了我们收看《李春天的春天》时忽然遭遇到《严肃的月光(Serious Moonlight)》的这类惊喜以外,观众简直不能抱怨什么。诚恳地说,如果有人爱好把美剧韩剧再看一遍,国产电视剧是个不错的选择。
文学来源于复制,但不是复制模仿,比如模仿别人的作品,而是通过复制一个瞬间一种情境,想象一种已经和未来、已知和未知之间的距离,在猎物前歌唱是一种,模仿劫匪的死亡也是一种,打猎和死亡因为模仿生产出额外的涵义,这是文学艺术的空间。但是由于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不自信,人们模仿其他文化里的作品,这个文学的空间就是作品和其他作品之间的距离,比起现实所能给予的想象空间,就太窄了。这就是没有想象力的文学艺术。
文学创作者看到开头那条新闻,应当感到羞愧,我们已经多长时间没满足人们的模仿欲了——文学作品太没有想象力,人们才冲上街头去看劫匪的丧身之地,并自发创作,这真是让人异常痛心的事。现在不是文学来自生活,而是文学跟随生活,捡拾生活的残渣——不用去求证有多少作家直接从社会新闻中翻找素材,而是要询问自己,难道我们要让更多的人徘徊在街头,没有一毫米对文学艺术的指望吗?
我们已经太习惯作家们的自我中心式的表达,不是没完没了的苦难往事、创伤体验、混乱年代,就是深刻的道德感、心灵的感悟、孤独的行走、奇特的生活方式等等。电影试图从其它角度教育和安慰观众,从《鬼子来了》、《让子弹飞》、《山楂树之恋》、《金陵十三钗》到《黄金大劫案》等,中国电影致力于文化教育、政治教育、怀旧、跨国恋和假装狂欢,除了文化内疚感和疲惫的脑神经,电影院里和电脑前只有一群被过度教育或奉承的观众。在复制自我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学艺术拉扯分裂着人们的本来还算正常的自我,在里面培育更多的内疚、自卑和愤怒,它的完整名称叫做痛苦。
这是个没有幸福感的时代。文化之病态首先从作家艺术家开始,他们模仿自我胜于模仿现实,怀念过去多于熟悉现在,眺望生活超过接触生活,所以他们轻率地评价人们和这个时代,因为自身的狭隘而认定这个时代一无所有,因为几个网络笑话就可以鉴定这个时代的道德品行,甚至根据社会新闻这架望远镜下的若干小故事,就编织出几十万字的小说。
文学艺术让我们为自己的文化和时代内疚和自责,这是自我复制的典型症状(请参看精神分析学相关案例分析)。看过《赛德克·巴莱》后,我们则为错过野蛮而遗憾,我们处在《变形金刚》和《赛德克·巴莱》之间,或者说文明和野蛮之间:纯粹的娱乐似乎有点儿奢侈,血性的炫耀更加遥不可及。
一种内疚自谴的文化会如何?因为放弃希望,噩梦一再出现。文学越来越平庸,人们才会在汶川地震后的旅游热中,在废墟前合影:到此一游。当港片、武侠小说兴盛的时候,人们以郭靖杨康为尺度,还知道什么是羞耻和正义;以黄蓉洪七公东邪南帝为尺度,还知道人性的正邪智慧荒唐深情等等的丰富有趣。人们通过模仿文学了解人性和正义。大众文化作品才是那个时代的神话,而不是陷入自我复制漩涡的所谓纯文学。每个时代都需要它的神话和传奇,当这个时代的很多作家作品还在不停意淫女人的乳房并以之为惟一精神食粮和安慰时,我们这个时代的软弱之精神质地和不幸的命运是何等触目惊心!
我们需要的是新的传奇和神话,需要《歇斯底里》(Hysteria)中的女权主义者似的打破常识推进变革的传奇人物,需要《独裁者》(The Dictator)里的反讽戏谑手法,需要文学模仿现实创造新的想象空间,需要新一代的行吟诗人。
相反的话,也许尼采所预言的永恒回归正在实现,我们的文学、艺术、生命、民族国家等等也将在内疚的循环回归中一直循环下去……
责任编辑 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