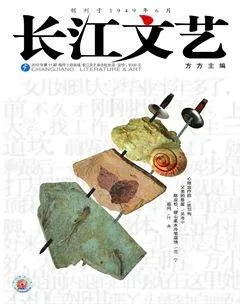对当下国学讲习应取辨析态度
一、“国学”名目的流变
作为汉字古典词,“国学”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如《周礼·春官·乐师》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此处的“国学”,指中央之学、朝廷之学,与乡遂设立的地域性“乡学”对应。隋唐以降科举制确立,设立于京师的掌管国家教育的机构(同时也是最高学府)称“国子监”,又谓“国子学”,简称“国学”。总之,在古代,“国学”略谓国家设立的学校。
时至近代,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为着与来自西洋的“西学”相区分,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国学”一名出现,是对强势的东渐之西学的一种反应。如江户幕府时期(1601—1868)的日本人,自18世纪起,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汉学(从中国传入)、兰学(从欧美传入,19世纪扩称洋学)、国学(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国学”一名,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1902年梁启超(1873—1929)撰文,以“国学”与“外学”对应,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梁氏曰:“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5年国粹派创刊于上海的《国粹学报》,公示“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宗旨,这里的“国学”意为“国粹之学”。该刊发表章太炎(1869—1936)、刘师培(1884—1920)、陈去病(1874—1933)等人的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方面文章,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自此,中国人开始在“中国固有学术文化” 意义上使用“国学”一词,为“国故之学”的简称。所谓“国故”,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此前清人多有用例,如魏源(1794—1857)认为,学者不应迷恋词章,学问要从“讨朝章、讨国故始”(《圣武记》卷11),这探讨国故的学问,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
经清末民初诸学者(章太炎、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黄侃、陈寅恪等)阐发和研究,国学所涉领域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史、哲相当,但突现了中国固有学术的内容,自有其存在与发展的根据。
二、“国学”讲习的双重目标
20世纪初年流亡日本的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分上卷 小学十篇,中卷 文学七篇,下卷 诸子学九篇,具体展现作为“国故之学”的国学的基本内容。章太炎在一封书信中讲到提倡国学的原由:
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答铁铮》)
认为民族精神的勃兴,就像种庄稼,需要灌溉,而“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的国学,便是灌溉之源泉。章太炎两度倡言国故之学:一次在清末排满革命之际,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抵抗日本侵略之际,都是试图以国文(语言文字)、国史(历史地理)、国伦(伦理道德)等国学内容激发大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本位精神。
如果说,章太炎等“有学问的革命家”倡导国学,是着眼于激发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那么,20世纪20年代开始倡导“整理国故” 的胡适(1891—1962),则更多的是从学术上树立与“西学”彼此对应、相互启发的“国学”。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给“国学”下定义: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
胡适反对将“国学”与域外学术对立起来、孤立开来,而力倡与域外学术作“比较的研究”,主张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从古今中外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这是一种着眼于学院式研究的国学观,同时也是一种对西学开放的国学观。
自20世纪初叶以来,“国学”之名在中国已经流行百年,其内涵大约包容章太炎、胡适倡导的那两层含义,是一个在学术界、教育界使用渐广的概念:某人研习中国传统学术有成,便被称为“国学家”;博学精研,成就斐然者则尊之“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1877—1927)、陈寅恪(1890—1969)等人荣膺这一称号。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所传习之“国学”即如上义。而清华国学研究院原拟聘请的导师有章太炎,章因故未应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1892—1982)。梁的博大,王、陈、赵的精深,皆一时之选,堪称“国学大师”。
中国素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而现行高等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科体制,高度分科化,此法有利有弊。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有人主张打通文、史、哲壁垒,于是便有综汇传统学术的“国学课”的设置,武汉大学依此旨开办“人文试验班”、“国学班”,前后已历十余载。近年中国人民大学还专设“国学研究院”,效尤者不少,仅武汉地区,已成立武汉大学国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国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这些作法都是试图在综合式的“国学”名目之下,开展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整理、研讨、传授和创发。
宋人张载(1020—1077)在《正蒙·大心》中把国故之学分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前者指通过感官接触外物获得的知识,约为智性知识;后者指通过内心修养参悟出来的知识,约指德性知识。唐人韩愈(768—824)谓:“教诲于国学也,严以有礼,扶善遏过”(《窦公墓志铭》),强调国学在养成“德性之知”方面的功能。此种分类自有道理,却又不必截然分作两橛。国学讲习应注意于二者的兼顾与互动,一方面介绍基本的国学知识(语言文字、典籍、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典章制度等),另一方面又彰显国故之学蕴含的大义,把“小学”功夫与“大学”授受结合起来,达成“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水乳交融。
德性之知当然有赖智性之知的浇灌,但二者不能替代,有些学识广博者德性并不高,而有些文化水准较低者蕴含着丰厚的德性。故德性之知的获得,并非单凭知识传授,还自有生成机制。
三、国学讲习当适度、健全发展
近年来,有的社会教育机构高张“国学”旗帜,提倡少年诵读经典,一些学人则利用大众传媒讲论古典,意在突破传统学术讲习的学院式门墙,以“国文”、“国史”、“国伦”对国人实施人文知识普及与伦理教化,一时洛阳纸贵,颇受大众欢迎,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专业研究者从学术规范角度提出的批评。凭心而论,讲习国学受到欢迎,显示了国学的感召力,反映了社会对它的渴求;遭遇批评,则有益于讲者和听者学术水平的提升,推动人文素养的上扬,故两者皆为好兆头。这样一种对国学的倡导,与胡适式的书斋国学颇相差异,而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章太炎式的国学运作模式的复归,即试图以国学滋养国人的智性与德性,特别是激发国人的爱国心、道德感,以因应现时代渐次发生的信仰危机、道德沉沦等社会问题。国学讲习由此汇入现实的人文教育轨范,不再仅仅是象牙塔中事。
对于“国学”在大众教化意义上的展开,似宜抱持谨慎的肯定态度。
之所以应予“肯定”,是因为在中国渊富的学术文化中,包蕴着多种积极健全的精神资源,诸如——
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
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政治哲学
和而不同、互动共济的和谐理念
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精神与物质兼顾的文明观
好学、善学的重教传统
诸如此类的中华元典精义,历千百年仍光耀万丈,经过现代诠释,可以转化为救治“现代病”的良药、滋养今人心田的营养。故我们有理由期待国学在人文教化方面取得实绩,并在国学普及进程中,实现古今推助、雅俗共进,开辟国故之学发展的新生面,以有益于众生。
然而,面对国学,我们又必须“谨慎”——
第一,国学中有粹亦有渣,昌明国学,切勿抱残守缺、视“国渣”为“国粹”,任沉渣泛起(如一度“厚黑学”泛滥)。即使是“国粹”,也有一个古今推衍、现代诠释的过程,不可生吞活剥、食古不化。
第二,昌明国学,不能夜郎自大、唯我独尊,排斥异域学术。健康的国学,应当古今贯通,后浪逐前浪,切忌以古蔽今,开历史倒车;健康的国学,应当开放胸襟,吸纳外域英华,在学术本体与方法诸层面,都要与异域学术既相辩难,又相吸取,在互相比较、互相观摩、互相取舍、互相融会中,达成新的综合与创造性转换。
第三,立足于现代文明,对国学有所辨析、有所取舍,如被视作国学核心内容的“三纲五常”,既不要照单全收,也不要全盘否定,而应加以分梳,扬弃绝对主义的“三纲”说,发挥双向互动和谐的“五伦”说。
时人应当清醒认识:国学孕育、生发于三千年农业——宗法社会,长期依附于专制皇权,国学虽有批判、制约皇权的成分(民本思想等),但远不足以救正专制皇权,建设民治的公民社会。因此,仅凭国学资源推动现代文明建设,不仅远远不够,而且如果对国学的某些成分作不恰当的伸张,还有可能对现代文明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当然是倡导国学的真君子所不愿见到的。
对于国学讲习,我们乐观期望其健全、适度的发展。
责任编辑 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