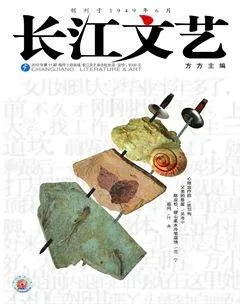说长篇小说
如果有人要说,长篇小说就是篇幅长的小说,我不能说他不对。因为这是一个事实。你看看,凡是被称为长篇小说的,哪一部的篇幅短得了,更不用说多卷体的或有一定关联性的系列长篇,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等。喜欢写长而又长的小说的法国人,还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大河小说”或“长河小说”。把小说写得像大河之水那样长流不断,你说篇幅长不长。当■,所谓“大河小说”或“长河小说”,并非单言其长,而是指所反映的人生或历史如长江大河,奔流不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育较早,因为分“卷”的概念不同(西方多为一部,中国古代多为一章一节),所以少见像西方那样的多卷体长篇小说,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家喜欢续、补前面的作品,所以类似于西方多卷体的长篇小说那样的续书、补书,倒不乏见。从宋元的讲史话本,到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莫不如此。尤其是那些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长篇小说,如从前称作“奇书”、“才子书”,现在称作“名著”的,续、补的作品就更见其多。如《后水浒传》、《结水浒传》(即《荡冠志》)、《后西游记》、《续西游记》、《西游补》、《续金瓶梅》等。仅《红楼》一书,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开列的续书、补书,就有《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梦补》、《红楼补梦》、《红楼重梦》、《红楼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增补红楼》、《鬼红楼》、《红楼梦影》等十余种之多。虽然这些续书、补书,并非出自原作者之手,也并非同一作者所为,但因其人物和情节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在性质上颇近似于西方的某些多卷体长篇小说。中国现代最早出现的多部头(或多卷体)长篇小说,是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从秦汉写到民国,计十一卷,可谓卷帙浩繁。但因其主要依托正史,并非纯粹的虚构小说,所以与西方的多卷体长篇小说还有所不同。倒是后来的武侠小说,如顾明道的《荒江女侠》、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等,由报刊连载而分集出版,较接近多卷体长篇小说的体制。真正有意识地创作多卷体长篇小说的,是现代文学史上写作“三部曲”的作家,如茅盾、巴金、■人等,尤其是■人,更属自觉地采用法国“大河小说”的体制创作长篇小说。到了当代,以“三部曲”的形式创作长篇小说的,仍不乏其人,如《六十年的变迁》的作者李六如、《红旗谱》的作者梁斌、《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等,都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三卷或三部。但也有些作家,似乎又倾向于把“三部曲”发展成超过三部的多卷体,如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写了四部,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写了五卷,《创业史》原计划也写四部,但因“文革”原因,成了断尾巴蜻蜓。今天写“三部曲”或多卷体的作家就更多了,别的例子不举,就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参评作品,张炜的《你在高原》写了十部,四百多万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写了六部(十一卷),五百万字,堪称当代小说篇长之最。我不知道坊间是否还有更长的小说(网络上肯定有),或将来还有人写出更长的小说,但仅就存世者论,可知长篇小说的篇幅是没有上限、无人封顶的。
话虽这么说,编辑出版部门对长、中、短篇小说的字数,似乎还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限定,一般说来,三万字以下的,可称短篇,三到十万字之间的,可称中篇,十万字以上的就是长篇了。也有把中、短篇字数的上限降得更低的。但因为不是文件的硬性规定,所以在实际区分中,仍有弹性。这样一来,有的小说就时而被说成短篇,时而被说成中篇,时而被说成长篇,远的不说,大家熟知的《阿Q正传》,似乎就常常被人这样随意归置。说它是短篇的比较普遍,但孙犁分明说它是“中国中篇小说的开山鼻祖”,我也见到有人说它是长篇的(当然主要是指它的思想和社会生活容量)。这倒也没什么大问题,因为长篇的字数边界本来就很模糊,它的界标还是一个约数,所以你怎么说都可以找到理由。更何况,长篇也有较长的、很长的,也有较短的、很短的,后者又常常被人称作“小长篇”,与中篇的规模差不多。现代文学史上,就有很多这样的“小长篇”。上个世纪60年代去了美国的一些台湾作家,如聂华苓、於梨华等,也爱写这样的“小长篇”,如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等,今天仍有许多作家喜欢写,如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篇幅都不算太长,都可以归入“小长篇”之列。对字数问题最不讲究,甚至搞得有些混乱的,是俄国人。19世纪那些为我们所崇拜的作家、批评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别林斯基等,就常常把长、中、短篇搅在一起,让你长短莫辨。尤其是长篇和中篇,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不过一个长得高些,一个长得矮些,区别并不太大。所以屠格涅夫的《罗亭》,才像《阿Q正传》一样,一时被说成中篇小说,一时被说成长篇小说,一时又被说成“大型的中篇小说”。最早确立中篇小说地位的别林斯基甚至说:“中篇小说也就是长篇小说,不过规模小一些罢了”,或说“中篇小说便是分解成许多部分的长篇小说;是从长篇小说中摘取出来的一章”;有些材料不够写长篇小说,就拿来写中篇小说等等。可见俄国人虽然发明了中篇小说的概念,但却并不太在乎字数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别林斯基常常把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放在一起讨论,彼此不分。如他说“长篇和中篇小说现在居于其他一切类别的诗的首位”;“长篇和中篇小说甚至在描写日常生活中最平凡而庸俗的散文时,也可以是艺术极境和至高创造活动的表现”;“长篇和中篇小说给作家的才能、性格、趣味、倾向等主导性能以充分发挥的余地”,如此等等。别林斯基这样说,并不是有意把水搅浑,而是因为俄国当时有一种后来被称作中篇小说的文体正在崛起,其势头恰如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的爆发。对这种新崛起的中篇小说文体,别林斯基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没有它,杂志就像是一个人在大庭广众间不穿鞋子,不打领带一样,今天大家都在写它,读它,它占据着上流妇女的闺房和著名学者的书桌,最后似乎连长篇小说都要给排挤掉。”但是,在他的心目中,最重要的还是在俄国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也是他向所推崇的长篇小说。虽然他也赞同“中篇小说是人类命运无穷的长诗中的一个插曲”的说法,但这“无穷的长诗”,却是长篇小说。只有当这些从生活的大书里扯下几页来的中篇小说,重新构成了一部文学的大书,才配得上“人与生活”这个标题,才是他所称道的那种“广阔的书”、“错综复杂的长诗”,即“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可见,别林斯基要求于小说的,是它反映生活的能力如何,而把这种能力发挥到极致,达到无与伦比的深广程度,无疑非长篇小说莫属。
作为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权威发言人,别林斯基对长篇小说的性质和功能,有许多特别的界定,同时也有许多特别的期待。他说:“我们时代的史诗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包括史诗底类别的和本质的一切征象”,“长篇小说还有一个绝大的优点,就是:个人生活可以充作它的内容”,在长篇小说中,“生活是在人的里面,诸如人的心灵的秘密,人的灵魂,人的命运以及这命运和民族生活的一切关系等”,“长篇小说更适合于诗情地表现生活”,“它的容量,它的界限,是广阔无边的”等等。这些说法,不但在今天看来毫不过时,而且,事实上一直在影响着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实践。尤其是他说的史诗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更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孜孜追求的理想目标。虽然最近三十年来,史诗性的观念在创作中逐渐地被放逐和消解,但陈忠实的《白鹿原》,却援引巴尔扎克的话,把表现“民族的秘史”,赫然标于卷首。这“秘史”二字,自然应当包括内外两个方面,既有外在的,即民族和个体的生命活动与生存活动的“秘史”;也有内在的,即别林斯基所说的民族的和个体的心灵活动的“秘史”,亦即张承志所说的“心灵史”。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要写出这个“秘史”,凸显出长篇小说的史诗性,单靠罗列历史事件,展示生活场景,描摹生活细节,显然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作家的思想。是将这些事件、场景和细节有效地组织起来,充分地显示其意义和价值的思想。因此,别林斯基对长篇小说的思想,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在他看来,一部长篇小说的思想深度和思想的组织力量,是衡量其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也是其区别于流行的大众文化读物的重要尺度。在这个问题上,他的一些意见,对当今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仍有重要的针对性和启发性:
作为艺术品,长篇小说就必须从日常生活和历史事件中剔除一切偶然的东西,透视到它们隐秘的核心——透视到那生气勃勃的思想里去,使表面和分散的东西成为精神和智慧的容器。长篇小说的艺术性之高低即赖于小说基本思想的深度以及这一思想在个别部分中的组织力量。如果达到了这一要求,长篇小说应该与一切其他自由想象的作品并列;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它与文学中满足公众日常需要的、朝生暮死的作品严格地区分开来。
责任编辑 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