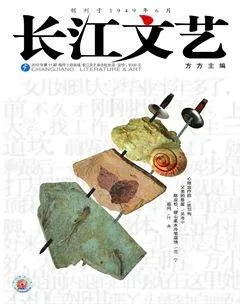陈应松:硬山柔水冷笔温情
陈应松, 1956年生于湖北省公安县黄金口。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出版有长篇小说《猎人峰》、《到天边收割》等,小说集《一个人的遭遇》、《陈应松作品精选》、《星空下的火车》、《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陈应松小说》等,随笔集《灵魂是囚不住的》、《所谓故乡》、《世纪末偷想》、《在拇指上耕田》、《小镇逝水录》,诗集《梦游的歌手》等40多部,《陈应松文集》6卷。小说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大奖等数十个奖项。中篇小说《像白云一样生活》改编成电影《复活的三叶虫》。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院院长。
山与水,是中国文化中相映照的一对儿,对一个文化生命而言,山山水水,交织一生。
仁者乐山,智者喜水,怀仁遣智,投射山水之间。作家有一双慧眼,一颗仁心,所以常常要与山水打交道。山迢迢,水漫漫,兜转人生,文字征程。
山硬朗,水绵柔,见诸文字,便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写山,可以浩荡磅礴,巍巍莽莽;写水,可以灵动清丽,逶迤腾挪。不过这些并非写山写水的止境,不同的眼睛看山水,会收摄不同的生活图卷;不同的人生观照山水,更会体悟不同的境遇。
游走山水之间的陈应松该是最有体会的人。
陈应松曾做过船工,早期文字里,有许多以江水和水乡为背景,虽然都是有血有肉的书写,但无法让他满意。文坛前辈如大江大流,在他面前汇成汪洋一片,即便走笔如飞,文学这支桨,似乎也摇不到彼岸。
44岁那年进入神农架,大山雄浑,让陈应松找到了骨力和锋芒,文字顿时硬朗冷峻,凭借“神农架系列”,他在文坛开始拥有独门绝技。
如今,过了知天命年后,陈应松的文字走出大山,又回到江汉平原,回到温润水乡,笔触之间增添不少岁月深厚带来的温情和暖意。
冷的山,暖的水,让陈应松的文字张力无穷。
一
“陈应松的小说给文坛带来的是一场审美惊奇。在当今文坛,他用他的艺术探索,突破了实与虚的边界,突破了人与物、生与死的边界,浓墨重彩地重现温暖、光明、善良、坚韧、勇敢等元素,突破了人性、人心的边界,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特殊标本。”
2004年,陈应松的小说《松鸦为什么鸣叫》,从187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距离他走入神农架大山仅仅4年时间。离开平原走入大山的陈应松,文笔也是峰回路转,开创出极具地域特色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他不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书写山区生活,而是在瑰奇的原始森林里,找到了各种现代主义的元素,相比那些概念化和脸谱化的山区作品,他觉得自己的书写更接近真实。
范宁(以下简称“范”):在您的创作生涯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分水岭”,那就是2000年进入神农架前后。在进入大山之前,您的创作情况是怎样的?
陈应松(以下简称“陈”):人们评价我有句话,说我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我深以为然。我以前做过船工,早期的小说里写过长江,还写过一些带有水乡特色的村庄。但是我写得很苦恼,回头再看过去的那些文字,我是不满意的。尽管我出生在江汉平原,来自水乡,但我没有把它写好,不真实,不丰富,不大气,所以得不到读者的肯定。我的船工小说系列也是,虽然有人评价很高,但我只能说是练笔而已。
作家常常会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开始写起,比如自己的家乡。但是家乡并不容易书写。我是湖北人,笼统地说,湖北就是我的家乡,但是湖北这么大,地域特色如此复杂,哪一块才是我要写的呢?当年我写的水乡很轻,像无根的浮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我的生命之根明明在这里。那时候我真的很苦恼。
范:进入大山之后,您的创作开始找到感觉了?
陈:不是常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吗?我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智者,而是视为一个胸怀宽仁的人,神农架的博大粗犷正好对应了我那时对于人生和世界的看法——不像水那样是温润流动的,而是像山一样干硬坚韧的,充满了某种我们难以言说的顽强定力。
范:我阅读您的小说时有种感觉,人们在写到山的时候,要么是“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的浩荡,要么是“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的深幽,但您的大山生活并没有停留在敦厚仁善这个层面,而是将大山冰冷、硬朗的一面展示出来,文风也非常冷峻。
陈:最开始我并不是为了写什么作品,或者为了形成某种风格去神农架的。当时是到神农架挂职,孩子读了大学,家里也没有什么事情,于是就想去大山里面静一静,逛一逛,写一部随笔出来。但是真正住到神农架,才发现这种生活对于一个城里的作家来说实在是太棒了!那种山区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各种新鲜的生活经验,让我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我是从武汉到神农架去的,当时就觉得城市生活,我所在的单位、工作、职务,一切都有若浮云,变得非常虚无,而大山里的生活是那么有意思,那么吸引我,那么实在有趣。那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我在那里找到了在武汉找不到的陌生感。
所以我时常在想,所谓写地域文化,未必就一定指家乡,它是一种身份认同,或者说是一种对身份认同的强化过程。我出生在平原,和山区没有关系,但是我认同山区的生活,也认同了山区在我作品中出现的必然结果,认同了这种书写的欢乐甚至是文字狂欢。每一篇小说对我都是一次节日。
范:那初到神农架,您和大山就一定那么契合吗?完全陌生的两种存在,我不相信可以做到如此天衣无缝。
陈:何止是不契合,我的身体对大山简直就是排斥的。我在大山里住下来之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海拔比较高的原因,或者是水土不服,我的身体一直不太舒服,经常会出现心动过速或心律不齐的情况,有几次还半夜送到医院抢救,有一次是被山民抬下山的,无数次体验到濒死的感觉。许多作家不会有我这样艰难可怖的经历。面对大山,我的身体有巨大的不适应,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心里还在念叨:老天爷一定要保佑我,让我在这里写出一点东西来啊!
范:这种身体和灵魂的矛盾是难得的张力,灵魂上是如此的靠近,而身体上却又这么疏远。这可以保持一种敏锐度,您可以切身感受到山区生活最真实、最切肤的一面,同时又可以带着感情去审视这样的生活。
陈:的确。我的“神农架系列”出来之后,一下子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因为这样的山区生活是许多作家、读者和批评家闻所未闻的。过去写大山,总是写山妹子是多么的天真水灵,山里的汉子又是多么憨厚善良,许多生长在大山里的写作者,对于身边的生活太过熟悉,即便是那些让他们不太舒服的情景和事件,他们也可能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他们对家乡投入了太复杂的感情,不忍心那么残忍真实地去书写故乡,所以他们把山区生活美化了,美化意味着脸谱化,浪漫化,平面化,这样做肯定会失去大山赋予的能量。
恰恰我是个外乡人,说句玩笑话,我可以下得了这个狠手,写的东西是刀刀见血的。我更容易感受到这种生活强大的矛盾张力,呈现出山区底层生活的严酷、峻急。我的小说有很多现代主义的元素在里面,其实不是纯粹的现实主义,但是我觉得这样更能表现真实的山区,特别是充满了鬼魅气息的神农架。
二
从诗歌到小说,再到散文,陈应松涉猎广泛,是个跨文体的高手。与他聊文学话题,往往能触动机锋,有一些非常独到的认识。求变是一个作家应有的状态,但是求变不等于跟风;热爱是一个作家应有的情怀,但是热爱不等于只书写美好。
范:十几年来,您的“神农架系列”不断壮大,其中有中短篇,也有长篇力作。这个系列已经得到了文学圈和读者的认可,这其中固然有全新的领域和题材所起作用,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成功原因呢?
陈:除了新鲜的题材之外,真实地表现生活,这让“神农架系列”体现出浓郁的文学性,得到文坛认可。这个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尽管经过了一二十年的转变,但在文学的写实功能上还是有欠缺。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应该是非常解放了,但是依然有大量作品是从概念出发的,并没有触及生活的真实。同样,在新世纪,文学圈也面临如何去写生活、如何有更多生活的问题。在这个圈子里,一些作家的生活是雷同的、类似的,他们交流的话题、产生的想象都很相近,所以出现了作家之间“繁殖作品”的现象。比如聊天时候,这个作家脑子里的一个创意或者一个情节,被另一个作家拿去用在自己的作品里,那这种只是在脑子和脑子之间传递的故事,能说与生活有多接近吗?还有的人可以接触到真实的生活,有第一手的素材,但是他有勇气、有力量表现出来吗?也未必。
范:创作了一系列“神农架系列”小说之后,您现在来回顾之前的创作,有什么不同?
陈:神农架就像一个炼丹炉,炼出了我的“火眼金睛”——我获得了作家看待生活应有的独特视角。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首先要明白,哪些东西是自己可以写的,哪些东西是自己不能写的,作家需要明白自己在创作中的身份和位置——往往并非置身其中,而是冷眼旁观。这种“冷眼”是非常重要的角度。
就像在神农架,我是充满热情地去拥抱大山的,我觉得大山给予我无穷的力量,它的硬朗和坚韧,直接投射在我的文字当中。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是站在一旁冷眼相看的——“冷眼”在这里是一个客观状态的词,也只有冷眼相看,才能更全面地看清楚小说所应该表达的现实与人生。
范:您提到的这种热情,反映在您的文字上,却充满一种冷飕飕的残酷感觉?这是否有些矛盾?
陈:并不矛盾。我相信,任何一个具有严肃创作态度的作者,都会怀着一种叙述的热情,甚至生命的热情,全身心地拥抱他书写的对象,拥抱那块土地。但是这种热情并不一定要有与“热情”相近的语言、人物、氛围来表现。不能说讴歌美好事物的作品就是热情的,有些热情几近虚假,几近发烧,几近谄媚,几近骗子。美不仅仅是美丽的,那种文字中体现出来的力量、疼痛,同样可以是美的,可以是充满热情的。就像一个外科医生,把你身体弄得血肉横飞,让你疼得死去活来,是在为你热情地动手术,是为你好。一个作家可以以非常真实严酷的态度去创作作品,但是这种严酷背后,一定有一种更深的热情存在,他的作品是有着深层的热度的。那就是对这个世界,以及身处其中的人本身的热切关怀。
范:我记得几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的小说《到天边收割》刚刚出版——您就说过,自己在文风上已经有了一些转变,因为到现在这个年纪,内心会因为岁月的积累,而沉淀下许多温情的东西,文字会温暖许多。那么从挂职神农架到挂职荆州,这种转变依然在进行吗?
陈:在荆州的时候,我又创作了不少的小说,比如《一个人的遭遇》、《夜深沉》、《野猫湖》、《无鼠之家》、《送火神》等等。很奇妙的是,从平原进入山区,我脱离了水而奔向山;后来在荆州挂职,我则又从山转向了水。
我开始重新讲述水乡的故事,也开始重新审视这里。我本身就是从水乡而来的,但这一次我更加深入它,对“水乡”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比如田垄里的杂草,过去就笼统地作为杂草除掉了,但我现在开始分辨它们都是什么草,从何而来,有什么特点和用处——理解水乡,理解某个地方某样东西,就从这样的细节开始。
现在我看到的水乡,也不是过去那种很浮于表面的风景,而是看到水乡生活也有残酷的一面。不过相比那些大山的作品,以水乡为背景的作品更有温度,投射的是我内心涌起的温暖。
范:所以您对自己与生活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
陈:我的小说也是在变化,我不会成为僵死的标本,因为我在不断地行走和写作。
我在最新的小说集《一个人的遭遇》后记中,梳理了一下我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我知道我的脚让我获得了新生,永远有泥巴在脚上,晚上再清洗鞋子,还带回一些过去曾忽略的植物。现在知道了它们的名字,它们的少年、盛年和老年。还知道了一些庄稼。过去我伏在它们中间,但并不十分了解它们。现在我与它们像彬彬有礼的客与主,可以探听一些陈年旧事,细看它们,不再是一个靠它们的产出养活的人。这是很好的事。我已经有了与它们对话而不是被它们奴役的权利。这是年龄赐予我们每个人的恩典。因为我们努力过,所以我们成为了田野的散步者,也成为了田野的生客、观察者和记录者。当然,我们会成为田野的亡灵,会在故乡游荡。我坚信,我们的作品也将永远在故乡的田野上游荡。”
三
作为湖北省作家协会文学院院长,陈应松也肩负着培养青年作家的重任。以“50后”为主力的“文学鄂军”,如今热切期待着新生力量。但青年作家们在创作上有自己的想法,对此陈应松有认同,也有反对。
范:省作协文学院肩负着培养作家的职能,您也非常关注青年作家的成长,您怎么看现在青年作家的成长?
陈:青年作家现在面临着一个怎么认识生活的问题,其中不少人的创作被商业化所绑架。好像他们总有东西要写,而且什么都能写,城市、乡村、官场、商场、职场、唐朝、宋朝、天上、人间,都能写,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这种“能写”可能会害了他们。
当一个作家感到自己不能写的时候,这可能就是一个进步的机会,“不能写”是帮助作家反省并提升自己的一个契机,只有认识到自己“不能写”,作家才可能有救。就像点穴一样,只有按起来发痛发酸才算是按到了穴位嘛,专门找舒适的地方按才是很可怕的事情。好的作家内心都是有伤口的,但现在好像很多年轻的作家都在为快乐和轻松在写作。写作固然是要获得快感,但是如果只图快乐和轻松,对作家自身的提高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世界上的文学经典都是写痛苦的,没有一部是写欢乐的。
我也经常在网上看那些很轻松的作品,因为我自己的写作就是痛苦的过程,所以我看同类的作品其实并不多。不过从湖北的传统看,有厚度和有重量的作品才算继承了湖北文学的血脉。
范:对于文学创作的未来,您有怎样的期待?
陈:年轻的作家必须要找到写作的根本道理——文学是一个不断反叛的过程,文学的传统就是在不停地反叛传统中去充实的,这就是文学的根本。就像我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之后,出现了很多后继者、模仿者,但是到目前为止,那些书写底层山区残酷生活的作品,也罕见有超过我的,因为“像我者死”嘛,必须要不同于我所写的内容、风格,你才有文坛的一席之地。
即便是类型文学、商业化的写作,这一原则也是不会改变的。无论是职场还是官场,你也必须是首创者才行啊,否则就是跟风。我希望青年作家能够不断地尝试新的东西,我也希望湖北文学出现焕然一新的作品,但那一定不能是跟风之作,不能看到官场小说火了就写官场,职场小说火了就写职场,穿越小说火了就写穿越。商业化是作家应该时刻保持警惕并要抵制的。稀奇古怪的写作不是创新,只是奇装异服罢了,小说的魅力在于内容。
范:“80后”、“90后”还有一种创作倾向,那就是情绪内化,他们的创作更多是针对内心,这种创作理念和您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有了很大的不同。
陈:不同时代的人,各有各的烦恼和痛苦,所以他们写的东西也绝不一样,文学读者群也随之细分,存在就是合理。但是,现在即便是1989年生的人也成年了,走上社会,马上要成为中流砥柱,他们应有自己的担当,不能总陷于个人的情绪中,同样需要关注现实。因为说到底,这个世界走下去,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他们的,他们有责任让世界变好一点。
范:您之前还提到过“作家经纪人”的概念?
陈:我想,作家经纪人对实现作品的价值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可以帮作家销售更多的书,让只卖5万册的书可以卖到10万册,就像那些歌星和影星的“推手”一样。港台作家普遍拥有经纪人,而在湖北,几个作家有呢?
我对经纪人的构想是:可以帮我吆喝作品、打开市场、维护权益,但必须尊重我的创作。我可以和他收益分成,但如果有违我的创作理念,再赚钱我也不写。我原来就这个事情发过微博,后来还真有律师发邮件给我,表示可以帮我追讨一部分网络版税,现在追讨的侵权稿费已经很可观了,这真是太好了!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