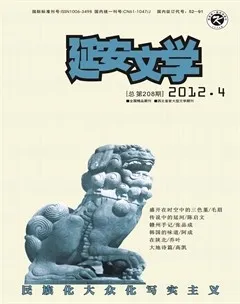父亲
一
那时我十岁,是个夜晚,春天的夜晚,八九点的样子,父亲咽下了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口气。那时候电视里正在播放着《塞外奇侠传》。在播放最后一集之前,父亲死了。
我在小房子里的炕上坐着,角落里,还坐着祖母。父亲躺在炕上已经两天了。就这样,小叔叔还招朋引伴,带了朋友来杀鸡吃。
父亲是因为喝了酒从窑顶上失足掉下去的,次日凌晨才在牛圈里发现了他。他口里一声声地叫着“妈”。他离世时,也是叫着妈,只要能喘得过气来,他总是叫着妈。
父亲在第二日就清醒了,他一点东西都不吃。放学了,我回来,他要喝水,示意我端过去。我很生气地递了过去……小时候他总是不在家,因此我与父亲很生分。那时候真小,什么都不懂,就因为这碗水,至死,我都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自己——我是不孝的女儿。
也许当时送医院,还能救得过来,可是太穷了。母亲又不在。
父亲去世时,身上只有18元钱。似乎在此之前,母亲离家的时候,把钱全部带走了。
父亲死的时候,母亲一直不在身边。那时候没有电话,也不知道母亲在哪里,直到春天过尽了,母亲才回到家,才知道这些。她们婆媳抱头痛哭,在窑洞——不是父亲掉下去的窑洞——的上面。三娘娘,对院的三娘娘一直跟我说一句话:“要好好孝顺你妈妈。”她知道妈妈的苦,可我不知道,至少那些年不知道。母亲抱着祖母痛哭,说了一句话:“四妈,无论怎样,我会为你养老送终的。”
她做到了。那时祖母大约八十了,又活了十四年,而在那之后的第五年,祖母瘫在了炕上。她一直伺候着她,无论有多少怨言,她都尽着一个儿媳的重任。祖母失去了儿子,母亲失去了丈夫,可是她们变得比以前亲近了,尽管也有争吵,可是母亲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家。她对父亲的离世也许有愧疚,之后再也没有嫁人。实际上根本不需要愧疚,这愧疚是我猜的。我不该去猜。
父亲快要离世了,小爹爹和二爹爹都在,还叫了上院的大爹爹,那是他们的堂兄。还有其他女人,我的一些婶娘们。站了一地,坐了一炕。
可是我不知道,我看不出人死前会是什么样子。
在最后一刻,对院的大妈,姓刘,但已经出了五服,把我带到了她家,跟亮亮堂姐和小军堂弟在一起。亮亮姐大我两岁,她比我懂事多了,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大约知道我就要失去父亲了,可是我不知道,也不懂得哭,知道哭会麻烦,让祖母不开心,所以尽管心里很难受,却也还是有说有笑的。
过了不一会儿,大妈过来,只说了一句话:“已经咽气了。”然后我就被带到二婶娘那里去了。那时候大堂哥刚结婚,整个家还蒙着新婚的喜悦,不是放着电视就是放着录音机,每日里都播放着“大花轿”、“窗外”、“同桌的你”等流行歌曲。他家总是人声鼎沸,但我不大去,不敢,二婶娘总是会拿眼瞅我,她总是会趁着祖母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蹬开房间大骂。她是个泼妇,却又是个在外面懦弱的泼妇,不过命也不好。父亲死了一月不到二爹爹也死了,她也成了寡妇。二爹爹到死都是穿着塌了底的鞋子,可是在他家里居然从房间里找出整整两箱子手工做好的鞋子。真是讽刺!她想要个好媳妇的名声,就每日里做针线。她给他做了那么多,却从来都让他穿旧的。世间居然有这样的女人?此后的这么多年,我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再没有见过像她一样的。她整日里希望他死,终是死了,可她并没有过上好日子。二爹爹是被车子轧死的,补偿金给的少,很快就花完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二爹爹死后她再也没有蹬门骂过她的婆婆——我那苦难的祖母。
我被带到了堂哥的新房里,二婶娘绷着脸。平日里我是要叫她二妈的,可那时没有叫。我怕她,心里也厌恶她。此后的很多年那种害怕虽然变成了同情,可是厌恶始终在。她是所有黑暗的代表,她的冷漠和刀子似的话语让我过早地知道了什么是生之艰辛。
《塞外奇侠》开始了,白发魔女骑着马在风中奔跑,她已经原谅了卓一航,却不想让他看见自己已经白发的容颜;而山中的优昙花找到了,唯一的一朵,她却给了自己的徒孙。
二妈在隔壁的厨房间说:“死了,彻底咽气了?”她带着怀疑和厌恶的语气,他的儿子说是的,他的儿子专心地看着电视,只是迎合她罢了。
我认认真真地看着最后一集的《塞外奇侠》,堂哥的老婆,我的堂嫂,那个刚娶不久的新媳妇嫌弃我的裤子弄脏了炕沿,厌恶地掸了一下尘,让我去旁边的沙发上去坐,沙发离电视不到二十厘米。
我坐了下去,心里哀哀,想着哥哥姐姐若在身边该多好,我们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了。
那是正月的下旬,沙漠里的沙一直吹一直吹,门口的对联被刮得哗哗响。很多年,沙漠里的沙,那夜的沙子一直吹在我的梦境里。
那一夜之后,我彻底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古书里说父母在是人生一大乐,我在年少的岁月,在对人世冷暖还不知道的岁月,就被剥夺了这一点。
如果死亡对父亲来说是一种解脱,我愿意他死去。此后的这么多年我一直给自己如此的解释,可是一想到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让我端水的画面,我就泪落如雨。那碗水阴阳两界,让我死多少次都愿意,只要能收回那厌恶的瞬间。
很早就想写写父亲,一点点地写,可是从来无法完整,无法还原,我知道的太少,而活着的人都是彼此不提的,很少提,这是一道伤。
这又是个春天,上午,南方阳光明媚,一只猫在我身边卧着,黄猫,我一直认为这种动物通阴阳两界,我开始写关于父亲的文字,但愿能一直写下去,我希望那夜的沙子声,响在周边。
二
一直无法回避,却一直在回避,我们从不去谈论父亲的死亡,以及他最后的贫困潦倒,我们只是说他死了。就如此,一个“死”字掩盖尽了所有他活着时的心酸。
父亲死时五十四岁。父亲欠债很多,也许死去,是当时最好的方式。因为已经五十过半了,在那个小城,在那个小村庄,很难有翻牌的机会,或者,他也无心去翻牌了,没有那力气。多年之后我不断恋爱,失恋。折腾几年之后,我发现我重走了父亲的老路,恋爱开始变得无心无力。晚年的父亲就是如此,所不同的是,我把恋爱当作了一项事业,父亲把事业当作了生命的一切。父亲在死前的那几年开始放羊,这是父亲的一项事业,或者是我祖辈的一项事业。爷爷喜欢放羊,我也放过。我们这个家族的特征,不得志了就去放羊,除了爷爷。爷爷把牧羊当作了一生的事业,他把一生的一半时光贡献给了羊群,贡献给了我小时侯的玩伴们。是的,我跟一群又一群的羊度过了童年,我是它们中间的一只,灰头灰脸。我忘记不了父亲赶着下院二爹家的羊群中午出行的场面,他把它们从小村里赶走,赶到山坡上,又赶到山沟里。白云清风,冬去秋来,那是怎样的孤寂?父亲的春风得意我没有参与,因为是在他得意之后的十几年后才生的我。我跑来观看的时候父亲的戏就快落幕了,我观看了父亲如何颓败,一个行将走向老年的中年男人的生活是如何地颓唐——此后的很多年,我偏爱这种颓唐失意的中年男人,我跟他们不断恋爱,然后我失恋,独自品尝一种叫做孤独的东西。我想这些人是我的那群羊,我接过了父亲的羊铲。上天并不是公正仁慈的,他把我派来见证父亲的失意,见证父亲的颓败。就像一种报应,在我刚开始人生的时候,上天就让我见证了什么是孤独,什么是寂寞。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为什么要在人生之初就承受这种孤寂?与生俱来,父亲虽然很早就死去了,可是他把他的孤独植根在了我的血液里。
父亲属羊,最后的几年断断续续的放着二爹家的羊,这是不是一种隐喻?上天的隐喻?我不知道。如果父亲是倒在一群羊之间,倒在清风明月下的山泉中,也许我以后不会那么不快乐,一再地思索他的死亡。但是命运不由我安排,父亲死掉了,死在了一个废弃的牛圈里,从上面的崖畔掉了下去……
父亲放养过的那群羊在他死后被变卖,留下的一些我来放养。我接过了他的羊铲,从此是一生。现在,因为退耕还林,羊被圈在圈里,这让很多人失去了牧疗的机会。我是说那些有心理疾病的人,包括我自己。我常常想,也许多年之后,我无法承受来自城市的重压,还会重新回到我的童年岁月,去赶着一队羊群走向山间,那少年时代听过的风沙,定会重新响起……乡村少年的牧笛声,足以牵引我的整个人生。
夏天,农历五月,小哥哥的生日,对,就那一天。我们黄土坡上的人过生日是要吃糕的,软米做的糕,甜,取节节高之意吧,反正是进取与吉祥。祖母总是不会忘记孩子们的生日。那天父亲也在,他是很少在家的,可那最后的几年,他在家经常一住就是几个月,经常,赶着他弟弟家的羊群,行走在山间小道。
那天父亲难得好心情。一大早,祖母淘了米,就拾掇着翻过崖畔找石碓子捣米做糕吃,老年人自然完不成这颇费力气的活计,所以叫父亲来完成。父亲居然同意了。
能吃到糕的心情自然愉快,而且父亲也愉快,整个家里面气氛很融洽。孩子们的心是雀跃的。孩子们知道恐惧,害怕风暴,可是风暴过去,一丁点的太阳就可以让孩子们忘掉一切,以为天好山好,水好人好。
我在别处玩了回来,看见有陌生的叔叔穿得整整齐齐地从自己家屋里出来,以为是亲戚,就觉得开心。孩子的心不设防,尤其是农村孩子。即便孩子有孩子的狡黠,可是怎么能骗得过大人呢?
那个衣冠楚楚的叔叔问:“你爸爸哪里去了呢?”我根本不会想祖母为什么不告诉他,我只觉得这个叔叔笑得面善,孩子根本不知道笑其实也不是面善的表现,孩子是需要很多年才能明白什么叫皮笑肉不笑什么叫笑里藏刀的,但到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是的,这个叔叔他问我:“你爸爸到哪里去了?”爸爸这两个字让人觉得新奇,因为平素叫父亲为“大大”,乡间都是这么叫的。所以我喜欢他。
我乐癫癫的,带着这个人翻过一座崖,走一段下坡的路,去找父亲。
远远的,我喊大大。
那个八九岁的小女孩一直带着一个陌生男人在我的梦境里跑,跑了十六七年了,还将继续跑,跑一辈子。
父亲听了小女孩的声音,挥舞的砧板停了下来。他的小女儿把灾难笑着引到了他面前,就是这些灾难,一点点要了他的命。
这个叔叔以后还来过,父亲总是好言相对。少年时代看到小罗卜头写年关家中被逼债的那一段,我总是哭得喘不过气来。有那么几年,我们家几乎天天如此。
父亲死了,一个多月了,这个人开着车子途经村子,听到父亲死了,居然说了一句:“死了好。”是别人家的孩子跑来告诉我的,我义愤填膺,可再怎么都是一群孩子。我是没有父亲的人了,他们有。后来的一些年,他们的父亲有的也死了,其中一个是心脏病,换肾后又活了几年,终是死掉了,但我的朋友那时候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只有我的父亲,是的,只有他,死在了我的童年,把我的人生一撇两半,让我成了半路失怙的半个孤儿。
多年之后,我常常想起那个上午,靠近中午的时候,农历五月二十五的太阳照得热烈,父亲在视线之内的不远处挥起木砧。父亲一锤锤捣下去,捣碎的不是做糕点的糯米,而是他的整个人生。而现在,父亲成了群山和沙漠之外的魂,他还会捣那些米粒吗?
那天父亲没有怪我,直接收拾了没有捣碎的米和没来得及筛的面粉回家了。在小屋里,他低低地说,对那人说了很多好话。而那人一脸阴沉,搬走了家里能搬的所有东西。
父亲始终没有说过一句指责我的话,可是我把哥哥的生日宴给破坏了。那天中午没有吃糯米做的糕点,一家人吃了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好像是面汤,挂面汤,放了几颗土豆,汤多面少。
祖母说要债的来了你怎么傻傻地带着去找你大呢?今天是你哥哥的生日呀。我在角落里端着饭碗,眼泪啪嗒啪嗒落在了碗里。我就着泪水喝汤,喉咙里发出呜咽的声音。祖母只是怜惜父亲,并不想埋怨我,他们知道欠债不还是不对的。父亲走过来说别说了,把孩子吓哭了不好。他抱我,在这拥抱里我又一次听见了喉咙里的呜咽声,从内心发出的,他的。
放羊汉从一开始就选择与土地亲密,不时地与土地交媾,最后回归土地,也许是最好的方式。父亲挥舞木砧,那声音是提前为亡灵唱的一首挽歌,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而那个时候我才抵达了他当时的灵魂。在不断的重逢和确认里,我抵达了父亲的灵魂所在,可是,也只是在某一刻,然后父亲就远远地甩开我,远去,再次远去,一次次远去。
我经常做梦,现实里也是,常常一个人在陌生的车站或者车子上辗转,内心恍惚,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手里握着不知开往哪里的车票。没有人,是的,只有我自己,在天涯海角,在每一次转身中寻找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