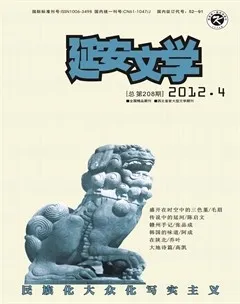李亮:通向语言的道路
李亮的散文创作蕴含着一个艺术思辨的基本命题,也就是以语言为中介,把文学功能从日常生活五色杂陈的混乱中分离出去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叫艺术的“升华”,也可以叫艺术的“概括”,但我从技术角度把它指称为“分离”。
我一直有个愿望,想要讲清楚这个类似于蒸馏实验的情状。我读李亮的散文《方位解》《银色交响》《门》《沙漠中的自语者》《如是我闻》《小岁月》,读得很高兴,讲这个题目的兴趣大增。这个命题前人讲过多次,但我认为还不够,还可以再讲。
一个人关于文学的感觉,要在语言中获得兑现的可能性。
虽然如此,但语言和文学的发生,从来就不是自然而然的进程,而是屈指可数的重大精神事件。很显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对于一个精神觉醒的人,在语言中寻找并建立文学的言说途径将会伴随他的一生。
这就需要开掘一条通向语言的道路。而文学,只是道路两侧的风景而已。
对李亮这样的文学写作者来说,语言的产生,和人的主体性的产生是一回事。
李亮散文的唯一主题,就是她自身莫可名状的心灵向往。像《银色交响》《方位解》《火车向着秋天开去》《如是我闻》这几个作品,都具有这种自我书写带来的优势。关于自我的沉思,是文学和语言渐渐合拢的征兆之一。
语言中的“我”,是李亮经常运用的神话思维倾力塑造的形象,也是此间的唯一形象。她似乎总是把自己置于一个远古的创世情境中,置于史无前例的烟云样的寂寞中。她用于创造的事物,并非河边的粘土和肉身上附赘的肋骨,而是最初的语言,是那不能发声的心灵——那时,它仅仅是她脚下大地上一条无限可能的小路,是她内心里一个小小的裂缝——语言和人,互为太极,互为环形视野中黑与白的风景。当李亮作为写作中的人介入语言领域后,“存在”问题便发生了。在她的作品中,有了讴歌,有了牺牲,有了蕴含神性的追思。有了逼近真理的人(他被称为“上帝”),有了虚伪的人子(他被唤作“基督”),有了压抑自我的人(他被写成“牧羊人”)。有了河流和被它冲刷的水车,有了山脉和草原以及被它养育的贵族、贫民,有了城市及其不断膨胀的肠胃。有了公交车和它派生的现代秩序。有了诗之外的事物。
诗的心灵,把诗和它之外的事物熔铸到一起。事物是诗的花纹和材质。
李亮散文的诗性,是她实现艺术分离的首要条件。
伴随这些事件的发生,也就有了文学语言的命名。
文学语言的发生,对李亮这样身临其境的文学写作者(她是作为语言发声必须借助的一种特殊器皿而现身)而言并非轻而易举,远不像我们平时认为的那样。一个善于说话的人,并不必然就是文学写作者。写作者的第一要义是冒险家。写作者寻求一个通道,一道狭窄的门,从那里(而且只能从那里)切入现实世界竭力压制的部分。这让她看似一个打破禁忌的言说者,她说出不被允许说出的一些秘密。在那个无疑是迷雾重重的黑暗地带,写作者发现了自身的孤独,而这种孤独引领她发光。她的语言,成为照耀黑暗中黯哑无声的事物的一种机制。
于是,语言转化且变形为一个特殊的文学事件,即写作。写作是语言事件发生后所能传导到的末端,是这一巨大事件的尾音。现代写作,将不得不是一项溯流而上的事业。这就是我所说的逆向写作,像是逆水行驶的孤舟。这舟船的指向,并非遥不可及的传统,而是它身后无尽到来的未来。这勇敢的人,把全部勇气用来逃离。她对目标的抵达,也就是对那个沉入黑夜的身后事物的回望。而回望,现在成为一种照亮过往的方式。
作为一个现代写作者,李亮不得不分化为无数属于过去时代的形象碎片。李亮语言意识足够敏锐的艺术世界,总是呈现出一种旧金属的光泽。这种光泽,只属于李亮这个心领神会、思骋八极的人,一个与语言展开对话的人。
找到语言的时机,比记录、写出语言说出的内容更重要。
李亮的语言发生,是诗的,而且只能是诗的。作为一个觉醒的现代写作者,李亮永远在写一首古老的诗。它具有过去一个旧时代全部应有的琐碎记忆,以及那种记忆反射出的奇特光泽。假如说文学语言的掌握是要进入“分离”过程,那么,李亮就是这样“分离”的:她从现世分离出一个底片泛黄的时代,并使自己成为开向那个时代的一扇窗子。通过那扇窗子,过去的风雨、烟雾、河流、山峰渐渐浮现出来,过去的寒冷、炎热、四季轮回、宿命感一一浮现出来,过去遗忘的故乡和关于它的故事浮现出来。和这种故事化的记忆不断对抗,是写作者建立主体的需要,也是她所掌握的语言意味深长的本性。在这一对抗过程里,写作者笔下的世界缓缓脱离尘世,而且,进入一首诗沉思的况味。
现代写作者负有一个很大使命,就是重新面对故乡发言。在中国,这可以说是一个掌握文学语言的人身上体现出的特殊历史现象。我想,这个情况在世界范围里绝对算得上是很罕见的。作为一个精神范畴,“故乡”是中国古典诗意的结构力量,而现在则是中国式现代性的一部分。
所谓“中国式现代性”,就是指背叛式的认同、回望式的姿态、对立式的和解等内在矛盾的抵牾或化解过程及在这一过程里主体的人与客体世界实现对话的结构性空间。
“故乡”是李亮这样的中国现代写作者内在精神结构的象征物,是他们最终必然要面对的终极话题,是一个源源不断展开在空白中的文本,也是这个文本加诸现实的命名策略,是写作者永恒不变的想象兴趣,是他们“且听下文分解”的信心和具体智慧。
“除了儿时在村里生活的记忆之外,我竟对其他事物——诸如一根柳椽所显示出来的生活经验与智慧从未注意并在意过。……同时,我也在明白了这根柳椽默默向我暗示的瞬间,看到更多村庄身体内部的秘密迅急汇聚在这道拱门那边,它们浩大繁杂,像被一个突然闯进它们世界中的孩子吓了一跳,先是惊惶地聚集在一起,继而开始窃窃私语,我看到它们开合的口型却听不到它们的言语——它们又开始逐渐缓缓向着四面八方离散而去了,我听到它们离去的脚步霍霍有声并渐行渐远。我呆立在门的这边,像惊醒了它们之后想惊喜地告诉它们自己是谁却又看到它们全部快速离去的那个孩子,心里充满了委屈与不甘。”(《门》)
在李亮的这篇短文里,对来自故乡的一根柳椽的命名,始于一种失语。失语状态是她展开命名的开始,比如《沙漠中的自语者》以飞鸟的命运来命名女人,《银色交响》以交响曲来命名母女之间秘密传承的归宿感,《火车向着秋天开去》以火车来命名隆隆行驶的生活进程,都源自“充满了委屈与不甘”的突然彻悟与“听不到它们的言语”的记忆判断。关于故乡的体认,直接呈现了李亮文本结构的也是精神结构的基本关系系统。失语后的命名冲动,维持写作继续进行。人与世界的分分合合,在“故乡”结构里得到认同和反响,得到对谈的乐趣。
李亮的文章意识很强,她清楚地明白自己是在“写”。在故乡生活和在故乡的精神包围里“写”,这肯定是两码事。在所有的结构关系中,她只分离出具有诗性的那个故乡。那是一片值得沉思、耐得住咀嚼的风景。这里发生的问题就是,她只看到了此种结构的魅力,而忽略了它的危险因素,她获得了沉浸其间的感动,而忽视了那种诗意结构的虚幻特性。
“故乡”结构对深具诗意的写作具有一种根本性。它既是结构世界的方针,也是瓦解这一结构的渊薮。当古典时代逐渐退隐的时候,它遗留下来的这个根本性结构却成为中国现代写作的基本原则。与这一结构原则发生冲突的事物,都站在“中国式现代性”这一想象前景的侧面,置身于浓厚的阴影中,是一个写作者最为沉默的不能发声的部分,同时也构成现代写作者深感畏惧、无法下笔的边界。如果要从整体上反思中国一百余年来的现代写作,那么我们可以说它依然有一种来自天性的根深蒂固的压抑感。我们在现代写作这一活力充沛的活动里并非一边倒地全部感受为自由的愉悦,也有迷惑和困顿,有无法说出的苦涩和悲凉感,有伟大的也是渺小的孤独,有鸡零狗碎敲敲打打的烦闷,有叮当作响的破裂和无法缝合的沟壑,有若有若无的遗弃感,有饥饿与苦寒的边塞时光。现代写作,并不引导我们自动占据本时代精神中心的位置,反倒有了更强烈的拒斥。我们关于“故乡”的言说,更多时候看似一种絮絮叨叨、无止无休的幽怨情绪,缺乏平静,缺乏柔和的喜悦,以及那种天人合一的光辉。
我们在远离故乡的时候回到那里,我们在迷离恍惚的准梦幻时刻开始写下“故乡”二字。我们结构故乡的过程,实际也是解构那种诗意向往的过程。这就是“故乡”这一文本结构在语言深处道明的意向。
“这个去往另一重世界的通道逐渐被一些碎石般繁琐的事情堵死了。曾与我一起表演过的我的伙伴们如今早已生疏不堪,他们和我一起被人情世故和命运淹没在各个角落。更多的时间,我和所有的观众一样,沉默地坐在舞台下的角落里,再在恰当的时间为舞台上的人用手掌拍击出赞美和羡慕。那些星星点点的偶尔滴落撒开在我们脸上的光,就像另一个世界穿越那些堵塞通道的碎石缝隙时的光芒。这些光芒怜惜而冰凉,带着让人绝望的浓郁的香。”(《门》)
这个阴郁而美丽的片段,是李亮作为写作者的清醒处。
她善于道出象征物具体而微的情绪,描述它们肉体的部分。而在灵魂最呻吟的端口,则透露出来自故乡的消息。这个,就是一个写作者进入并建立了“故乡”结构的最好注解。在经历危机四伏的背叛后,故乡与它的写作者握手言和。
面对故乡,重新发言,这就是李亮散文艺术的结构辩证法。
文学语言的文学性,不表现于内容为何,而表现于编制内容的形式感。促使形式得以成立的即是说话人的腔调,即语调的高低、轻重、缓急、流畅与滞涩、亢奋与平和、精确与模糊、雅致与粗糙、尖刻与柔顺等等极微小的区别。这个区别,一般是很难觉察,但对于写作的人又必须有所把握。稍有差池的语感,就让写作者如坐针毡。别人不必准确的种种枝节,在这里却必须交代得分毫不差。
文学性的欠缺,不是词汇不足,而是对词汇的感知能力不足。
一个词语和另一个词语有着全然不同的色调,传达着迥然有异的表情质量。怎样说出那种特定的表情,总是令人犯难。躲避词语的召唤是全然无能的表现,是才华匮乏与心灵枯竭的表征。写作者总是会有选择地使用一些词语,从而构成他的写作基础。这些词语里包含的情味他心知肚明,而且能够主动赋予它们新增加进去的思维成分。文学的思维力量,体现为这些词汇合奏出的大致统一的语调,一条近乎于音乐调性的波浪线。一个作家的思想,不是僵死的尸骸一样的结构图,而是词语系统富有魅惑力地辐射出的生命感受,读者从中得到的也将是一种具体的带有风格烙印的语感。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语感,是说出事物的特定语调。强有力的语调,和小溪一样淙淙流淌的声调显然具有不同的美的感觉。能否调整不同词语的发声比例,使之融汇在美的名义下,是一个作家进入文学殿堂的衡量标志。
李亮的散文,还在不同声调之间徘徊,还有犹豫不决的时候。《方位解》和《如是我闻》在语言的调性上显然不是那么统一,而《小岁月》肯定不如《银色交响》那么畅通和令人愉快。
“外爷不爱说话,夜饭时他的影子巨人般可怕地在一侧墙上晃动。他让我上到炕上去吃饭,他说吃了饭就到了明天,到了明天,你妈就回来了。”(《小岁月·1》)
“一块钱在公社旁的豆厂能买到多半桶看起来油光闪闪闻起来喷香的豆渣。能吃上如此美味的小黑猪真幸福,它享有两三天花一块钱的特权。而我们,一礼拜最多也就能奢侈地吃根冰棍儿。冰棍儿一根一毛钱。捱到卖冰棍的即将回家时可以用一毛钱买到两根或三根,这得依照残货的大小体积而定。这些最后的冰棍儿既没有正价时令人激动的白色冷气,也没有了那可以在牙齿间嘎嘣作响的脆感。”(《小岁月·2》)
这两段文字有一种令人难受的做作,好像是作者咬着牙写出来的。“夜饭”、“特权”、“残货”、“脆感”这样笨拙的词汇,对李亮来说过于坚硬了。那种字里行间拥堵着的半是夸张的矫情很难理解,为什么非得这么折磨自己呢?只有一个解释,这是未能找到那个统一的语调而又要“做文章”时必然会有的线疙瘩,把明丽珍贵的记忆给缠在里边,如同蚕要做茧蛾要扑火那一瞬间的惊慌。
这种过于琐碎的毛病,是连文章圣手张爱玲都犯过的。
在李亮通向语言的道路上,还有需要清理的沙砾和必得克服的障碍。
李亮的散文语言富有节奏。这种节奏是一种S形的周折,具有舞蹈的外观和赏心悦目的氛围,恰如山涧石缝的溪流,在它可以触及之处便停下来瞻望一番,迫不及待地要和沿途的草木、山光、云影、鸟兽尽数嬉戏一场。她开发了一项可称为“停顿”的文章技术,而且运用起来得心应手。
在她这里,节奏不是“前进”的艺术,而“停顿”却是。
停顿是心灵的憩息状态,犹如花鸟画里飞鸟的姿态。那花和鸟尽可以随风飘摇,但置身于画中却有运动着的静态,是动极而趋向于静的境界,是人类渴望抚慰的心灵某一瞬间倏忽迸发出的绮思异象。李亮长期从事绘画的经历,显然影响到她对文字的直观感受。她对文字的判决,是以动与静作为选取标准的。
她显然更倾向于停顿下来的事物,而且并不掩饰这种美术家才有的喜好。
她的文字之美,在于强烈的雕塑感。这些雕塑的排列方式也是美的,呈现为弯弯的灵巧的曲线,而不是直通主题。表面上看起来,她的文章是无主题的变奏,只有略带悲凉感的美可以配得上这种独特的节奏感。独特的心灵,需要足够独特的心灵表现,一朵暗褐色的饰以金边的云彩就是这种美感的对应物。
那朵云彩,擦着一座黛青色的山峰,映照出北方地带那些令人难忘的文学风景:沙漠、飞鹰、歌唱中的芨芨草,以及她目光所及的故乡。
广阔而盛大的故乡,开放在永恒的梦里。那注定是她童年时就屡屡梦见的一个世界图景。
她在写作中的漫长跋涉,最终是要接近那个清晰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