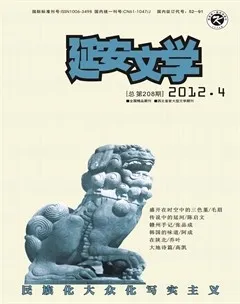跟着感觉走
我以前并不认识李亮,听朋友们说过几次,听名字好像是位男人。可是,当我见到后却吓了一跳,原来是位亭亭玉立的大美女!我问她,你怎起这样一个男性化的名字?这个名字太有力量感了。她答:这是父母起的,一直就这样叫。我想,在陕北农村给孩子起名字并没有太多的文化含量与美学追求,名字只是个符号。陕北农村人认为孩子要贱养,一般给孩子一些既好叫,又具有泥土味的名字,如“满囤”、“满仓”与“二妮”、“三女”之类的名字。当然,在起名字的过程中,也会添加一些心理期盼。这样,我猜想是“李亮”的父母之所以要让女孩叫“李亮”,就是期望这个本身是女孩子的孩子应该是个男孩子,或者是想在这个女孩子的后面生出个男孩来的……
我在好奇李亮的名字之时,走进她用文字所精心建构的童心世界。这些天阅读了她近年来创作的散文作品后,更惊诧于她的文学感觉与精彩的语言表达,感觉到她是“跟着感觉走”,活在感觉里,她从本真上应该属于精巧与灵动的烟雨江南,而非深沉厚重的苍凉陕北。因为,她写作的路数与一般作者不同:一是,她由于受过很好的美术训练——上过延安师范学校的美术班,也在西安美术学院进修过,有很好的视觉捕捉能力与瞬间转化成形象的能力,她的文字中表现出的不单单是诗性的内涵,更具有弥漫的复合式的画面凝固能力。因此,她的语言是灵动的与新鲜的。二是她的散文文本似乎较少地受到文学理论与传统散文技法的影响,往往表现出随心所欲与自由飞扬的一面,往往是“以心写境”,强调感觉的作用,具有“新感觉散文”的特征。因此,对于她的散文判定,不能简单用传统抒情散文“借景抒情”与“托物言志”的模式来概括,而必须换种思维方式。
李亮散文书写视角独特,她的散文大都是以其自身的女性视角或成长的儿童视角切入,来构织其散文文本。从2007年以来,她先后在国内权威的散文期刊《散文》杂志上连续发表诸如《一朵花,两朵花,三朵花》《浴女》《小城物事》《银色交响》《青梅》《野孩子》《月光啊月光》《屋顶》等八九篇散文作品,另外还在《十月》《美文》《延河》等刊物发表多篇散文,并被《散文选刊》选载。这对于著名散文家来说也是十分难得的成绩,更何况李亮是一位刚刚绽放美丽的青春女性呢!我的感觉,她散文书写题材范围相对较为简单而透明,大都以其视力与身体所及来展开的,审美意象大都琐碎。如《小城物事》的审美对象细小而琐碎,书写“绣花鞋”、“虎头帽”、“我,女儿,和小城的月亮”等,充分体现了女性的审美特点;《浴女》,是对女性身体的自我审视;《屋顶》是在现实与过去的思绪中弥漫开来的怀旧心绪;《陕北的宋词》基本上也是童年的回忆,展示几经过滤的单纯而美好的诗意意象;《陕北春雪》抒情更体现出童话视角;《小岁月》撷取了“我”童年人生的几则片段——月夜里小女孩与外婆的对话与联想,小卖部里小女孩偷吃柿饼的伎俩,采蘑菇时的感觉,上小学时的体验等。尤其是《小岁月》,以儿童的视角展示童年情趣,题材范围琐碎而细小,但真切而鲜活地刻画出一位耽于想象的小女孩的心理,颇有萧红与迟子建等人作品的味道。有文学阅读经验的人大都知道,女性视角与儿童视角是萧红与迟子建等人写作时的拿手好戏,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后花园》,以及迟子建的《原始风景》《白银那》等等。这些作品展示了童心的纯与真、善与美,童趣盎然,令人印象深刻。
就审美对象而言,任何作家都有一个从自身经验出发而认知世界的过程,李亮也不例外。就她新近写作的散文而言,题材空间开始增大了,而不是拘泥于原先狭小的童年体认与身体经验的天地。如系列散文《如是我闻》,把审美的触角伸向“京剧、秦腔、昆曲”、“钟”、“笛”、“手风琴”、“箫”、“蝉”等与声音相关的舞台剧、乐器与昆虫上,用女性的直觉来审视这些拥有生命灵性的事物。作者在不经意间,随意地拎起一连串似乎随意而却十分熨帖的感觉,令人不得不感叹她的才气。李亮言:“北,南,西,东。人有时只能像飞鸟一样从上空掠过,并记忆瞬间的风向。”其系列散文《方位解》是关于“东、南、西、北”的琐碎感觉与记忆而沉淀下来形成的文字。这组文章的肺活量明显增大,但底子还是李亮的,其文字仍是诗性的、透明的与感觉的。再如《戈壁中的自语者》,状物的对象伸展到了茫茫戈壁滩,这说明她行走的空间范围加大了。而《门》的意象具有复合性,它既是记忆之门,也是情感之门,把作者对土地与城市的交缠情感通过细腻的感觉体现出来。
在文学作品中,散文对语言的要求极高。感觉再好的散文倘若没有语言的支撑,就是一个空中楼阁般的幻影。可以这样说,散文的成功首先是语言的成功。我在前面说李亮善用女性视角与儿童视角来写作,这是通过语言来呈现出来的。受过严格美术训练的李亮懂得如何把内心世界涌动的内在情感用带有丰富视觉触角的语言固化下来。我们不妨抄录一些她散文的语言片段来一探究竟。
“柳树们则是另一番景象。它们多状如从地底努力擎张而出的粗糙手掌,手指分开,只从指尖抽生出柔韧向上的柳枝来。此刻,每只手掌里都小心翼翼地捧了一窝雪,如同终于迎来等待已久的爱人映下轻柔一吻,它们就那样沉浸着,任这雪之吻把柳条儿变得柔润。”(《陕北春雪》)
“可火一会儿又高兴了,它呜呜地吹起了口哨,让火苗恣意发芽生长壮大,直至最后结出彤红透亮的火籽儿。经常有树枝在完全燃烧了之后仍保持着它本来的形状,甚至连枝节疤痕都未曾有丝毫改变。它们狂热地把自己炼成一种晶莹通透的红,以这样的颜色和状态新生了一次。这简直是在变魔术。可最后,魔法失效,它们的光彩慢慢黯淡,最终沉没在灶膛中变作黑暗的一部分。那一段灶膛那样死黑沉寂,就像逐步来到的夜,不知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哪里结束。”(《小岁月》)
“陕北的柳树大多呈蘑菇状,圆而低矮。当山上尚有存雪时,便见它们枝头蕴藏了远观才有的一种暗红色,蓄势待发的感觉。这让我在寒冷中想到受了风寒的美人鼻尖上透着的那抹红色。一旦春意滚滚时,也必定又是它们最早显现着蓬勃,青绿了根根向上的枝条,抽吐了新芽,剪裁出狭长优美的叶片。”(《陕北的宋词》)
“这些朴素的瓦片屋顶,很多人都应该储存着与之相关的记忆。——下雪了时它们就穿上蓬松的花边衣裳,下雨时就淅淅沥沥笃笃咚咚为人们弹奏,消雪时总垂挂出童话般剔透闪亮的冰凌……”(《屋顶》)
“记得第一次行走在南方的天空下时,雨水如预料中一般丰沛地密洒而下。伸手接住一粒雨珠,它绵软轻巧地在掌心碎成一朵水花,竟带着微温——仿若有纤巧的南方女子轻启朱唇与过客打了声招呼。雨声浸泡出大片的寂静与儒雅,一时,眼观心见均是深浅不一的绿,丝丝缕缕,团团和和,微妙地衔接着,一个空灵的梦境般,几乎要漂浮摇曳起来了。”(《方位解•雨》)
“昆曲要温柔贴心一些。像自然界中一些植物色彩的混合。扎染过却没有任何具体图案的棉布般,只深浅不一的绿或玫红,一片松软梦境中的团团光晕。棉布总会让人心中泛起一丝温柔清新的缠绵感。昆曲宜一个人或两个人听。”(《如是我闻•昆曲》)
“笛是山中鸟,善鸣清平调。它从某些生活的角落中,带着惬意,把嫩笋般的声音一节节向着明丽的天空拔上去。又如一支碧江中的竹篙,一点,便生出一圈圈涟漪来……涟漪是对听觉的最轻微却又恰到好处的拍击……如生活中的资深按摩师。”(《方位解•笛》)
“那辽阔的地面上正汩汩流动着颤抖而透明的热流。阳光偶尔透过云彩间的空隙漏下来铺满一面舒缓的坡地,一棵单独站立的沙柳,一座遥远的小房子,一片明亮耀眼的青草地,几头或静卧或默立的牛,在这阳光中,它们像是天地间单独突兀出来的一小块舞美背景。”(《戈壁中的自语者》)
这些语句都是我在阅读时随意勾勒下来的,像这样充盈着水分的湿漉漉的语句比比皆是。李亮的许多语句是把捕捉到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复合式地通感共振,转化成感觉化的具有穿透力的语言。这样的语言,也打破了传统谴词造句的规范,形成独特的语言张力。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言:“代客观为主观,代物象为意象;把难以言状的心理状态转化为物质的,可捉摸的生理状态。”(汪曾祺《夕阳又在西逝•序》,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有意味的是,李亮的许多散文文体杂糅,甚至拥有“跨文本”的“跨界”魅力。如《银色交响》是叙述两代女性的故事,使用第三人称“她”,而不是第一人称“我”。这篇作品善于捕捉细腻而灵动的女性感觉、女性经验,俨然是一篇“新感觉派作品”。文章的联想力异常丰富与细腻,把女性生命与成长的意象有效地化入文本。《野孩子》是讲述“我”——一位具有叛逆性格的女孩子的成长故事,反抗父亲,初恋,婚姻失败,等等。文章的起笔这样写道:“二十几年前,当父亲靠他手中的鞭子把我一步步赶回自家院子中时,我记住了离开一种既定命运的小小快感……”文章的落笔这样写道:“孩子唯一知道一点,不管哪个方向,他们的前段都是远方。”《青梅》也是篇叙事散文,讲述“我”的童年伙伴、表妹梅与眉的故事。依照作者的写作叙述方式,人们很容易认定成小说。类似这样的文本还有一些。小说与散文的最大区别在于,小说是一种“虚构性文本”,而散文只能是一种“非虚构性文本”,也就是散文中的人物、时间和事物必须遵循“真实性”原则,不能胡编乱造,这是小说与散文问题界限的篱笆。但是,话又说回来,文学文本的魅力就在于不断越轨,就在于不断翻越文体的篱笆,产生新的杂糅性文体样式。像我这样的中年人,“久在樊笼里”,已经“不得返自然”,思维也好、手脚也好,往往被诸多有形与无形的东西所捆绑。就李亮而言,她却是80后的文学写作者,她虎虎有生气,是轻装上阵者,身上没有那么多沉重的传统与历史,这给自身创作的求新求变提供了无限可能。
我有时在想,创作者好像草原上狂野不羁的野马,而批评者则似乎是挥舞着手中的长杆、始终想给前面的野马套个合适笼头的人。他气喘嘘嘘地追逐着前方奔跑的马群,可是,这一切却异常艰难,因为风向与马的速度、马的姿态等都是不断变化着的。对于李亮的批评而言,我的难度与限度同样存在。我坚信一点,即她在保持个性的同时,还会不断创作出更多具有“力量”感的散文来的。
栏目责编:魏建国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