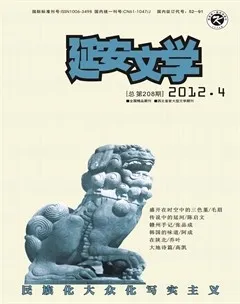赣州手记
2011年5月22日(赣州)
这一天赶去赣州参加全国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研讨会,不仅如此,我也把定点体验生活报到的日子也定在了这几天。一是省得走两趟,海南至赣南,近来没有开通直达的飞机,来去有点麻烦。二是明天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九周年的日子,多少有点纪念的意义。
初夏的天气,赣州处于赣南,夏天比江西别处来得早一点,感觉与我所处的海口气温差不多。也许这种日子让人心情都很好,章贡区区长廖长荣一定要请我吃顿饭,我也乐意前往,便把王松、高伟也叫上同去。会议期间,龙一和我住一个房间,本来我也叫了龙一的,可临了却见不着人了。《潜伏》热播后,作为原作者的龙一,走哪都被人抢了去搞“活动”,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几个就去了赣州宾馆。章贡区的同志已经将酒宴布置好了,廖长荣先生笑容满面迎接我们。我和他的相识也和文学创作有点结缘。去年,云南军区萍乡籍的老作家彭荆风带了他的女儿彭鸽子(亦是作家)一行去萍乡,想去他少年时期客居过的赣州走走,萍乡的朋友有点为他担心,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们打电话到海口找我,问赣州有无好朋友能接待一下彭荆风。我辗转找到廖长荣先生,他满口答应,后来我才知道,他任章贡区区长,把接待任务交由区接待办的同志完成。这当然让人放心,这些同志,搞接待是专业和专长,细心而周到。
据说彭荆风先生对赣州之行很满意。
这以后我和廖长荣有了来往,去年在赣南拍系列数字电影《红色行动队》,制片人和导演等主创路经赣州,来来去去都是由廖长荣他们接待的。当然没少麻烦章贡区接待办的诸位——小王主任,还有那个笑容像贴在脸上一样的一脸阳光的曾键。
这次来赣州,廖长荣立即嘱我一定要小聚。我当然很想见见他和章贡区的朋友们。
席间,说到定点体验生活的事。长荣说:你选赣南就对了。我说:我一直写这片土地,选别处也难写好。我是有红军情结的人,之所以能成作家,也许是这种情结使然。
话题很对路,朋友很对路,天气也很对路。
那天我们几个都喝高了。
2011年5月25日(宁都)
宁都这几年我来得很勤,从2008年始,我来了不下五趟了吧?此前近30多年的时间里我只回来过一趟。那是1986年,我在赣南诸县游走,当然也去过宁都。这里是我少年成长阶段度过的地方,也是我一生中经历最苦难日子的地方,当然,也是对我其后的文学创作,对我的人生影响,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的地方。
至今我母亲的坟墓还在宁都那个叫石上的地方。1968年,我随父母被下放到了那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悲从天降,我母亲病故了,那时,我父亲还关在牛棚。实际上,那时只有我和弟弟相依为命。我十一岁,弟弟不到九岁。其后,苦难伴随了我们五年,当然,大自然也随便了我们五年。虽然不能正常上学,但这个偏僻山村教会我们许多。说心里话,我很感激这片土地,感激老区纯朴的人民。我的红军情结、老区情结皆产生于此。这五年,对我一生极其重要。
同行的有高伟、王松,还有赣州文联的卜利民。王松这一年来一直在赣南深谋游走,近来写了很多红色小说。卜利民很热心地一次次陪他在各县走,这一回当然也不例外。王松想去石城走走,想了解石城保卫战的一些史实。宁都与石城相邻,也就先期来了宁都。
县委宣传部部长许勇接待了我们,听说我要来宁都定点体验生活,他很高兴。他说:《翠岗红旗》要能捣鼓拍成电视连续剧就好,你能不能为此做点事情?我笑言,还没报到就摊派任务了?其实我和许勇相识已经多年,那年我的长篇《红刃》和温燕霞的长篇《红翻天》一起在赣州开研讨会,去上犹走访时,是许勇陪同的,他那时在上犹任宣传部副部长。
去宁都,不得不去翠微峰。此前许勇提到的期望改编成电视剧的那部电影就是在此拍摄的,那部电影叫《翠岗红旗》。
这部1951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由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演员共同担当主角的故事影片,在那个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著名演员于蓝扮演的向五儿,是一个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仍保持气节的红军家属。影片所着力表现的也不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血肉拼杀,而是向五儿在逆境中坚定等待毫无音讯的丈夫、将幼儿抚养为革命后代的生活侧面。尤其是向五儿坚定信仰不变,这对当今的中国新一代,有着启迪作用。这正是该片的成功与独到之处。
这部影片曾引起周恩来总理的注意,他专门指出:《翠岗红旗》这部影片使人很受感动,有的地方催人泪下。向五儿在白色恐怖如此严重情况下,依然坚强不屈,等待红军归来,这怎么不是英雄形象呢?他还对该片主演于蓝说:“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三遍,主席很称赞,并嘱咐干部不要忘记老苏区人民。”这一讲话精神传出后,引起热烈反响。
现在近六十年过去了,作为中国首部在国际上得奖的影片,在群众中依然有着很深的印象。尤其是在屏幕被单一的歌颂领袖和军队的声音画面充斥的今天,这部影片会让我们想起主席的那句话:“不要忘记老苏区人民。”
该片曾在1952年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第7届国际电影节获摄影奖。这也是新中国电影首次获得国际大奖。
那天下午,我们几个爬上了翠微峰主峰。山势当然险峻,一路上我们爬得胆战心惊的。而我最顾虑的是下山,那几丈垂直的山体让人怯步。可到得山顶,发现有位82岁的老人竟也攀上绝顶了,下山就不再胆怯了。
这事有点怪。
2011年9月25日(信丰)
这次来是参加卜谷作品研讨会。昨天已经开过,开得很成功,赣南不缺优秀的作家,缺的是向全国推荐和介绍的好举措,这次研讨会只是第一步。
另一件重要的事是去信丰,得把中国作家协会那份公文交信丰方面。不巧的是信丰县领导都在赣州开一个重要的会,不在县里。
我的定点体验生活地点改在了信丰,其实我最初定点选定的是宁都,那儿我生活过多年,同学朋友较多,会很方便。但后来几经考虑,觉得选一个较为边缘的地区比较利于我的创作。瑞金、兴国、宁都、于都等,当年都是红色中心,一来建国六十多年来一直饱受关注,二来,清一色的“红”可能难看透当年的历史。红白相间的地方可能素材更丰富,有些东西可能更能引人深思。信丰当年就是这么个特殊的地区,有时属于白区,有时又被辟作红区。尤其三年游击时期,信丰是项英、陈毅浴血坚持的主要根据地。
这是我改来信丰定点的主要原因,当然,廖长荣同志调来此地工作也是原由之一。长荣那次长谈,就和我说到文化,提出一个地区,以经济衡量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将来是以文化拼高低。这话不错。不说将来,就是眼下,地区文化的差异已经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可持续性的发展。
一个作家,来地方上多少能带动地方文化的发展。廖长荣先生是这么看的。这种想法给我一定的压力。但我觉得既然中国作家协会很严肃地派作家下基层,无论是谁,只要迈开第一步,那就必须做工作,而且要做出业绩来。我觉得信丰这地方应该不错,就是地名也和别处不一样:人信物丰,有这两点,就够了。
那天我去了陈毅广场,陈毅同志的雕像就立在那里。雕像塑得很不错,人物的主要神态和气质尽显其间。其实,真实的历史里,项英同志在三年游击战中所立下的功劳亦是难以磨灭的,只是项英死得早,而陈毅其后成了元帅。这地位就显然不同了。在我看来,这座广场,这个地方,是应该给项英和另外一些三年游击战中浴血坚守直到取得胜利的那些同志留有一些位置的。这让我想到自己来信丰这地方所负的责任。
我很清楚,这也是我要做的重要工作之一。
2012年3月29日上午(信丰)
去新田是第二次了。
这次请了南昌大学社会管理学院的一个调研组来。一位教授带了七位研究生,可谓兵强马壮。他们要搞两项调研:一是“农村新农合”;二是“农村宗族势力和社会管理”,这也属于文化的范畴。想想,我还是强把他们拉来信丰。好在教授刘桂莉是我大学同学,我还叫她二姐,我这点面子她还是给的。
廖长荣来信丰主政,提出文化兴县的理念,并且言行一致。这很难得。现在上头提繁荣文化发展文化,各地把文化放在首位自不必说,但扎实地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的人为数不多。即使是认识到了的,也未必真心于文化。解放后,年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上头把农业看得可谓重要吧,可有的地方喊是那么喊,真抓的不多。以我所居住工作的那个省为例,农业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有关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他们一直喊着农业强省,农业是重中之重,但实际的情况是看重房地产,看重更有经济效益的旅游业。以致在那里种水果的多是台湾人,种蔬菜育稻种的多为江西人。
我到信丰时,主人告诉我,将在信丰建设的佛博园,4月1日将举办动工仪式。坐中有人戏说,张作家你和信丰还真有缘分,上次你来时佛博园的项目正处于谈判胶着阶段,谈了好长时间没谈下来,你到信丰第二天合同就签了。这回你来,却正赶上开工仪式。
他们这么说,我只笑笑。
比如与新田,比如和该镇的党委书记朱新梅,都算是有缘。
去年初到信丰时和新任的宣传部长张伟聊起信丰的红色,也说到我想要了解的信丰革命历史重大题材。张伟说到“长征第一仗”,我愕然。搞红色苏区史近三十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长征第一仗之说。有长征第一渡,长征第一关,长征第一日,长征第一村,长征第一桥,长征第一山等等,关于长征的“第一”很多很多,但此前我还没听说过长征第一仗。过去读过军事科学院编辑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那本书里说道:中央红军长征过粤北,历时18天,无战事。
没想到却是打过一仗的,没想到长征的第一仗却是在信丰境内打响的,可是关于长征的其它“第一”,解放后皆浓墨重彩,然而只长征第一仗却语焉不详。这是令我诧异和疑惑的事情。我当下决定在信丰的采访以第一仗为开始。
就这么认识了朱新梅。
红军长征开始的第一仗便是在赣南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打响的,此地也是中央红军遭遇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的地方。朱新梅是新田镇的党委书记。说起红军,朱新梅很热情,一看就是有红军情结的人。她一定要先带我去看红军标语。百石村是新田镇最偏远的一个小山村,当年红军从于都出发长征,要突破的第一道封锁线就设在这里。红军攻破封锁线后,在这一带短暂歇息,但依然不忘写标语宣传革命。这些标语虽然历经七十多年,但依然清晰,只是书写标语的老屋子都相继破旧,有的已经坍塌。对于红军标语这重要文物的保护,是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事情。
标语中有署名“红天月丙三支”的,我一直弄不清红军的这个代号。长征初期,为了长征中的指挥和安全,中革军委规定军委及各部队对外使用的代号,它们分别是:军委为“红星”,军委第一纵队为“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此多为中央首脑机关和苏维埃国家机关各部门。野战军则多以地名为代号:红一军团为“南昌”,红一、红二、红十五师依次为“广昌、建昌、都昌”;红三军团为“福州”,红四、红五、红六师依次为“赣州、苏州、汀州”;红五军团为“长安”,红十三、红三十四师依次为“永安、吉安”;红八军团为“济南”,红二十一、红二十三师依次为“定南、龙南”;红九军团为“汉口”,红三、红二十二师依次为“洛口、巴口”。但这个“红天月丙三支”,我查了很多资料,找不到具体所指。
与第一次来百石村比,这次更显殊然。也许是接近清明的缘故,也许是春来草青花绽的缘故,反正心情挺那个。同来的还有江西的几位朋友,一位年轻导演,一位《影剧新作》的主编,还有位江西高校出版社的编辑。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充满了新奇感。
洪超的烈士墓前,有人在那儿放置了一个花圈,再有几天就是清明,会有更多的人来此祭扫。洪超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十八岁就参加“八一”起义,在井岗山时期担任过朱德的警卫班长,是由朱德一手培养出来的红军最年轻的师长之一。
离烈士墓不远的旧战壕已经被清理了一遍,壕里的乱草和灌木被砍了去。我上次来,几乎看不出那儿有战壕,现在,则一目了然了。
长征第一仗没人写过,长征第一仗也有许多难解之谜。但我觉得我应该迎难而上,从中挖掘出感人至深的东西来。自去年来信丰始,我就把长征第一仗的文学作品作为我的挂点期间的重要作品来创作,前期的阅读和史料的搜集工作一直在进行,期间也多次向中国作家协会汇报进度,我很高兴中国作协的有关领导能认可我的选题并予以鼓励。
我把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暂定为《红碑》。
2012年3月29日下午(信丰)
油山我也是第二次来,上次来油山带了王松来,王松先前写知青题材什么的,自前年来赣南走了一遭后,写起了红色。他是较成熟的作家,对某种题材稍加关注,就能写出很不错的作品。事实果然如此。他写的十几个关于红军的中篇小说这两年在全国有一定影响。
油山是陈毅、项英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信丰县、大余和广东南雄3县毗邻地区,北与诸广山相连,南与九连山接壤。在其周围还与南康、赣县、龙南、全南、定南、崇义及广东仁化等县连接,群山连绵,地势险要,森林茂密,人烟稀少,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场所。1934年红军长征后,陈毅和项英领导的游击队就是以此地为中心,在其周边地方与强敌周旋。
听说我要来,镇党委书记刘贤联早早就等候了。刘书记见面一脸的笑容,说我有两件事让他“耿耿于怀”:一是说我上次来油山没吃餐饭就急急走了;二是说作家你答应来油山住些日子搞写作也没见你来呀!我也只笑笑。他很认真地说,真的,我在那边水库风景区准备了三间房哩。
刘贤联是个热情但很文人气的镇领导,很健谈。他是当地通,对当地很有感情。他说,你知道不?我和老婆的恋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年从另一个乡到这里很远,路也不好走,骑自行车要骑六七个小时,周末,我硬是骑车往返两地。我说:光这就叫任何姑娘都感动哟。
我们去的第一站又是油山镇上乐塔,那座塔据说是游击队对外联络的一个点。交通员常常将情报和药品放塔尖。爬到那地方得冒点险。游击队员身手敏捷,且不怕死,就是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亦能从容攀爬到塔顶。那座塔见证了那个年代中的那些人。然后,我们去了坑口村。那地方是陈毅伤重时养伤的地方,据说那里有个山洞,不仅隐秘,敌人不易发现,重要的是从早到晚都能晒到阳光,这对伤员身体的康复有好处。刘贤联和大家说到三老俵,这些故事我听过多次,但同来的那些大学生觉得很新奇。
这“三老俵”是指刘老俵——刘新潮,李老俵——李绪龙,朱老俵——朱赞珍。他们的故事在解放后久为留传,充满了传奇色彩,足够写好厚的一本书。
我们的车正好经过三老俵之一的朱老俵的家。刘书记说进去坐坐,我们一行便走进那家民宅。据说后来朱老俵做了副县长,他的房宅在当初应该算是不错的。朱老俵早已作古,他和他夫人的遗像挂在大堂正中。这个传奇性的人物看去很平常,其实赣南的客家人看去都很平常,但却是这些人曾经做出过轰轰烈烈的大事。没有他们,就没有共和国的今天。
2012年3月30日上午(信丰)
去古陂有点偶然。在新田午餐时,正好县武装部政委一行从古陂下乡考察回来,古陂镇党委书记李大春和镇长把他们陪送回来,午宴时也坐在席间。
有人介绍说这是古陂镇的书记,我便说很希望去古陂走走。因为长征第一仗不仅只在新田打的,古陂也是战场之一。陆定一的诗句“古陂新田打胜仗”,也是将两地连在一起说的。
听说我要写长征第一仗,李大春也很激动,一定要请我们去古陂走走。席间我喝得有点晕,连连点头。后来有人扯我衣角说,昨天廖长荣书记建议你去大塘埠看看,你昨天答应了大塘埠的书记明天上午去大塘埠的。我拍了个脑门。天!
没办法,只好给大塘埠方面电话,说因故改在下午了。
李大春弄来一辆森林公安的消防巡逻车,我心上“咯噔”了一下,这清明前后,森林消防可是一级战备的呀。但我没来得及问,一路上也插不上话。李大春真可谓能言善语,连同车的大学教授也听得入了迷,更不要说那几个研究生了。和油山的刘贤联不一样,李大春没有说古陂的红色历史,他说的是农村基层工作的一些亲身感受,有经验也有成就,有迷惘也有困惑……
李大春也没有安排我们到什么红色遗址,也没有去镇上看看。其实古陂在江西是名镇。赣南四大名镇为:一,南康的唐江;二,信丰的古陂;三,会昌筠门岭;四,于都的小溪。古陂在赣南四大名镇中排第二。
森林公安的专用车直接驶进了大山,那座山叫金盆山。现在我才知道,这辆车一车两用。一来进山巡视执行公务,二来捎上我们这些特殊“游客”揽胜观景。一举两得,乡镇干部总能把事情做得很巧妙,我这回算是领教了。
金盆山竟然有这么好的一条路,出乎大家的意料。后来知道,这有家国营林场。中途有人内急,司机开进了那家林场的分站,竟然是很美丽的一处院落,中间一株很大的桂花。林场就是林场,树木花草与别处就是不一样,不一样的还有干净的院落。李大春说:盛夏到这地方住些日子,避暑也养生,会让人长寿。我相信他的话。
汽车直开到山顶,这大概就是最高峰金盆岭的主峰了吧?那有个火警观察哨。三层的小洋楼,在屋顶能俯瞰四围的群山,视野能看到很远,何况还有望远镜。有两个男人在那里值班,据说常年守在那寂寞的山顶,他们对四下里的美景很淡漠了,更关注那台彩电里正播放的一部古装剧。突然到来的一群人,让他们生活多了几分热闹。他们似乎已经不习惯这种喧嚣,用诧异的目光看了我们好一会儿,便自顾忙着自己的事情去了。
小楼的四周都很平坦,通了电,也有自来水,但用的却是柴灶。为什么不用煤气呢?年轻的研究生大惑不解是有道理的。两个人,一瓶煤气能用上两三个月,多省事?好好的一幢小楼,就让这眼灶给弄得不伦不类了。他们当然不知道一眼灶的好处。一来,这里的拾柴成年烧不完,冬天遇冰冻雨雪,会有竹木压折断损,春里一枯,就成火灾隐患。护林员拾了烧火就减少了这种隐患。二来柴灶做的饭菜好吃,不是感觉上的,可能是物理上的。我在乡间餐馆,看见柴灶炒菜就兴奋,知道那菜必定别有一番滋味。三者,居住的人想拾柴种菜,是给自己找点事做,白天黑夜地观察,成天面对山野,很是枯燥无聊。拾柴种菜甚至养鸡,都是调节的一种手段。
果然,小楼前后种了些蔬菜。有一群鸡在远处刨食,很悠闲的样子。我在想,两个男人一定也很悠闲,不过被崇山峻岭相拥相掩,白天倒是满眼的风景如画,秀色扑面,但夜里呢?孤守荒山野林,又是怎么样的一种苦处?
看得出李大春很得意金盆山,他的“得意”是有道理的。这地方被称之为“赣南小庐山”也有其道理。竟然还真有个三叠泉,竟然还真有秀峰,竟然还有庐山和张家界都没有的仙女池。
天工造物,一条溪淌过一片石头滩,经千年万年,竟然冲刷出很多坑凹。十几个坑凹像珠串一样被水流串起,本身景致就殊然别致,何况那些坑凹被水流冲得恰到好处,形似大小不一的浴池。说是七仙女各用一个,共七处浴池,细细数来,却不下十几个。这仙女池,是金盆山独一无二的,况且此时尚未开发,纯属“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可谓出尘脱俗、天姿绝色。你再加上点仙女出浴的想象,那种感觉不是在都市繁华中所能体会到的。
我很喜欢金盆山,也很感激李大春的有心安排,但愿金盆山能成为信丰的金盆,造福于信丰人民。
2012年3月30日下午(信丰)
大塘埠镇,我初听成了大唐镇,让我想起盛世大唐来。
午饭后即去了大塘埠。午饭是在金盆山脚的一个村镇上吃的,主人弄了许多山珍。有几种别说没吃过,甚至闻所未闻。一种植物的根块竟然吃出糕点的口感和滋味。问当地人,他们只说和“奶”有关。我问是不是因其形而名,他们说不是,还说这种东西女人产后发奶最为适用。
县里因为佛博园开工,来了许多官员和记者,大塘埠的书记钟小琴被叫去搞接待,而接待我们的是镇上一位年轻的副书记。
我们在大塘埠看了一下脐橙园,应该说这没什么特色,在信丰,脐橙是主打产品,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脐橙园。不过,在信丰,大塘埠还是把脐橙文化做足了,竟然有个脐橙文化公园,石刻的画和文字很简洁地简述了脐橙在赣南的发展。
后来知道大塘埠还真始于大唐。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分南康县东西地置信丰县大塘埠镇属信丰县,明嘉靖年间为大塘铺,为古驿之一。清光绪年间改为大塘埠。民国19年(1930年)至民国22年(1933年)曾是县府所在地。民国19年(公元1939年)7月,实行乡镇制大塘乡。1984年4月改为大塘埠乡。1988年12月改为大塘埠镇。2001年5月,原坪石乡并至大塘埠镇。
一行中有人问道大塘是否也有山,主人说有个叫云台山的地方不错,值得一去。
云台山大塘埠镇樟塘村石竹坑,车子疾驰而过时看见有座中学在路边。上山的路还没有硬化,天气晴好,行走不成问题。说是山,其实与古陂看到的金盆山比,就小巫见大巫了。主人说起了云台山名的由来:云台山山顶有一座古寺——云台寺,由于云台山常年山清水秀,云雾袅绕,特别是下雨后,人在山顶有身临仙境之感,故此,一名得道高僧在山顶上建立了云台寺。该寺始建于明朝成化年间,距今有五百余年的历史。但不知道是因山名而得寺名,还是因寺名而有了山名。且不管这些,这地方有了这座山有了这座寺就有了一种文化气息。
山虽不高,但在山上能把大塘埠尽览眼底。
大塘埠的萝卜最出名,这里做的脚板萝卜远销海外。大塘埠镇的肖镇长,说起萝卜来眉飞色舞。他说: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吃我们的萝卜打败了吃巧克力的美国大兵。大约是1952年冬,信丰萝卜干运入朝鲜,为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菜肴之一。至1953年,共运去23万斤。这是史实。传说的是,朝鲜天寒地冻,人不能缺盐,战场上有时盐一时运不上去,而信丰萝卜干含盐,志愿军吃了力气就来了。对面坑道里的美国兵就不一样了,吃巧克力和压缩饼干,没盐,打仗就没力气了,必吃败仗。
不仅是萝卜干有名,抗美援朝时大塘埠还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开展了捐款购买“合作字号”飞机活动,把子弟送往前线。1950年冬,信丰全县有395名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投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次年,又有247名青年入伍。在朝鲜战斗中,信丰有67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362名官兵立功受奖。
大塘埠现在是江西28个示范镇之一,正加紧进行小城镇的建设。我站在云台山顶,看见一些年轻男女蹦跳着从那条山道上走上山来,陪同的主人说那是山下学校的老师,下了课他们喜欢结伴来登山,登山的路有人计算过,恰好符合人每天的运动量,不多也不少。这很好,那些年轻人朝气蓬勃,就跟这个叫大塘埠的地方一样。
很多地方都有山起名叫云台,以河南焦作云台山最为有名。我就想,要是我,就将大塘埠的两处地名改一下:给云台山多个提手旁,名云抬山,既不与别处的云台同名,亦别致富有诗意——云抬起的山,多好的名呀;另一处则是大塘埠,减去其土字旁,就叫大唐埠了,无论是大唐镇还是大唐埠皆振聋发聩。
责任编辑:侯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