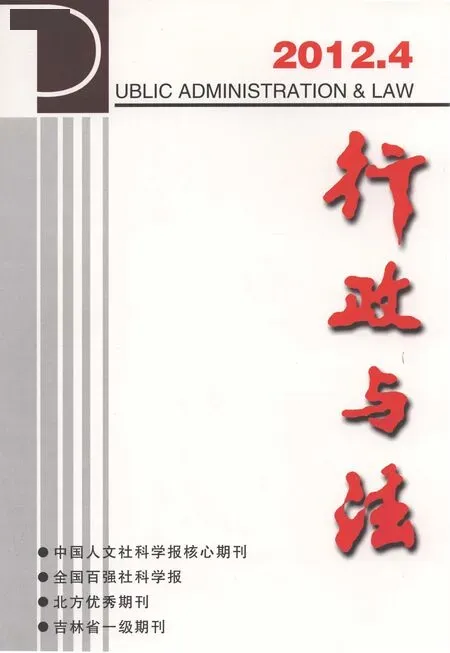结社自由的基本权利属性定位
□ 杜筠翊
(复旦大学,上海 200448)
结社自由的基本权利属性定位
□ 杜筠翊
(复旦大学,上海 200448)
结社自由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属于自由权范畴,并与其他基本自由权、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属性和内容上存在一定的交叉与竞合,因而结社自由具有复合属性之特点。从法律文本以及宪法理论考察,结社自由是一种独立的自由权类型,而非全然为表达自由或政治权利所吸收。厘清结社自由的权利属性定位,对于结社自由的实现、尤其是非政治性结社行为的保障,以及对于结社自由限制措施的合宪性审查和其他相关基本权利之法律救济均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结社自由;基本权利体系;独立性;复合属性;权利保障
结社自由是指人们为了一定的宗旨和目的自愿地结成一定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并采取团体行动的自由与权利。结社自由不仅是人在社会群体生活中所拥有的应然自由与权利,同时也是一种由法律规范所确定并保障的实然的基本权利,并已成为现代社会各国宪法理论和实践上的共识。我国《宪法》和法律对结社自由亦有规定和保障,而且目前正在对与之相关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进行修订。然而,我国宪法文本及理论中对结社自由的权利属性定位尚有不足,并影响到对结社自由的全方位保障。本文以基本权利基本类型为切入点,以多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的文本与实践为视角,指出结社自由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具有独立性和复合属性之特征。对这种独立性和复合属性的深入认识有助于加强对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权利的法律保障。
一、结社自由的自由权属性
(一)结社自由是自由权
自由权是第一代人权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其他基本权利如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的基础。自由的基本含义是指不受他人的限制和妨碍,而自由权是指个人要求他人不干预自己行为的权利。[1](p169)结社自由是不同个体在意志和行为上的社会性和群体性地结合,一方面作为人之为人、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所应有的基本自由,另一方面具有消极自由——即不受国家和他人强迫与干涉的特征,因而符合自由权的一般属性要求。此外,从多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文本中基本权利体系安排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结社自由亦作为自由权来加以保障。
多数现代国家宪法文本和国际人权公约已就基本权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结社自由在内的基本权利系统化地成为宪法和公约文本组成部分。德国《基本法》中的基本权利体系采取“独立列举”立法模式,第9条“结社自由”被安排在第8条“集会自由”和第10条“邮政和电信秘密”之间。《日本国宪法》与之相似,其第21条规定“结社之自由保障之”,而第20、22条则分别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和迁徙自由。以体系解释之方法,可以认为德日两国宪法均将结社自由归于自由权范畴。美国宪法文本中虽未直接规定结社自由,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58年“NAACP v.Alabama”案[2]中以宪法第1和第14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推导出“结社自由”,所以在美国宪法中结社自由亦属自由权当无疑问。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基本权利体系采取“分类”立法模式。该公约核心的第三部分规定了一系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除第三部分第25条特别规定了“政治权利”、第26条规定了“平等权”,第三部分其余条款均是涉及各项自由权的规定。第22条规定了“结社和工会自由”,而其前后两条分别是“集会自由”和“婚姻与家庭”。《欧洲人权公约》第一部分为“权利与自由”,其中第11条“集会和结社自由”位于第10条“表达自由”和第12条“婚姻权”之间。《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在文本上更是明确区分了基本权利体系下的自由权和公民权利。其第二部分规定了“自由”,而在第五部分规定 “公民权利”(包括选举与被选举权等在内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而第二部分“自由”第12条规定了“集会和结社自由”。以文本解释和体系解释方法,可以认为上述各公约均将“结社自由”归为自由权之列,自由权是结社自由的首要和主要的属性。
(二)结社自由与其他基本自由权的关系
结社自由作为自由权,就其内容和实现方式会与其他一些基本自由权产生交叉和竞合,可能会导致对结社自由的属性及其独立性产生混淆和模糊。
⒈结社自由与表达自由。我国不少学者将结社自由归于自由权类下的精神自由项下的表达自由。通过对表达自由的研究,有学者将结社自由作为表达自由的一种形态,或是将结社自由视为表达自由的外延之一。[3](p215)而美国学者埃默森亦认为,表达自由是一组权利,“它还顺理成章地包括集会的权利和结社的权利,也就是团结他人共同表达的权利”。[4](p13)而我国学者侯健在深入研究表达自由时则较为严格地区分了结社自由和表达自由,并认为表达自由不包括结社自由。他指出,“结社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增强人们在公共论坛上的表达能力,也可能是其他,例如交友、内部交流、共同行动,等等,不一而足。社团的活动既包括言论表达活动,也包括其他性质的活动。”至于美国宪法实践中从表达自由推演出结社自由,他认为,“在有的国家中,宪法和法律没有规定结社自由,这种自由只好从表达自由条款中引申出来。这是一种特殊情况。”[5](p14)进而他得出结论性判断——“结社自由是与表达自由相竞合的另一种自由形式”。“表达自由与结社自由有竞合的地方。社团享有结社自由,结社自由自然包括开展活动和以社团名义发表言论的自由,而社团同时也是表达自由的权利主体。社团进行言论表达活动,既可以援引表达自由也可以援引结社自由来辩护。表达自由也意味着可以设立一定的组织机构以表达和传播某种观念。”[6](p15-16)笔者认为,除了社团之外,当个人组建、加入或退出社团并在其间发表言论,同样会产生结社自由与表达自由的竞合。尽管结社自由与表达自由可能会、事实上经常会发生权利竞合,但是结社自由仍然应当属于独立于表达自由之外的基本自由权。
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宪法判例中结社自由源于表达自由,但是在判例法中还是对两者进行了区分。在著名的“Roberts v.United Stated Jaycees”案[7]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布伦南大法官区分了“亲密性结社自由”和“表达性结社自由”。前者以个人纽带来分享理念,具有小型和选择性特点;后者则是为了行使言论、情愿或宗教自由而结社的权利。而奥康纳大法官进一步区分了“商业性结社权利”和“表达性结社权利”,两者在宪法保障标准和强度上有所区别,前者只能获得最低程度的宪法性保护。[8](p1399-1340)可见,在美国宪法判例中,结社自由并非完全属于表达自由范畴,而是有其相对的对立性。
在“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v.Moreno”一案[9]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强调,为社会、政治、种族或宗教目的选择和其他人结社是联邦宪法机构中的一项基本选择。联合起来是表达了一种在美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结社自由这一权利。美国学者拉吉认为,道格拉斯法官的“表达了结社自由这一权利”的提法与“通过结社进行表达的权利”这一传统提法,有很大的区别:在后者,结社受到保护只是因为其和表达自由有关;在前者,结社本身,不管其存在的理由如何,在联邦宪法上被赋予一种明确的承认。这一区别的重要意义在于,新提法着重的不是结社的表达性质,而是结社的群体性质。拉吉进而强调,结社的基本价值在于,它使个人通过群体的努力,实现单凭个人努力无法实现的目标。这一基本价值使结社不全然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表达。如果不对结社自由这一权利的性质有新的定位,非表达性的结社行动就可能得不到宪法保护。确认结社自由的独立权利地位,才能保障非表达性的社团活动得到宪法保护,以免个人在日益工业化的社会里显得孤立无助。[10](p559-560)
在《欧洲人权公约》的司法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同样认为结社自由是一项独立的基本权利,“与表达自由一样是民主社会中个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并且是构成民主社会的支柱之一”,保护个人观点也是保护结社自由的目的之一。但是,如果权利主体认为其信息和思想交流的自由受到干预时,法院应适用有关思想自由条款的特别规定,而不应适用结社自由的条款。[11](p276)
综合上述学者分析、文本和司法实践,应当承认结社自由是一种类型化的独立的权利。尽管结社自由与表达自由在行使方式上存在着交叉和重叠部分,可能发生竞合关系,但是只有强调结社自由在自由权类型中的独立性,才能防止结社自由尤其是非表达性结社自由被表达自由所吸收。而当两种自由权发生竞合时,可以依照行使目的确定独立适用结社自由规范,或者与表达自由规范共同适用。
⒉结社自由与宗教自由。依据上述的分析方法,可以发现结社自由与宗教自由也会在宗教结社领域产生交集地带和竞合关系。鉴于宗教结社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内心信仰和宗教行为自由的实现,因此,各国在法律上普遍将宗教结社排除在结社一般法或社团一般法的规范之外。德国《结社法》第2条关于“社团的定义”中,第2款明确规定“各种宗教组织和社团”不属于本法所称的社团。俄罗斯《社会团体法》第2条亦明确将宗教组织排除在该法适用范围之外。日本《促进特定非营利活动法》第2条第2款第2项规定,该法所适用的“特定非营利组织”的活动目的“并非为了宣传宗教信仰、举办仪式或者发展信徒。”在美国,虽然《非营利法人示范法》(1987年)第1.80条规定了宗教法人,以及《统一非法人非营利社团法》(1996年)序言规定该法适用于教会,但这仅是两部示范法,并没有真正的法律效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部示范法属于私法,规定的是宗教团体的私法人格与法律地位问题。在 《非营利法人示范法》中亦援引联邦宪法和/或各州宪法,要求宗教法人之教义受限于联邦宪法和各州宪法。因此,当发生结社自由与宗教自由竞合情况,也主要适用宪法上的宗教自由及其特别法之规定。
⒊结社自由与集会自由。集会自由是指公民或个人聚集在一定场所讨论问题、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自由。结社自由与集会自由具有显著的共同点,即都表现为人的聚合。但是两者的差异也是明显的。第一,集会往往是临时性和短时性的,集会结束人群即散去;而结社是长期性、持续性的。第二,集会的参与者通常是不特定的;而个人一旦加入社团则成为特定成员。第三,集会的目的主要在于表达意见;而结社的目的呈现多样性,并以成员利益或其他特定主体利益的实现为主要目的。第四,集会所形成的多数人群体并不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法律地位;而结社所形成的社团具有独立性、自主性,能够享有法律人格和法律地位。
结社自由与集会自由的竞合主要发生于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社团组织成员以集会方式开展活动。第二种情况是,社团以独立法律人格与其他主体共同参加集会活动。对于前者,可以同时适用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两种法律规范;对于后者,则主要适用集会自由之法律规范。
二、结社自由的政治权利属性
政治权利是指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从而在政治生活领域作为自决、自主的存在的权利。从政治权利所表达的基本功能来看,各国宪法文本所规定的政治权利可以概括为:⑴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决定权,主要包括公决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及担任公职的权利;⑵发表政治见解以及从事政治性活动的自由权利;⑶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权,主要指请愿权;⑷某些国家(如土耳其)宪法规定的“公民资格的取得与保护”也属于政治权利。[12](p88-90)多数国家将“发表政治见解以及从事政治性活动的自由权利”列为政治权利,这其中通常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
我国1954年《宪法》第87条、1975年《宪法》第28条、1978年《宪法》第45条,以及现行1982年《宪法》第35条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虽然我国现行《宪法》只是在第34条规定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时规定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权权利的人除外”,在其他《宪法》条文中并未明确“政治权利”的内容和范围,但是现行《刑法》第54条规定 “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其中第(二)项包括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由此可见,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文本上结社自由属于政治权利范围。
对于结社自由与政治权利的关系,国际人权法专家诺瓦克首先对“政治自由”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权利”进行了区分。他在解读《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给该公约第25条设置了独立的标题“政治权利”,[13](p429)尽管该公约正式文本中并无“政治权利”的标题。该条规定了公民享有参与公共事务、选举与被选举、平等参与本国公务的权利。诺瓦克指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权利仅指第25条所列举的权利。只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以及选举权和平等参加公务的权利才完全具有民主参与的性质。”同时“(公约)包含了许多对于民主决策过程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其他权利。这些政治自由——意见自由、表达自由、信息自由、媒体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至少在其公共功能上也可以(在广义上)被理解为政治权利。”之后,诺瓦克又分析了两者的差别。“对这些交流沟通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并不仅仅出于民主这一公共利益,而且还出于形成自已的意见、传播消息或成立社团这些私人的、非政治性的利益。”由此,他得出结论:“将这些权利看作是处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交叉地带也许更为恰当。”[14](p430-431)鉴于结社自由具备政治自由和非政治自由的双重属性和功能,《欧盟基本权利宪章》明确地将结社自由规定在第二部分“自由”之中,而在第五部分规定了以政治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公民权利”。
笔者认为,结社自由的自由权属性是首要的,其与政治权利的联系可以从结社自由的行使目的和方式上加以区别对待。非政治性目的的结社属于结社自由而非政治权利之行使,主要适用关于结社或社团的一般法。对于以政治参与为目的、以政治活动为方式的结社,则属于结社自由和政治权利双重权利之行使,基于公共利益维护的需要以及政治活动的特殊性,应当主要适用有关政治权利、政治活动和政党的特别法。例如,德国《结社法》第2条第2款规定,该法不适用于⑴《基本法》第21条里的政党;⑵德国联邦议会和各州议会里的党团。俄罗斯《社会团体法》第4条规定,包括政党在内的独立型的社会团体的成立、维持、改组和解散可由依照该法通过的各种特别法来调整。日本《促进特定非营利活动法》第2条第2款第2项规定,该法所适用的“特定非营利组织”的活动目的不包括为了宣传、支持或反对某个政治理论,也不包括为了提名、支持或反对准备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或可能候选人)、正担任公职的人或政党。
三、结社自由的社会权利属性
在人权理论发展史上,第一代人权以自由权和政治权利为核心内容,第二代人权则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为核心。尽管一般认为,第一代人权具有更多的消极自由与权利的特征,第二代人权具有更显著的积极自由与权利的特点,但是两代人权彼此之间充满着更多的依存和整体关系。正如1966年联合国大会制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序言所宣称的,“按照世界人权宣言,只有在创造了使人可以享有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正如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一样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
作为第二代人权的广义社会权利包括经济权利、狭义的社会权利以及文化权利,结社自由与之都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叠关系。工会是一种特殊的结社,工会权是结社自由与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的交集产物之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第1款规定,人人享有的结社自由 “包括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其利益的权利”。工会自由与权利也是一项重要而传统的经济权利。尽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其规定在“结社自由”项下是为了强调工会自由的自由权或公民权利属性,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进一步突出了工会权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属性。该公约第8条第1款第1项明确规定,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以促进和保护他的经济和社会利益。①《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第1款规定了工会权的主要内容。包括:⑴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以促进和保护他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这个权利只受有关工会的规章的限制。⑵工会有权建立全国性的协会或联合会,有权组织或参加国际工会组织。⑶工会有权自由地进行工作。⑷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
在其他一些保障弱势或特殊群体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国际公约中同样包含着结社自由的规定,结社是实现这些经济和社会权利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如《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5条第4款第9项和第5款第2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7条第3款,《儿童权利公约》第15条,《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5条,《农业工人结社权公约》第1条,《三方协商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就业政策公约》和《劳动行政管理公约》等。[15](p167)此外,各国法律亦对结社自由与文化权利的结合地带加以规定,例如允许设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对作品及其著作权进行管理。综上可见,结社自由与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等第二代人权存在交叉关系。当结社自由与第二代人权产生权利交叉和竞合时,通常首先适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的特别法,如无特别法则可适用结社自由之一般法。
四、结社自由权利属性定位的意义
结社自由就其基本权利类型的属性而言,具有鲜明的复合属性特征。结社自由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自由权的属性,同时又可能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基本权利产生竞合。厘清结社自由的权利属性对于我国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具有积极意义和作用。
第一,结社自由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具备基础性地位和支撑作用,诸多其他基本权利能够通过结社自由的行使而得以更充分地实现。当结社自由与其他基本权利尤其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发生法律竞合时,可以先适用关于其他基本权利的特别法,当相关特别法无法适用时可以适用关于结社自由的一般法。因而,无论是从保障结社自由本身还是实现各种基本权利的全面保障,我国均有必要加快制定保障结社自由的基本法律。
第二,明确结社自由的自由权属性有利于对非政治性结社的保障。我国现行《宪法》、法律和法规中将结社自由归为政治权利范畴,而忽视了结社自由的自由权属性,这就使得大量的非政治性的结社行为和社团无法基于其自由权属性来行使结社自由,不得不依据政治权利属性来主张结社自由。而《刑法》第54条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亦会导致公民丧失非政治性的结社自由,并有可能进一步损害某些以结社自由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例如加入工会的权利、组建公益社会团体和参加文化体育组织的权利等。譬如,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第13条不仅排除了正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的个人担任社团发起人、拟任负责人的资格,而且还排除了曾经受到剥夺政治权利刑罚的个人的上述资格。正是对于结社自由权利属性的认识不充分,导致了对前述个人的结社自由的不合理限制,并且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等基本的合宪性原则。因此,相关行政法规的修订应当从结社自由的权利属性定位和一系列合宪性原则加以综合考量。
第三,厘清结社自由的权利属性对于基本权利限制措施的合宪性审查具有重要作用。现代宪法理论和实践上都肯定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同时也强调对基本权利限制进行反限制的必要性,其中,对基本权利限制措施进行合宪性审查是最为基本和重要的方式。当代两种主要的合宪性审查基准,即德国式“三层密度”合宪性审查基准(明显性审查、可支持性审查、强力的审查),以及美国式的“三重基准”(严格审查基准、中度审查基准、合理审查基准),都针对不同属性的权利类型采取了不同密度或强度的类型化审查基准。其中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通常采取低密度或低强度的审查基准;而对于基础性权利,例如与人身相关的基本权利、与民主政治有直接关联的基本权利,则采取高密度或高强度的审查基准,以严格保障基础性权利。[16](p37,84)就结社自由限制措施的合宪性审查而言,当其发生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竞合时,可以采取低密度或中度的审查基准;而当其与其他自由权(如表达自由)、政治权利(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或其他基础性权利(如生存权、人格尊严)产生竞合时,则应当采取高密度或严格审查基准,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结社自由以及相关的基础性权利。
第四,结社自由可以充分发挥对其他基本权利的救济渠道作用。结社自由能够为其他基本权利提供法律救济途径。人权法和宪法理论一般认为,以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为核心的第二代人权主要表现为积极权利,即要求国家采取积极措施来保障和促进这些权利的实现。但是在公法上尤其是针对国家义务和责任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直接可诉性就显得较为薄弱,这就使得此类权利无法得到有效和充分的法律救济。而结社自由作为自由权,其可诉性和法律救济方式在各主要国际人权公约、各国宪法和法律上都得到充分承认和规定。因而,当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与结社自由发生竞合时,以结社自由受损害而提出诉讼、主张法律救济就成为一种较为有效的途径和方式,从而实现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障。
[1]徐显明.人权法原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2]NAACP v.Alabama,357 U.S.449(1958).
[3]韩大元主编.宪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我国其他诸多学者的相同或相似观点可另参见姜明安主编.公法理论研究与公法教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7,151.
[4]Thomas I.Emerson:The System ofFreedom ofExpression,New York: Random House,Inc.,1970,p3.转引自侯健.表达自由的法理[M].上海三联书店,2007.
[5][6]侯健.表达自由的法理[M].上海三联书店,2007.
[7]Roberts v.United Stated Jaycees,468 U.S.609(1984).
[8]See Gerald Gunther,Kathleen M.Sullivan:ConstitutionalLaw,New York: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97.
[9]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v.Moreno,413 U.S.541(1973).
[10]Reena Raggi:An Independent Right to Freedom of Association,Harvard Civil Rights-Civil Liberties Law Review,1977,Vol.12,pp2-4,pp9-17.转引自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陈欣新.结社自由的司法保障[J].环球法律评论,2004,秋季号.
[12]秦奥蕾.基本权利体系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13][14](奥)诺瓦克.民权公约评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M].毕小青,孙世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5]周少青.中国的结社权问题及其解决:一种法治化的路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16]何永红.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审查:以审查基准及其类型化为焦点[M].法律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张雅光)
Properties of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Du Yunyi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in the system of fundamental rights belongs to the type and area of freedom.There is a cross and overlap on the content of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other basic freedoms and political,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So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has the compound characteristic.From the legal texts and constitutional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is the freedom of an independent type,rather than completely absorbed by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or political rights.To clarify the properties of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has an important and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reedom,especially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non-political association,as well as for constitutional review of the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and legal remedy of other basic rights.
freedom of association;system of fundamental rights;independence;compound characteristic;rights protection
D921
A
1007-8207(2012)04-0081-05
2012-03-05
杜筠翊 (1973—),男,上海人,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同济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比较宪法、法制史。
本文系同济大学文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结社自由法律保护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701219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