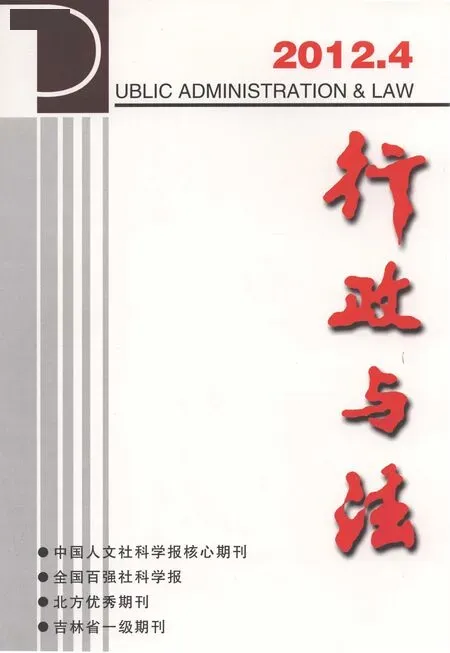未来的国际法实施:从强制执行到遵守管理
□ 潘德勇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未来的国际法实施:从强制执行到遵守管理
□ 潘德勇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20世纪以前,国际法以强制执行为主要实施方式。因缺乏强制执行手段,国际法的法律属性因而受到广泛质疑。20世纪后半期以来,国际法在规范结构和实施机制上有了较大发展。在某些领域,国际法规范开始由消极性规定转向积极性规定,而国际法的实施机制也由传统的自愿遵守和强制执行转向报告监督、帮助激励等遵守机制建设上。国际立法正在经历由权利体系的立法到救济管理的立法转变的过程。
国际法实施;强制执行;遵守管理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国际法以及其他国际规范性文件急剧膨胀,国际法的结构也呈现出质的飞跃。然而这种变化并未受到国际法学者的关注。主流的国际法理论仍然以传统国家间的战争、军事、外交等为主要适用场景。经济、社会、人权等领域国际法规范和体制的发展,并未被置于一般国际法理论体系中加以研究。
一、国际法的实施:强制执行与非强制执行
执行是英美国际法学界关于国际法实施问题最常用的术语。[1](p13)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 执行是“强迫遵守(法律等)的行为或程序”。[2]在国内法上,法的执行在狭义上通常指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不涉及法律适用活动。因此,普遍接受的观点似乎是,执行是由外在的力量(警察、军队、政府部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
国际法的执行在一般意义上指强制执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国际法被认为由于缺乏一般性的强制执行机制而不具有法律属性,或只是“弱法”。长期以来,国际法学者为了反驳这种观点,提出国际法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主张,他们认为,自卫、反措施、集体制裁是强制执行的形式。这种观点是基于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不同而提出的。国际社会不存在类似于国内社会的行政机构和警察系统,因而缺乏有组织的制裁机制,不存在一般性的执行,强制执行仅针对特别重大的违法事件,例如战争、恐怖主义等。然而,国际法具有强制执行力才能被实施的主张,只论证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未能注意到国际法执行制度具有特殊性的另一方面。
首先,并非所有的国际法规则都需要以强制执行为后盾,这与国内法规则相同。虽然几乎所有的国内法规则都有强制力作为最终保障,但对于大多数的规则而言是不必要的。日常性的国际法规则一般都能得到国家的自愿遵守,因而强制执行措施在通常情形下是不需要采取的。
其次,二战以来,国际法的执行出现了新的趋势。在新兴的国际法领域,如国际贸易、国际环境法等,以国际组织和国内行政机构为执行主体的执行模式开始盛行,并有向其他一些国际法领域扩散的趋势。其特点是:该领域内的国际法规则通常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国际义务或条约目标的实现方式,并规定由专门的机构予以执行。例如,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政策评审机制”规定,在贸易政策评审机构的组织下,定期对成员的贸易政策和实践及其对多边贸易体制功能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再如,国际环境条约中的“报告机制”要求,缔约方应将履行公约而采取的措施以及履行效果等定期向条约全体成员或组织提供。这些执行模式是整个国际法履行机制的一部分。与传统的强制执行方式不同,新的执行方式将国际法的目标进行量化,不依赖于一次性地强制成员遵守,而是强调对条约履行的各个环节积极介入,对执行过程进行全盘管理,从履行的最初环节一直到最后遵守,随时对成员方可能发生的违反行为进行纠正。世界银行副总裁依布拉希姆·沙哈塔在分析国际环境条约的实施、执行和遵守时指出,这种执行方式是一种“组织程度较低的执行方式”。①“执行这一概念较具限制性,通常指在国际义务没有得到实际履行的情况下,由有权机构共同或单独采取措施,以确保国际义务得到尊重。然而,在国际环境法文献中,组织程度较低的执行方式(如检查和监督) 也包括在这个术语内。Ibrahim F.I.Shihata,Implementation,Enforcement,and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practical suggestions in light of the World bank’s experience,Goergetown Internation 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Vol.9,1996,p.37.
然而,长期以来,国际法在这一层面的执行并未引起学者的重视。但事实上,很多国际法学者都认为执行一词具有两种含义:强制措施和非强制措施。②温树彬博士在其专著《国际法强制执行问题研究》中详细介绍了“强制执行”、“执行”在中外国际法学者著述中的含义。指出单就“执行”一词,需要在具体语句中去判断是否包含强制性措施。温树彬.国际法强制执行问题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1-18.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和对和平的向往,强制执行在战争时期以及冷战时期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而在和平与合作时期,非强制性执行措施在管制性的条约履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确切地说,这种执行方式更类似于一种组织或管理方式。它是强制执行的替代。有学者称之为“软执行”。[3]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问题对于国际法的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传统国际法的关注在于国际法的强制执行,现代国际法则侧重于研究国际法的非强制性执行措施。非强制性执行措施将重点放在国家的自愿遵守上,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非强制执行措施的发展也是遵守机制的发展。
二、非强制执行的规范性条件:从消极性义务到积极性义务
国际法规范与其功能的实现紧密相关。国际法的功能是调整国际关系。从国际法的性质和功能可以看出,国际法既是“规范秩序”,也是“社会组织的要素”,且两者相互依存。国际法作为规范秩序的产生是由于履行特定职能的需要;而能否实际履行则依赖于规范质量的提高。简言之,国际法律秩序能否实现其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规范的质量。没有高质量的法律规范,国际法的功能发挥将受影响。[4]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分支,其规范具有一般法律规范的特点。国际法规范依其义务性质的不同,也可以分为命令性规范(必须做)、禁止性规范(不得做)、允许性规范(可以做)。然而,由于国际社会的结构因素使国际法呈现出规范结构发展不完善的特点。巴黎第二大学国际法教授普劳斯伯·威尔指出,国际法存在结构性的缺陷。这种结构性缺陷不仅表现为制裁机制的不充分,而且体现在其多数规范的平淡无奇上。在特定领域,国际法甚至呈现空白,无任何规范。在另一些领域,规则的实际内容太过于争议,以至于无法有效地调整国家行为。而在某些领域,规范仍停留在抽象的、一般的阶段,需要国际法的缓慢发展才能赋予其具体内容和准确含义。[5]
哈特也认为,国际法律秩序是简单社会结构的典型体现。其仅包含首要规范。因为其缺少集权式的立法机构,有强制管辖权的法律体系以及有组织的执行方式。因此,还没有形成可以确认、发展国际法规则,或是检验其他所有规则有效性的次要规则。因此,国际法规则并没有构成一个“体系”,而仅是“一套规则”。[6](p228-233)
毫无疑问,哈特和威尔关于国际法规范的认识都是建立在将国际法作为一个规范整体进行认识的基础上得出的。实际上,在个别领域,国际法规范结构同传统国际法规范相比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国际法规范的行为模式结构复杂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威尔教授所提出的“规范仍停留在抽象、一般的阶段”不能作为对国际法规范的一般看法。在贸易、环境保护、人权、海洋法等领域,尤其是在贸易领域,规范对于事实和行为的规定已经相当系统全面,例如,GATT关于要求缔约方不得对进口产品实施数量限制的规定,不仅明确规定了限制的类型,而且考虑到在特殊情形下进行限制的需要又规定了六项例外。作为首要规则,此类规则在当代国际立法中非常普遍。其特点是通过在立法环节将所规范的行为可能涉及到的各种情形都考虑进去,一方面可以尽可能地确保规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司法的自由裁量对规范的客观性造成影响。规范的行为模式由简单到复杂的转变是立法技术的提高,反映了立法者对于规范要适用的事实的认识深入而具体。这一做法实际上来源于国内立法实践,以欧美国家为典型。因此,哈特所提出的首要规则具有的不确定性的缺点在一些 “政治性程度”较低的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克服。
其次,国际法的责任机制与裁判机制正逐渐形成。哈特所提出的“国际法规则并没有构成一个体系”的看法也是不充分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教授奥斯卡·沙赫特尔曾提出,国际法不仅存在首要规则和次要规则,而且还有第三类规则。国际法的首要规则是确定行为合法与否以及义务内容的规则;次要规则是确定违反行为存在及其法律后果的规则;第三类规则是关于义务的实施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法律后果的规则。不过,沙赫特尔认为这些规则并非在同一法律规范或法律部门中同时存在。首要的规则存在于任何实体法领域;次要规则构成国际责任法,适用于国际法行为,而不论其产生何处;第三类规则是关于义务的实施,包括处理国际诉讼的规则和实践、争端解决程序,国际仲裁庭以及其他机构的管辖、执行和制裁。[7]这些领域都是在二战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尽管关于国家责任和国际争端解决的制度并非适用于一切国际法领域,但在特定领域,国家对其认同的加强以及机制效力的增强,无疑也是国际法规则“体系化”的一种方向或形式。
最后,国际法规范的义务积极化日益明显,并由管制性条约向双边条约渗透。国际义务的积极化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一发展是与国际关系的发展主题紧密相连的。传统上,国际法以禁止性和消极性义务为主要内容,国家在对外关系中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不得”实施侵略行为,“不得”干涉他国内政,“放弃”对不正当利益或法律所禁止的利益追求。即便是在贸易等管制性条约中,国家的义务也至多以“配合”性为补充。而在上世纪末期,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人权保护等领域,国家根据国际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不再是“不作为”义务,而是被要求积极地作为。在这些领域,国际义务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国家是否履行了其国际义务,最终取决于国内的政府机构、商业组织、甚至个人。例如,在国家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如果一国根据《知识产权协定》承担了对他国企业或个人知识产权保护的义务,则这种保护已经不再限于司法救济,即:国家通过立法、行政或司法机构对争议中的权利进行确认并给予救济,要求国家对本国企业、国民侵犯另一国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积极地管理和惩治。并且,这一义务也不是停留在抽象的一般性规定的层面,而是在条约中规定具体的实施机制,如机构设立、信息收集和报告、监督检查机制等。在环境领域,义务积极化也表现为一系列的机制建设,如协商、公共参与、项目建设和研究等,也表现为国家通过“积极行为”控制国内污染。例如,国际环境条约是国家之间的协议,尽管其义务也是施加于国家的,如在特定时期内消减30%的SO2排放。但是,协议真正的目的不是影响国家行为,而是调整排放SO2的非国家主体的行为,如发电厂、汽车使用人等。[8]值得注意的是,在21世纪以来,一些国家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对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进行规定,从而将国际义务积极化由多边层面推向较为激进的双边层面。①这主要是由于当多边谈判遇到僵局时,一些国家寻求在双边层面突破谈判,或是谋求区域性利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双边条约中将其在多边谈判中关于知识产权、环境、劳工等高水平的标准规定其中,而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可能无法做出更好的选择,只能被动接受。从长远看,这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
三、非强制执行的制度保障:国际法遵守机制的发展
法律的发展并非在所有领域都齐头并进,一些领域的法律规范发展得较快,而在另一些领域,规范仍因各种原因保留其原始性或不确定性。试图对所有领域的规范都得出同一结论,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正如马尔科姆.N.肖教授指出:“国际社会的发展以及对不同文化和传统进行认可的需要,导致了普遍性的衰落,从而突显出侧重特定问题的具体场景的必要。[9](p62)
法律具有适应性与稳定性的特点。即便是现在,也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具有较明显的“命令”加“制裁”的特征。对各种社会关系设置不同的调控力度的需要,决定了法律规范的弹性。如果将法律的功能设置为长久地确认权利或事实,法律的调整对象是静态的物或权利,则简单而明确的权利义务的规定足矣。例如,在国内法有关财产权、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在国际法关于国家在地域界限(领土、海洋)的权利的规定。然而,如果法律被作为一种长期的管理和规范体制,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动态的行为,则不仅要明确权利,规定救济途径,而且需要实施机制。例如,在国内法关于金融监管的规定;在国际法上关于贸易政策的规定。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在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都面临着政府低效或是政府失灵的问题。对于国内社会而言,腐败、社会治安、失业、野蛮执法等社会黑暗面通过网络被迅速扩大,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持续降低。近几年,日本首相的任期都不足一年,充分暴露出政府在国内社会治理方面面临的问题。而埃及、利比亚的局势演变之快大有苏东剧变重演之势。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在警惕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对于国际社会而言,9.11、美伊之战、空袭利比亚、朝核问题等无不反映出国际社会在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上的不足之处。在网络与通讯时代,无政府状态正在以新形式侵蚀着国内和国际主权。这些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涉及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管理者的重新定位以及管理方式的转变。在国际社会,管理者包括国际组织和条约机制,管理方式主要是国际法。管理方式的转变即法律调整手段的转变。
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以及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可知,法律在现代社会已经偏重于社会治理的属性。如果基本权利只是受到偶尔的侵犯,司法救济可能是有效的。然而,当侵犯具有长期性,则司法救济就显现出不足。因此,即便是一些传统的私法领域,在近年来也呈现出很强的公法化趋势。其原因是,当权利的反复侵犯使单独的司法救济低效时,制度性的行政救济是必然的选择。②例如,在国内社会,如果宪法、财产法等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如物权)在受到经常性的侵犯时(例如强制拆迁),尽管《物权法》等法律赋予了公民基本财产权,但司法救济途径远不及公众舆论。这就表明,该权利的实施效果需要通过行政方式予以强化。在国际社会,一些领域的国际合作是以成员遵守国际法为前提的,法律所担负的职能主要不在于对违反行为施加制裁,或是对受害者进行救济,而在于维护体制的正常运行。在这些领域,国际法的实施制度获得了较大发展,从而有效促进了国家对国际法的遵守。
奥斯卡·沙赫特尔提出了六种遵守和执行国际法的方式:⑴报告监督机制;⑵帮助激励机制;⑶惩罚机制;⑷非军事行动;⑸军事行动;⑹司法执行。[10]查伊斯在《新主权》提到了报告和数据收集机制、检查和监督机制、能力建设机制、争端解决机制、政策评审和评估机制等“管理”机制。[11]就这些机制存在及运行的领域而言,通常在环境、人权、知识产权等公约中。许多环境条约包含了实施和遵守审查机制,这些机制通常包括定期收集相关信息(经常是政府部门自我报告),履行审查以及根据新信息调整机制义务的程序等。很多环境条约设有持续性的履行评估机制,如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机构包括实施委员会、不遵守程序、发展中国家成员多边基金以及各种专家评估组,通过创设这些机制,实现对复杂的规制性义务的遵守的管理。人权条约也采用了类似的评估机制,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将其功能界定为“帮助成员国履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的义务,使其可以获得委员会在检查其他报告中得出的经验,以及与成员国讨论与公约中规定的权利行使有关的各种问题”。[12]这些审查机制,以其非对抗式和前瞻式的方法,在集中监督和促进履行方面发挥作用,因而处于管理理论的中心位置。[13]
四、国际法的新发展:从权利体系到救济机制
几乎大多数法律的演进都是非激进的,总在不经意间。从人类社会的历史维度看,从古代法到现代法的转变,是人类社会从身份到契约、从等级依附到自由民主的明显转折。然而,在特定时期,法律是否取得较大的发展,却总是能引起学者的注意。
对于国内法而言,法律的发展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现代、由自力救济向公力救济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规则的演进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而法律功能的转变也与社会发展保持着高度一致。国家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所担负的职能因而也随之变化。在法律产生的早期,习惯或国家制定的法律主要以“定分止争”为主要目的,确认权利从而维护社会秩序是立法的主要任务,19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大民法典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其中包含了该特定时期法律的基本功能。进入20世纪以来,科技进步导致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形成,公共领域逐渐成为国家事务的重心。经济、行政、邮政、通讯、公路、气象、医院、教育、社会保障等在国家事务中的位置愈来愈突出。经济与行政领域的立法与民事立法并驾齐驱,自由与干预的手段并重。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公共领域的事务持续增多,国家对该领域的管理和立法继续加强,另一方面,对于私人领域,此前的“自治”式立法逐渐呈现出问题,以“权利”为中心的立法普遍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由此,国家对平等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积极干预成为新时期立法的发展趋势,私法的公法化倾向已经越来越明显。其与之前的立法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同,突出的表现是在同一法律部门中,公私法出现交融的现象。而不是各行其是,重叠调整。国内法规范内部的执行机制在一些领域已经初现端倪。
对于国际法而言,从近代国际法产生到现在,虽然发展时间不过四百年,但国际法制度也经历了与国内法类似的发展历程。只不过由于国际社会的特殊性,国际法规范发展的程度相比国内法要缓慢一些,而且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法律形式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从习惯、双边条约、多边条约、管制性条约的转变。早期的国际法以习惯和基本原则为主,这些规范确立了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对国际交往的规则做了最基本的规定。在国际法产生的初期,国家利益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军事为主的安全方面。后来,随着各国及其人民交往的频繁,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逐渐由政治和军事职能扩展至经济和社会领域,通过双边条约的方式来规定彼此之间在领土、外交、司法、通商、侨民保护等事项,在18、19世纪以来成为欧洲国家通行的做法。在这一时期,国际法基本上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19世纪末期以来,一些重大事项需要多国共同参与或协调彼此立场,多边条约逐渐被用于战争、争端解决、国际组织与国际机构等领域,国际法独立于各国外交政策的“本体性”特征开始显现。20世纪中期以后,国家利益由抽象到具体,由政治到经济、社会,由特定阶层利益到多数群体,具体表现为国家安全、公民权利、商业团体利益等。国际法一方面在编纂中逐渐完善传统制度,一方面在经济与社会领域迅速发展出以管制性条约为特征的国际规范。这些条约在聚合国家利益、凝结国际社会多元结构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20世纪末期至今,国际社会面临来自各个领域的挑战,改革传统国际法制度的呼声持续高涨,诸如恐怖主义、海盗、全球环境等国际性问题对国际法提出更高的要求,国际法作为国际社会治理工具的属性日益体现。
由此可见,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在现代社会,仅有完善的“权利”体系是不够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如欲发挥其预定功能,不能仅依赖于外在的“救济”机制,还要依靠内设的“实施”机制。
五、结论
国际法仍处于发展过程中。哈特称国际法为“原始法”。显然,这一提法在有意无意地类比国内法,不符合国际法的特殊属性。并且,当代国际法在很多领域的纵深发展已经形成较为系统的法律体系,这使国际法成为调整和塑造国际关系的重要工具。经历近四百年的发展,今日之国际法已经从关于正义战争学说的探索,走向谋求国际社会合作发展之路。
任何制度都要经过产生、发展到相对完善的过程。权利确认——认定违法——提供救济这一过程是法制完善的必经阶段。为适应社会关系,法律的制定通常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置于社会慢慢检验,一蹴而就极有可能脱离社会实际。在制度发展的早期,是权利义务确认的阶段,通常在基本法律中规定某项权利受法律保护。在确定权利的另一方面是认定违法。现代科技在缩小人与人之间距离的同时,也使得人们之间的冲突和摩擦不断加剧,社会形态愈加复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在这种情形下,立法仅仅确定权利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各式各样的违法形式进行规定,由此导致在上世纪开始法律已朝行为规范复杂化方向发展了。
救济制度的充分发展是法制进步的标志。然而,它却不是法制进程的终点。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而救济制度的功能也在于惩罚违法行为。但救济制度本身只是事后救济,无法事前阻止违法的发生。因而,有效地预防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管理,避免造成损害就成为法制进程的下一个目标。这一目标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而且对于国际社会同样适用。
对于国际法而言,救济制度严格来说并未形成高度发展的状态。由于国际社会缺乏执行机构、司法机构的特点,救济制度很难完善发展。尽管强制性的外在机构未能充分发展,但在一些领域,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对国家行为的管理已形成系统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既包括正式的条约和习惯,也表现为大量的程序性文件和实施性制度。其中大多数以“软法”的形式出现。这些软法在国际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正逐渐增强,并因国际组织的经常实践而由“软法”规则逐渐转化为“硬法”或习惯法。
美国国际法协会首任主席艾利胡·鲁特曾说,“对国家行为积极管制的加强,是这个时代政治运动的标志,它使每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能对其国际权利和义务有正确的理解变得愈来愈重要。”这一特点在20世纪后半期,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领域管制性条约的不断增多而逐渐为人们深刻感知。然而,值得国际法学者注意的是,国家行为管制的工具已经由传统的条约和习惯,转向更广泛的国际规范,其中,程序性规范在近年来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
[1]温树彬.国际法强制执行问题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2]布莱克法律词典(第八版)[M].2004.
[3]吉田.条约的软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不遵守程序和国际机构间的运行[J].科罗拉多国际环境法律和政策杂志,1999,第10卷:95-141.
[4][5]普罗斯伯·威尔.国际法走向相对规范化[J].美国国际法杂志,1983,(03):413-414.
[6]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7]奥斯卡·萨赫特尔.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M].马蒂努斯·尼约夫出版社,1991.
[8]罗伯特·基欧汉.承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M].手稿,1993.1-49.艾伯兰·齐亚斯,安东尼亚·汉德勒·齐亚斯.论遵守[J].国际组织,1993,(02):193.
[9]马尔科姆.N.肖.国际法(第五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奥斯卡·萨赫特尔.论联合国法[J].美国国际法杂志,1994,第88卷:9-16.
[11]艾伯兰·齐亚斯,安东尼亚·汉德勒·齐亚斯.新主权:国际管制性协定的遵守[M].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
[12]联合国大会人权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40条下的工作[R].UN Doc A/48/40 ,1993.
[13]卡尔·劳斯提亚拉,安妮·斯劳特.国际法、国际关系与遵守[A].载沃尔特等主编.国际关系手册[M].塞奇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徐 虹)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to Enforce Compliance with Management
Pan Deyong
Before 20th century,enforcement is the main method of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 law.Due to the lack of powerful means,international law has been disputed of its legal character.From late 20th century,international law has evolved greatly in norms structure and mechanism of implementation.In some area,negative norms turns to positive ones,mechanism of implementation thus go from enforcement to compliance mechanism.International law has undergone the process of right legislation to remedy legislation.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enforcement;compliance management
D990
A
1007-8207(2012)04-0115-05
2011-12-31
潘德勇 (1978—),男,辽宁庄河人,湖北经济学院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