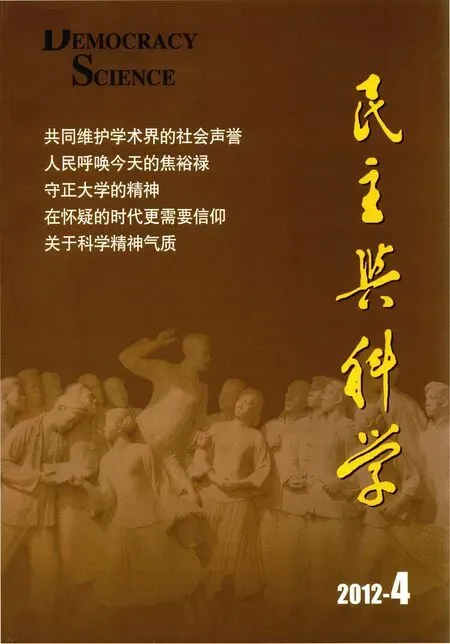大学人的饭碗与转向
■孙传钊
大学人的饭碗与转向
■孙传钊
贝尔托·博比奥的《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中文版(陈高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问世了。博比奥这本书出版时,意大利国家政治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时期——全国大选前夕,东欧解体、冷战结束后,意大利政坛正在发生巨变变化:意共势力日益衰微导致与意共曾多少结成过同盟的1940年代参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老一辈主流左翼政治家,与他们生理的衰老一样,影响力也日趋低下。相反,意大利学界的历史修正主义抬头,政界极右翼的新纳粹主义政党兴盛起来。当时意大利左翼学人为此忧虑,把这种政治现状叫做“反法西斯者的危机”。这种担忧不是杞人忧天,1994年大选结果是中右的力量党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eo Berlusconi)组阁,与新纳粹党的民族联盟(Alleanza Nazionale)联合执政。博比奥在这本书中力图说明:在左翼政治势力走向衰弱的时代,今后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是否还要划分左与右?划分左、右的标准是什么?“左”的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博比奥本人不久前(1992年)遭遇一件很难堪的事情。他年轻时参加“自由与正义”反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运动,1935年26岁时,被法西斯秘密警察逮捕,逮捕后给墨索里尼写的一封效忠信偶然被发现。博比奥出于恐惧,为了保住自己大学教师的饭碗,信中向墨索里尼保证“自己将有坚定政治立场、拥有成熟的法西斯者的信念”。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此信的暴露,博比奥个人声誉大受损伤,他不仅是著名学者、上议院终生议员,而且更是因为是反法西斯主义老战士、在抵抗组织“自由与正义”基础上组成的行动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国民心目中德高望重;更重要的问题是,尽管80多岁的博比奥事发后对自己半个世纪前的失足作了沉痛、深刻反省(可以参见1996年出版的他的遗著《论老年》),他的名誉受损,给当时老一辈反法西斯战士正在政界影响力衰退势头,雪上添霜。同属左翼阵营后辈鲁扎托(Sergio Luzzatto)10多年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封讨厌的信件,26岁虽说年轻,但他也已经完全是成人了。尽管这是意大利历史暗处的一件小事,可也是不容争辩的证据。”(《反法西斯的危机》,日文版,第71页)但是,鲁扎托还是为博比奥辩解:他之所以变节,“不仅说明反法西斯者的软弱,更说明法西斯的残忍。……是乔凡尼·杰恩提尔(Giovanni Gentile,意大利著名新康德主义派哲学家、墨索里尼政权教育部长,直至1943年,还参与墨索里尼在德军庇护下成立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府,1944年被反法西斯游击队暗杀——引用者)在四年前开了先例:他在1931年强制意大利全国大学教员向法西斯政权集体公开效忠宣誓,全意大利总共1200名大学教员中只有12个人拒绝宣誓,这是意大利知识分子普遍追随权力的耻辱的证据,而今天却有人要对这位哲学家(杰恩提尔)作重新评价”。鲁扎托还认为:博比奥为了保住大学饭碗,“只是宗教改革时代以来,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知识自由换取俸禄已经成为普遍的事情,并不是新鲜的证据”。(第72~73页)鲁扎托的这一句辩词并不算太勉强。因为民主、和谐的社会中的大学教师有时也只能以知识换取俸禄。
极权主义体制下,大学里发生的事情却是大同小异。洛维特在《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12月)这部回忆录中生动地记录了1933年前后,他熟识的德国知识阶层、众多的大学人对纳粹“革命”的广泛共鸣和支持,只有个别人进行微弱的、却是难能可贵的抵制。1933年纳粹“革命”之后,洛维特几乎失去了他原先学术圈内所有的友人,包括最亲近的友人贝塞勒、老师海德格尔及其弟子们,人们像避开瘟疫那样远离带有犹太人烙印的洛维特。即使流亡在日本时,他也时刻感觉到纳粹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压力无所不在。绝大多数在日本的德国人都小心翼翼地迎合纳粹的反犹思潮。就连1937年来日本作学术演讲的斯普兰格(Eduard Sprager)也一反纳粹取得政权后不久与柏林大学校长科劳施、心理学家苛勒公开宣布与新体制的教育“告别”那样强硬的反纳粹立场。在东京的演讲,斯普兰格似乎“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代表”。他只能私下对洛维特诉说自己如何受到纳粹当局的密谋和暗算的折磨,描绘德国大学的沉沦。洛维特把斯普兰格行为作为德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典型,做了如是批评:
他是一个德国人,必须在德国生活下去,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能接受,……所以放下他的顾忌,把自己投身于一件任务之中,并将之视为一种爱国者的义务,……于是便跟大家一起扛起一件恶劣之事的责任,……没有人愿意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做得很好的工作。(《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第140页)
“不愿意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很好的工作”的大学人,不一定就放弃良知。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名声之所以战后60余年中不断被英雄化、神圣化,除了他的著作和学术影响外,很大部分源自他生涯最后的英雄义举。1942年起积极投身于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6月被盖世太保逮捕,与其他19名战士遭受酷刑后被枪杀。但是,布洛赫真正豁出去全力参加抵抗运动,也是在1942年11月德军占领了维希政府管辖的地域之后,因为他是犹太人,按照维希政府种族法,他失去了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之职。之后,申请转往蒙贝里亚大学执教也未能如愿以偿。他不得不“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很好的工作”——本来他要献身于历史学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20世纪是一些急骤转型国家、动乱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转向的世纪。与德国、意大利一样,日本的众多知识分子在20世纪也经历了让人眼花缭乱的转向。这种思想和信仰的改变,被称作“转向”。
鹤见俊辅的关于“转向”研究,把昭和年间频频出现知识分子“转向”,分成三个高潮时期。第一次“转向”潮头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政党内阁成为军队的附庸,国家权力强化对共产主义信仰者镇压,另一方面又采取怀柔策略,对变节、转向的知识分子给与生活、职业上的出路——使他们作为顺从的国民,回归社会生活。特别是1933年佐野学、锅山贞亲声明脱离共产党后,左翼激进知识分子纷纷“转向”。具体的理由大致有:1.回归传统,转向民族主义(佐野学、锅山贞亲、林房雄等);2.自己的激进的理想脱离庶民现实生活,理论与实践相分离(德永直、太宰治等);3.厌恶左派内部宗派分裂(妹尾义郎、大宅壮一、三木清等);4.认识到左翼运动集体主义的弱点,批判的主体依存于传统的个人(植谷雄高、荒正人等)。第二次高潮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家权力对左翼的镇压扩大到禁止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1938年议会通过国家总动员法案,1940年大政翼赞会的国民重组运动,使得日本微弱的自由主义者群体几近绝迹。1937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是自由主义者纷纷“转向”的高峰期。这一风潮中“转向”的著名的学者还可以列举出清水几太郎、大熊信行、田边元等人。第三次高潮是战后,又分两阶段。第一阶段,1940年代末美国占领军主持的民主改革,日本进入了“新社会”,不少当年屈服于军国主义、超国家主义的文人墨客又纷纷紧跟时代潮流,“转向”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追求进步起来了。第二阶段是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代初美国对日本政策的转变-——对日共政策的转变,导致1952年日共内部宗派公开分裂,影响整个知识分子左翼,左翼出现大分裂过程中,不少人从共产党内“转向”出来。所以,也就在当时,日本学术界、知识界部分人对眼前这个知识分子新的纷纷“转向”现象产生兴趣,甚至感到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思想史就是一部“转向”史。
50多年前,鹤见俊辅在《共同研究:转向》的序言中,对研究对象“转向”的主、客观根源之间关系做了精辟分析:
“转向”其实有时与“思想发展”、“成长”、“成熟”是同一个意思,但是,这些词在使用时都遗漏了“转向”受到权力的强制这个核心问题。相反,从“屈服”、“挫折”等词的词义中,只能看到被权力强制这个侧面,却遗漏了思想者本人自发性的侧面。而“转向”这个词包含了强制和自发性两个侧面。没有其他词儿能同时反映这两个侧面的微妙关系。……强制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在共同研究对强制作十分广义的理解,不仅指暴力强制(监狱、判刑、拷问),还包括物质利诱、媒体宣传等间接强制。虽然可以说没有权力的强制就不会有个人思想的变化,自发思想变化被作为一极,特定权力强制作为另一极,但是还是可以在两者之间任何一点找到个人思想的位置,现实中发生的转向,经常同时具有自发和强制两个侧面。……比如,因为参与反对帝国主义运动被检举,不久又发表赞美满洲国建设的文章——这就可以既看作出于个人自发的言行,也可以看作是转向。自发与转向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概念。(《共同研究:转向·上》,第2~7页)
鹤见俊辅在《共同研究:转向》的序言中,还提出另一个尖锐的重要问题,当时来自权力的压力是否强大到非屈服、“转向”不可?他说:
战后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当有谁拿出关于“转向”的资料,一提出“为什么当年不得不转向?”这个问题时,那些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政治家、学者、宗教家就迫不及待出来辩解说“(转向)是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对这“为了生活”说法,有必要用“为了维持特定水平的生活”的内涵来限定。根据这个“为了维持特定生活水平”的前提,也就排除了以下六种选择的可能性:1.死亡、2.发疯或其他病态、3.流亡、4.判刑、5.转业、6.沉默。大部分日本的公共名人(public figures),对这六种选择连考虑也不曾考虑过。(《共同研究:转向·上》,第8~9页)
鹤见俊辅认为前四种选择对于人生来说,当然太残酷了,避免这样结果是人之常情,那么后两种选择怎么样呢?
转业,在昭和年代几乎没有人尝试过,也是这个阶段日本史的特征。学者必须依然当学者,政治家、评论家也是如此。与固定的身份意识、从封建社会延续下来的身份意识的存在密切相关,所以他们都拒绝转业来维持生计。这个课题值得注意,需要与欧洲、美国和中国作一比较。……沉默,……很多人就此会脱离公共生活,难以确保既有的社会地位,所以沉默对于日本的公共名人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是一个不能使得“转向”仅仅停留在内心(而必须公开的)原因。(《共同研究:转向·上》,第9页)
当年也有身不由己不得不离开大学的:1933年泷川幸辰因为批判“治安维持法”被京大解雇后,成了开业律师。日本制造出一个满洲国后,战争势态带来了的经济增长,不仅改变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老问题,即使有政治前科的知识分子已不难在转向后找到谋生饭碗。
鹤见俊辅等人关于转向的共同研究中,不是单纯分析转向者思想演变过程,不仅注意到他们遭受外来权力强制的类型和程度,还考虑到他们出身家庭、学历、成年后的职业、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方方面面的个人要因。这些要因对转向产生非常重要、直接的影响。中册收录的鹤见俊辅《翼赞运动的学问论》(《翼賛運動の学問論》)一文涉及清水几太郎当年转向及其学风转变,也是为了证明了上述个人各种要因,在一定外界条件刺激下,会诱发一种在他人看来是急骤180度转弯的思想、信仰上的“转向”。可惜,鹤见俊辅在这篇50多年前的文章中,关于清水几太郎谈得太简单了,清水几太郎这个人物可以说是昭和史上最典型的“转向”代表人物,集“转向”、“假转向”、“半转向”、“再转向”于一身,因此也是一位对其评价具有争议的知识分子。
中国读者大多只知道清水几太郎是个1950年代日本站在安保斗争前列的左翼进步文化人,和平运动的领袖、大学教授、评论家、社会学学者,殊不知清水几太郎在战争时期附和大政翼赞运动,鼓吹战争新体制下“新国民文化”建设的“转向”言行;中国读者大多也不知道1970年代末起,他从左翼岩波书店的综合性杂志《思想》、《世界》的写手,转变为右翼杂志《诸君》、《文艺春秋》的写手,晚年又在一些文章中,批判战后民主主义,发表为战前治安维持法辩护,主张日本为了强化国防甚至可以核武装等言论,从进步左派文化人的立场上又急骤向右激进“再转向”。这个“再转向”当时引起文化界、学术界、出版界很大震动。
清水几太郎在大学时代、昭和初年曾在“苏维埃之友”左翼团体学过俄文、读过布哈林的《唯物史论》,对孔德、杜威、西美尔等人思想感兴趣。1933年因为教授户田贞三不再让他当助教,不得不离开东京大学后,他靠为媒体写时评为生,最开始写的文章多是从自由主义立场批判超国家主义。近卫文 的大政翼赞运动展开不久,舆论媒体受到严格统制,清水几太郎很快顺应时势,“转向”依附国家权力。1938年至1941年为《朝日新闻》写文化专栏。1941年起到战败一直是《读卖新闻》评论委员,专写社论。
从1930、1940年代转向追随大政翼赞运动的媒体人,到1950、1960年代成为反安保条约的左翼进步文化人,1970年代末起,晚年再度向右转的社会学学者——同一个清水几太郎,几度“转向”。其信仰一生摇摆不定。
book=73,ebook=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