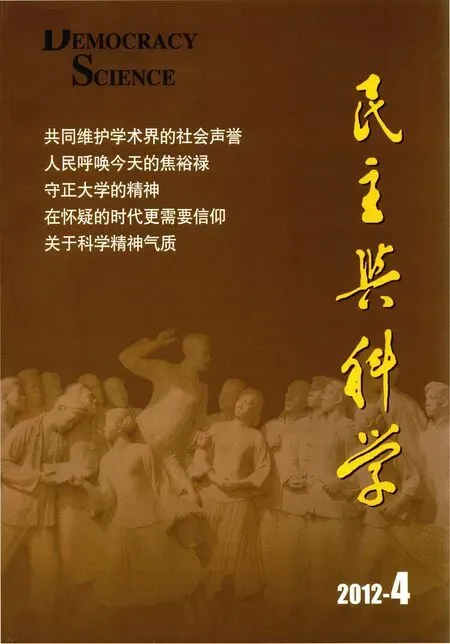成为你自己
■周国平
每个人的自我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每个人都理应在唯一的一次人生中实现这个自我的价值。谈论人生的意义,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出发点。尼采也作如是观。他强调天才在文化创造上的决定作用,那是另一个问题,与此完全不矛盾的是,他同时也确认,人与人之间在自我的唯一性、独特性价值上是平等的。在本书中,他一再指出,“每个人都是一个一次性的奇迹”,“每个人只要严格地贯彻他的唯一性,他就是美而可观的,就像大自然的每个作品一样新奇而令人难以置信,绝对不会使人厌倦”。“每个人在自身中都载负着一种具有创造力的独特性,以作为他的生存的核心”。因此,珍惜这个独特的自我,把它实现出来,是每个人的人生使命。
可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人们都在逃避自我,宁愿躲藏在习俗和舆论背后。尼采就从分析这个现象入手,他问道:“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他在世上只存在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巧合,能把如此极其纷繁的许多元素又凑到一起,组合成一个像他现在所是的个体。他明白这一点,可是他把它像亏心事一样地隐瞒着——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因为惧怕邻人,邻人要维护习俗,用习俗包裹自己”。这是怯懦,怕舆论。“然而,是什么东西迫使一个人惧怕邻人,随大流地思考和行动,而不是快快乐乐地做他自己呢?”原因之二:因为懒惰,贪图安逸,怕承担起对自己人生的责任。“人们的懒惰甚于怯懦,他们恰恰最惧怕绝对的真诚和坦白可能加于他们的负担”。二者之中,懒惰是更初始的原因,正是大多数人的懒惰造成了普遍的平庸,使得少数特立独行之人生活在人言可畏的环境中,而这便似乎使怯懦有了理由。
世上有非凡之人,也有平庸之辈,这个区别的形成即使有天赋的因素,仍不可推卸后天的责任。一个人不论天赋高低,只要能够意识到自我的独特性并勇于承担起对它的责任,就都可以活得不平庸。然而,这个责任是极其沉重的,自我的独特性上“系着一副劳苦和重任的锁链”,戴上这副锁链,“生命就丧失了一个人在年轻时对它梦想的几乎一切,包括快乐、安全、轻松、名声等等;孤独的命运便是周围人们给他的赠礼”。所以,大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宁可随大流、混日子,于是成为平庸之辈。
非凡之人为什么甘愿戴这副锁链呢?仅仅因为天赋高就愿意了吗?当然不是。尼采说:“伟人像所有小人物一样清楚,如果他循规蹈矩,得过且过,并且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他就能够生活得多么轻松,供他舒展身子的床铺会有多么柔软。”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偏要折磨自己呢?尼采的回答是,只因为他决不能容忍“人们企图在涉及他本人的事情上欺骗他”,他一定要活得明白,追问“我为何而活着”这样的根本问题,虽则这便意味着活得痛苦。
环顾周围,别人都不这样折磨自己。一方面,人们都作为大众而不是作为个人活着,“狂热地向政治舞台上演出的离奇闹剧鼓掌欢呼”。另一方面,人们都作为角色而不是作为自己活着,“戴着形形色色的面具,扮演成少年、丈夫、老翁、父亲、市民、牧师、官员、商人等等,踌躇满志地走来,一心惦记着他们同演的喜剧,从不想一想自己”。“你为何而活着?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全都会不假思索自以为是地答道:‘为了成为一个好市民,或者学者,或者官员。’”尼采刻薄地讽刺道:“然而他们是一种绝无成为另一种东西之能力的东西”;接着遗憾地问道:“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唉,为什么不是更好呢?”
尼采真正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看来,逃避自我是最大的不争,由此导致的丧失自我是最大的不幸。他斥责道:“大自然中再也没有比那种人更空虚、更野蛮的造物了,这种人逃避自己的天赋,同时却朝四面八方贪婪地窥伺……他完全是一个没有核心的空壳,一件鼓起来的着色的烂衣服,一个镶了边的幻影……”
如此作为一个空壳活着,人们真的安心吗?其实并不。现代人生活的典型特征是匆忙和热闹,恰恰暴露了内在的焦虑和空虚。人们迫不及待地把心献给国家、赚钱、交际或科学,只是为了不必再拥有它。人们热心地不动脑筋地沉湎于繁重的日常事务,超出了生活所需要的程度,因为不思考成了更大的需要。“匆忙是普遍的,因为每个人都在逃避他的自我,躲躲闪闪地隐匿这种匆忙也是普遍的,因为每个人都想装成心满意足的样子,向眼光锐利的观者隐瞒他的可怜相,人们普遍需要新的语词的闹铃,系上了这些闹铃,生活好像就有了一种节日般的热闹气氛”。
匆忙是为了掩盖焦虑,热闹是为了掩盖空虚,但欲盖弥彰。人们憎恨安静,害怕独处,无休止地用事务和交际来麻痹自己,因为一旦安静独处,耳边就会响起一个声音,搅得人心烦意乱。可是,那个声音恰恰是我们应该认真倾听的,它叮咛我们:“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所想、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这是我们的良知在呼唤,我们为什么不听从它,从虚假的生活中挣脱出来,做回真实的自己呢?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自己呢?首先要有一种觉悟,就是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这个责任只能由你自己来负,任何别人都代替不了。这个责任是你在世上最根本的责任,任何别的责任都要用它来衡量。“对于我们的人生,我们必须自己向自己负起责任;因此,我们也要充当这个人生的真正舵手,不让我们的生存等同于一个盲目的偶然”。那些妨碍我们成为自己的东西,比如习俗和舆论,我们之所以看重它们,是因为看不开。第一个看不开,是患得患失,受制于尘世的利益。可是,人终有一死,何必这么在乎。“我们对待我们的生存应当敢做敢当,勇于冒险,尤其是因为,无论情况是最坏还是最好,我们反正会失去它。为什么要执著于这一块土地,这一种职业,为什么要顺从邻人的意见呢”?第二个看不开,是眼光狭隘,受制于身处的环境。“恪守几百里外人们便不再当一回事的观点,这未免太小城镇气了”。你跳出来看,就会知道,地理的分界,民族的交战,宗教的倡导,这一切都别有原因,都不是你自己,你降生于这个地方、这个民族、这个宗教传统纯属偶然,为何要让这些对你来说偶然的东西——它们其实就是习俗和舆论——来决定你的人生呢?摆脱了这些限制,你就会获得精神上的莫大自由,明白一个道理:“谁也不能为你建造一座你必须踏着它渡过生命之河的桥,除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这么做……世上有一条唯一的路,除你之外无人能走。它通往何方?不要问,走便是了。”
我们可以不问这条路通往何方,不管通往何方,我们都愿意承担其后果,但我们不能不问:一个人怎样才算是走上了这条唯一属于他的路,成为了他自己?我们真正的自我在哪里,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它?对于这个困难的问题,尼采在本书中大致做出了两个层次上的回答。
第一个层次是经验的、教育学的,就是认识和发展自己最好的禀赋。尼采指出,一个人不可能“用最直接的方式强行下到他的本质的矿井里去”挖掘他的真正的自我,这样做不但容易使自己受伤,而且不会有结果。但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中寻找那些显示了我们的本质的证据,比如我们的友谊和敌对,阅读和笔录,记忆和遗忘,尤其是爱和珍惜。“年轻的心灵在回顾生活时不妨自问:迄今为止你真正爱过什么,什么东西曾使得你的灵魂振奋,什么东西占据过它同时又赐福予它?你不妨给自己列举这一系列受珍爱的对象,而通过其特性和顺序,它们也许就向你显示了一种法则,你的真正自我的基本法则”。
出自真心的喜爱,自发的不可遏制的兴趣,是一个人的禀赋的可靠征兆,这一点不但在教育学上是成立的,在人生道路的定向上也具有指导作用。就教育学而言,尼采附带涉及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协调全力发展独特天赋与和谐发展全部能力这两个不同的教育原则。他只指出了一个理想的方向,就是一方面使独特天赋成为一个活的强有力的中心,另一方面使其余能力成为受其支配的圆周,从而“把那个整体的人培养成一个活的运动着的太阳和行星的系统”。
第二个层次是超验的、哲学的,就是寻找和获得一个“更高的自我”。那些曾使得你的灵魂振奋和幸福的对象,所显示的其实是你的超越肉身的精神本质,它们会引导你朝你的这个真正的自我攀升。尼采说:“你的真正的本质并非深藏在你里面,而是无比地高于你,至少高于你一向看作你的自我的那种东西。”因此,我们应该“渴望超越自己,全力寻求一个尚在某处隐藏着的更高的自我”。这个“更高的自我”,超越于个体的生存,不妨说是人类生存的形而上意义在个体身上的体现。
宇宙是一个永恒生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宇宙一个小小角落的短暂时间里,世代交替,国家兴灭,观念递变。“谁把自己的生命仅仅看作一个世代、一个国家或者一门科学发展中的一个点,因而甘愿完全属于生成的过程,属于历史,他就昧然于此在(dasDasein)给他的教训,必须重新学习。这永恒的生成是一出使人忘掉自我的骗人的木偶戏,是使个人解体的真正的瓦解力量,是时间这个大儿童在我们眼前耍玩并且拿我们耍玩的永无止境的恶作剧”。用宇宙的眼光看,个人和人类的生存都是永恒生成中稍纵即逝的现象,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站在“此在”即活生生个人的立场上,我们理应拒绝做永恒生成的玩具,为个人和人类的生存寻找一种意义。
动物只知盲目地执著于生命,人不应该这样。“如果说整个自然以人为归宿,那么它是想让我们明白:为了使它从动物生活的诅咒中解脱出来,人是必需的;存在在人身上树起了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生命不再是无意义的,而是显现在自身的形而上的意义中了”。通过自己的存在来对抗自然的盲目和无意义,来赋予本无意义的自然以一种形而上的意义,这是人的使命,也不妨视为天地生人的目的之所在。否则,人仍是动物,区别仅在于更加有意识地追求动物在盲目的冲动中追求的东西罢了。
我们如何能够超越动物式的盲目生存,达到那个意识到和体现出生命的形而上意义的“更高的自我”呢?单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到,“我们必须被举起——谁是那举起我们的力量呢?是那些真诚的人,那些不复是动物的人,即哲学家、艺术家和圣人”。青年人之所以需要人生导师,原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