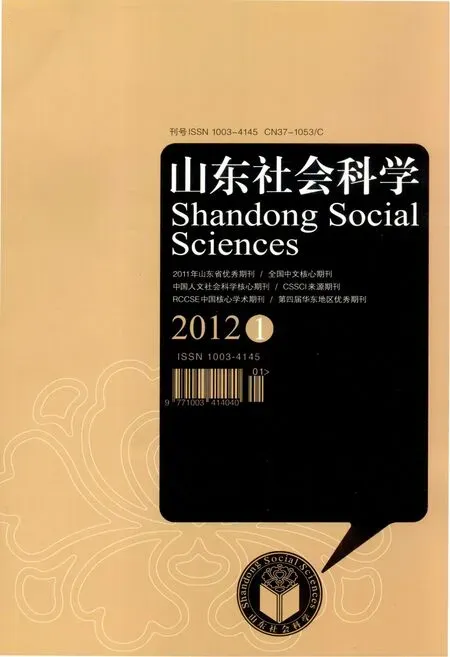隐喻型的章学诚和转喻型的戴震
章益国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隐喻型的章学诚和转喻型的戴震
章益国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西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以比喻类型作为区分史家的依据。以此为启发,从章学诚和戴震各自的一个早年回忆入手,可得出一个推论:章学诚的“语言—思维”习惯带有隐喻型的特点,而戴震则可以说是转喻型的。这个差异,是他们两人分歧的原始根源。这个推论既符合了以往研究的一些共识,也能为乾嘉学术研究史上一些争论提供新的思路。
章学诚;历史认识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
近数十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经历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思潮接踵“分析的历史哲学”而起,①彭刚:《叙事的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其最令人惊眩的成果,就是海登·怀特的“元史学”理论。怀特“借助比喻理论寻找想象与历史之间的合理关系”②陈新:《历史认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揭示出特定历史学观念赖以构成的语言学基础,从而确定历史作品的诗性本质,结论大胆,引得史学界一时侧目。
怀特理论的关键一步是个归类游戏,他以西方传统诗学和近代语言理论中常称的四种比喻类型引申出四种历史意识模式:隐喻、提喻、转喻和反讽。“转喻型的马克思”、“隐喻型的尼采”、“反讽型的克罗齐”③参见[美]海登·怀特:《元史学》第八、九、十章,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这些说法,自然会引起史界“某史家归于某比喻型”的普遍尝试,以验证(或证伪)怀特的理论——虽然这种做法有比附之嫌疑。本文以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为例,并将之与其一时瑜亮的戴震作为参照,④学术史回顾:“章学诚对抗戴震”这个学术史公案,自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发其蕴意后,仍有反复咀嚼的价值。余本人复有《章学诚对抗戴震》一文(载于《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另外一位钱穆弟子戴景贤也有《论戴东原章实斋认识论立场之差异及其所形塑学术性格之不同》(《文与哲》第十期,台北2007(6))。章学诚的语言观念,可参考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第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李洪岩有数篇文章:《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的理论与实践》(《文史哲》2006年第5期)、《历史文本与历史认识》(《学人》第8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等,对传统史学的文本论做了整体的概览。王晴佳有《以史解经——章学诚与现代诠释学》(《思想与文化》2003年第1期),周建刚有《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笔者有《也谈章学诚的言意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4期。以怀特的比喻类型方法作为分类试纸,探讨怀特理论这个新工具能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什么新启发。
一、章学诚和戴震的两个早年故事
早年故事蕴含了一个人此后的精神成长,这类故事多为成年后回忆所得。回忆是对自己成长过程的返观和确认,虽混入后来看法而有不再“纯粹”之虞⑤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但“回忆/遗忘”——这一机制筛选出了对后来的自己“有意义”的往事,并改变之使之“服务于以后的趋势”⑥[奥]弗洛伊德:《达芬奇和他童年时代的一个记忆》,载《论艺术与文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20页。。缘此心理史学常常把人们的精神特征追溯至早年,⑦[奥]弗洛伊德:《〈诗与真〉中的童年回忆》,载《论艺术与文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37页。以完成所谓“倒序制造”(Reverse Engineering)式的“倒果求因”心理分析任务。⑧参见[美]丹尼尔·夏科特:《记忆的七宗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下文我们也想从章学诚、戴震各自的早年时代的故事入手,揭示“戴章对抗”典范意味的某些面向。通过章学诚的自述,我们得知他成学之路上形成“自我认同”的一件关键事件:
犹记二十岁时,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此处指章学诚的父亲)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吾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①章 学诚:《家书三》,《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山口久和指出章学诚一个记忆疏漏:清代吴兆宜《庾开府集笺注》此句注所引用的不是蔡邕的《月令章句》,而是《韩诗外传》。
生当乾嘉之世,章学诚一生几乎无时不受到浓厚的考证学风的压力,这件事情可算是章学诚心中对训诂牢笼的第一次冲决,使他摆脱“中无张主”②章学诚:《跋甲乙剩稿》,《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19页。的状态,恢复心理平衡,形成“自我认同”③心 理史学自从经典之作埃里克森《青年路德》(台北巨流出版社1989年版)始,就注意“自我认同”的形成。在埃里克森笔下,青年路德与成年路德绝然不同,三十岁以前的路德被他称之为“马丁”,三十岁以后才被称为“路德”。章学诚的成年期大概始于发生本文所引故事的廿岁,《家书六》中自己回忆“乃知吾之廿岁后与廿岁前,不类出于一人,自是吾所独异”,可视为其精神成人的标志。可参见[美]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里,吴兆宜注庾信诗,执着的是“意义”的索求,而使得“意味索然”。而章父(章镳)的解释保存了诗意,使得章学诚明白:训诂牢笼之外,别有天地,而自己的长处在于“神解精识”。且看章学诚回忆自己少时的读书习惯: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少年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惊空虚,盖未尝不然自喜,以为得之。④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这个样子读书,大概不会被戴震许可的。在差不多同样的年纪,戴震便养成了“每一字必求其义”的读书习惯。在花了三年时间研习《说文解字》及《尔雅》、《方言》等字书后,17岁的戴震便主张“一字之义,必贯群经本六书以为定诂”⑤洪榜:《戴先生行状》,《戴震文集》附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页。。在戴震的童年,也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比上述章学诚的故事要著名得多,而同样可以看作戴震成学之路上的标志性事件。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记戴震十岁时(1732年):
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久矣。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师无以应,曰:“此非常儿也。”⑥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附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6页。
作为戴震一生中值得记载的第一个故事,这似乎预示了其后一生的方向。⑦有 些心理学者认为:所能记忆的头一件事,是了解其人个性的关键。参见[奥]阿德勒:《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56页。它颇能彰显戴学的方法论风格,进而亦体现清代朴学的基本精神。梁启超有个很好的评价:
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⑧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将这两个早年故事并观,章戴两人思维风格的差异清晰可辨。章学诚通达、戴东原坚执;章学诚灵动跳跃,而戴东原“层层逼拶”、步步推求、一疏一密。这种差异值得咀嚼。两个故事,说的都是解经释诗的语言活动,下面我们借用语言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来发掘一下章戴这两个故事的蕴含。
二、隐喻与转喻
若说两个早年故事的对比,便充分喻示章戴两人治学上的不同路向,显然有点简单化。但由此拈出两人在“语言—思维”观念上的歧异,至少在象征意义上是成立的。如果我们引入一些现代语言学的观点(也就是这些观点后来也影响了历史学,造成所谓“语言学的转向”),也许我们能对这一分歧有着更深层的理解。当代语言学有一个基本思路:语言有两个方面。此最早为索绪尔提出,任何语言系统的活动都是在两个坐标轴上进行的⑨[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0-176页。:
1.是横向的、历时性的句段(组合)关系。我们说一句话,是一个词接着一个词出现,直到最后一个词出现。这是一个时间上的连续性运动,每一个词和在它之前的一个词以及在它之后的一个词都有一种水平横向的相邻性(contiguity)关系。如“僧-敲-月-下-门”①以贾岛此句说明结构语言学理论的文章很多,最早可能是张隆溪。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13页。,从“僧”开始,各词依次出现,到“门”结束,该句的完整意思才呈现。
2.是纵向的、共时性的联想(选择)关系。如上句诗歌中的“推敲”。“推敲”存在相似性(sim ilarity)关系。当我们选择了“敲”字,那么“推”字实际上仍然以“不在场”的方式,和“敲”字垂直排列着。这个未被选中的词(如这里的“推”),亦以自己的空缺,参与了筛选和提炼那个现存的词(如“敲”)的意义。如果我们明白了“推敲”的差别以及如此选择的缘由,我们就能更加明晓原句的意义。
雅各布森②[美]雅各布森:《语言的两个方面和两种失语症“紊乱”》,载于《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9-373页。发展了索绪尔这一观点。他认为,语言的这两个方面,分别对应隐喻和转喻:③本 文对比喻的分类有必要解释一下。西方的文学理论把修辞手段划分得非常琐细(最多达250种。参见韦勒克:《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但其中最常见和简明的是索绪尔、雅各布森和列维施特劳斯使用的“隐喻-转喻(提喻)”二分法。海登·怀特的历史比喻型是分成四类的。在《元史学》导论的一个长注中(第41—43页),怀特解释了自己“析二为四”的理由(另参见陈新《历史认识》,第120页)。对于繁复的比喻理论,本文无意深涉,取列维—施特劳斯说的那种“无需拘泥于语法学家的繁琐”(《野性的思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3页)的态度,把提喻看成转喻的一种(两者都基于相邻性),略去反讽,仍用“隐喻-转喻(提喻)”这最常见的二分。
1、转喻的构成基于横向的毗邻性原则。在转喻中,一个符号被联系于另外一个符号。这种联系可以是“整体—部分”的,例如“50张船帆”代表“50艘船”;也可以是“先—后”的、“因—果”的关系,如“雷吼”这个词中,雷的声音的产生过程被分解成两个现象:一方面是原因(雷),另一方面是结果(吼声)。
2、隐喻的构成是基于纵向的相似性原则。在隐喻中,一个符号因其与另外一个符号的相似而被代替。例如“我的爱人,一朵玫瑰”,这是缘于“爱人”和“玫瑰”的某种相似。④这里的几个例子,均取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5页。其中“雷吼”的比喻,则是怀特取自维科。所谓“隐喻用法”,通俗的讲,就是意义的“转换”,“以他物之名名此物”,通过另一件事来理解某事,即成“隐喻”。人们一般理解词语在既定规则约束下的意思,但人们又总是容易在不同规则中滑动(即索绪尔所谓“能指”与“所指”之间有随意性),这就导致词语的“隐喻用法”。
在“隐喻转喻”之分的基础上,雅各布森提出他对诗的理解:人们平常说话的时候,是先从一系列可能的对等词中选择,然后把选择出来的词组合成一个句子。然而,在诗中的情况则变成了这样:诗人把各个词联系起来的过程,也像选择词语的时候一样注意种种对等词,诗就是把语义上、韵律上、语音上或在其他方面能对等的词语组合在一起。由此,雅各布森提出了他关于诗的一个著名定义:诗性活动就是把选择轴上的对等原理投射在组合轴上——也就是说,在诗中,相似性被添加于相邻性上。在平常说话中,种种词语被串在一起组成一句话,是因为他们意义上的连贯,而在诗性活动中,种种词语被串在一起组成一句诗,是因为它们在音响、形式、韵律和意味上的相似(以及对立、平行等等)。
有了以上理论的准备,让我们回头看看章学诚那个早年故事。“春水望桃花”这一句诗中,“春”、“水”和“桃”、“花”这些字有很多可能组合:如“春水”、如“桃花水”、如“春水中桃花的倒影”等等。以一句诗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使得它们成为组合轴上相挨着的东西。但是这多个意象能连撮到一起,并不是它们构成了“因—果”或“整体—部分”之类的逻辑(转喻)关系,而是它们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意味我们不好明说出来、不好全部说出来——说出了就限定了诗的意味,而且这些相似性都不是排他的,我们可以多角度多元地发现它们的相似。“春”、“水”和“桃”、“花”两相对照、相互映射(“望”),相互发掘、相互感应,维系一种毗连而对比的关系。从而使这短短5个字,有足够的天地,容读者的寸心“周游”其间、反复回旋。正因为这种相似性的开放意味,加上“春”、“水”和“桃”、“花”这些意象本身的朦胧感,给人带来“绵邈”的神思。所以,这些意象之所以能在一句诗中连贯出现(连续轴),是因为它们的关系实际上是在纵轴上(选择轴)的。章镳的解释有诗意,就是因为他感悟到了“春”、“水”和“桃花”这些在一句诗中“并置”的意象具有相似性⑤严格说来,章镳这一解释,仍然只是庾信原诗的意义之一。原诗并无“于……之中”这一限定。介词的省略是中国古诗的一个常见现象(参考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这会使位置状语作为诗句的主语出现,因而庾信诗至少还有一种解读:“春水”作为拟人化的主语,去“望”(对视)桃花,两者自相连辍。章镳的解释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这一种解读则是“无我之境、以物观物”,似更佳。多年后章学诚有诗《庾开府摘句图赞》(《章学诚遗书》,第340页)称庾信“刳剔山骨,琢冰煮泉”,赞的就是其诗“清新”的特点。,也正核实了上述雅各布森对诗的定义。①程抱一曾经以李白的《玉阶怨》来核实雅各布森这个诗的定义。《玉阶怨》的句式为“状语+动词+宾语”,从结构上讲,全诗和庾信这句“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都是同构的。本文此一节(包括图示)正是参考了程抱一的结构主义方法。参见《中国诗画语言研究》,第108-112页。或者拿我们自己的话来说,这些意象“并置”,并非因为它们“意义”上的相邻,而是它们“意味”上的相似(见图1)。
如果说章学诚这个早年故事说明,章在庾信这句诗的解释活动中领悟到了“语言—思维”活动的断续性和相似性,从而悟证了一种隐喻式的诗性思维;那么,“戴震难师”的那个故事中,戴震死死抓住的却是思维的时空连续性。童年戴震一连五问,问问环环相扣,他的逻辑是:朱子之言可疑,是因
为朱子和孔子、曾子相去几二千年,没有时空上的连续性。梁启超评戴“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这个“间”,就是戴震容不得的,“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我们看到,在戴震的思维中,他接受不了从孔子到朱子的“蒙太
奇”,他非要一个连续的“长镜头”②雅 各布森以为,转喻对应长镜头,隐喻对应蒙太奇,前揭雅各布森文第373页。另参见[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实际上后来戴震在学术方法论上的一些著名口号,都是建立在延续性基础上。例如③这几句话无论在当时、还是在近代,都是戴震最受推崇的学术口号。可参见考丘为君:《戴震学的诞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这句我们下文要详细讨论);“字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与是仲明论学书);“所谓十分之见,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竟,本末兼察”④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页。。
从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有些推断,章和戴在思维方式上便是两种人:一个悟于语言的相似性,一个执于思维的连续性。我们的依据是,雅各布森曾经从语言的“隐喻转喻”之分,引申出两种人的划分:有的人更倾向于使用隐喻,有的人则更多使用转喻。每个人的个人风格和“语言—思维”偏好,或多或少有其中一种倾向。对于戴震和章学诚两人,我们或可做一个推测,戴震的思维方式,更多地关注语言和思维的转喻方面(连续性),而章学诚的思维习惯,关注的是语言和思维的隐喻方面(相似性)。他们左右配剑、各执一端,这也许是他们分歧的源头之一。

图1
三、章学诚的相邻性紊乱
让我们再为这个推测补充些有趣的证据。颇吊诡的是,戴震和章学诚这两位一辈子和文字打交道的人,幼年时期却都经历过一定的阅读和书写障碍。前引戴震年谱已载,戴震这个“文字—音韵”学大师,十岁才会说话。而章学诚也有这样的回忆:
二十岁以前,性绝呆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尤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⑦章学诚:《家书六》,《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由于缺乏进一步的材料,我们不可能追溯这一现象的“生理—心理”原因。但若要由此窥见章戴两人思维方式某些特点,或许也不算是空穴来风。因为我们知道,雅各布森提出的“隐喻转喻”之分,其源在于他对失语症的研究——他实际上是通过对语言交际的失败,来反观人类的正常语言交际:
语言研究中基本的二项对立概念是了解失语症二分法的钥匙,这种二分法很明显也就是诸如编码—解码、组合关系—聚合关系、邻近性—相似性等二分体(dyads)。这些概念已经逐步进入高级神经心理学对失语症之谜的研究。邻近性和相似性的对立在语言和诗歌当中有种表现,也可以描绘成换喻和隐喻的对立。⑧[美]雅柯布森:《雅柯布森文集》,钱军、王力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失语症种类繁多,各不相同,但雅各布森判定这些症状全部介于两种不同的错误之间:要么是“选词”能力的缺失,要么是“造句”能力的缺失。从而失语症可归结为两种类型:
1、相似性紊乱患者丧失了(纵轴上)选择替代词的语言能力。如果把零星的字句提供给这类患者,他们是能够将之连辍成句的。他们也能进行谈话,但是让他们自拣话题进行对话却有困难。当表达越是依赖于语境的时候,他们就能越好地应付表达任务,但像独白这样的封闭性话语,对他们来说却很困难。他们往往也不能理解别人说话中的比喻、隐语等等。
2、相邻性紊乱患者丧失了(横轴上)组合和构造的语言能力。病人首先丧失的是把词语组织成更高级单位的语法规则。病人口中的词序会变得很混乱,往往不存在并列或主从等语法关系。这种失语症病人不会说完整的句子,他们说话会一个词一个词地往外蹦,说出来的话只是一个一个要听者自己去完成联系的词。
也就是说存在着这样的“跷跷板规律”:当一个词越多地依赖于句子的语法关系,它就越容易被相邻性紊乱患者所丢失,而越容易被相似性紊乱患者所保留;反之亦然。例如,相邻性紊乱患者不大会用连词、介词、代词、冠词等只具有语法功能的词语,使他们的说话常常“语法缺失”,句子只是词语的堆砌,呈现“电报式语言”的特点,而在相似性紊乱患者中,这些词是最不易被丢失的;相反,像句子的“核心主语词”,通常被相似性紊乱病人最先丢失,而在相邻性紊乱病人的说话中,“核心主语词”却是最不受影响的。
雅柯布森认为,失语症中偏向于语言的某一极而排斥另一极的现象,与“转喻/隐喻”这一语言的两极结构是相关的。具体表现在:相似性紊乱与转喻偏爱相关、与隐喻相悖;相邻性紊乱与隐喻偏爱相关、与转喻相左。两类失语症中对语言两极的欹轻欹重,亦会体现在个人的思维风格中,表现出某一极的优势地位。雅各布森曾经捡出了一个例子:俄国小说家乌斯宾斯基。雅各布森从他晚年饱受言语紊乱精神病折磨的事例分析,这个作家的思维风格是相似性紊乱。而相似性紊乱和转喻偏爱密切相关,所以,乌斯宾斯基所偏好的文学风格便应该是倾向转喻一端。文学研究中对乌斯宾斯基的定评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雅各布森对乌斯宾斯基研究富有启发。他的推论逻辑完全可以移用到本文的主角章学诚身上——不过这种移用是反用:章学诚和乌斯宾斯基刚好相反。乌斯宾斯是“转喻偏好+相似性紊乱”型,而章学诚是“隐喻偏好+相邻型紊乱”型。两人相映成趣、相悦以解。那么何以判断章学诚是“相邻型紊乱”,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论据。这便是上文所引的章学诚对自己童年时代语言障碍的回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此句背后有关故事,见于实斋在纪念其少年时代的塾师柯绍庚的《柯先生传》:
又编纂春秋家言,戏为纪表志传,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然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①章学诚:《柯先生传》,《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
此处所言“编纂春秋家言”的旧事,有关章父章镳对实斋的另一个教诲。十五六岁时,实斋尝取《左传》删节事实,章镳见了,乃谓编年之书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不如用纪传体重新分合事实。实斋受父亲启发,才“戏为纪表志传”,经营凡三年后为馆师所觉而中废。此事涉及史事的重新“情节化”,虽为儿戏,但对少年章学诚体会不同史例的短长显然有好处。②章学诚:《家书三》,《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而章学诚在这一工作中,发现自己语法方面的缺陷:对虚字掌握不够。虚字有一个特点,也就是于章学诚9岁那一年(1746年)付梓刊刻袁仁林的《虚字说》中说的:
(虚字)本为语中衬贴之声,离语则不能自立。③袁仁林:《虚字说》,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2页。
虚字不能单独成句。它的作用在于:句子的语法关系更多地靠虚字来建构,或者反过来说,虚字更多地依赖于一个句子的语法关系,而不是一个句子的实质句义,正如前文所引雅各布森的研究表明:一个词越多的依赖于句子的语法关系,就越难被相邻性紊乱病人掌握。童年的章学诚对虚字的迟钝,是不是恰巧说明他习用相似性思维却有一定程度上的相邻性紊乱呢?
当然,本文绝非断定章学诚得了失语症,我们只是想基于失语症理论描述他的某些思维特征。而且我们自知,这种对个人精神成长史的回溯,并非正统史学研究法,是一“危途”④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03页。,我们点到为止。下面,让我们转入对章学诚思想的直接分析。
四、章学诚思维的隐喻偏好
《文史通义》第一卷“内篇一”,有《易教》三篇、《书教》三篇、《诗教》二篇和《礼教》⑤《礼教》一篇,“大梁本”《文史通义》未收。刘刻本《章氏遗书》始有。一篇,“五经”中仅缺了《春秋教》①何以《文史通义》没有《春秋教》,是个有趣的学术史话题(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7页)。笔者认为:章学诚看来,春秋是由前四经的不同“教”构成的(书、诗之兴、易之象→春秋之体;礼之官、易之辞→春秋之用),所以春秋不是“原子”级别的,而是第二等的,因而《春秋教》可不写。(不过在章学诚著作的其他各处,“春秋教”这个元素仍经常出现)。刘咸炘《文史通义识语》讲“《通义》全书以三教篇为纲”,这是章学诚整个理论的核心,也是章学诚学说中令人费解和歧义较多的部分。我们想通过此部分的分析验证上文对章学诚隐喻型思维模式的判断。先看《易教下》开篇一句话:
《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礼》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谨严而不可假借矣。
这句话中,章学诚在四经中各自拈出一个要素:易学的象,诗学的兴,春秋的例,周礼的官,并把四经区分为两个系列:以《易》、《诗》为一方,以《礼》、《春秋》为另一方。这里的划分依据,并非这四个要素在知识内容和主题上有什么逻辑联系,而是这四个要素象征二种知识风格,所带给人不同的“动感”:一类是“变化”的;一类是“谨严”的。这句话可用表1表示。

表1
这样把经书分解成在纵轴上“谨严/变化”两种风格上的对立。这个表还可以扩大到全部五经:
1、《尚书》“因事命篇”、“无定法”,是“变化”精神的一个极致。
2、不仅五经整体上可以分成“变化/谨严”两端,其中《易经》和《春秋》在同一经内部,也呈现着这种对立。此两经内部有两套意义系统。《易》中“蓍/卦”(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象/辞”;《春秋》中“义和例”、“体和用”,都体现“变化和谨严”对立。
于是,表2即为表1之升级版。五经呈现出二元结构。可以说,明白了这个结构图,我们就掌握了章学诚思维最基本的元素及其组合。我们可以把章学诚思维模式作一个结构主义的形式分析:每一经之内的二个因素构成横轴上的相邻关系;而经与经之间,则构成纵轴的相似关系。表2中横行为相邻的句段关系,竖列为相似的联想关系。这正如罗兰·巴特所说:一个人穿的一套衣裤之间(帽子、衣裤、鞋子从头到脚)是相邻关系,他选穿的鞋与他没选穿的鞋、他选穿的衣服与他没有选穿的衣服之间则是相似关系;一桌依次上来的菜(从冷盘、主菜到点心)之间是相邻关系、选的菜和未选的菜之间则是相似关系。②[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对照此图,就是顺着章学诚思维方式切入他的理论核心,他那些以往令学界费解的命题也就豁然开朗。为下文叙述方便,我们为纵横轴编了符号,③类 似的符号表,可参见[法]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生食与熟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和列维—斯特劳斯一样,这里的符号不用于证明,只用于诠释。这样我们甚至可用符号来表达章学诚的命题。例如,上引《易教下》开篇的那句话,可表达成4B=3B;1A=5A。又如他说过:

表2
《易》象通於《诗》之比兴;《易》辞通於《春秋》之例。(4A=3A;4B=3B)
对照表2,此一句讲的就是经与经的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似关系。“易之象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因此“《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易辞)一字出入,谨严甚于《春秋》”,因而,《易》辞通于《春秋》之例。在这里,“《易》辞”与“《春秋》之例”,水平轴上是分属两经的,但因为它们各自在自己一经中的结构性地位是相似性的,所以,在纵轴上就是“通”的。章学诚此一类命题的思维特点,即把水平轴上的相邻关系(如此句中的“易辞与易象”;“春秋之例与春秋之义”),投射到了纵轴上(“《易》辞”与“《春秋》之例”),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诗性思维或隐喻性思维。我们再看他一个更著名的命题,《文史通义·易教下》中称:
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4B=12345;4B=2B)
前半句讲4B和所有12345的关系,后半句突出讲4B和3B的关系。“易象包六艺”,章学诚是这样解释的,他把道的呈现,当作一个拟象。所有知识,都是通过拟象来呈现道。“象”就是道体似要表露又没有完全显现的东西,“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④章学诚:《易教下》,《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大道恍惚,人不可直接求道,而必须通过象的中介,因而“象”在认识论上具有普遍意义:在“拟象”这个方法上,六艺贯通。实斋所谓“易教”,主要指“以象为教”。《易》中体现了象征隐喻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普遍和广泛的。取这个理解,不仅仅六经,战国诸子、乃至外来的佛教①《易教下》一文中章学诚提出“佛教本源出于易教”的论点,以这种观点方式看待佛教,与现代西方学者用隐喻理论研究基督教,有异曲同工之妙。约翰·希克在《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提出“上帝道成肉身”不是字面真理,而是隐喻真理。这个论点,拿章学诚的话来表达就是:“上帝道成肉身”是“以象教”。,都为“易象”所包。所以说,“象之所包广矣”。
那么,“象”、“兴”如何“为表里”呢?它们都是籍形象寄寓义理或情义、意蕴,“深於比兴,即其深於取象者也”。《易》立象尽意,系辞尽言,言辞止乎于是,指陈有限;象意概括无穷,遗味悠远,言有尽而意有余,所以可以成为言意之间的桥梁。而由“以此状彼”、此言及彼意的思维过程,即“比兴”。“象”是贯通所有知识的凭借物,为表;“兴”是贯通所有知识的思维方式,为里。②此就其相同处而言。其相异处,钱锺书有清楚的辨析。钱钟书:《管锥编》第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12页。
于是,我们可以引出章学诚一个重要的命题。这个命题恰当地说明了,章学诚明确提出过隐喻思维是历史思维的基础。只是以往治章学者,似乎未曾留意。在《史德》篇的最后,章学诚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2B=5)③章学诚:《史德》,《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春王正月之书”即《春秋》,此处代指全部史书。章学诚的意思是,“知比兴方可言史”。这是讲5与12345的关系,特别是讲5与2B的关系。这个命题在认识论上把史(5)与诗(2)联系到一起。章学诚把历史和史书的有形部分,整体上当作一个“象”,通过这个“象”,运用“兴”的意象思维,才可能达到“道”。史为传道之器,即史明道,其间的认识过程是“兴”。同沟通“象/辞”之间的桥梁一样,沟通“《春秋》之例/《春秋》之义”(即沟通历史学形下一端和形上一端)之间的,是类似与“诗”之比兴的史家的整体性直觉。
让我们顺着“知比兴方可言史”的命题转入史学。“五经教”部分“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④章学诚:《上朱中堂世叔书》,《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五经可以抽象出“谨严/变化”两种属性,这一区分可以移而论史。章学诚看来,历史知识内部也呈现一个同样的二元对称:一端是有形的、谨严的,例如史事、史例、史法等等;一端是无形的、变化的,如道、理、意等等。从“经的二分”投射到“史的二分”,章学诚的依据有三:
1、《尚书》与《春秋》。五经中这两种史书,分别可成为“变化/谨严”这一二元结构两端的代表:“《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1B:5A)
2、《周礼》与《尚书》。《周礼》,代表着有序保存典籍和严整收集资料的精神,“《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书”,章学诚把《周礼》看作供《尚书》取材的记注之书,因此,《尚书》和《周礼》两者也构成了“变化/谨严”的二元对立。“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就是分指周礼和尚书而言。对立即统一,“周官之法”和“尚书之教”相互对立也相互依存,去其一则失其二,所以章学诚讲:“《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1A:2B)
3、《春秋》的内部,也存在这样的二元结构。《书教上》中讲:“王者迹息而《诗》亡,见《春秋》之用;《周官》法废而《书》亡,见《春秋》之体也”(3B=5B:1A=5A)。春秋之“体与用”的二分,可以说代表了历史学的“事与理”二分(亦对应“器与道”二分,易之“象与辞”二分,诗之“言与意”二分)。因此,一方面,“事有实据”,故“记注有成法”,是以春秋之体,谨严不可假借,通于易之辞(4A),礼之官,见于周官法废 (1A);另一方面,“理无定形”,故“撰述无定名”,是以春秋之用,变化不可方物,通易之象(4B),诗之兴,见于诗之亡(3B)。
由此,从五经中抽取的“变化和谨严”二元结构,便构成了章学诚史学的两条线索。在五经中的《尚书》和《春秋》分别代表史学这两种传统的源头。在《春秋》内部,对应这两种传统的则分别是“春秋之义”和“春秋之例”。这两种传统在后世史学史的发展,就是章学诚区分的“撰述与记注”、“圆而神”与“方以智”、“史记”传统和“汉书”传统的两两对立,正所谓“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应智,多得官礼之意也”(2B→6B;1A→7A)。以这种风格上的二种传统去理解史学史的流变,是章学诚史学最重要的创见。为明白起见,我们可以把章学诚版本的史学史之基本编码,用表3表示:章学诚所建构的上古史书“一以贯之”的系谱如《书教上》所述:

表3
《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六艺并立,《乐》亡而入於《诗》、《礼》,《书》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王子虎之命晋侯,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同著於篇,则《书》入《春秋》之明证也。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
这样,“周官1A→尚书2B→春秋5AB→史记6B→汉书7A”,这个别具一格的章氏史学史谱系,就气势阔大地把上古诸家史学都统在一起了。
可以看出,章学诚的所有论述的基础,都是在纵轴上的某B和某B相似,某A和某A相似,即他的思维擅长抓住事物的相似性关系。而他所标举的“象”与“兴”,对译到现代史学理论的术语,大约也就是“想象和比喻”。于是,如果我们把章学诚放到了怀特理论的试纸上,那么自然可以得出了“章学诚是隐喻型史家”的结论。这个结论富含启发,既契合了以往章学诚研究的共识,也能解决一个章学诚研究史上一些聚讼纷纷的问题,或能为章学诚研究别开一生面,篇幅所限,我们略举其大者如下:
1、“史意”概念。章学诚主张“作史贵知其意”,这个“史意”不仅仅是通常解释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它有“意义”的层面,但还有“意味”的层面;它不仅仅是“主题”,而且是“风格”。“意义”对应转喻,由横轴上前后邻接的字词呈现,“理论”、“观点”、“主题”等等是通过逻辑推演获得的;而“意味”、“风格”则对应隐喻,“史意(味)”要靠隐喻思维意会。“史意”这个概念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对历史认识过程中的默会维度的深刻理解。而章学诚自述其与刘知幾的区别:“章言史意/刘言史法”,不是研究对象上的不同(不是章学诚研究叫“史意”那个知识领域,而刘知幾研究叫“史法”那个知识领域),亦是思维风格上“隐喻/转喻”的不同。法则建立事实,隐喻勾勒模式①[德]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法”、“意”之别,该从这个层面去找。
2、“文史通义”所谓的“通”,不仅要从转喻、提喻层面理解而还要从隐喻层面理解。不仅仅指的是时间和逻辑上的贯通,不仅仅指与专史和断代史相对的通史,更不是西方“思辩的历史哲学”那样把历史整合进一个意义体系(提喻),而是指历史的某种形上意蕴。
3、“圆神”“方智”这一“史体”划分,不是“体类”之分,而是“体性”之分。这种分类不是“归纳—演绎型”,而是“隐喻型”。这种分类方式把历史著作与史家的主体性挂钩,从而不仅仅限于历史编纂学范畴。从人类思维的不同风格出发,归结出一对二元因素,通过勾勒出它们的此消彼长和分离融合,足以写出一部思想学术的历史。耍玩这种把戏最成功和最著名的高手正是怀特谓之为隐喻型的尼采。他的《悲剧的诞生》以日神与酒神的二元性隐喻的对立和融合构建了悲剧生成的历史。章学诚也是在史学史中拈出“圆神”“方智”这一组二元对立,假想某种隐喻的“意”,在史学史中流变。
五、隐喻思维对抗相邻性思维
转喻对应事件,隐喻对应结构。年鉴学派以结构取代事件,②一般认为,年鉴学派这一主张,是当时整个结构主义思潮中的一部分。参见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第13页。曾造出一场史学革命,这是我们熟悉的。在我们这篇思想史文章中,我们以“结构”来取代“主题”,以思想“风格”的研究取代思想“观点”的研究。正如布罗代尔称“事件的历史”是“表面的骚动”,是带泡沫的浪花,“结构”的历史才是根本,是“深海暗流”③[法]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页。。同理,主题、观点是表面的,思维方式在完形上的整体特征是更深层的因素。在《元史学》的结语中,海登·怀特曾经总结,拿比喻范畴描绘史家的风格,可以取代通常用以形容史家观点的如“浪漫主义”、“唯心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范畴,还能从认识论、美学和语言学的层面上,揭示后者赖以寄居的作品的结构④[美]海登·怀特:《元史学》,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页。。也就是说,风格是在背后决定观点的东西。于是,让我们通过章戴论争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次“观点”上的交锋,来呈现这种表面冲突背后,两人“语言—思维”模式上转喻型和隐喻型的“结构”差异。我们仍然用戴震对自己的童年回忆(1757年戴震35岁时追忆⑤此年份据段玉裁《戴震年谱》。钱穆有不同说法。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4页。):
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①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页。
这一段话可谓是戴震最著名的一个学术方法论口号。少年戴震从茫然无觉而卒有所得,其所领悟的思维技术,说出来倒也十分平常,即所谓的“问题分解”术:每当我们面对一个遥远的、大的、总的目标的时候,可以把它分解成一些子目标,然后再把这些子目标分解成子子目标,如此用递归的方式进行下去,最终能得到一些非常简单的目标,于是大问题就被分解成一个个小问题来解决,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若干步来解决它。例如在这里,大目标是“通其道”,次级目标是理解全文全书,小目标就是理解一字一词。这个“问题分解”的思维技术,其特点是紧扣“相邻性”,即一连串相邻的小目标“组合”成大目标。这种“问题分解”法在人们的思维中运用得十分普遍,有着很朴素的理性力量。早于戴震120年,笛卡尔就把这列为“正确思维和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论”的四条基本原则之一:
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总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②[法]笛卡尔:《谈谈方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6页。
但是,这种方法也蕴含着一个陷阱。为简便说明之,我们可参考一个著名的例子:芝诺“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的悖论。芝诺称,运动是不可能的。由于运动的物体在到达目的地前必须到达其半路上的中点,若假设空间无限可分则有限距离包括无穷多点,那么运动的物体需要在有限时间内经过无限多点,这是不可能的。芝诺用的其实就是“问题分解”的技术,他把从A到B的总目标,分解成两个子目标:先走一半,然后再走一半。然后,再把这两个子目标,分解成四个子子目标:先走一半的一半,再走一半的一半……这样无限递归下去,你就会得到一个无比巨大的目标群,最终你将寸步难行③参考侯世达:《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壁之大成》,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02页。。戴震讲过,寻行数墨,要如“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走楼梯要一级一级走,但是,多少微量的程度才算楼梯的“一级”呢?这就像芝诺说的,你在从A到B的过程中,总要经过A和B之间的中点,如果固执于“不可以躐等”,这样无限分解,你就永远不可能从A到B了。《庄子·天下篇》中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是描绘了这样一个困境,戴震自然知道庄子这句话,却不知自己把整体分解成部分的思路就陷入了这样一个不竭的深窟。
1766年,戴震的上述观点,曾向前来问学的章学诚面陈,给予后者巨大的精神震荡,留下“仆重愧其言……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④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的记录⑤章学诚、戴震初晤的情形,可参考余英时《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17页。。多年后,学术上成熟自立的章学诚,对戴震的观点有了系统的反驳。章学诚的论战策略,就是锲入戴震的“相邻性”观念,指出“问题分解”的技术,忽视了机会成本,会导致“无穷递归”,从而使人陷入浩淼的琐碎之中:
戴(东原)氏言曰:“诵《尧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则不卒业。诵《周南》、《召南》,不知古音则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其方。”⑥章引戴震这段话,见于《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页。戴氏深通训诂,长于制数,又得古人之所以然,故因考索而成学问,其言是也。然以此概人,谓必如其所举,始许诵经,则是数端皆出专门绝业,古今寥寥不数人耳,犹复此纠彼讼,未能一定,将遂古今无诵五经之人,岂不诬乎!⑦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338页。
戴震讲,读《尚书》的《尧典》,要想理解文中“乃命羲和”这一句话,这个问题会衍生出一个子问题:你必须知道恒星和七政(日月木火土金水)的天文知识,若非如此,便无法读懂《尚书》;读《诗经》的《周南》、《召南》诗篇,如果不解决古音的这个子问题,句读就会有误;读《仪礼》的“士冠礼”,就得先解决古代宫室衣服等各种制度的问题。这样的读法,自然就引出了许多许多的“专门绝业”,天文学、音韵学、仪礼制度之学,而这些学问的任何一种,都是人们终其一生未必能够穷尽的专门之学:
六书小学,古人童蒙所业,原非奇异。世远失传,非专门名家,具兼人之资,竭毕生之力,莫由得其统贯。然犹此纠彼议,不能画一,后进之士,将何所适从乎?或曰:联文而后成辞,属辞而后著义,六书不明,五经不可得而诵也。然则数千年来,诸儒尚无定论,数千年人不得诵五经乎?⑧章学诚:《说文字原课本书后》,《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3、74页。
“此纠彼讼,未能一定”,必须交给专家去处理,一般读经人如果纠缠于这类问题,每一步都追求戴震所谓的“十分之见”,那么过程的自我目的化终将会淹没最终目的①梁 启超亦评戴震此法容易“把手段看成目的”(梁启超:《戴东原哲学》,见汪学群编:《清代学问的门径》,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50页)。,“步步推进”的计划会变得“寸步难行”,这样下去,章学诚双手一摊道:“将遂古今无诵五经之人”——就像芝诺耸耸肩膀: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了。正如戴震的学生段玉裁讲(据段的外孙龚自珍述):“学问门径,自殊远而望之皆一丘一壑耳;深入其中,乃皆成泰山沧海”,于是,我们如何能“以有限之神识、观无涯之注记”(《史通·杂说》)、“以有尽之生,而逐无穷之闻见”(《文史通义·假年》)呢?
西方史家中,柯林武德讨论过历史学中的“量”的问题,可以与章戴这个争论相并观察。他提到,有种意见认为:如果你不了解高卢的台纳文明是怎么样,你就不会知道凯撒征服这片地区时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进而,你就不会理解凯撒生命的主要目标,也就不能理解罗马共和国结束时这个主要人物(这个设问和上引戴震的说法是一样的)——这样说,是不是太苛刻了呢?因为忽略台纳文明而导致对整个罗马史的误解的可能是非常小的,但是,那会有多小呢?在校正误解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失误和我们了解台纳文明所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那个更大呢?事实上,历史学总是会碰到忽略这个还是忽略另一个的“选择”问题。因而,追逐“终极的全面的历史事实”精神可贵,但是这是一个无尽的目标,历史研究不可能在完成这个目标后才开始,历史学家也不应该把自我限制在历史的细节中:
一个特定的作者,或者特定的一代作者,就某个特定主题占有的只有数量有限的证据;而另一位作者,或者后一代作者成功地开启了新的信息之源,那么,这个过程会在哪里终结呢?在历史研究终结之前,这个过程绝不可能终结。因此,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了把自己限制在细枝末节中而给出的种种理由都是些糟糕的理由。它等同于:这样的细节需要严格地、科学地对待,而“更大”的问题却不需要。②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2页。
戴震是脱不开这样的批评的——他严格地对待了细节,却忘记了更大的问题。而章学诚却抓住了问题的另外一端。以下一段,笔者认为是章学诚对自己认识论最要紧的阐述:
理之初见,毋论智愚与贤不肖,不甚远也;再思之,则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则眩惑而若夺之矣。非再三之力,转不如始也。初见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则入乎其中,而身已从其旋折也。必尽其旋折,而后复得初见之至境焉。故学问不可以惮烦也。然当身从旋折之际,神无初见之全,必时时忆其初见,以为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几哉有以复其初也。吾见今之好学者,初非有所见而为也,后亦无所期于至也,发愤攻苦,以谓吾学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系之舟,虽日驰千里,何适于用乎?③章学诚:《辨似》,《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如果说戴震的方法是“积小以明大”,那么章学诚的方法便是“先立其大”。所以他竭力保持“神全”的精神状态,时时返归“初见之至境”以避免“手段—目标”的倒转。戴震的“字→词→道”,三者构成水平轴上的提喻关系,而章学诚的“初见之全”和“再思”“三思”,三者保持了纵轴上的、“相似”的等阶关系,相互比观、构成了诠释的循环。④参见[日]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页。和戴震元素主义的组合分解法不同,在习惯隐喻型思维的章学诚心中,整体总是大于部分之和的。戴震的方法论下,三角形要分解成三条直线,一条一条来认识,而章学诚的感觉中,三角形首先是三角“形”。或许,章学诚反对戴震,其观点可以用安克施密特的话一言概之:
历史叙述是历史叙述只是在于历史叙述的(隐喻的)意义在其整体性上是超越其单个陈述的总和的(字面的)意义。⑤[荷兰]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曾几何时,戴震的方法被当作清代朴学“科学精神”的代表,而时至今日,“科学”的发展已经非胡适那代人所能想见。卡西尔等人曾经指出,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界发生了一场“思维方式上的革命”:机械论基础上的元素主义思维被整体论所取代。如在物理学中,古代的“实体理论”被“场论”取代,所谓“场”,不能被理解为部分递加组合而成的结集,非由“件块”拼组而成,而是一系统、一整体⑥[德]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另参见[法]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页。,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也均经历“元素→场”的范式变迁,“自然不会跳跃”的观念遭到否定。若就这点而言的话,戴震转成非“科学”,章学诚反而是“科学”的了。舟已行矣,而剑不行!这种移形换位,倒使得我们思考,用西方观念来比照中国思想史研究,如何避免郢人燕说、看朱成碧、相互破坏呢?
这是个大的问题,在此,容我们仅就本文做一点小声明。像戴震、章学诚这样的学者,不可能化约为一种思维类型。海登·怀特的比喻理论含混处很多,如果拘执于比喻类型上的对号入座的话,那就成“粗野的”和“荒诞不经的”——即使怀特本人,在判类划分上也是力求灵活的,例如他把马克思划归“以转喻模式为史学进行辩护”之后,仍然说“无论马克思分析什么”,都倾向于将研究对象对应为四种比喻。①[美]海登·怀特:《元史学》,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页。因而在本文中,虽然我们有中西互参的企图在内,但对我们的中心论旨而言,海登·怀特的比喻理论只是借力,我们无意奉其为金科玉律,我们只是消费它。我们的问题全从本土研究的语境而来,我们对章学诚学说的新解释,即使摒去对“西方”隐喻理论的借用,也是成立的。我们完全有可能纯用传统史学的术语,表达同样的解释,只是那些术语涵义混沌且已为人熟用,敏感度不够。因此这只是一个学术传播策略的问题。因此,不管是叙事主义的史学理论、还是结构主义形式分析,②海登·怀特本人的态度就颇堪寻味,《元史学》中译本前言的第一句,便说该著作是“结构主义”时代的产物,要是在今天,他不会这样写了。他本人如此说,我们自然不必对他的理论过泥过执了。以及心理史学的方法,于本文只是一个参照系统。房子盖好后,脚手架是可以拆除的。
K092
A
1003-4145[2012]01-0070-10
2011-11-15
章益国,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蒋海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