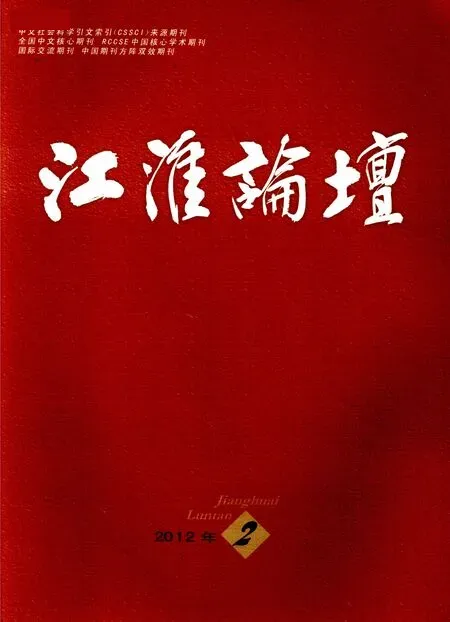“兼以易别”
——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比较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兼以易别”
——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比较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孔孟推崇仁,墨子提倡兼爱,爱是他们共同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追求。与天本论的价值旨趣相一致,孔孟和墨子都请出上天为爱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做辩护,这使爱与天成为儒家和墨家哲学及伦理思想的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孔孟与墨子所讲的爱具有相去天壤的理论意蕴和价值旨趣,在立言宗旨、思想内涵、价值取向、存在方式和行政操作等方面展示出种种差异和对立,体现了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功利主义、维护宗法制度与提倡兼爱平等,以及轻视自然科学与热衷自然科学的不同。如果说儒家和墨家思想的共同点正是两家在先秦成为“显学”的根本原因的话,那么,两家思想的不同点则绝好地解释了秦后儒墨两家相差悬殊的历史命运。
仁;兼爱;孔孟;墨子
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之中,儒墨两家卓然超群、号称“显学”。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之主流,一度被“独尊”、二次被奉为官方哲学;墨学在秦汉之后走向衰微,乃至成为绝学。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先秦,儒墨共显的原因何在?秦后,儒墨一荣一毁的悬殊命运又是为何?本文拟从剖析、比较孔孟之仁与墨子兼爱入手,破解这一千古之谜。
一、爱与天——共同的伦理原则和立论根基
先秦时期,中国思想界学说蜂起、异彩纷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其实,先秦诸子百家的哲学都是围绕着人如何安身立命来展开论证的。在安身即如何进行道德修养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儒家和墨家走到了一起,都把治理国家和改善人际关系的希望寄托于爱;在立命即探寻人的本体依托和形上玄思方面,儒家和墨家不约而同地企盼上天的恩赐与庇护,将人的伦理原则与上天联系起来。呼吁爱与奉天祭天不仅拉开了儒墨与道法诸家的学术分野,而且构成了儒家和墨家思想的相同之处。
1.仁爱与兼爱:爱的渴望和美好情愫
孔子明言“吾道一以贯之”,表示自己的学说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对此,其弟子曾子一语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点明忠恕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与主题。所谓“忠恕”即仁。这不仅证明了孔子思想以伦理思想为核心,而且证明了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在孔子那里,仁最基本的含义是爱人。《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从积极方面看,仁是忠;从消极方面看,仁是恕。忠和恕都是爱人之方,合而言之即是仁。孟子对于仁的弘扬比孔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从人性论角度论证了仁为人性所固有、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且在本体论、认识论领域为仁的确证提供论据。更为重要的是,孟子的“仁政”直接阐述了仁的贯彻实施,使仁从道德观念、先天本性转化为具体行动和治国方略。
无独有偶,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墨家同样以爱来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表现了对爱的渴望和呼唤。墨子作《兼爱》三篇,竭力劝导天子及明君以兼爱施政,臣众以兼爱处世,企图“以兼易别”来避免战争、争夺、厮杀和犯罪,通过“兼相爱”达到“交相利”的目的。
仁爱也好,兼爱也罢,其基本含义与核心都是爱。孔孟之仁与墨子兼爱表明,儒家和墨家都把爱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交往原则,都试图通过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来达到最真诚、最切实的爱人目的。呼唤爱、渴望用爱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儒墨伦理思想的共同之处。这一点在与道家和法家的比较中则看得更加清楚。与道家的超脱出世、对他人的漠不关心和法家的冷酷无情、阴险狡诈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儒家和墨家对人的美好情感和善良之心的呼唤与渴望,仁与兼爱便是这种美好情愫和良好愿望的宣泄和倾诉。孔子强调:“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爱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想要的,要想着别人,给别人机会;自己不想要或不愿面对的,也不强加于人。这用孔子的话说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与此相似,墨子强调,兼爱的具体做法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其”,指自己。兼爱就是在感情上和心理上把别人的一切(包括国、家乃至身)都看成是自己的,就像对待自己的一样倍加爱护和关心。试想,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更真诚、更实在的爱呢!
2.天:立论根基和人生准则
如果说将爱视为最基本的伦理原则是儒家和墨家伦理思想的共同点的话,那么,两家的另一个共同之处便是请天来为爱作证。换言之,为了表明仁和兼爱的正当性、合理性及权威性,儒家和墨家都在上天那里寻找立论根基。孟子认为,正如公侯伯子男是人爵一样,仁是上天赋予人的天爵。因此,仁是天下最尊贵的爵位,也是人心最安逸的住宅。三代以仁得天下,以不仁失天下;个人则以仁保家和保身,以不仁毁家和自毁。墨子同样请出上天为兼爱张目,断言上天具有意志和好恶,兼爱就是上天最大的意志和愿望。
大致说来,百家争鸣的先秦哲学从本体论上可以归结为两个阵营:一是天本论,一是道本论。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之中,只有儒家和墨家哲学以天为本、把天视为宇宙间的最高存在和绝对权威。以天为最终权威注定了儒家和墨家思想的天命论倾向,也预示了其伦理思想与上天密切相关。同样,到天那里为爱寻找立论根据反映了儒家和墨家用上天抬高仁和兼爱的地位的理论初衷,表明了爱与其本体论(天命论)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孔子一面断言上天主宰人的命运、安排人的生死寿夭和贫富贵贱,一面宣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如此说来,既然上天对人命运的注定是一种随机莫测的无言之举,人们无法洞察天机,那么,“畏”便成了人们对待天命的最佳选择,以仁爱等道德方式修身俟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同时,当恪守天命论的孟子把仁说成是天爵时即暗含了仁是上天赋予人的神圣使命和人生追求之意,尽力行道而死、以得正命的主张便是孟子这一心态的最好注脚。墨子一边坚信天志,断言上天可以对人事进行赏罚,一边竭力非命,否认既定之命,断言人的一切命运都与自身的行为有关——为天之所欲得赏,为天所不欲遭罚。既然交相亲爱是天之所欲、相恶相贼是天所不欲,那么,兼爱也就成了人们顺天、法天的不二法门。
总之,渴望爱、呼唤爱、相信人都有爱使儒墨与心仪淡于水之交的道家及血腥残酷的法家在交往原则和为人处世上相去甚远;天又使儒墨与效法自然之道的道、法诸家在本体依托和哲学建构上差若云泥。爱和天在彰显儒墨与道法诸家学术分野、成为两家特色思想的同时,也突出了儒家和墨家思想的共同点。
二、“爱人”与“兼相爱”——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的区别
儒家和墨家都把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并由此产生了与道家、法家的学术分野。进而言之,什么是爱?如何爱?儒家与墨家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充分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思想旨趣和理论特色。简言之,儒家之爱的基本范畴是仁,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墨家之爱的基本范畴是兼爱,兼爱的基本含义是“兼相爱”。孔孟的仁者爱人与墨子的“兼相爱”不论是立言宗旨、理论蕴涵、存在方式还是价值目标、行政操作和社会效果都不可同日而语。这表明,儒家和墨家都高举爱的大旗,但各自的爱之旗帜上却书写着不同的内容、传递着不同的信息。
1.道德理想主义/现实功利主义——理论初衷和立言宗旨之分
同样是对爱的渴望和呼唤,孔孟与墨子的出发点和主观动机判然分明。仁的理论初衷是道德之完善,兼爱的立言宗旨则是功利之追逐。
孔子是一位道德主义者,“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表达了对道义的殚精竭虑。孔子的道,主要是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孟子把仁奉为上天最尊贵的爵位和人心最安逸的住宅。于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便成为最高的道德操守。与对仁的朝思暮想、寤寐以求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孔孟对物质利益和衣食住行的淡漠。正如孔子所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同上)君子具有“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的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为仁而生、为仁而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是行仁义于天下。孔孟之仁的提出是出于道德完善和精神追求的目的,具有浓郁的道德理想主义情结。
墨子提倡兼爱是出于现实的功利主义考虑。在他看来,仁人行事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主观动机和行为后果;要兴天下之利,必须先除天下之害。天下之害是什么呢?墨子解释说:“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人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墨子·兼爱下》)天下之害“以不相爱生”,为了除天下之大害,必须兼爱。兼爱的基本要求是 “兼爱天下之人”(《墨子·天志中》); 兼爱的原则是 “兼以易别”(《墨子·兼爱下》)。可见,兼爱是兴天下之利的根本途径和治天下的最好办法。墨子之所以为实施兼爱奔走呼号,其目的有二: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达到“交相利”的目的,在天与人的关系层面得天之赏。
必须指出的是,墨家和法家都有功利主义倾向,但是,与法家的极端功利主义——损人不利己、为富不仁有别,墨子反对“亏人自利”。兼爱的目的就是追求利益共享,即“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墨子·非攻下》)。按照墨子的观点,推行兼爱是利益均沾、天鬼人共同获利的唯一办法。
2.别/兼——思想内涵和心理机制之别
泾渭分明的主观动机和理论初衷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儒家与墨家之爱的思想内涵和心理机制之别。如果说孔孟之仁的精神实质是别的话,那么,墨子兼爱的原初含义则是兼;如果说仁的心理机制是由己及人的层层推进的话,那么,兼爱的心理机制则是放射性的释放和平铺。
儒家强调“爱有等差”,注重分别是爱人的基本原则。在孔子关于仁的论述中,当作为思想内涵、内心情感和道德观念的仁转化为外在形式和道德行为的礼时,必须做到尊卑有等、亲疏有别、长幼有序,以期整个社会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状态。为了凸显被爱者与爱者的名分和把握爱的分寸,孟子把仁者爱人的等差原则概括为“亲亲”、“仁民”和“爱物”三个等级,进而强调其先后、本末之分,其间的秩序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孔孟之仁的等差原则决定了其心理机制崇奉先后、远近和厚薄之别。对于仁的逻辑结构,有子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表明,孔子所讲的仁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然后将心比心,由己及人,推广到爱别人之亲。于是,孟子宣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在仁之爱人的心理机制上,儒家试图从家庭关系入手由点到面、由近达远、由己及人,达到由爱己之亲、再爱路人乃至爱天下人的目的。这正如孟子所说:“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这再次印证了仁之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的行为路线和逻辑思路。其实,孟子所讲的亲亲、仁民和爱物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更是血缘上的亲疏关系和情感上的厚薄关系。
如上所述,墨子兼爱要求“兼爱天下之人”,并且在向天下之人施予爱时,“兼以易别”:平等地、一视同仁地、同时地加以对待。这里,不仅没有了大国与小国、大家与小家的对峙,而且没有了君与臣、贵与贱、上与下、尊与卑的区分,更没有了强与弱、父与子、众与寡、诈与愚的差异。一旦达到这种境界,便可断绝尊卑、长幼、厚薄和亲疏,不仅可以同时兼爱天下之人,而且平等地兼爱天下之人。
兼爱的平等、同时之内涵预示了其心理机制必然是超越尊卑、贵贱、人我之别的平面铺开。事实果真如此。墨子强调,在给予和承受爱时,人与人之间关系平等。这种平等关系表现为时间和心理上的同时而无先后、本末之分,同时表现为空间和效果上的互动而无强权特权。兼爱的平等原则不仅体现在动机上,而且体现在效果上。首先,从动机来看,兼爱并非“无私的奉献”,兼爱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为此,必须首先去爱他人。墨子断言:“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墨子·兼爱下》)这清楚地表明,兼爱绝不是无偿的,我之所以爱利天下之人,就是为了收获天下人爱我利我之效。其次,从效果来看,只有“兼相爱”才能达到“交相利”的目的。墨子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互动的,并称之为“所染”。在这种关系中,要想获取别人的爱,必须先给予别人爱;你先给予他人爱,他人也会以爱来回报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墨子写道:“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
3.人生目的/获利手段——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之差
孔孟和墨子都讲爱,然而,大相径庭的立言宗旨使儒家与墨家之爱在其价值系统中占有的位置和拥有的地位大不相同。从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来看,仁在追求道德完善的孔孟那里是人生目的和最高价值,兼爱在追逐功利的墨子那里是获得利益、达到“交相利“这一价值目标的手段。
孔孟视仁为价值目标和人生追求。孟子声称:“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这就是说,作为人的本质,仁不仅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内在规定,而且是判断君子与小人的衡量标准。因此,人要由野蛮臻于文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就必须时时刻刻“以仁存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一再强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人的神圣使命使人必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以天下为己任,一有机会便把仁之道德和理想普播天下——孔孟和荀子周游列国,其目的皆在于斯。这表明,儒家把仁视为人生的价值目标和神圣使命。仁不仅是人安身立命之本,而且是为人处世之方。仁是人生的唯一意义和最高价值。
在墨子那里,兼爱既非人的本质,也不是人的本性,兼爱与人之所以成为人并无直接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之所以兼爱具有权衡利弊做出选择的意味。对于兼爱,人们可为可不为。为与不为,对人之所以成为人没有直接影响,不同的只是结果,或得赏而天下治和富贵饱暖,或遭罚而天下乱和贫贱饥寒。换言之,兼爱或不兼爱对人的影响只在于生活境况不同,对人的本质和人之为人却毫发无损。其实,墨子的兼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一个步骤和手段,是达到“交相利”这一目的的过渡环节,绝非目的本身。正因如此,在墨子的话语结构中,“兼相爱”与“交相利”如影之随形。“兼相爱”之后总有“交相利”相随不仅反映出墨子以“兼相爱”之名行“交相利”之实的良苦用心,而且反映出在墨子那里“兼相爱”是手段和前提、“交相利”是目的和后果。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因此,“兼相爱”总是紧紧围绕着“交相利”这个终极目的展开,并且受制于后者。按他的逻辑,“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墨子·天志中》)。天之所欲为何?天所不欲为何?人何为而得天赏?何为又遭天罚?墨子宣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如此一来,兼爱与其说是人的道德操守,不如说是人与天的一种交换。人们兼爱是迫于天的威力——求天之赏、惧天之罚的结果。这正如墨子所说:“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子·法仪》),“今若天飘风苦雨,臻臻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墨子·尚同上》)兼爱是天之所欲,福禄是我之所欲。我行兼爱,天予我以福禄;不行兼爱,必遭天罚。
4.内在本性/外在约束——立论根基和存在方式之异
从立论根基和存在方式来看,孔孟和墨子都在上天那里为爱找到了合理依托和本体证明,这是两家的共同之处。然而,上天如何为爱作证?两家的辩护和具体解释并不相同。儒家尤其是孟子把仁视为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使仁成为人的内在本质和先天本性;墨子把兼爱说成是天之所欲,即上好之、下从之的外在约束。这使仁与兼爱显示出内与外、先天本能与后天抉择等差异。
按照孔子的一贯主张,人的一切命运包括生死富贵、智力才华等都是上天注定的,那么,仁等道德观念也在上天生人之时的命定之列,所以才有了“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的自负。道德是天生的,可见仁对于人而言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东西。孔子的这一思想端倪被其后学孟子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孟子那里,正因为仁是上天生人之时即已赋予人的一种本性和本能,所以,人见孺子入井产生惕怵之心。这种同情、恻隐之心的产生,既非想在乡党之间沽名钓誉,也不是与小孩的父母有交情,更不是因为讨厌小孩的哭声,而是先天的一种本能反应。有鉴于此,他断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孔孟乃至后来的儒家都强调仁与生俱来,是人的一种先天本能或本性。这表明,从存在方式来看,仁是先天的,也是内在的。
墨子的兼爱与上天具有某种内在联系,但决不是孔孟所说的先天赋予,这从墨子的“非命”思想中便可一目了然。兼爱是上天对人行为的一种外在约束。墨子强调,天是宇宙间最高贵、最智慧的存在,人的行为“莫若法天”。对于如何“法天”,墨子写道:“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墨子·法仪》)这清楚地告诉人们,法天就是人的一切行为都以天为法,上天喜欢的便做,上天不喜欢的便止。相爱相利是天之所欲,必须为之;相恶相贼是天所不欲,绝对不能去做。由此可见,兼爱是天之所欲,并非人之所欲,更不是人之本性或本能。所以,兼爱只是人上同于天、顺天、法天的一种方式。甚至可以说,人们之所以兼爱只不过是敬畏上天、讨好上天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已。这再次表明,兼爱对于人而言,只是来自上天的外在约束,决不是内在本性或本能。
5.主体自觉/上者威慑——行政贯彻和操作措施之殊
从行政贯彻和操作措施来看,儒家和墨家的设想有相同之处:因循上层路线,注重由上而下的运作,把推行伦理道德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但是,具体做法却不同。孔孟之仁的贯彻实施依靠君主以及统治者的礼乐教化和率先垂范的道德引导,墨子兼爱的推行凭借上天、君主的好恶、赏罚等行政命令和措施。前者侧重主体自觉和道德自律,后者侧重上天权威和利益驱使。
孔子一再告诉人们:“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正如仁者爱人在孔子那里是道德规范和伦理范畴一样,仁的推行和实施信凭统治者的人格力量和道德感召力,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靠行政命令。基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的认识,孔子把仁的推行寄托在统治者的道德感召力和榜样作用上。他宣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条路线就是孔子的德治主张,德治的突出特征就是靠统治者的榜样作用来带动百姓。按孔子的说法,“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风往哪边吹,草自然就向哪边倒。如此一来,“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孟子行仁义于天下的仁政讲的也是以德服人,主要通过统治者率先垂范的榜样作用和道德感化使老百姓心悦诚服,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孟子的仁政主张进一步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注重主体自觉的思想导向,并且为其具体操作提出了经济上(井田制)、管理上(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和思想上(庠序之学)的保护措施。从孔孟关于仁的贯彻措施和推行操作中可以看出,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是出于主体自愿和道德自觉。行之,没有好处——行仁于天下没有物质利益和经济奖赏;不行,没有恶果——不行仁不会遭罚。孟子的三代以仁得天下、以不仁失天下是就人心向背而言的,与上天的赏罚无关。这使仁始终是道德观念和伦理范畴,不具有法律效力或威严。韩非正是因此揭露儒家伦理道德的软弱无力进而推行法治的。
墨子的兼爱与其说是伦理、道德范畴,不如说更接近于一种法律条文:上天所欲、上者(天子、君主等)所命。正因为兼爱具有法律意义,所以,行或不行兼爱结果不同:正如行之得赏一样,不行遭罚。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子主张兼爱侧重的不是人的主观意愿和主体自觉,而是行为后果。墨子所讲的“尚同”即同于上:在天与人的关系层面,人同于天;在君与民的关系层面,民同于君。“尚同”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在下者必须以在上者的是非为是非,这便是:“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中》)据此,墨子把推行兼爱的希望寄托在君主的命令和好恶上,相信只要君主提倡,上行下效,兼爱很快便会成为一种时尚风行天下。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墨子列举了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楚灵王好士之细腰和越王勾践好士之勇等例子加以说明。在他看来,恶衣、少食和杀身而为名都是老百姓难以做到的,然而,“苟君悦之,则众能为之”(《墨子·兼爱中》),更何况兼爱既容易做到又可以获利,只要君主肯行,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呢!
三、“兼以易别”——儒、墨悬殊命运之探讨
一种学说的历史命运取决于两个因素:理论本身和社会需要。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社会需要最终受理论内容的决定和制约。以此观之,儒家和墨家思想在先秦时期并称“显学”和后来一盛一衰强烈对比的命运轨迹,只有到其理论本身才能找出根本原因。通过对儒家和墨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天和爱:儒、墨同为“显学”之原因
如上所述,儒家和墨家思想的共同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上天的尊崇,一是对爱的渴望。这两点在春秋战国时具有一定的现实需要性,与儒、墨成为“显学”不无关系。
作为中国哲学的萌芽阶段,先秦哲学与宗教处于浑沌未分的合一状态。中国古代没有出世宗教,中国古人的宗教情结却绵长而浓厚,不仅巫术出现很早,而且祭祀之风盛行不衰。在中国先民的世界里,祭天不仅是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大事,而且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早在殷周之际,中国人的上天观念就已根深蒂固。孔孟和墨子以天为本,伸张了上天的地位和权威。孔子断言:“巍巍乎!唯天为大。”(《论语·泰伯》)在此基础上,他一再告诫人们对决定其生死寿夭的上天要敬畏,并虔诚以时地对天进行祭祀。墨子宣称:“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墨子·法仪》)上天的这些美德和品质使其成为宇宙间最高贵、最智慧的存在,人的一切行为“莫若法天”;天有意志和好恶,人们不仅要为天之所欲、不为天所不欲,而且包括天子在内都要“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墨子·天志中》)。孔孟和墨子的言论使天具有了某种宗教意蕴,俨然成了一尊人格之神。这些观点既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传统,又满足了中国人的感情需要,并且弥补了中国出世宗教的欠缺。儒、墨成为“显学”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原因。
有人说,东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酷烈、最黑暗的一页,臣弑君、子杀父事件屡屡发生,致使西周之礼遭受致命打击。与此同时,法先王和复古情结更让人感到今非昔比。面对群雄逐鹿的混乱不堪,爱对于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社会现实不啻为一种心理安慰和理论补偿。正因如此,尽管用道德手段治理国家和以爱处理人际关系不如法家的法治主张来得直接实惠、收效明显,但爱的主张和以爱为核心的德治、仁政主张表面上易被统治者提倡。这一点在孔孟周游列国的遭遇中得到了绝好的说明。各诸侯国不采纳儒家以道德手段治理国家的主张,却在表面上表示欢迎,孟子还被“加齐之卿相”(《孟子·公孙丑上》)。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爱的呼吁和主张在先秦时期具有一定的现实土壤,迎合了统治者的某些需要,如收买人心、笼络人才等;同时也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心声,如向往和平、改善人际关系等。循着这个逻辑,为爱奔走呼号的儒家和墨家成为“显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2.别与兼:儒、墨命运悬殊之秘密
儒家和墨家思想具有相同之处,其间的差异和对立同样不容置疑。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与墨家的兼爱不仅浓缩了儒家与墨家思想的差异和对立,而且生动地展示了其悬殊命运的真正原因。
第一,根深蒂固的宗法等级观念。中国古代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宗法等级社会,自然亲情和人伦纲常被视如神圣。同时,中国是闻名于世的“礼仪之邦”,礼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思想内涵和社会功效来看,礼在中国古代社会集道德与法律于一身,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中国古代社会之礼,最基本的特征和功能就是分、别。与此相联系,君权神授、君主就是法律、父权制、家长制和人情网等得到绝对认同。在这方面,儒家关于“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说法以及“爱有等差”的原则直接为宗法等级辩护,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儒学在汉代和南宋两次被奉为官方哲学便是明证。与此不同,墨子的兼爱要求视人之国、人之家乃至人之身若视其国、其家和其身,这淡化了人、己之别,直至隐蔽了吾之君、吾之父优于人之君、人之父的特权。更有甚者,兼爱中流露的天与人、上与下的平等、互惠和互利原则冲击了在上者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孟子抨击墨子的兼爱思想是禽兽逻辑,指出“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和大众心理。由此,儒家与墨家一传一绝的不同命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注重道德完善、漠视物质需求的义利观。中国人的义利之辨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辨,指分别。义利之辨强调义(道德完善和精神追求)与利(物质利益和生理需要)的区别及对立。在义与利的这种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中,中国人注重前者、热衷于义,淡漠后者、耻于言利。
前面的比较、分析已经显示,孔孟与墨子所讲的爱具有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之别,这在仁与兼爱的理论初衷、思想内涵、操作方式和社会效果等各个方面均有反映。与孟子所说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相反,墨子以“兴天下之利”为目的。孟子的“何必曰利”符合中国人耻于言利的大众心理和价值取向,为历代统治者所提倡,墨子的尚利倾向却为中国人所不耻(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儒家与墨家不同的历史命运可以在其对中国人心理倾向和价值评判的一迎合、一逆忤中得到解释和说明。
第三,轻视自然科学的价值取向。大致说来,人文科学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自然科学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与义利之辨相对应,中国人历来对自然科学以及相关的科学技术采取轻视乃至蔑视的极端态度。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学说被奉为“大学”,意即高深、高等的学问;与之对应的小学是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由此可见,不论是高等的还是低级的学问之中都没有自然科学的位置,自然科学根本不在学问之列!孔孟之仁涵盖了哲学、伦理、政治等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惟独没有自然科学。墨子兼爱不仅具有哲学、伦理和政治内涵,而且包括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等内容。技术是达到利益的手段,在这一点上,科学技术与兼爱异曲同工,价值是一样的。例如,为了非攻,墨子研制了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和备蛾傅等技术、技艺和设备。此外,墨子的思想体系中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的内容,如力学、物理学、光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工艺技巧在中国古代被贬为雕虫小技,热衷于自然科学被视为玩物丧志和不务正业。不难看出,蔑视与崇尚自然科学与儒墨之间一荣一辱的历史命运具有某种对应关系和内在联系。
总而言之,如果说以天为本和爱的呼唤是儒家和墨家在先秦成为“显学”的共同原因的话,那么,儒家与墨家之天和爱的理论精髓和社会效果的迥然相异则是两家历史命运相差悬殊的根本原因。正如维护宗法等级制度、追求道德完善和轻视自然科学是儒家显赫地位的理论支撑一样,兼爱平等、利益追逐和浓厚的自然科学情结及工艺技巧之长则是拉开墨家与儒家学术地位之距离乃至墨学最终沦为绝学的主要原因。
[1]吴毓江.墨子校注[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2]孙诒让.墨子间诂[M].孙其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3]刘宝楠.论语正义[M].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4]程树德.论语集释[M].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5]焦循.孟子正义[M].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责任编辑 吴 勇)
B222;B224
A
1001-862X(2012)02-0079-007
魏义霞(1965-),女,安徽濉溪人,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哲学与文化。
——Revisiting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betwee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Confucian Tra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