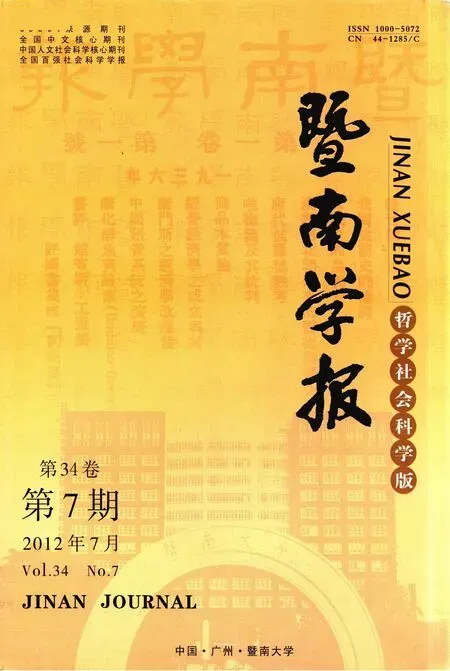“他者”的想象
——解读《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的构想
陈 瑜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他者”的想象
——解读《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的构想
陈 瑜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杜赞奇认为,民族“自我”大多都是相对“他者”而定义的。在晚清文人志士的自我认同和民族想象中,“西方”和“妇女”是他们指称的最多的“潜在的他者”。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所展开的想象,不仅展现了作者书写异域文化的策略,也可让我们从中一窥晚清知识分子在倡导民族革新的过程中,如何通过“他者”来认知“自身”。
民族想象;他者;自我;西方;妇女
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民族主义一般被看作一个社会中压倒其他一切认同,诸如宗教的、种族的、语言的、阶级的、性别的、甚至历史之类的认同,并把这些差异融会到一个更大的认同之中。然而,即便此种融会一时一地取得成功,但不同的自我意识群体对民族的构想和表达仍大异其趣。”[1]8他提出:“民族观的多样性以及政治认同的变动不定性使我们最好把民族主义看做相对性的身份。……作为成员之间的关系,民族‘自我’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对于‘他者’而定义的。民族自我还根据对立面的性质和规模而包含各种更小的‘他者’——历史上曾经互相达成过不稳定的和解的他者和潜在的、正在建构其差异的他者。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正是这些潜在的他者,因为他们向我们展示出创造民族的原则——志愿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有意突显自己的差异并掩盖把它与社会学意义上的近亲联系起来的文化纽带。”[1]14
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场运动的主导者是男性知识分子,正如杜赞奇所说,这些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民族“自我”大多都是相对“他者”而定义的。在他们言论中,充满了“他者”和“自我”的二元对立表述。而被指称得最多的“潜在的他者”有两个,一个是“西方”,一个是妇女。中国民族意识启蒙初期,“西方”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意义丰富的符号,它既是进步、文明的代表,是中国人欲求的对象;它又带着无法革除的异族色彩,被人抵御和排斥。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宰者是男性知识分子,“妇女”,在男性知识分子的眼中,同样具有双重面向。就历史脉络而言,从晚清到五四,传统妇女既被当作异类的他者,排斥在“新”民族之外;同时又被当成“国民之母”,成为民族振兴的重要力量。“西方”和“妇女”就这样在“民族”的“内”和“外”之间摆荡,左右着中国人(主要是男性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和民族想象。为此,我感兴趣的是,这些男性知识分子在倡导民族革新的过程中,是如何操纵“西方”和“妇女”这两个元素,并利用了怎样的语言和修辞方式来建立对此二者的想象?
要探讨上述问题,晚清文人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极富研究意义。它是中国近代本土知识分子翻译的最具影响力的外文小说之一。在这部小说身上,集结了“西方”、“妇女”两种显而易见的元素,而且该作品得到了当时大部分读者的认同,并成为了中国本土作家学习模仿的对象。此作品的翻译不仅展现了作者对异域文化的颇具成效再现策略,同时也能让我们从中一窥晚清时期“异域文本”是如何融入本土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建构中。
《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原著为法国作家小仲马(Alexandre Dumas(fils)1824-1895)出版于1848年的La Dame aux Camélia。小说讲述了一个悲情浪漫故事。巴黎名妓马克(以下人物均按林纾作品中的译名),别名“茶花女”,爱上了资产阶级青年亚猛,马克为了表示对爱情的忠贞,拒绝了其他情人的供养,希望放弃一切与亚猛厮守。亚猛的父亲得知后,横加阻挠,劝说马克为了亚猛的前程和亚猛妹妹的婚约着想,牺牲自己,结束这段感情。马克接受了亚猛父亲的请求,制造了变心假象,让亚猛怀着怨恨离开了她,她自己也在悲痛和疾病的折磨下,郁郁离世。亚猛在她死后才发现事情的真相,但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
《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于1897年,1899年在福州印行出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该书的翻译者林纾并不懂外文,他是通过别人的口译来完成翻译的。对一个不懂外文的翻译者来说,要凭他人的口述来想象一个异域的世界,起码在技术层面上充满困难。但是这部小说出版后,却取得极大成功,一时文人学士争说“茶花女”成风。“茶花女”形象,深深打动当时的中国青年。晚清著名翻译家严复形容这种状况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2]305。“茶花女”成为当时知识青年心仪的对象,它的影响贯穿整个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时期,为知识青年探求西方、想象妇女提供了重要的窗口。通过《巴黎茶花女遗事》,我们可以窥探“茶花女”是如何从一个异族的“他者”变成一个本土的偶像,林纾及其他的阅读者又是如何通过“茶花女”想象西方、民族和“自我”。
一、林纾译书的背景
茶花女故事讲述的大约是1842-1847年间法国巴黎发生的事情。翻译者林纾从未到过国外,也对外文一窍不通,他是如何想象这个异域的呢?
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过程。林纾生于1852年,正值“西方”入侵、中国国势渐弱的年代。林纾在乡间接受传统的诗文教育,28岁中了举人,成为中国清朝知识分子中的一员。19世纪90年代,林纾的生活出现了几件大事。首先是国事,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大败;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海军被日本海军打得全军覆没。这些事实无不告诉林纾,在他的生活里,有一个强大而充满危险的“西方”。林纾曾做《国仇》一诗表达对“西方”入侵带来的危机感和愤恨之情。诗云:“国仇国仇在何方?英俄德法偕东洋。东洋发难仁川口,舟师全覆东洋手。……波兰印度皆前事,为奴为虏须臾至。”[2]300其次,是家事。1895年前后,林纾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女人——母亲和妻子相继离世,林纾心中充满了对她们的思念和哀悼之情。以上的陈述,是为了说明,“西方”的入侵和母、妻的离世,这两件看似毫无相干的事情,却直接促成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因为,“西方”带来的危机感,使得林纾开始积极地投入改良维新运动。他与一帮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友人紧密接触,议论中外时事,共谋救国大计。1897年的一天,友人齐聚,聊起法国小说,林纾请他们讲讲,其中一位叫王寿昌的就谈起了小仲马的《茶花女》,朋友们见他因母亲、妻子的离世郁郁寡欢,就劝说林纾翻译这部小说,以此消解愁闷。林纾答应下来,便与王寿昌一起翻译《茶花女》。
王寿昌精通法文,他曾被清政府选派留学法国。据林纾记载,他们的翻译过程就是王寿昌口译,他笔录。所谓“为余口述其词,余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3]251-252。这样的翻译方式和翻译速度,在今天看来,实在有些匪夷所思。“口译——笔录”的翻译方式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恰是这样的翻译方式,造就了一部奇异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巴黎茶花女遗事》讲述的是一个异域的故事,但是在小说中,却充满了中国的物质、礼俗和人物形象。如果按照直译的评判标准看,将林纾的译文与原文对比,肯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按照归化理论看,正如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所说:“一般而言,翻译者的目的在于传述一个异域文本,因而翻译工作便为一个变化多样的对等观念所制。……因此,一个译本传述的异域文本总是有偏颇的,是有所改动的,补充了译语的某些特质。事实上,只有异域文本不再是天书般地外异,而是能够在鲜明的本土形式上得到理解时,交流的目的才能达到。”[4]9-25林纾在对异域文本的改造和本土文化的建构上,自有他的困难和成功之处。以下本文便通过物质和观念意识两个层面的再现来分析林纾在《巴黎茶花女遗事》文本中所使用的修辞策略以及被他放逐的“自我”和“他者”的想象。
二、林纾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如何描摹“西方”物质世界?
相比精神世界,西方的物质世界对中国人来说,更加奇异、直观。林纾在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描摹法国——这一个陌生的物质世界。
我们先看一段描述,马克死后,她生前所积累的财物被人拍卖,英文译本是这样描写拍卖场上的物品:
For the rest,there were plenty of things worth buying.The furniture was superb;there were rosewood and buhl cabinets and tables,Sevres and Chinese vases,Saxe statuettes,satin,velet,lace:there was nothing lacking.①法文原文:Du reste,il y avait de quoi faire des emplettes.Lemobilierètait superbe.Meubles de bois de rose et de Boule,vases de Sèvres et de Chine,statuettes de Saxe,satin,velours et dentelle,rien n’ymanquait.(Alexandre Dumas(fils).La Dameaux Camélias[M].Paris:CALMANN -LÉVY,1965.p20),[5]7
但林纾对这些琳琅满目的奇异物品,只用了一句话来描述:
“唯见其中瓷器锦绘,下至玩弄之物,匪所不备。”[6]1
译文的精简显而易见。原文作者精心描写的富丽堂皇的物件,在林纾的笔下,变得那么模糊、生涩。译文的生涩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1897年,远在中国的林纾根本无法想象这些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过的奇异的物品,自身见闻的不足使他难以展开他的想象;第二,古代汉语,一种已扎根于中国近2000多年的古老语言,在描绘奇异的西方物质世界时,显出了它的局限。林纾从他熟悉的这种语言中,根本无法找到可以描摹这些物件的词汇。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谈民族想象的时候,非常强调语言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比语言更能将民族的不同个体联系起来,让民族成员在情感上互相呼应[7]66-79。但此时看来,语言,对林纾来说,成了一把双刃剑。他使用本土的词汇和语言,虽然能将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历史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能引起本民族读者的共鸣;但另一方面,这种语言,又无法帮助他探索一个“他者”的世界。在这个层面上说,林纾的翻译充满了挑战。当然,林纾不会因为语言和自身见闻的局限而放弃了对西方的探知和描摹。由是,他所采用的应对策略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1)英文译本:I remembered having often met Marguerite in the Bois,where she went regularly every day in a little blue coupé drawn by twomagnificent bays…[5]13
林纾的译文:马克常好园游,油壁车驾二骡,华妆照眼……[6]2
马车是19世纪法国妇女出行的重要工具,它是法国妇女财富和地位的象征。马克搭乘的马车本是“两匹栗色骏马驾着的蓝色小四轮轿式马车”[8]9,雍容华贵。但林纾将它写成“油壁车驾二骡”,他用中国十七八世纪仕女出行的工具来指称马克华贵的马车,虽然在现代读者看来,这有些啼笑皆非,但是经过林纾这样的中国化的转译,原来非常西方化的女子出行场景,竟被勾画成一位古代中国仕女的出行图,任何西方的色彩都没有了,变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场景。
从上面例子可见,面对一个陌生的西方世界,林纾采用了删减和转译的方式,为异域的物件披上了本土的外衣,但是这样的做法也并非总能行得通。看以下一个例子:
(2)英文译本:The first time Ihad seen her was in the Place de la Bourse,outside Susse’s .[5]56,①David Coward在他所翻译的《茶花女》一书中已经考究过这两个地方,同时发现以下信息:Michel-Victor Susse(1782-1853)是一名艺术品经营者、古董收藏家、纸及艺术品原料的供应商。除了在德拉交易所31号的这家商店外,他在“7 and 8 Passage des Panoramas”还有一些其他的商铺。(见 Alexandre Dumas(fils).La Dame aux Camélia[M].Trans.David Cowa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4,p42/p210)。
林纾的译文:余第一次遇马克于刳属之市,……坐一丽人,翩然下车,适一珠宝之肆,……[6]8
这个例子,亚猛回忆起他和马克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们邂逅在交易所广场的Susse’s商店,Susse’s商店坐落在法国的交易所广场旁,这个地方在法国巴黎的第二区,第二区位于塞纳河的右岸,以巴黎歌剧院为中心的地区,它是巴黎商业活动最密集之处,也是充满了文化气息的地域。Susse’s商店专门卖艺术品,小说写到,亚猛看着美丽的马克轻盈地走入商店,高贵文雅。但是林纾却将Susse’s商店译为“刳属之市”。“刳”为古代汉语的用词,是屠宰的意思,“刳属之市”,意思就是牲畜交易、屠宰市场。在晚清中国,最典型的交易之处就是牲畜交易市场,林纾由此直接用“牲畜交易市场”来指称“la Bourse”,将“交易所广场”这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场域变成一个血腥污浊的屠宰市场。或许林纾本人也觉得马克,这样一位窈窕淑女,只身前往屠宰市场,实在有些说不通,所以,他又灵机一动地在屠宰市场旁兀自加上一个“珠宝之肆”,然而无论他怎么润色,都让现代人无法理解,怎么屠宰市场旁会有珠宝店,马克又会到屠宰市场旁的珠宝店买东西?本来清雅的艺术品商店,在林纾的笔下,变成了粗俗的屠宰市场,这不得不让现代人觉得匪夷所思。而这一类的破绽,也恰恰能让我们看到林纾在翻译中所放逐的“想象”。
当然,林纾也努力去弥补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可能带来的谬误。比如,林纾在翻译中,遇到“法郎”(franc)这种货币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音译词“佛郎”来翻译。并在“佛郎”后加上一段注释,说明“每佛郎约合华银二钱八分”[6]2。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林纾是怎样把他本人的东方经验巧妙地置换到西方的物质世界中。比如,歌剧院,他译为“戏园”;咖啡馆,他译为“茶肆”;而沙发,则变成了“长凳”。
这一切无不说明,林纾的翻译,总体上是一种典型的以主体文化代入的做法,就是将西方的、异域的东西全都置换为本土的、熟悉的物事,这样做的直接效果就是,“西方”被他主观地同化了,“西方”并不是一个他意欲探索的未知的新的世界,而是一个假想的与本土一致的“同化”(naturalized)的世界。对“西方”世界中的现代物事,林纾并没有用一种异化的方式来描摹他们,而是把它们改造,让他们进入自己原有的认知体系中。在林纾的眼中,“四轮马车”就是“油壁车”,“他者”仅是“自我”的印照而已。
在林纾生活的那个时代,“西方”的物件其实已进入了中国,李欧梵曾介绍说,“事实上,现代都市生活的绝大多数设施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传入租界了:银行于1848年传入,西式街道1856年,煤气灯1865年,电1882年,电话1881 年,自来水 1884 年……”[9]6-7但当时的传统知识分子,还在固守在他们的语言和词汇,还没有准备在自己的认知系统中赋予“西方”一个位置。“西方”只是被他们作为一种工具,用以实现救国的理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林纾在他的一篇序言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他说:“今黄人之慧,乃不后于白种,将甘于红人之逊美洲乎?余老矣,无智无勇,不能肆力复我国仇,日苞其爱国之泪,告之学生;又不已,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10]167此番言论,将他通过译著实现报国理想的想法表露无疑。事实上,“西方”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是他实施救国的领地,是他在飘摇的世界里,感知自我能力、价值的工具。
林纾一生翻译了160多部外文小说,他所有的译作基本都用文言文进行翻译,林纾始终固守着他的“语言”、他的“想象”,他通过这些想象建构了自己探知西方世界的独特方式,在这种方式的背后,是他对自我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事实也证明,他的这种执着一直持续到他死去。根据《清史稿》记载,他数十年内坚持拜谒清朝皇陵,通过这种方式坚持自己对那个逝去的清朝帝国的怀念和难以割舍的深情。
三、林纾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如何改造“马克”?
谈及林纾的翻译,周蕾(Rey Chow)曾说,相传林纾和王寿昌合译《茶花女》时,两人经常为某些情节而大哭起来,声闻屋外。而每当她引述这个故事给旁人听,听者莫不大笑,屡试不爽[11]235。在周蕾看来,听众之所以大笑,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两位血气方刚的男子会为一篇情节虚构的小说和一个虚拟的“美人”(马克)大声痛哭。这种过分的情感表现,在现代人看来,确实非常戏剧化。可是如果联想中国古代文人的赋诗作词经历,就会发现这样“痛哭”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遇见卖唱的琵琶女,不同样也是潸然泪下?无论是林纾还是白居易,在“美人”面前大声痛哭,其实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感动,而是由此及彼,借“美人”之象,哭己之怀而已。
中国自古,借“美人”而哭,以“美人”自比的现象十分常见,且在春秋时期的屈原那里登峰造极。屈原的《离骚》等诗篇全都是以“美人”比喻君王、自我和贤臣的。这种借“美人”抒发自己胸怀的修辞方法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中已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习惯。
在林纾生活的年代,借用“美人”及“美人”的爱情故事来表达自我情怀的做法并不少见,所谓“以今日小说界上大放光明,多有借男女之浓情,曲喻英雄之怀抱者”[12]209,而且这个时期的“美人”书写还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屡屡使用“西方美人”。有人统计,“在1910—1920年十一卷《小说月报》中,‘西方美人’是出现得最为频繁,且所用描述性词汇最为固定的形象。其刊登的470篇以‘异域’为表现题材的小说作品里,直接以‘美人’或‘女郎’为标题的小说就有15篇之多,平均每卷有一篇。而标题中出现与美人相关意象者,则更是多不胜数。”[13]70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美人”和爱情故事都能成为抒发情怀的对象,都会受到赞许,只有那些“诚贞而不淫者”[14]287才会被人认可。为此,很多文人都写文章力图辨析清楚,哪些小说所写的情是有利的,哪些情是有害的。一位署名“伯”的作者写道:“艳情小说云者,非徒美人香草,柔肝断肠,导国民于脂粉世界中,作冥思寐想之讨生活已也。彼作者,固早挟一至情之主宰,借笔墨而形容之、流露之,以寄托其固结之爱情而已。……然则小说家之注意一女子,极写其缠绵恻怛之意者,是诚默体社会之情,而主动其无形之输灌力也。”[12]209林纾也持有相近的观点,他提出:“小说足以动人者,无若男女之情。……余译书近六十种,其最悲者,则《吁天录》,又次则《茶花女》,……”[15]331而且,他还将欧洲女子分为几种,只有“有学而守礼”者,才最为他看重。
用上述标准审度《巴黎茶花女遗事》,按照原小说所写,马克是巴黎名妓,她生活奢侈,夜夜笙歌,这样的一位女子要达到以上“诚贞不淫”、“有学而守礼”的标准实属不易。但客观的事实是,当时中国读者,大部分都被林纾笔下的“茶花女”感动得泪眼涟涟,直把“茶花女”视为心中的偶像。林纾是怎么有生花之笔,将一位名妓变作一位感人至深的“美人”?从小说内容看,林纾起码做了以下的努力:
第一,将女主角“马克”的形象东方化。
马克是绝色美女,这在小说原文中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林纾却在他的脑海中构想了另一个更切合中国审美观、更东方化的马克。
Edmond Gosse的英译本是这样描写马克的美貌:
It is impossible to see more charm in beauty than in that of Marguerite.Excessively tall and thin…Her cashmere reached to the ground…
Set,in an oval of indescribable grace,two black eyes,surmounted eyebrows of so pure a curve that it seemed as if painted;veil these eyes with lovely lashes,which,when drooped,cast their shadow on the rosy hue of the cheeks;trace a delicate,straight nose,the nostrils a little open,in an ardent aspiration toward the life of the senses;design a regularmouth,with lips parted graciously over teeth as white as milk;colour the skin with the down of a peach that no hands has touched,and you will have the general aspect of that charming countenance. The hair,black as jet,waving naturally or not,was parted on the forehead in two large folds and draped back over the head,leaving in sight just the tip of the ears,in which there glittered two diamonds,worth four to five thousand francs each.[5]14
林纾的译文则是:
马克身长玉立,御长裙,仙仙然描画不能肖,虽欲故状其丑,亦莫知为辞。修眉媚眼,脸犹朝霞,发黑如漆覆额,而仰盘于顶上,结为巨髻。耳上饰二钻,光明射目[6]2。
两相对比,两个不同的马克跃然纸上,前者热烈娇媚;后者则端庄娴静,一如古典美女。细看林纾的描写,“长身玉立”一词与 Edmond Gosse笔下的“身材歆长”基本相吻合;“御长裙”一词则取代了“开司米大披肩”,最明显改变的,就是头发,Edmond Gosse的译文中,马克的头发是分两咎披在额前,还有波浪型卷曲。林纾却写成一个大髻,中国女人的大髻,实在妙。
只要看林纾自己所写的小说中女子的模样,便可明白,林纾对马克的这番描述其实是他对“美人”的定势印象。在他自己创作的小说《柳亭亭》中,江南名妓柳亭亭的样貌和马克的如出一辙:“亭亭天然美丽,发黑如漆,初无钗珥之属,但缀明珠于髻端,光色照明,愈增其发美。”[2]67
林纾对马克的这番改造不仅符合他脑中“美人”应有的模样,而且也是当时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对女子的普遍“想象”。吴燕对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上所写“西方美人”形象进行总结,发现翻译作品对女性人物的外貌描写也都“惊人地类似,无比空洞”,如:“身高而貌丽”、“明眸斜盼”,“灿艳夺目”[13]71。看来,以自己的理解,来想象西方的女子,是当时中国文人普遍的做法。
第二,美化“马克”的品性,规范其行为。
在晚清文人眼里,女子的德行比美貌更为重要。林纾在他的诗文中,不断夸奖那些有良好品德且遵守礼法的人。他说女子应该“深于情而格于礼,爱而弗乱,情极势逼,至强死而自明”。[16]165甚至,林纾觉得提倡女权、女学,都应该把遵守礼法作为重要的准则“惟无学而遽撤礼防,无论中西,均将越礼而失节。故欲倡女权,必讲女学。”[16]165
何谓“礼法”?按社会学家费孝通介绍,旧式中国是一个“礼治的乡土社会”“礼”,指的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17]71。胡缨对林纾笔下的“礼法”也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
“礼法”,或者简称为“礼”,是林纾在译作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作为儒家经典中的一个核心原则,“礼法”的大意是指礼节的正确性或合宜的准则。在特指约束两性关系的准则时,“礼法”与男女各自领域的区分紧密相关。[18]96
如前所说,林纾翻译小说,除了介绍西方之外,更重要的指向是以译书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但毕竟西方的人和事,未必都能符合他救国的理念。特别是《巴黎茶花女遗事》这种,描写风月女子、谈论男女之情的,更是容易触犯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恪守礼防、以“礼”约束的做法成为林纾在翻译过程中,规避情欲和礼法冲突的重要手段。由此,林纾的译文,要特别注意他是如何巧妙地、不动声色地将其中有违礼法的举止行为正常化。
我们从译本中摘取一例,便可看出林纾的巧妙笔触:
马克面对亚猛的求爱,坦诚地对亚猛说明,按照她的身份,难以忠贞地对待亚猛的爱情:
英译本:Supposing one day I should become yourmistress,you are bound to know that I have had other lovers besides you.[5]91
林纾的译文:我何能于未识君前为君守贞?且我迎南北送,匪君一人,若人人初见时悉如君憨状,我将何堪?[6]14
此处,林纾做了巧妙的转换,英译本说,“即使我成为了你的情人,我都不可能钟情于你一人”。但是林纾却将译文改为,“我未认识你,我怎么能为你守贞”。林纾稍稍改动其中的时间,就让马克的行为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英译文说的是,即使我们认识后也不可能钟情于你一人,用情不专之念表露无疑。但林纾的改动,使得马克的行为变得合情合理,因为不认识,所以谈不上对你忠贞。对于我成为你情人后,我是否会为你守贞,则隐而不谈。
从上面的例子可见,林纾在翻译中多处微妙用笔,将原本有违于礼法之事变得相对合乎情理,甚至在原来与礼法毫不相干之处也被借用来大书特书礼法之重要。经过他不动声色的改造,原文小说的妓女马克在林纾所译的小说中也被称为“至贞至洁”的女子。
我们再回到林纾和王寿昌大哭的问题,如果说林纾不懂外文,在翻译过程中任意遐想,这情有可原,但是王寿昌是精通法文的,他就不知道林纾的译文与原著存在偏差吗?为何反倒受其感染,并与他同声大哭呢?他们在“茶花女”形象身上寄托了怎样的情思?
林纾是这样描写他哭的情景的:
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士大夫,而士大夫中必若龙逄、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竞。盖马克之事亚猛,即龙、比之事桀与纣,桀、纣杀龙、比而龙、比不悔,则亚猛之杀马克,马克又安得悔?吾故曰:天下必龙、比者始足以竞马克。[19]198
从上面看,林纾触景而哭的原因,不独独在马克之死,更重要在于两点,第一,无论马克还是龙逄、比干,他们都是因其主宰者的误解而死,这种报忠无门的委屈让人动容;第二,马克、龙、比至死都仍然不后悔。这种至死不渝的态度,让人悲泣。
联想林纾和他的朋友王寿昌等人的现实经历,他们何尝不也是报忠无门,但又恪守救国大志至死不渝?而且,晚清,这一类文人比比皆是,从这个角度看,“茶花女”其实被用作了纾解晚清知识分子心中悲怨的工具。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她使林纾和他们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成员”们能跨越“空洞的时间”[7]8(导读)和遥远的地域连接在一起,共同捍卫他们的群体——民族。
四、结 语
以上,本文以《巴黎茶花女遗事》小说为例,探讨了在中国语境下,“西方”和“妇女”这两个符号是如何被民族知识分子想象、改造以实现其民族理想的。但西方、东方,妇女、国族之间的复杂关系,还存有很多探索的空间。台湾学者刘人鹏曾就中国女权主义的翻译,引用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话指出在“东—西”二元框架下,妇女面临的复杂境遇:“西方是外在世界,而内在于家的东方,既不能心醉西风又不能墨守故纸。在国族内部性别与国家的关系上,一方面要求妇女要成为‘新女性’,一方面又充满了对‘新女性’之不纯净的焦虑;‘她’既要与西方女性不同,又要与传统女性不同。又由于国族主义对于男/女、内/外、物质/精神的思考形构未变,‘新女性’也就仍要在新的父权体制下被定义。”[20]86
在民族主义话题继续升温的今天,在不同民族主义计划里,妇女承担了什么角色,妇女的特殊境遇会给我们重新审看民族国家、公民身份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开辟了什么新的视角?这一切问题都有待我们继续思考。
[1](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林薇.林纾选集(小说卷上)[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3]林纾.孝儿耐女传序.转引自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G].北京:中华书局,1960.
[4]Lawrence,Venuti.“Trans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In Cultural Function of Translation[G].Eds.Christina Schäffner and Helen Kelly -Holmes,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6.
[5]Alexandre Dumas fils.Camille(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M].Trans.Sir Edmond Gosse.Intro.Toril Moi.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2004.
[6]林纾.茶花女遗事[M].素隐书屋托昌言报馆代印本,乙亥夏(1899).
[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法)小仲马.茶花女[M].王振孙,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
[9]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0]林纾.雾中人叙[C]∥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0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1]周蕾.中国妇女与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M].台北:麦田出版社,1995.
[12]伯.义侠小说与艳情小说具输灌社会感情之速力[C]∥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0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3]吴燕.清末民初的“西方美人”——以《小说月报》为例[J].上海文化,2006,(5).
[14]光翟.淫词惑世与艳情感人之界线[C]∥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 -190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5]林纾.不如归序[C]∥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0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6]林纾.红礁画桨录序[C]∥见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0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7]费孝通.乡土社会[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18]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彭姗姗,龙瑜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9]林纾.露漱格兰小传序[C]∥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
[20]刘人鹏.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
I106.4
A
1000-5072(2012)07-0103-08
2012-02-15
陈 瑜(1979—),女,广东吴川人,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妇女、性别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