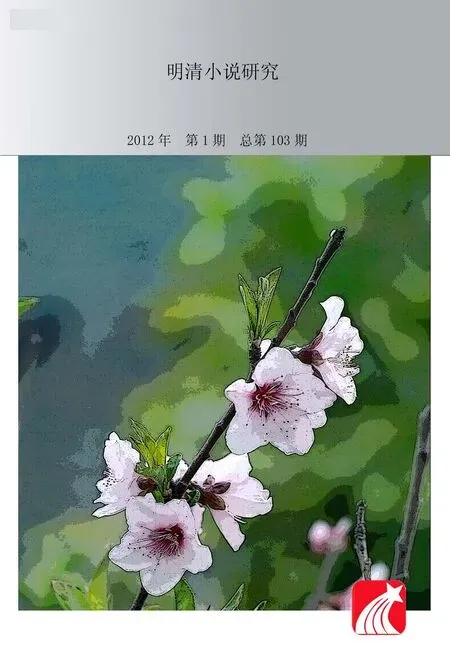断裂的叙事:《醒世姻缘传》之长篇章回短篇化
··
《醒世姻缘传》洋洋洒洒一百回,按照因果报应轮回的观念模式,敷衍出以晁、狄两家为中心,勾连计、薛、童诸家并触及社会众多层面的两世恶姻缘,表达了作者警示劝人、醒世讽人的目的,不可不谓用心良苦。面对这部大书,病中偶得之的徐志摩惊以为神。他在序言中誉之以“我们五名内的一部大小说”①,详述其与太太共读之乐,并为《醒世姻缘传》做了热情洋溢的推销之辞。徐志摩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但颇多诗人之浪漫与夸张,“或许只是故作惊人语”②。事实上,“这部小说,如今没有几个学生会有耐心仔细地阅读它,更不会有多少人会对它进行彻底的批评分析。除了少数讨论作者问题的学术文章外,实际上还没有将这部小说作为文学文本而进行的认真研究”③。浦安迪不无惋惜地一语道破了目前学界对于《醒世姻缘传》研究的尴尬——一方面将其视为上承《金瓶梅》,下启《红楼梦》的过渡桥梁,“堪称明清‘人情小说’的三朵奇葩之一”④,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却又囿于作者及成书年代的考证、主题思想辨析和方言语料分析等狭小圈子而难以迈出“文学”研究的脚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而徐氏与浦氏两人判若天地的评价也着实令人疑窦丛生——《醒世姻缘传》的“文学”价值究竟怎样?
“小说的基本层面就是讲故事的层面”⑤,这似乎将我们的目光固定并聚焦在了小说的内容上。因此,我国传统白话小说的研究往往无法逃离伦理道德批评的藩篱。重视故事本身无可厚非,但仅有故事还远不能为小说,因为故事必须被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讲述出来。于是,叙事——小说形式层面的重要标识,便成了小说的命脉,成为研究小说“文学”价值绕不过去的话题之一。然而目前学界对《醒世姻缘传》叙事的关注不够。仅有的研究成果部分地承认了小说叙事中存在的冗杂、混乱等问题,但总体倾向是在混乱中寻找秩序,在无法中寻求法度,为这部小说的叙事建立起坚实的合法性。即便就是断言“《醒世姻缘传》绝不是一部经过精心锤炼的小说”⑥的浦氏,也不得不套用“十回的单元”模式来解释作者其实存在精细的构思,颇有一点欲扬先抑的味道。于是,研究界遂有了“平行结构”⑦、“初始牛排结构+网状结构”⑧、“外在因果报应结构+内在虐恋结构”⑨、“立体性双坐标结构”⑩等诸多模型,从不同层面阐释、证明《醒世姻缘传》叙事的精巧和作者构思的缜密。这一倾向无意中透露出学界的焦虑——地位如此重要的小说怎能没有完美的叙事与之相匹配?这一倾向也反映出研究者缺乏直面缺陷的勇气。事实上,西周生真的有这般精巧的构思和流畅的驾驭么?在笔者看来,事实也许并非如此。
《醒世姻缘传》一书内容驳杂,两条线索交织错乱。“从故事内容来看,《醒世姻缘传》出现过的人物多达二百三十余人,这样的‘阵容’本来就容易导致主轴故事流于庞杂繁冗,因为过多的人物或是过大的空间,对小说创作者本就是一大难题,对读者来说也很难仔细逐一品位,反倒有乱枝杂刺的遗憾。”如果说刘佼的批评多少还有点客气的话,那么浦安迪则无疑尖锐了很多,“大多数现代读者所得到的最初印象是该作品结构上的极度混乱,或者至少其叙事运作是不规则的”。探究产生这种混乱、不规则的感觉的原因,也许有人物过多、空间过大等诸多客观因素,但究其根本在于作者西周生并不擅长百万字长篇小说的宏观驾驭,在于其书叙事的断裂,在于长篇章回体制意外地短篇化——长篇小说成为短篇小说的并不高明的连缀。
首先,就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在“醒世”的功利性说教目的下,作者采用了常见的,甚而有些俗套的因果报应结构,并敷衍出一百回的文字,可谓气势恢宏。按理说,有了逻辑关系清晰、鲜明的因果报应框架的支撑,小说的叙事应该随之井然有序、条理分明,从而完成一环扣一环的情节连缀与细节填充,但在西周生的具体驾驭过程中,却出现了小说结构的萎缩与位移。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结构的“短篇化”。其具体表现有以下两点:
一者,重果轻因。西周生将大量笔墨用于第二世狄希陈的惨淡报应上,而对前世晁源的因缘交代不足。从篇幅上看,第一世仅有二十二回而第二世却有七十八回。如此不平衡的比例以至于让人难以相信小说真的有前后两世的叙事线索,而更倾向于认同只有一条主线,即狄希陈的怕老婆故事,而前二十二回不过是后七十八回“一个似乎过分长些的楔子”、一个可以独立成篇的“入话”和“头回”罢了。事实上,原本应该支撑起第一世因果报应的前二十二回也确实发育不良,萎缩成为一个伸展了的楔子而没有十足起到应有的作用。一边萎缩,一边却又伸展,这吊诡的叙事效果恐怕并非作者本意。但不管怎么样,随着晁源的死,我们被迫进入第二世狄希陈的故事,也被迫放弃对第一世发育不良的追问。也许有人会说,当我们熟悉前世晁源的性格特征和遭遇的时候,对第二世狄希陈的出场便不会感到陌生,颇有几分未见其人而已闻其声的妙处,甚至可以推测出故事的进一步发展,这应当是西周生高人一等的叙事策略。可惜的是,情形并非如此。旁敲侧击的烘托写法一般都是选取他者作为观察自己的视角,反面着笔,如“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以兄弟明思自己道出自己暗想兄弟。可是西周生并没有这么做,而选用的恰恰是狄希陈前世的自己(晁源)来为后世自己的出场进行渲染和预热。虽然有前后两世时间的差异和名字的不同来标识此己非彼己,也可以算作是他者,但事实上这一他者身份在生命轮回的往生观念中被贴上了相同的标签——自己,于是所谓的他者被消解而缺失了。这种以己观己的写法并没有达到烘云托月的效果,反而弄巧成拙,给读者造成了“主线位移”的错觉并陷入身份指称的混乱——读者先入为主地将前二十二回晁源的故事当成了主线,却意外地发现狄希陈出场之后,主线变成了副线。当读者被迫接受故事重新并真正开始的时候,却又不得不更错乱于第二十二回之后晁家这条与主线内容并无太大关系的副线还在继续。
从两世姻缘的内容上看,晁源是因,而狄希陈是果。然而狄希陈的果报之重也远非晁源的因缘可以承载。“晁源最初的罪过杀死白狐仙,并没有传达出同后来他受到的巨大惩罚相称的严肃性;甚至计氏所受的虐待和最终的自杀,正像我们看到的,也仅具有某种模糊的含义”。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世姻缘中出场次数很少的白狐、计氏成为第二世果报中的主要人物,而前世姻缘中几乎没有缺席的小珍哥却在第二世果报中匆匆掠过。这种不平衡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作者坚持并宣扬的因果报应理论是否真的具有严肃的合法性。于是,众多失衡的因果链条被硬塞进整体结构之中,因缘被弱化为一个短篇故事,而果报则被延展为一个长篇。胡适曾道:“这一部大规模的小说,在结构上全靠这个两世业报的观念做线索,把两个很可以独立的故事硬拉成一块,结果是两败俱伤。”确是如此。不过胡适先生没有注意到其实关联这两个故事的本就不是什么因果报应,而是潜藏的“虐恋情结”。
二者,整体结构位移。“《醒世姻缘传》研究中最困难的批评问题无疑是如何解释构成这部作品结构的说教的因果报应框架”。蒲氏的焦虑不无道理。“醒世姻缘”一名本就暗含了“醒世”与“姻缘”的内在张力。西周生本意在于“醒世”,而“姻缘”只是手段。正如东岭学道人所题:“大凡稗官野史之书,有裨风化者,方可刊播将来,以昭鉴戒。此书传自武林,取正白下,多善善恶恶之谈。乍视之似有支离烦杂之病,细观之前后钩锁,彼此照应,无非劝人为善,禁人为恶,闲言冗语,都是筋脉。所云天衣无缝,诚无忝焉。”这段话先抑后扬,虚贬实赞,退一步承认叙事上尽管存在支离烦杂的毛病正是为了更好地进一步指出毛病处皆有深意。这一方面可以看作以退为进的宣传、推销的积极策略,另一方面也将潜伏的“道统”和“文统”提出表面——这两个大帽子既反映出作者对小说稗官野史地位的焦虑,也确乎为今天的道德伦理批评提供了充足的立论基础。然而令作者始料未及的是,在具体操作中,“醒世”之意湮没在琐碎的“姻缘”之事中。“醒世”所代表的因果报应这一外在大结构意外地被“短篇化”,终于无法装载下日益膨胀而“长篇化”的“姻缘”所代表的内在虐恋情结,从而发生整体结构由“醒世”向“姻缘”的位移。于是,整部小说成为各种施虐、受虐的细节的轮番表演,成为狄希陈与妻妾的打情骂俏的载体,在读者猎奇的沉迷中,“姻缘”一点一点解构掉“醒世”的严肃目的,并亮出最后的虐恋底牌。正如上文提及,晁源和狄希陈的两世因果报应其实并不真正具有严肃的合法性,倒是那些穿插在两世轮回之中的若干短小精悍的“现世报”,如第三十九回汪为露死后妻离子散,又如第五十四回雷劈尤厨子,更能激起读者的崇高情感、净化心灵,从而使因果报应显得更加合法、有力而大快人心。事实上,也正是这些短篇“现世报”力保小说整体结构只是位移而不是颠覆。然而位移既成,缝隙已生,不愿看到如此局面的西周生不得不在小说中现身,通过直接发表议论的方式来撑开大结构、压抑小结构,提醒读者不要忘了“醒世”的目的。而议论的大量出现加剧了小说叙事的断裂。
其次,章回体制短篇化。西周生在驾驭长篇、设置章回之时,借鉴了“说话”的一些艺术手法,并很明显地学习、模仿短篇话本、拟话本小说,导致文本中长于叙事的章回体制和长于议论的短篇体制的紧张和冲突,有以短笼长的倾向,其具体表现为“入话”和“头回”的大量加入,议论失控,割断连贯的叙事;情节观念淡薄、悬念弱化,故事整体感不强。
《醒世姻缘传》的具体章回开始之前都引有诗词,往往是对一回之内故事情节的概括。之后或是直接叙述故事,或是加入议论,或是插入小故事。这一结构特征与现在较为常见版本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早期长篇章回小说不同,亦与《红楼梦》等后期长篇章回小说有异。通常的长篇章回小说似乎一般较为关注叙事的连贯和悬念迭起的设置,即便偶有“看官”之类提示说书人直接发表议论的痕迹,但很少出现在章回的开端;也不会担心故事不够精彩而不惜在每回开始之前多说几个别的故事以赚取所谓的得胜头回。事实上,叙事文学,特别是长篇章回小说,从故事被讲述的第一个字开始,文本内部便会产生一种急切奔向结局的“加速度”——这一文本中的“加速度”与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加速度”是同步的,并越来越强烈,以至于这一内在“加速度”成为推动叙事的主要动力。因此,长篇章回小说家往往将精力集中于讲故事而无暇他顾。可是《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似乎更看重议论,一百回里共有二十六回开头有入话或头回,甚至“第1回、第26回、第94回等14回是话本体制”,从而使长篇章回小说呈现出短篇说话的体制特征,显得整体感不强、叙事不畅、风格迥异。试看:
人间的妇女,在那丈夫亡后,肯守不肯守,全要凭他自己的心肠。只有本人甘心守节,立志不回的,或被人逼迫,或听人解劝,回转了初心,还嫁了人去;再没有本人不愿守节,你那旁边的人拦得住他。你就拦住了他的身子,也断乎拦不住他的心肠,倒也只听他本人自便为妙。
……
奉劝那有姬妾的官人:把那恩爱毕竟要留些与自己的嫡妻,把那情义留些与自己家的儿子,断不可做得十分绝义。若是有那大识见的人,约得自己要升天的时节,打发了他们出门然后自己发驾。这是上等。其次倒先写了遗嘱与那儿子,托他好好从厚发嫁,不得留在家中作孽;后日那姬妾们果然有真心守志的,儿子们断不是那狗彘,赶他定要嫁人;若是他作起孽来,可以执了父亲的遗嘱,容人措处,不许他自己零碎嫁人。所以说那嫁与不嫁只凭那本人为妙,旁人不要强他。
只因要说晁家春莺守节故事,不觉引出这许多的话来。(第三十六回)
春莺守节之事是第三十六回的正话,但是在正话开始之前作者竟然用了洋洋洒洒两千余字的篇幅进行纯议论的入话,且论证方法多样,不仅有举例论证,还有对比论证。甚而作者以一种极其怜悯之姿态奉劝有姬妾的官人明了爱妻御妾之道。这不得不令人惊讶作者的“不务正业”。作者显然是要通过对不守节女子的批评来反衬春莺守节的可贵,进而回应在入话中宣扬的爱妻御妾之道。西周生也似乎感觉到了两千余字的入话太多了,影响了故事整体,于是用了“不觉引出”四字为自己开脱。然而“不觉”并非不觉,相反,是相当的自觉。事实上,西周生一旦议论起便很容易从叙事的“加速度”中停滞下来而进入一种非叙事的亢奋状态。于是,叙事便被暂时抛到一边,而议论便出现了失控。这一失控现象并不仅见于篇首的议论,在景物描写、历史议论上,作者同样醉心于自我言说,于是出现了第二十三回、二十四回中作者用“多达六千三百多字的内容,详细描绘绣江县明水镇的四季风光,地理人文环境、历史渊源等特色,直到第二十五回才又回到故事主题的说明”的失控。
诸如此类的议论失控,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文本权威的焦虑;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作者“炫才”的姿态。不管怎样,众多的议论是作者有意为之,而这种有意识、长篇议论性的入话与“三言”、“二拍”等拟话本小说的入话颇多相似。就话本或拟话本小说来看,其篇幅都较短,故事也不复杂曲折,因而叙事的连贯与否并不是文本的中心,而能否在小说中显露一己之声、树一世之型,才是作者迫切关注的焦点。因此,作者们不仅要在小说开头用入话进行议论,用头回进行或正或反的衬托,在末尾发通感慨,还要在行文中不断现身、发表议论,如是,方才心满意足,转入下一篇故事的叙述。由此,入话在充当作者传声筒的同时,不自觉地成为话本、拟话本小说篇与篇之间的实际分隔。此外,拟话本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保留了不少说书现场的痕迹。入话和头回因能起到静场作用便于更好地展开正话的叙事而显得非常必要。作为成熟的长篇章回体制的《醒世姻缘传》,已经基本脱离了说话的现场,而更多的只是对曾经说话记忆的追思。尽管入话和头回已经不再是文人创作长篇章回体小说必须的组成部分,但西周生还是借鉴了短篇说话的体制形式,以此设置章回,并通过入话和散落于文中的大量议论,诸如“依我想将起来”、“依了我的村见识”、“依我论将起来”,使得作者成功地成为不死的在场,幽灵一般游走于字里行间,发出“醒世”的提醒。然而,西周生有意识地学习、模仿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反倒弄巧成拙:入话潜在的分隔功能却意外地割断了叙事的连贯,使章回成为短篇的片段,并消磨掉迭起的悬念。这无疑是以故事取胜的长篇章回小说之大忌。
《醒世姻缘传》中入话的插入有一定的特点:前二十二回少,后七十八回多,并集中于第二十三回至第四十四回之间,集中程度高达72.7%(据笔者粗略统计,第二十三回至第四十四回共有16回有入话或头回)。因此有学者根据入话的前后数量多寡与文风差异认为《醒世姻缘传》是由两部不同的小说改编而成。这一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论者似乎没有注意到《醒世姻缘传》从头到脚都存在着“话本化”、“拟话本化”——《引起》是入话,而后一百回是正话,此一者也;前二十二回是入话、头回,而后七十八回是正话,此二者也;一百回中有二十六回(笔者粗略统计的数据)具备长篇入话或头回,此三者也。若从这一角度看来,其实《醒世姻缘传》前后的思路还是比较一致的——用长于议论性的短篇体制笼罩统领长于叙事性的长篇章回体制。以短笼长的不协调的策略势必造成了叙事的整体紧张。此外,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入话前后多寡的差异,但似乎对第二十三回至第四十四回入话高度集中的奇怪现象并未留心,然而这才是更为关键之所在。晁源死于第二十二回,意味着第一世姻缘的结束,而第二十三回则交代因果轮回的道理,点出山东济南府绣江县明水镇的风貌,是第二世姻缘的开始。至于第四十四回,则是叙述素姐被换心之后嫁入狄家,此乃第二世因果报应的真正开始。如此,开始又未真正开始的吊诡叙事,在第二世姻缘开始与第二世因果报应真正开始之间拉开了长达二十二回的“真空”地带。在全书最宽广的叙事断裂带里,作者在主线推进的同时插入了大量支线的小传故事,如第二十三回杨乡宦等明水镇人物故事,第二十六回麻从吾、严列星故事,第三十一回李粹然、杨无山故事,第三十五回汪为露故事等。既然是短篇的小故事,那么也就无所谓叙事的连贯。于是,作者可以任意穿梭于晁、狄两家不同的时空,得以在主线的“真空”中安插众多小故事并发表大量的议论。于是,这二十二回的叙事显得尤为跳跃和断裂,令读者满头雾水,摸不着头脑,抓不住重点。正如浦安迪所说:“在这个本来已不稳定的结构框架中,作者又分出一些章节,使它们离开了两条叙事线索去表现一系列的逸闻,这些段落和主要故事之间上有松散的主题上的联系。”然而当“真空”结束,一回之中的故事尚且说不完整要留待下回续说,作者也就没有了精力和文本空间来展开议论。虽然叙、议可以相夹而并行,但事实上,叙事固有的连贯规定性对见缝插针的议论有着本能的抗拒。这或许就是前二十二回与后五十六回少有入话等议论的真正原因所在。
尽管前二十二回与后五十六回少有入话隔断,可以顺畅接续,但短篇化已全面渗入《醒世姻缘传》的章回体制之中,没有实际内容的起伏跌宕和欲言又止,漫不经心的程式化的“且听下回分解”,逐步丧失了制造悬念的紧张机制,冲淡了悬念,造成各回故事冲突的相对完整与自足。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相反常有厌倦情绪。何以徐志摩和陆小曼“一连几天我们眼看肿,肚子小痛”?且看:
我随手翻了一回给她看——也许是徽州人汪为露那一回,也许是智姐急智那一回,也许是狄希陈坐“监”那一回,也许是相于廷教表兄降内那一回,也许是白姑子着贼请先生那一回,我记不得了,反正哪一回都成。(《〈醒世姻缘传〉序》)
徐志摩说他忘了具体是哪一回,这可能是真的。但哪一回都成的说法,恐怕掺杂了不少诗人的夸张。他本可以一笔略过模糊处理,但他在序言中特别列出了若干回目。这说明他对这些回目印象深刻。然而这些故事大部分都是在长达二十二回的叙事断裂带里插入的支线中的小故事,即便就是狄希陈坐“监”这样的主线情节,也不过是第六十回“相妗子痛打甥妇,薛素姐监禁夫君”的后半部分,篇幅并不甚长,也没有情节的波澜起伏,只能算是素姐施虐、狄希陈受虐的插曲之一。事实上,大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一些单个章回及其中的短篇故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周生在构造短篇故事的时候还是颇为精巧、游刃有余的,但是在结构长篇时,则缺乏整体驾驭的能力,显得左右支绌。而西周生避重就轻,企图以短篇说话的经验来结构章回小说,则违背了长篇叙事文学的一般规律,是一大失策。
再次,细化到章回之中的叙事,我们发现“短篇化”表现为时间概念的混乱:一方面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冲突;另一方面,故事时间呈现琐碎状态,拆解了本应浑成的整体叙事,而使小说成为短篇的日记。
时间这一概念是“作家对生活的把握方式和对各种感受、体验和想象的组织方式,也是作家结构作品的主要手段之一”;时间是叙事文学的关键要素之一,既决定着叙事是否合乎逻辑,也推动叙事向前发展。一般而言,时间这一概念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文本的叙事时间,二是文本中的现实时间,也就是故事时间。二者既相互联系又彼此不同。若处理不好,轻者会出现情节漏洞,重者颠倒错乱、自相矛盾。对于长篇叙事文学来说,由于其整体结构的宏大而对时间有着更高的要求。就《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来说,时间似乎不成为问题,只需要跟着历史的脉络走下去,七分实三分虚,读者阅读过程中也不会产生时间的错觉,但是在《醒世姻缘传》中情况却并非如此。尽管《醒世姻缘传》在故事中同样交代了年代,营造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但很显然,《醒世姻缘传》并非历史小说而只是世情小说。其交代的历史背景对于故事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因此,《醒世姻缘传》没有办法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参考历史的时间,它必须自己为自己制定出一个时间表。然而,西周生在时间的把握上再次遭遇困境。
错觉之一在于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常常冲突,其具体表现便是预叙和倒叙的矛盾。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莫过于第九十回晁夫人去世前的一段遗嘱:
晁夫人道:“你哥虽是我的长子,淘气长孽,我六十岁没过个舒摊日子。自从得了你,后来你又娶了媳妇,我倒散诞逍遥的,过了这四五十年。这要你哥在,他凡事都拦着,只知道剥削别人的,他也不叫我行这些好事。你两口儿又孝顺,又凡事的安当,我也没有话嘱咐你们。千万别要住了。你看这们些年,天老爷保护着咱,那一年不救活几万人,又没跌落下原旧的本钱去?小琏哥两口儿好看他,你孤身没有帮手,叫他替你做个羽翼,也是咱晁家的后代。况且他又是个秀才,好合你做伴读书。万一后来同住不的,好割好散,别要叫他过不得日子。陈师娘是个苦人儿,既养活着他,休叫人下觑他,别叫他不得所指望。你再生个儿,过给你哥,你偏偏的不肯生。停在乡里这们些年,也不是事,替我出殡,带他出去罢。就是我,也别停的久了,多不过五七,且坟是甃停当的,开开就好葬的了。”
在这么长的遗嘱中,晁夫人提到常平籴粜的事、小琏哥两口儿、出殡安排等,因前文都有所铺垫、伏笔,所以读者会感到前后照应、顺理成章。然而偏偏冒出一个“陈师娘”,这却叫人不知所云。笔者翻遍前九十回也没有找见陈师娘的影子。这里却突然出现,何也?再往后翻到第九十二回才发现作者在这里进行了一整回补写性质的倒叙。于是,陈师娘的一桩“悬案”才终于尘埃落定。作者似乎有些贪婪地想在百回的篇幅中自由支配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时间段。事实上,作者也这么做了,但在叙事时间的把握上难免出现照应的疏漏。因此,从整体上看,《醒世姻缘传》还达不到“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精巧境界。
预叙和倒叙的矛盾在《醒世姻缘传》中比较普遍,但还不是最成问题的。最成问题的是故事时间的琐碎。颇为讽刺的是常常照应失调、叙事时间感不强的作者却对故事时间有着近乎偏执的敏感和迷恋,将故事时间一再精确,以至于将百回长篇切割成每日一记的流水惧内账。
在小说文本中,标识故事时间的方法大概有三种,其一是年号纪年,如第十一回“那时正是景泰爷登基”;其二是直接交代日月,如第一回“一日,正是十一月初六冬至的日子”;其三是附着在既定日期上大量的“次日”、“过了N日”。凭借着这些琐碎而详细的日期,有学者做出了《醒世姻缘传》的故事编年,并验证出“作者所说的第一世的晁源等人‘托生’到第二世,在时间上是相当吻合的”。
作者对故事时间的精确是极现实主义的,不仅保障了故事时间的线性推移,也增强了小说文本的真实性与生活化——更多的生活细节得以进入文本空间。肯定这种写法的同时我们换一个思路便会发现,小说的叙事时间同其结构一样,存在着吊诡——时间跨度宏大,却又被明确的时间节点分割成众多短小的片段。在整体缺乏悬念丛生、高潮迭起的平淡叙事下,这样如日记般的精确其实并没有为小说锦上添花,相反却有流水账之嫌,给小说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割裂了连贯,琐碎了浑成。在笔者看来,频繁地交代故事时间是叙事混乱的一个表征。它显示出作者对叙事时间掌控的不自信——既然两世的时间无法掌控,那不如分割、细化到每一月、每一天。这便可以减少叙事的难度与压力,从而可以轻松应对。它也显示出作者习惯于对生活零碎的感悟、细腻的捕捉,而对人生的整体性想象则比较陌生。或许作者也发现了两世姻缘的宏大时间跨度在叙事上的困难,因而不得不频繁交代故事时间以保证其叙事的合法性与合逻辑性,但事实上,这种并不高明的方法并没有为西周生带来叙事上的改观,反而暴露了更多,并给阅读带来了倦怠的消极情绪。
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以家庭为观察视点,勾连起社会,特别是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的各组成部分,赞颂了生活中善的守望,抨击了恶的堕落,确乎做到了“劝人为善,禁人为恶”。因此,《醒世姻缘传》不仅在当时有其重要的道德意义,也对当下的社会生活有重要的启发、警醒作用。然而在道德层面之外,于小说本身的美学性而言,作为我国17世纪长篇章回小说的重要代表、被誉为《金瓶梅》向《红楼梦》过渡的桥梁的《醒世姻缘传》,尽管在家庭小说这一题材上有所发展,在惧内主题上有所突破,在写实性上有所坚持,在叙事上有被众多学者归纳、总结出来的种种独特性结构模式,但这些成就并不能遮蔽《醒世姻缘传》从整体结构到章回体制再到细节叙事中叙事断裂、结构混乱的真相以及读者“不忍卒读”的事实——这无疑是小说作为小说自身的悲剧。我们在肯定其应有之价值的基础上也应该有勇气直面文本本身,清醒地认识并承认《醒世姻缘传》并非精巧、成熟的小说,“在艺术成就上不及明清五大奇书”,其叙事上的拙劣在于其对于话本小说的承袭和对传统章回小说的背离——长篇短篇化、章回话本化。
注:
② 陈平原《中国小说中的文人叙事——明清章回小说研究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④ 徐复岭《〈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页。
⑤ [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⑦ 参见乔力《论〈醒世姻缘传〉的结构特征与情节关系》,《东岳论丛》1996第4期。
⑨ 参见吴存存《〈醒世姻缘传〉的深层结构》,《辽宁大学学报》1991第2期;夏薇《〈醒世姻缘传〉研究》第三章,中华书局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