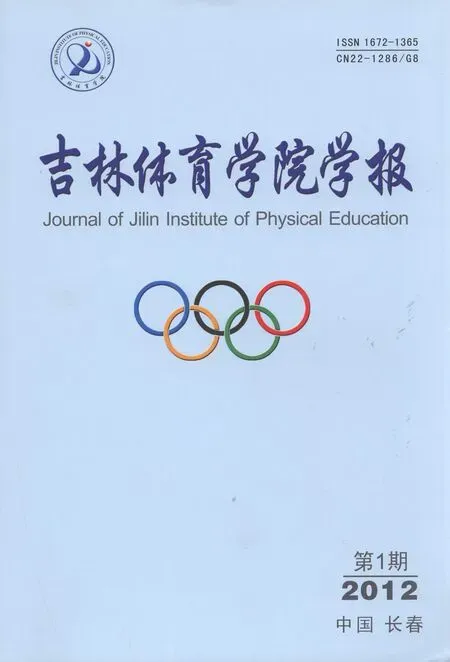我国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纠纷解决现状与责任承担方式研究
柳春梅 曹龙辉 吴明华
(1.湖南城市学院 体育系,湖南 益阳 413000;2.益阳高级技工学校,湖南 益阳 413000)
我国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纠纷解决现状与责任承担方式研究
柳春梅1曹龙辉2吴明华1
(1.湖南城市学院 体育系,湖南 益阳 413000;2.益阳高级技工学校,湖南 益阳 413000)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立足于我国法律实践和相关法律规定,根据我国公共体育设施存在形式,分析我国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纠纷的现状,探讨我国公共体育设施致人伤害纠纷的解决机制和法律适用问题。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公共体育设施致人伤害纠纷解决应该确立公私法二元调整的责任承担方式。希望对我国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问题解决提供参考。
我国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纠纷解决方式;法律责任;承担方式
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体育健身需求,我国行政部门大力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新建、改建、扩建居民居住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划和建设相应的文化体育设施,……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项目和功能,不得缩小其建设规模和降低其用地指标。”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小区体育设施有人生没人养,小区体育设施被随意损坏存在安全隐患,健身设施该‘健身’了……”[1]。因此,公共体育设施该由谁维护,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后受害者该如何进行救济,这种承载公共利益的体育设施致人损害后如何均衡各利益主体?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纠纷解决方式的现状,探讨其法律适用问题,以期对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问题解决提供参考。
1 我国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纠纷解决方式现状
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引起的纠纷解决方式,由于没有相关的专门立法对公共设施致人损害问题进行调整,在实践中,处理方式、处理结果可见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主要有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
1.1自力救济主要是自动和解
所谓“和解”是没有第三方介入,双方当事人自己协商谈判,对各自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由于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所以对双方的约束力很弱。实际生活中,当事人和解后反悔而诉讼的比较常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原告不丧失起诉权,但通常丧失了胜诉权。
1.2公力救济主要是法律诉讼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因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而引起纠纷的案件如双方当事人愿意进入司法程序进行解决的,都是作为普通民事案件来进行处理的。民事法律诉讼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范进行操作。可以说在某些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的案件中,按照现行法律的规范,会使受害者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目前正式、权威、主流、公平、最终的处理方式。
2 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的法律适用
2.1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主要适用民法调整
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没有专门的立法,民法中也没有专门的规定,只是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的说明》(简称《说明》)对此有些涉及,“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管理欠缺发生的赔偿问题不属违法行使职权的问题,不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受害人可以依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向负责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请求赔偿”。依据《说明》,处理该类问题的法律依据是民法的“有关规定”。
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关于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的规定,既包括一般规定又包括具体规定,一般规定主要有民法这一私法来予以规范,具体规定主要分散在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之中。正是由于法律和部门规章在整个法律的渊源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现行规定的“一般”与“具体”。由民法这一私法予以调整的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问题,在整个民法体系中可以被看作是侵权行为中的一种,根据侵权行为法的渊源,其适用的主要法律依据为《民法通则》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那么,针对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的不同情形,又该如何适用?仔细推敲后,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予以澄清,以便为下文的进一步分析奠定基础。
2.2《民法通则》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关系
第一,《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行为法的规定。我国《民法通则》一改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体例,未将侵权行为规定在债法中,而是单设民事责任制度,将侵权行为作为民事责任的一部分加以规定。这些对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定是侵权行为法的重要渊源。
第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关于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司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之一,是指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司法解释必须坚持合法、合理、法治统一的原则。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司法解释并不属于法律渊源,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或检察院不是享有立法权的机关。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立法的不完备,最高司法机关作了大量的司法解释文件。这些解释已远远不是被看作普通司法解释看待,在实践中均被作为法律渊源援用[2]。
第三,《民法通则》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具体应用。由于《民法通则》对侵权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审理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原则虽有所补充,但仍不能适应当前审判实践的迫切需要。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较之《民法通则》具有理念、操作技术上的先进,反映了我国侵权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进步。《民法通则》是《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基础,而后者对前者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学界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可以说属于侵权普通法,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则属于侵权特别法[3]。具体到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这一侵权行为,笔者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是对《民法通则》的补充[4],并不存在两者谁优先适用的问题。
2.3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法律适用中引起的困惑
公共体育设施是全民健身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载体和依托,是体育事业得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保障条件。参照《民法通则》、《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以及《产品质量法》等基本法律规定对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问题进行处理。依据以上基本法律规定,民事赔偿能否使受害者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救济,这种承载公共利益的体育设施能否平衡各利益主体,有没有考虑到体育事业发展的特殊性?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解决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问题的关键之处。
2.3.1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法律适用范围
《民法通则》第126条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6条规定,在民法理论上可以称作是物件致人损害责任。按照物件致人损害责任构成的主体要件,公共体育设施是否涵盖在民法通则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范围内?民法通则第126条所适用的范围是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6条适用的范围只限于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堆放物、树木及果实等。可见,界定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建筑物和设施的范围是非常必要的。所谓公共构筑物,是指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所提供的为公众使用的建筑等有体物及设备;设施是指有体物或物的设备。由此,民法通则第126条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6条的规定范围只能说是囊括了一部分的公共体育设施。因为在我国有些公共体育设施属于公物或公共营造物,其最明显的特征在于这部分体育设施紧密地和行政主体联系在一起。民法作为私法,其调整范围限于平等主体,因而决定了民法不可能对所有的公共体育设施进行规范。很显然,对于那部分属于公物、公共营造物范围内的公有公共体育设施,应当属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2.3.2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法律适用的侵权归责原则
对于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这一特殊侵权行为,在侵权责任的认定中适用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特别规定——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具体而言,受害人只要证明加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并存在因果关系,无需对加害人的主观情况证明,就可推定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受害人为免除责任,应由其自己证明主观上无过错。这势必加重原告在举证责任方面的负担,被告可以举出无过错的证据以免除责任,那么原告将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不利于体现“有损害,就有救济”的法律精神,也不能对公民享有的体育权利得以周全的保护。这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反之,对于公共体育设施的管理者来说,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使公共体育设施的管理者使原本沉重的管理义务因为举证责任制度的安排又陷入了另一不利益。
可以说,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是介于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之间的一座桥梁。过错责任原则对于原告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证明要求,无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关注的是对于被害人的救济,它的基础是使得损害的发生在最有效、最经济的范围内尽快地恢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而过错推定在逻辑上依然属于过错责任的范畴,而在经验层面或操作层面却具有某种中性的事实。其产生的实质是权利的相互冲突。一方面,被害人由于对于损害发生全然不知,从而不能证明侵权人的过错,导致不能得到救急将有违正义的理念;另一方面,对于建筑物、设施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加以过重的证明责任又将导致新的不正义产生。
2.3.3公共体育设施管理者法定的管理义务
无论一般法律规定,还是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都提及了管理者负有对公共体育设施的维护、管理义务,那么公共体育设施的管理者也就是解决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问题的症结所在,现行中公共体育设施的管理者究竟为谁?管理者的管理权范围多大?这里所说的维修、管理义务在民法理论上可以称作是安全保障义务,是《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第六条所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之下基于分配正义的需要发展起来的。按照民法侵权行为理论,安全保障义务主要包括:一是设施设备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二是服务管理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三是对儿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四是对防范制止侵权行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如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的损害,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按照这样的逻辑和物件致人损害侵权责任构成要件适用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管理者则必须证明自身在管理中不存在过错,而且已经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才方可免除责任。这样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公园等一系列全民健身工程的受赠主体就会为害怕承担责任而“积极拒绝”这种赠与的体育设施,其他公共体育设施的管理者也会消极不作为,贷于行使管理职责。据统计,当前我国的公共体育设施破损率为10%左右,健身设施存在着相当大的安全隐患。如小区和公园及其他受赠单位在接受全民健身体育设施时存在种种疑虑和顾虑;积极投身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社会力量望而却步。
2.3.4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选择
对于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而导致的赔偿问题,尚未发生过国家赔偿的判例,但是此种情况在其他公共设施致人损害案件中已经存在。《羊城晚报》2006年4月3日的报道《公共设施致害,损失该谁赔偿》,“广州遭遇十年最严重水管爆裂,‘管水’部门表示补偿商铺损失,开管理部门主动担责全国先河”,对于公共设施造成损害进行补偿,在全国都还“应者寥寥”。重庆纂江县的虹桥坍塌一案,当时关于是由纂江县政府还是由建筑商对事故造成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一直争论不休。但是最终紊江县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由县财政出资对死难者家属进行了赔偿。另外如辽河桥意外垮塌事件,最后实际也是由国家机关进行处理,由国家出钱赔偿。因此,尽管我国立法上尚未有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的规定,但实践中早已有国家赔偿的先例。另外实践中也有直接判决政府进行赔偿的案例,该案判决认定该设施管理人为水利站,但是却判决乡政府承担赔偿责任,其判决己突破了现有法律规定。
2.4公共体育设施的公私法调整
纵观公共设施的发展历程,我国公共设施的法律规范系统从公法一元化向公私法二元调整方向转变,将解决公共体育设施致害纠纷的重要趋势。
2.4.1民法、行政法对公共体育设施的规范
从公共体育设施提供者角度看,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公共体育产品的提供者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以此来确保、维护人民群众公平享受社会体育生活的利益,提高民族的身体素质,所以说这部分体育设施可以称作是公有公共体育设施。在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上,规范的称法为“公物”或者为“公营造物”。这里所称的公有公共体育设施,“公有”的概念有别于我们常理上所认同的“公有”含义,绝非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换言之,不是以所有权为标准的。和公物、公营造物牵连在一起的“公有”并不限于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或者说并不关注所有权的归属,凡由国家、集体以及其他社会团体设置或虽非其设置但事实上处于行政主体管理状态,均可称为 “公有”。显然,这部分公共体育设施就要由行政法调整,称之为公有公共体育设施。对于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种公共体育设施,有一部分可以化为行政法调整,但仍将有一部分则要由民法这一私法进行调整。
如何准确判定公共体育设施适用何种法律关系,德国学者的公物权理论,为我们开辟了新的思路:如果宪法意义上的某项财产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被某种特定使用或地役所约束,并使得所有权人在公用使用的存续期间内不能享有其所有权的全部全能,那么实际上就已经存在一种优先于所有权并排挤所有权的公共权力,我们称之为公物权。依据这一原理,根据公共体育设施上存在争议的权利性质,采取适用不同的法律,基本原则是:如果争议的对象是有关公物权的,应适用行政法;如果争议的对象是有关私人物主剩余权限的,按照民法有关规定予以调整。
2.4.2公共体育设施致人损害的公私法责任承担方式
第一,公共体育设施以及设施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因设计、施工不当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属于公物和公营造物范畴的公有公共体育设施,就会导致行政法上的责任,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的体育设施致害理应由行政主体承担(可以追加设计者、施工者为第三人);凡集体以及其他社会团体设置或非其设置但在事实上处于行政主体管理状态的公有公共体育设施,仍由行政主体承担责任(可以追加所有者、设计者、施工者为第三人)。属于社会力量举办的公共体育设施,则由民法进行调整,由公共体育设施的所有者、管理者、设计者、施工者承担连带的民事责任。
第二,公共体育设施以及体育设施上的搁置物、悬挂物,由于后期维护不当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发生在公共体育设施的管理环节,应由公共体育设施管理者承担责任,公有公共体育设施会产生行政法上的责任;其他的公共体育设施应当纳入民事法律的调整范畴中。
第三,公共体育设施功能、结构存在缺陷致使使用者伤害,同样发生在公共体育设施的设立环节,适用规则同因设计、施工发生倒塌、脱落、坠落的情形,属于公物或公营造物的属于行政法上的责任,只是非由行政主体设置的则要追加所有者为第三人。民法范畴的公共体育设施由所有者和管理者承担连带的民事责任。
第四,由于管理者未尽到告知义务,致使使用人使用方法不当造成人身伤害,属管理权范畴,适用规则同于后期维护不当致害的情形。
第五,由于所有者未尽到告知义务,致使使用人使用方法不当造成人身伤害,属所有人所有权范畴,应由公共体育设施所有者承担责任,与第一种情形类似,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的体育设施致害理应由行政主体承担,凡集体以及其他社会团体设置或非其设置但在事实上处于行政主体管理状态的公有公共体育设施,仍由行政主体承担行政法上的责任(追加所有者为“第三人”)。私法领域的公共体育设施则由所有者和管理者承担连带责任。
[1]刘丽,李月.公共设施:是共同的享用,不是共同的忧患,黑龙江法制报[N],2005-08-19.
[2]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9.
[3]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9.
[4]杨立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释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AResearchonDisputeResolutionandResponsibilityMeansofPersonalDamageofChinesepublicSportsFacilities
Liu Chunmei1,Cao Longhui2,Wu Minghua1
(1.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413000,Hunan,China;2.Yiyang Senior Technical Schools, Yiyang, 413000,Hunan,China)
Using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legal practice, the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and the existing forms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status of dispute personal injury caused by the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explored the disputes settlement mechanism and legal application of injury caused by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and concluded: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 personal injury caused by the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should establish the dual adjustments responsibility mean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aw. We hope that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solution of personal injury problem caused by Chinese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Chinese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dispute resolution to cause damage; law applications
G80-05
A
1672-1365(2012)01-0035-04
2011-05-10;
2011-07-02
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0C0517)
柳春梅(1979-),女,黑龙江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体育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