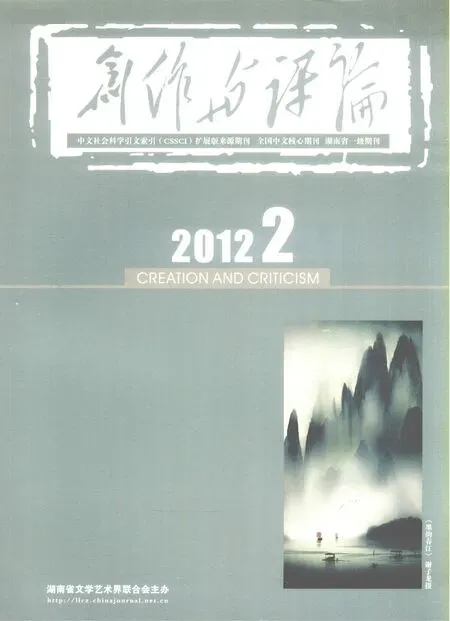价值重建与复调叙述——评何顿《抵抗者》
■ 颜小芳
何顿给人的印象是都市欲望世界的叙述者或代言人。他的小说大部分以当下都市市民生活为表现对象,基本围绕“钱”和“性”两大欲望主题展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形成的商业价值观给普通市民思想带来巨大冲击,何顿的小说对此进行了真实记录,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幅欲海浮沉的个体生存图景。对当下社会与阶层变化的敏锐感知及“还原现场”的叙述方式,使何顿赢得了不少美誉。但太靠近现实的叙述,使何顿的小说缺乏纵向的深度;同时,他的欲望书写似乎只停留在消费这一意义表层,像很多后现代影视画面一样,突出的是感官刺激。从文学的表现范畴而言,这还仅属于皮毛;从文学的精神出发,它还缺乏更深刻更持久地感动人心的力量。这是就何顿前期创作而言。
著名作家东西曾说过,作家不能停止写作,否则不能称之为作家。如果这个作家曾经写出过几部作品,然后只是坐享其成,不再努力创作,也不能称为作家。这就把真正的作家与那些沽名钓誉之辈区分开来。从创作态度上看,何顿是勤奋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超越自己。
2002年,何顿出版了他自认为可能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抵抗者》。这是一部讲述革命抗战历史的小说。这部小说的出版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何顿小说创作的转型和超越,用何顿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调动了我的全部文学才能”。①在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到何顿作为一名严肃作家在纯文学写作与探索方面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突破和收获。
历史,尤其革命历史,是当代作家们钟爱的小说题材。从“十七年”开始,再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革命历史的书写逐渐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传统革命历史时期,以单一的意识形态叙述、二元对立的战争思维、机械的历史本质论以及阶级决定论为主要特征,多采用宏大历史叙事方式,从正面建构历史。其次是新历史主义阶段,以对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的反对、颠覆为主要特征,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和虚无性,从而将历史解构。无论是传统革命历史小说还是新历史小说都无法逃脱二元对立的框架,它们都强调以某一方面为中心,从而排斥和打击另一方面。第三种则抛弃传统历史叙事及新历史叙事的二元对立框架,抛弃对革命、历史、战争的一切前理解,从个体生命存活的基本欲望出发,还原战争的残酷,解构英雄和反英雄,还原人的真实本性,从而达到重新审视战争与抗日精神的目的。
《抵抗人生》中,作者跳出了传统“正义与非正义”、“胜利与失败”、“崇高与卑下”的二元对立意识框架,褪去了笼罩在“战争”名义上种种意识形态的东西,不从任何主义出发,而是从生命本身的角度揭露出战争的残酷及其对弱势生命群体的暴力与剥夺。作者并没有站在狭隘的民族立场,像传统抗战小说那样对日本军队采用俯视,对抗日英雄采用仰视。作者从生命的角度,对一切战争都进行了控诉。例如在衡阳保卫战中,国民党的飞机在空中扫射,轰炸日本军队的时候,也没想过要顾及那些和日军在一起的国民党俘虏与伤员。
仍然是从生命角度,作者不动声色地对一切不尊重生命、漠视个体存在的行为进行了无形嘲讽。例如作者写到文革时期造反派逼供黄抗日时的问话:
他们质问我老爹:如果像你交代的,你参加国民党军队是为了抗日,那么,那么多英勇的抗日将士都倒下了,死得都很不错。为什么你不光荣地死去?
我爹无言以对。
你们算什么抗日?你们国民党在日本人的铁蹄下节节败退,那也算抗日?
老爹无言以对。
你说你参加了衡阳保卫战,衡阳还不是失陷了?那算保卫衡阳吗?
老爹低垂着一张污垢的脸,不敢申辩。②
很显然,在作者笔下,造反派的话语显得十分荒谬。“我老爹”——黄抗日,就是在这种荒谬逻辑的逼供下,整整一年时间,被逼得精神失常了。
对于“文革”政治,作者的态度不再含糊和隐蔽,而是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看法:“政治需要一些有污点的人,因为有污点就有文章可作。在极‘左’的年代,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升官发财建立在有污点的人身上,这样的人是他们的阶梯。”③而人的生命价值则在“极左”政治的摧残下,被肆意践踏,连草芥都不如。
衡阳保卫战中,作者借小新兵毛领子与黄抗日的对话,重新探讨了意义与生命存在之间的取舍问题。毛领子的同学猪鼻子和勾嘴巴都在战争中英勇地死去,毛领子因此有了如下感慨:我还真的不如死了好。……我想要是以后有人晓得我成了日本鳖的俘虏,那多没面子!…我的老师会看我不起,猪鼻子和勾嘴巴的父母也会看我不起。很显然,毛领子的想法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意识观,这是从孟子的言论中继承下来的“道义”生死观,即“舍生而取义”。毛领子的这番话却遭到黄抗日的反驳:面子比一条命还重要么?黄抗日没有读过书,脑海里没有任何观念及条条框框的束缚,他贪生怕死,却又朴实善良,重情重义。他几乎没有任何政治觉悟,只是凭借朴素而又顽强的生命本能,战胜了一次又一次困境,成为了抗日英雄。
何顿不擅长写政治,他笔下的抗日英雄没有几个有政治觉悟。例如黄抗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稀里糊涂地被入的。虽说换了一种题材,但何顿仍然保留了他描写人物的一贯特征,即抓住普通人的基本欲望。在何顿的笔下,只有人的欲望是真实的,其他一切道德观念、政治主义之类的是何顿一直回避的话题。在消费语境下,人的欲望表现为对金钱和性的追逐和热衷,何顿前期的小说,不是写普通人这两方面欲望的压抑,就是写他们这两方面欲望的放纵,而无论是压抑还是放纵,作者都很少对他们的精神做深入剖析,他们似乎只是一个个平面化的人物。而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中,普通人最大的欲望就是生存,就是活着。对于像黄抗日这样卑贱的山民而言,活着是最大的真理。其次是善良,这是他们身上最朴素也是最闪光的品质。活着是为自己,善良是为他人。“活着”的欲望令黄抗日贪生怕死,而“善良”的品性令黄抗日在紧急危难时刻能挺身而出。
如果说何顿前期的小说(大部分是都市欲望小说)让人看到的是欲望膨胀下的精神迷失,那么在《抵抗者》这部革命历史小说中,作者通过“黄抗日”这一平民英雄的塑造,将信仰重建的基石落在了农业社会时期人们那未经工业现代社会资本和物质熏染过的朴素道德情感之上。这既不同于传统革命历史书写中的政治主流意识,也不同于新历史小说中的反意识形态立场,这是一种植根于个体生命立场及民间朴素道德情感的温暖重建,传达了一种平民个体化的新价值观。
然而,这种平民个体化的新价值观显然无法担当起救赎的重任。对于黄抗日而言,“抗日英雄”这个称呼只是一个令他感到陌生和不自在的符号,并不能令他完成自我意义的提升和重建。晚年的他一心想要找回的是与岁月一同失落的战友情谊。只有与那些与他共同战斗过的同伴对话,才能令他找回失去的自我。然而当他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两个曾紧密伴随他的幸存者毛领子和田国藩时,新的隔膜又在他们彼此的心中产生了。还是在战争时期,绰号田矮子的田国藩就经常欺负黄抗日。然而进入新社会,两个耄耋老人重遇时,共同的抗战经历却又都让对方在彼此的生命历程中刻下永不磨灭的记印,成为各自自我的一部分。但现实又是残酷的,由于家庭条件的差异(黄抗日的儿子开着奥迪小车接送老爸和他的战友去高级宾馆消费,对家境相对清贫的毛领子和田国藩可能产生了刺激)黄抗日的两个昔日战友却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黄抗日。这令重情重义的黄抗日心灰意冷,不久便离开了人世。黄抗日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同时也把遗憾留给了他的两个战友。可见,黄抗日的命运悲剧暗示了农业时代平民化的个体朴素价值观只是当代社会的一曲挽歌。面对新的社会现实和阶层分化,这种朴素的乡里之情显然无法拯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更无法担当起精神家园重建的重任。
黄抗日是孤独的,虽然他顶着一个“抗日英雄”的光环,但这并非他真正想要的。在作者笔下,原名黄山猫的黄抗日,只是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长着一张猩猩脸的山民,由于长得难看,黄抗日受尽众人歧视和冷落。他的遭遇其实比普通人还不如。也许正是因为世人嫌弃他,上帝才如此厚爱他,让他一次次从死神面前逃脱,最后成为众人眼里的大英雄。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反差如此之大,令黄抗日这个形象一下子复杂起来,从而获得更多的阐释空间。所以“黄抗日”是作者塑造过的最为成功的文学形象。
还值得提及的是作者在叙述形式上的探索。首先,作者摒弃了单一线性叙述的结构与时间。在结构上,作者设计了主、副两条线索。作者以“我”带领“我”爹(黄抗日)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寻找衡阳保卫战遗址与故人为主线索,中间穿插对“我”爹生平事迹的回忆;以“我”创作的小说《抵抗者》为副线索,这条线索叙述的文字全部用小号字体,以区别于主线索中的叙述。
从内容设置上看,主线索以现实为叙述对象,而副线索以小说的形式来讲述故事,成为小说中的小说,从而使得作者在叙述方式上带上了元小说的特征。这样,叙述者“我”,就变成了跨层叙述者。一方面,他是小说中的人物,是黄抗日的儿子;另一方面,他又是小说的叙述者,是黄抗日抗战故事的讲述者。这样一来,叙述者的身份就变得复杂起来,形成一种复调叙述,从而使整个小说的叙述变得更加丰满和有立体感了。
复调叙述会有不同的声音。例如,副线部分的叙述分为两层。第一层的叙述者是“我”,黄抗日的儿子。第二层叙述则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视角叙述。其中讲述了一个场景:衡阳保卫战中,田矮子训练的娃娃兵第一次上战场时,个个吓得两腿哆嗦,不敢向前打鬼子。这令田矮子极为恼火。在几次动员都失效的情况下,田矮子枪杀了一个娃娃兵,以期杀一儆百。在主线部分,叙述者“我”是第一人称叙述,“我”既是叙述者,也是黄抗日的儿子,也是副线部分第一层叙述的叙述者。大约五十年之后,“我”陪着“我”爹找到了他曾经的战友田矮子——我喊他田叔叔。“我”和“我爹”就田叔叔到底有没有枪杀那个衡阳学生展开了对话。老爹回忆说,他不会记错,是田老杀了那个衡阳学生,只是他不明白田老却说是龙连长枪毙了那个衡阳学生。而此刻,“我”完全成了局外人,“我”对于事实的真相完全不知情,只能凭借推理和猜测,“假如这件事儿没折磨过他,他早就忘记了。这事儿一定折磨过他,我想。”④可见,在副线中,田矮子杀死衡阳学生是小说中确定的事实,然后在主线中,由于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叙述的设置,田矮子杀衡阳学生这件事顿时变得扑朔迷离。这样一来,小说中的叙述者就发出了多个声音,形成了复调叙述。
在时间安排上,主线索讲述现实中的事情,多用一般现在时,同时穿插对“我”老爹生平的回忆,又多用插叙和倒叙;副线索则讲述另外一个时空中发生的故事,采用的是过去现在时的讲述方式。可见,作者在结构与时间的安排上经过了精心、缜密的设计。
在副线中,叙述者“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黄抗日的抗战故事的时候,经常插入黑体印刷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叙述。将历史与小说形成对照,这是一种互文的写法,形成了一种虚实交织的艺术效果,这也是元小说写法的一种。
总之,《抵抗者》使何顿的小说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在笔者看来,这是真正奠定他纯文学作家地位的坚实之作。
注 释
①②③④何顿著《抵抗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前言,第4页、第49页、第83页、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