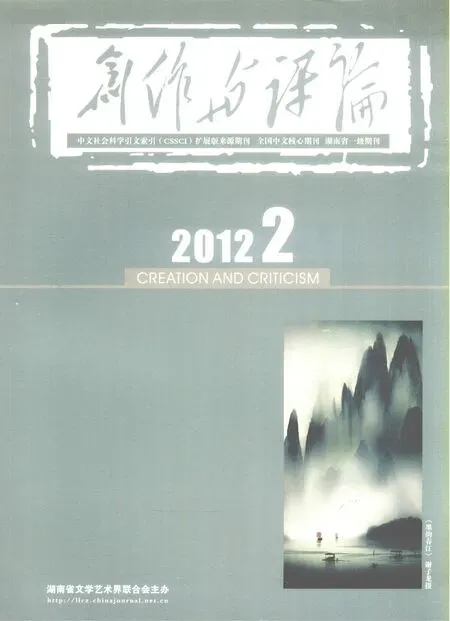一个家族的精神史诗——读何顿《湖南骡子》
■ 王迅
作为长沙本土作家,何顿的小说创作以长沙地域文化的发掘和市民生存形态的书写著称。《湖南骡子》的叙事依然立足长沙,不过,何顿把这座城市的世俗生存引向更为深入的探究。这部小说以历史的深度和人性的深度实践着他在小说叙事上的超越。从文学史上看,关于长沙四次会战的历史,以往的文学叙事几乎很少触及,《湖南骡子》这样的鸿篇巨制更是没有。无论是对长沙四次会战的描述,还是对“文革”时期及当下长沙生活的呈现,作者都能严格遵循人物性格自身的发展逻辑,以雄浑的笔力去展现长沙市民近百年的集体性格史和精神史。
从清末中兴名臣曾国藩到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从呼唤民众警醒甘蹈大海的陈天华到为建立共和而出生入死的黄兴,从为国民争人格的湖南骁将蔡锷到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湖南人在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开始了接力式的救亡图存。然而,这一切高大的身影以历史文献的形式存放于我们的记忆中,而这种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大写的、粗糙的,也是概念的、抽象的,终究无法给出湖南人性格发展史的清晰脉络。
如今,湖南人遍布全球,我们身边时常浮现他们的身影。那么,在我们印象中他们是什么样子?湖南人的精神特质究竟是什么?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描述。要对湖南人精神气质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恐怕还是要回到可触可感的世俗生活,回到鲜活的历史现场。何顿《湖南骡子》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这部小说以一个军人世家的人事沧桑,折射出湖南人的一种群体文化人格——“骡子精神”:“无论平时怎么浪荡,关键时刻身上却展示出坚挺、倔强的性格,宁可掉脑袋,也不屈服!”
作为何顿叙事的精神线索,“骡子精神”贯穿在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和故事推进中。为了凸现这种精神在各个时期的流变历程,作者把审美视点聚焦在一个军人世家的命运沉浮与变迁,这种视角的选择使这部小说在叙事上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美学效果。在小说中,何家四代人都有一种不屈的倔强性格和反叛意识,犹如一群倔头倔脑的湖南骡子。何金山十几岁就不满于军阀统治而参加护国军,而何金林、何金石则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他们义无返顾地加入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何金林、李雁军位高权重,但从不唯唯诺诺,随波逐流,而是敢于直言,大胆质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决定。第三代中,何胜武虽然加入了国军队伍,但在抗日战争中却表现出神话般的勇猛和威力,战绩赫赫,轰动全国。而何陕北则属于社会上的问题青年,但他个性中却也展现出敢为人先的特征。在何家女性中,何秀梅对婚姻和爱情的那种带有悲壮色彩的坚守,以及她在生活中那种刻薄坚硬的作风,都是叛逆精神的表现。到了第四代,这种精神血液又遗传到白玉、五一身上,这一代人感知时代风向的触觉相当发达,一旦发现政治新气象,他们很快就能领会其本质和要害,并找准时机谋求个体的自我发展。
这种偏执的个性是这个家族所有成员的共性,它赋予人物以浪漫精神和传奇色彩,形成一种偏离常态的个体生命形式。从从军经历看,作为职业军人,何金山的职务从排长升到军长,其间历经艰险与磨难,但他稳扎稳打,能屈能升,始终没有失掉那股子“骡子精神”。在何世家族的外围成员中,李雁军比较典型地显露出这种精神品质。他生性耿直,敢于为愤愤不平之事进柬“中央”。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其命运可想而知。建国后的二十年,政治运动处于频繁期,这构成了白玉、陕北这一代人精神成长的文化背景。“文革”伊始,白玉最先领会“中央精神”的要义,很快组织起自己的派系“工人革命军”。白玉要做的头等大事,当然是为自己领导这支派系的合法性作出辩解。显然,家族中有五个烈士帮了他的大忙,在这场运动中,这种血统的荣耀无形中充当了挡箭牌。在这个精神符号的感召下,白玉顺理成章地组建自己的队伍,并日趋壮大。而陕北受其影响,紧随其后,成为另一支派系的头头。陕北属于高干子弟,那骚动、火热和沸腾的血液让他无法安守本分,他似乎天生就要干点出格的事,以示自身价值的存在。只是迫于那个十几岁就干革命,生活中不苟言笑的父亲的呵斥和压制,积蓄太多的能量却苦于没有释放的通道。因此,在父亲被造反派关押后,那根反叛的神经如冬眠的蝮蛇被惊蛰的春雷唤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语境中,陕北和白玉如鱼得水、无所畏惧,在这场运动中可谓呼风唤雨、大展宏图。然而,“文革”结束后,陕北和白玉的所有过激行为遭到清算,其文化身份的合法性也再次受到质疑。作为“打砸抢”分子,他们原本难逃法律的制裁,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何白玉的牢狱之灾最终还是得以豁免,当然,这主要归功于家族光环的恩庇,一切的罪恶皆以“烈士家属”的名义得以化解。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何家子弟的兴趣转向经济,但毕竟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终结,在效益优先的时代,仅靠那股蛮干的狠劲已是无济于事。显然,何顿看到了“骡子精神”在这个新时代所遭遇的宿命。从整个生命历程来看,白玉的人生追求尽管荒诞不经,却有着深刻的时代悲剧性,从他的婚恋经历来看尤其如此。在小说中,与白玉有染的女性不少,但没有一个忠贞于他。
在男性主人公中,何五一也是一个充满反叛精神的人物。小说写到这个人物时已接近尾声,可以推断,他生活的年代大概处于世纪之交。关于他的反叛意识,从他对社会的解读就能看出:“我不喜欢这个社会,人都被扭曲了,找不到忠诚,找不到同舟共济的朋友,都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损人利己的货色。”所以,面对学校同事对他的出卖,敏感而高傲的个性驱使他断然选择了逃离。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属于这样的现实,“讨厌那种按部就班地生活”。在我看来,这个人物是作者审美理想表达的载体。相比而言,何五一已不像他的前辈们那样,仅仅依赖于武力打斗和政治投机实现人生价值,而是代之以现代艺术精神的,而这种知识者身份显然更符合现时代的生活价值观。我以为,何五一那耽于幻想的气质和狂放不羁的生命激情,不仅是众多女性为之疯狂的原因,更是与我们这个时代精神需求相契合的重要表征。
小说中的女性不少,在所有女性中,何秀梅别具光彩,无疑是最富有精神深度的艺术形象。何秀梅属于何家第三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看得出来,关于这个人物,作者是很用心的。甚至可以说,相对于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何秀梅的形象某种程度上更具有悲剧美感和审美意义。“骡子精神”在这个人物身上主要体现在她对情感的态度上。其实,那种以倔强和反叛为主要标志的“骡子精神”,在何秀梅这里,已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从行为方式看,这种精神表现为一种自残自虐和我行我素的作风。但从根本上看,何秀梅的悲剧,缘于她内心根深蒂固的传统少女贞操观。由于她十七岁就曾遭遇军痞轮奸,这对于抱有传统观念的女性来说无疑是致命伤。所以,即使她要死要活地爱着李文华,但却没有向其表白真相的勇气。尽管两人之间一直情书不断,但在历经多年马拉松式的恋爱后,李文华那海枯石烂的激情一点一滴从他的笔端流淌尽了,他终于决定另折他枝,选择了门庭显赫的何军花。面对这样的现实,何秀梅只能心碎,选择逃避。四十多岁时,她误以为姻缘已到,便与失偶男人肖楚公闪电式结婚,但终究因为不堪忍受其猥琐和粗鲁的行为方式而离婚。何秀梅选择离婚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她对男权思想的反抗,她说:“男人都自以为是,以为女人离不开他们,我就是要他认识到,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在经历这场婚姻后,何秀梅已不再怀有先前那份孤傲而自卑的心态,而是变得更加挑剔和尖刻,透出偏执狂的秉性。在何氏家族成员各奔东西曲终人散之际,晚年的何秀梅却回到了青山街三号,这似乎隐喻着她要固守着何家的精神血脉。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血性四溢的女人,在人生的晚年却再次遭遇强奸,死于暴力。这是一个富有意味而又充满宿命色彩的生命轮回,在这个意义上,何秀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而这种悲剧性很大程度上来自性别的错位。从生命个体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来看,何秀梅的反叛气质与这个家族的文化价值观不无关系。何氏家族中,长辈们给下一代的教育有着鲜明的倾向性,他们意识中,崇尚的是一种雄性意识和英雄情结,以此显示出军人世家的本色。而花木兰、武则天、穆桂英等历史人物则是长辈们宣教时常用的文化标本,他们通过历史上女性雄性化的原型来塑造后辈的文化人格,引导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何秀梅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生长出来的一支冷艳的花朵,她虽是女儿身,但生性好强,不愿服输。而这种要强的个性在小说中是以一种变态的思维方式呈现出来的。在秀梅看来,自己至少要当个教育局长才配得上李文军,更何况她内心藏有那不可倾诉的青春期隐痛。所以,“尽管李文华就坐在她门前拉二胡,用二胡那忧伤委婉的曲调向她倾诉爱情,向她述说大西北的凄凉和他心灵上的愁云惨雾,她却告戒自己不能软弱,不能在二胡那愤恨的怨天尤人的曲调中乖乖就范。”此外,何家女性中,何家桃的隐忍、顽强的生命意志,何军花炽热、猛烈的性格,与人对着干的脾性,也与何秀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比如小说写道:“我大姐(何家桃)是那种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女性”,“她是能用自己的肠胃消化苦果的女人,哪怕那只苦果再坚硬再枯涩她也能消化,因为她有一副能战胜铁屑钢渣的肠胃”。
正是有了那种不怕死不怕祸的倔强性格和反抗精神,以及那种隐忍、顽强的生命意志,那场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就不足为怪了。而这种集体精神的揭示,主要得力于作者客观冷静的叙述。小说的叙述者是何家第三代的何文兵,而这种叙述视角贯穿整部小说,不仅包括叙述者这一辈人(第三代)及其晚辈生活的叙述,也含盖了叙述者出生前对爷爷辈生活的叙述。叙述者不仅见证了何家百年间的沧桑,也目睹了中国整个20世纪的历史巨变。这样的叙述既保证了小说叙述的历史连贯性,又使整个叙述显得真实可信,显示出何顿在美学形式上的独特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何顿的叙事偏离了主流叙事的既有模式,这种审美异质性表现在作者能更为人性化地看待战争,在战争叙事的意义上实现了对以往“红色叙事”和“英雄叙事”的反叛,换句话说就是“去英雄化”、“去红色化”。何顿说:“我写战争,是想让读者知道,就战争本身而言,不论正义的或非正义的,都是血淋淋的屠杀。”从作者的战争观及其文本实际来看,何顿的叙述显然不同于正史的叙事模式和叙事态度,因为其叙述重点不在参与工农革命红军的何家子弟,而是指向军阀和国军中的何家军人。在何顿看来,无论处在战争或政治运动的哪一方,军人世家的几代人,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人”。何金山对日抗战也好,对红军的包容和顺从也罢,他似乎从未抱着什么主义,而是凭着一股子正义和正气。即使是后来的投诚起义,也是为了求得心安,不想让他的士兵作出无谓的牺牲。当然其中也存在兄弟之间私人情谊的考虑,但正是这些因素的介入,把军人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本身,才使得这部小说与主流的“红色叙事”和“英雄叙事”有了明显的区分。这就是何顿的叙事伦理,它不仅表现出相异于主流价值观的叙事向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这部小说下部内容的真实性。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何家军人文化身份的复杂性,他们中的部分成员后来被打成“右派”才有了深层的根基。也正是因为精神基因的代代遗传,陕北、秀梅、白玉、五一的反叛气质才得以一以贯之,没有丝毫突兀的感觉。
何顿把叙事空间择定在长沙市青山街,在审美的意义上显得意味深长。小说中的人物无论走多远,总会时不时回来看看。所以,青山街是一个承载着巨大审美兼容功能的场所,它不仅是长沙城乃至湖南省百年日常生活的缩影,更是辐射出整个中国在每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面影和精神面向。某种意义上,青山街何氏家族的兴衰史,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镜象。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以一个家族的性格史和精神史,清晰地照见了中国人一个世纪的精神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