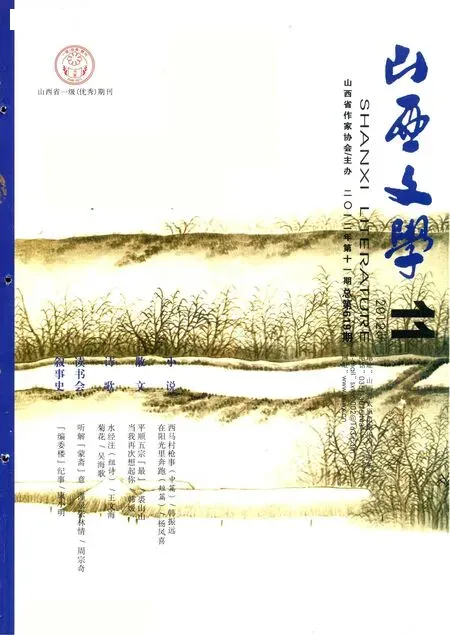东园公之泪——读林鹏先生《东园公记》
王书鹏
处于高层建筑雨后春笋般矗立的都市,林鹏先生依然几十年如一日起居于并垣省府宿舍。这个地方在解放前是政府东花园,时过境迁,花园之说已是传闻,可是院子当中几棵入云大树,寒暑往来,繁茂凋零,犹可以使人想见当年东花园的气派。
林鹏先生住在东花园的老平房里,又年事已高,自称东园公自然贴切。但是我以为,林鹏先生私淑另一位东园公的德行,以东园公自称,乃表明自己的志向。另一个东园公,是秦汉间的一位隐士,他的事迹被收在《高士传》里。
据东汉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东园公唐秉,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秦政暴虐,东园公和甪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夏黄公崔广四位老人相约,结茅山野,隐居起来,过着“岩居穴处,紫芝疗饥”的生活。四人皆修道洁己,非义不动,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安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而肆志。”秦败,高祖想邀请他们出山,他们拒绝了。但是,当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时,四人又出山相助,挽救皇权于动荡之中。刘盈称帝后(汉惠帝),欲对其加官封爵,他们又婉言谢绝,重新回到商山,继续过起了清贫的隐居生活,直至终老。四人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齿,衣冠甚伟,隐居的地方是商山,于是后人称四人为“商山四皓”。
对于他们的行为,宋人王禹偁给予这样的评价:“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刘,知存也;应孝惠王之聘知进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俱备,而正在其中矣。先生危则助之,安则去之,其来也,致公于万民;其往也,无私乎一身。此所谓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贤而已!”(《四皓庙碑》)四皓墓在陕西丹凤县商镇西端,隔丹江与商山相望。相传,汉惠帝曾派三千御林军每人自长安携土十斤,来商山为四皓墓陪土,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商山四皓的故事如竹林七贤一般被历代文人墨客反复咏唱,大诗人李白曾作《过四皓墓》:“我行至商洛,幽独访神仙。园绮复安在,云萝尚宛然。”陶渊明《桃花源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商山四皓也是绘画的好题材,颐和园著名的长廊上就绘有商山四皓的故事。他们的形象也常见于文人清玩、室内陈设。四人或清谈,或喝茶,或下棋,或赏琴,无疑这种形象是画家的理解与世俗观念达成一致后的产物,而实际情况也许是,隐居的生活很清苦,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风雨侵蚀酷暑难耐也是常有的事。皇甫谧对远离政权和世俗的隐居行为解释作“不能屈己”。对于东园公来说,隐居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态度。
读《平旦札》,我见到这样的文字:
“天下大道多歧路,迷途知返时已暮。白首一言公无渡,公无渡,公无渡,枯鱼过河泣谁述?”枯鱼就是死鱼,死鱼是不会哭的,会哭的是人。人在事后不禁不由得落下泪来,在旁人看来简直莫名其妙。我抱头痛哭的事,也有过,深夜哭醒的事也有过,那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现在老了,看见什么也不再惊奇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抱头痛哭、深夜哭醒与林鹏先生豪放不羁与声震屋瓦的形象产生较大反差。什么事使林先生伤心难过,我略知一二,不得详解,心存大惑,暗忖,要是再有本《林鹏蒙难记》这类的书就好了,就可以解释林鹏先生何以为哭了。
眼前这本《东园公记》解答了心中的疑惑。《平旦札》定位是读书笔记,《东园公记》定位纪实散文,虽体裁不一,但思绪连绵,首尾互接,浑然一体。是挨整三十年读书三十年的进一步阐述,如果说《咸阳宫》、《平旦札》、《蒙斋读书记》、《丹崖书论》,以及林鹏先生的篆刻和书法是谜面的话,那么《东园公记》就是谜底。他揭示了一个小八路何以成为东园公的心路历程。如果说,在《平旦札》中,林老还是啜泣的话,那么这本书简直就是大哭了。在谜面,我们看到了林先生的刚硬,在谜底,我们触到了他的柔软。
东园公说,人到八十,经历了几次大的战役,民族的浩劫,看见什么也不惊奇了。可是回忆起一些人和事,却忍不住要流泪。很少有作家在书中如此大规模地记载自己的哭泣。
周宗奇先生在《四个林鹏》一文中说到了林鹏先生的四个侧面:一是能写字,二是喜爱书,三是会动脑,四是爱哭。概括得非常准确。且听《东园公记》里的哭声——
得知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樊金堂去世的消息,林鹏先生一边写下“伟大的民族英雄樊金堂永垂不朽”的挽联,一边泪流满面。(《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
1991年春天,从大同去北京的路上,车坏了。没办法,只好下车一边活动活动,一边等司机修车。一抬眼,大海沱山,新保安!思绪一下子就回到四十二年前的那场战役。想起昔日的战役,想起牺牲的战友,林鹏先生情不自禁。汽车修了半个钟头,林鹏先生的眼泪流了半个钟头。(《白发青山两无言》)
1952年,林鹏先生在部队受到打击报复,被定为“思想老虎”,受到处分,正连入伍,副连转业。在最困难的时候,陈亚夫政委呵护有加,支持林鹏先生与宗宝女士的恋爱。一年,陈亚夫来山西,一下汽车,就嚷嚷:“林鹏来了没?”1990年,陈亚夫去世了,林鹏夫妇二人闻此音讯,都哭了。(《回忆陈亚夫》)
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赵虹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自杀,林鹏先生多次梦到他,两人在一起抱头痛哭。(《平旦札记·一○二》)
清风店一战,二千三百人只剩不足五百人,虽然打了胜仗,可是撤离战场时,没人说一句话。多年以后,老战友说起往事,都纷纷落泪。(《我所经历的战争》)
有一天,心绪烦乱,不能入睡,就起来,站在防空洞前,望着东方鱼肚白的天空中,渐渐的泛出朝霞的火红的颜色,不知为什么,突然落下泪来。也许想到了儿时曾经滚下过的台阶和母亲的笑容。(《童蒙忆零》)
为李玉君烈士立碑之后,林鹏先生想起自己曾作过一首小诗:“儿时戏耍地,山顶有棋盘。老张一张望,心酸不可言。”(《南管头人》)
2003年的一天,林先生乘车从徐水路过,使劲朝路边张望,想找到谢家营,没找到,十分难过。他怀念张学义,一个农村出来的小八路,一个农民子弟兵,一个有高度文化素养的革命军人。(《英雄失路张学义》)
抗美援朝时期,战友张世禄被派往南朝鲜从事地下斗争,林鹏先生送了一里多路。林鹏先生很难过,心想,以后可能永远见不着了。以后一想起张世禄就难过,难以释怀。(《白发青山两无言》)
梁诚祭奠,为在冤假错案中屈死的冤魂哭泣。结尾是回到家,姑娘悄悄对妈妈说:“爸爸病了。”其实哪里有什么病。(《罪孽》)
好友王朝瑞先生去世了,林鹏先生夜半无眠,打开电视,直到天亮。衰年变法的讨论犹在耳边,正值艺术创作多产期的好朋友却遽然辞世,怎不神伤。(《纪念王朝瑞》)
康八里见到了梁朴,大哭起来:“我对全体职工,真诚相待,开诚布公,我们无话不谈。我们非常团结,人和人之间没有一点隔阂。这样的单位,再也没有了。一次运动,一棒子把所有正派人都打下去了。这样的单位再也没有了,他们没有任何问题,却都被判了刑,我连问都不敢问哪。”(《康八里章》)
1960年,许多人饿死,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并没有纠正当时的极“左”政策,失望之极的林鹏先生跑到野地里大哭一场。(《平旦札记·一○二》)
林鹏先生何以为哭?是为了个人莫须有的冤屈,为了已经失去的文化传统,是为了在以革命和斗争的名义而奋斗的过程中失去的美好人性,是为了渐行渐远的人间情谊和知遇之恩。眼见许多美好的事物衰败下去,许多战友、老朋友离世,他无可奈何,于是哭。
无疑,写作对于林先生来说,是哭泣之后的行动,他不能这么哭完拉倒,他要说,要写!并且是非说不可,非写不可!林鹏先生哭的时候心是软的,写的时候心是硬的。思接千载,所向披靡。人们惊叹,八十岁的人了,竟然发出骇人之语,许多篇章不经删减难以面世。人们惊叹他敢写,却无人指责他瞎写。
某日,于林老的书中见有《万里长征万里线》一书,便查询网络,很巧,旧书店有售,便买了回来。
下班后,骑车去林老家,握手寒暄完毕,林老见我提着纸袋,便问:“拿着什么?”
我从信封里取出这本书,递与林老。林老一见,大声叫道:“哎呀,这个珍贵!”于是便介绍起作者张帆来。
“张帆,那大记者,可了不起,和杨朔一起的,只不过没有杨朔名气大。”弹弹烟灰,趁着兴致,林老说起当年行军渡河的事。
“都把裤子脱了,顶在头上,齐腰深的水,好冷呀,那是桑干河的水呀。刚过来,命令来了,要赶紧回去,于是再回去,刚回去,命令又来啦,说,既然过去了,怎么又回来了?赶紧再过去。一晚上过了三次河,战士发牢骚骂娘呀,睡就睡在地上。”
正说到兴奋处,老人突然沉下脸来,把手里的纸烟捻灭,随即说了句脏话,感叹一声“唉,今天说这些有什么用?没人听。”
当他说出“没人听”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他的身后已是著作累累,一版再版,拥趸者日众了。
我注意到这样的事实:
一九九五年三月七日,林鹏先生在其长篇小说《咸阳宫》出版后赠书与好友王朝瑞先生,随即在书的扉页上写下几句打油诗,诗曰:“十年出一书,恰似磨一剑。谁有不平事,也是瞎扯淡。”这里瞎扯淡是自嘲,也是失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林鹏先生致王朝瑞先生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自上班以后,终日忙于琐事,就像一头驴子,被拴在橛子上,十步之外芳草青青,可望而不可即,奈何!”
我还注意到,曾经有两位领导明确告诉林鹏先生,不许读书!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在朝鲜开城前线,一位老红军下的命令。一次是一九七七年,一位老八路下的命令。但林鹏先生不听话,硬硬地把书读了下来。
而林鹏先生的烧书与藏书,颇有自行了断的意味。1967年,四十岁生日那天,林鹏先生当众烧掉一个长篇,两个中篇,同时在日记本上写下构思已久的小说名字《沙丘》,这就是长篇小说《咸阳宫》的前身。1976年,街上是庆祝打倒“四人帮”的游行,而林鹏先生却在家焚烧字迹,整理书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为避灾祸,他将一包书稿寄于老战友毕俊林家,一包书稿寄于好朋友田际康家。深夜十二点,田际康老先生将包袱塞进自家鸡窝的夹缝里,对林鹏先生说的一番话,至今读来惊心动魄,如断肝肠。“即使有人抄我家,也不会注意到这个鸡窝,即使我被抓,这地方你也知道,事情过后,你自己来拿。”
不让读书与非要读书,烧书与藏书,写书与出书,言说的有意义与无意义,像拉锯一样在林鹏先生身上较量着,撕扯着,最终他响当当地说:“我有资格!”
柯文辉先生说林鹏先生继承了吕不韦刚的一面,所以在仕途上是个失败者,然而在思想上,尤其在文化素质和艺术造诣上,他必将是个胜利者(见柯文辉《咸阳宫·序言》)。林鹏先生自刻有“难畜”一章,乃出自《儒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我又想起关汉卿那句有名的话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这句唱词倘若让演员走着台步唱出,那一定是激昂清越充满了骄傲和悲壮的气概,使人仰慕且垂泪。
林鹏先生写出了《咸阳宫》、《蒙斋读书记》和《平旦札》,在外,乃是舆论环境有所松弛,师友的期待与鼓励,在内,乃是非写不可的冲动与执著。对于死去的战友、朋友,乃至死去的时代而言,他无疑是代言者,他是他们推举出来的代表,他在替他们活,替他们说!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白死,林先生也没有白活!有一种“我不写谁写”的气概,或者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
对于写作的动机,林鹏先生有如是反观:“当有朋友问到我写作《咸阳宫》的过程时,我说,像我这样地位低下的老革命,有吃有穿,儿孙满堂,欢度晚年,然后默默死去,有何不可?当然没人责怪我。不过对我来说,对一个参加了革命又读了书的人来说,那就等于白活了,白到人世间走了一遭。”(《第四十一章》)回溯到汉代,司马迁在《报任安少卿书》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司马迁还说:“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林鹏先生强调做学问搞艺术要业余。对于林老而言,这是什么样的业余状态,在战争中的沉思,是运动中的偷闲,是被压迫之后的追问,是夹缝中的生存,是苦闷中的自得与消遣。没有官方的命令与不得已的应付,没有图解政治的遵命文学,这种业余的努力本身就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如吴冠中先生向来强调的,艺术家应该是“野生植物”,不是靠“圈养”就能出成果的,要有浇不灭烧不死的热情。这样的认识与表述其实和林鹏先生对搞艺术应该是业余的认识是一致。而这热情的原点,乃是温柔的良心。无疑,《东园公记》所记载的只是林老生活历程的片段与点滴,可是透过这片段与点滴,我们感受到林老柔软又坚硬的情怀,正是这种情怀,维系着他对善良人们的爱,对美好人生的珍惜,对逝去岁月的感怀,对中国文化的信念。虽然喜读先秦典籍,高头讲章,虽然也自称东园公,可是心底里却始终牵挂着普通人们的命运,平凡人间的悲欢。林鹏先生的散文平实易懂,却让人激动,让人深思,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做“接地气”。林鹏先生的人生经历,他的治学历程,他的如椽之笔,使我们感奋,也使我们哀伤。
江苏省苏州西山岛凤凰山有个叫东村的村子,传因东园公隐居于此而得名。东园公未必在此隐居,但这正反映了人们对其的崇敬与怀念。村中有东园公祠,门楼正面书“东园公祠”楷书大字,背面横额为“商山领袖”四字。现在,祠堂已经败落。偶有好事者驱车来到此处,打量门头横匾,但见杂草丛生。好事者踩上梯子,摘除匾额上的乱草野花,“商山领袖”四字便突显了,楷体榜书斑驳残破却风骨逼人。望着刻在石头上的字,好事者迟迟不愿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