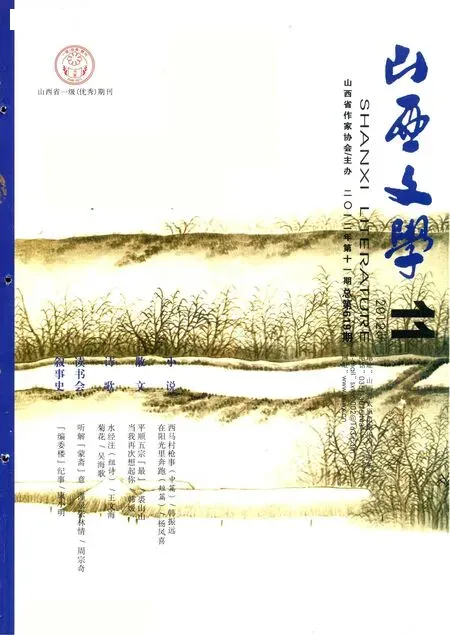“编委楼”纪事
康小明
每每回一趟山西日报社宿舍大院,看望九十岁的老母亲,总能想起许多儿时的回忆。走在宿舍院子里,看着一栋栋楼房,有时却有几分失落,因为我魂牵梦绕的编委楼早已不复存在。
编委楼,那是当年山西日报社宿舍唯一的一栋宿舍楼,因为居住的都是编委及总编辑,大家习惯称为编委楼,这个叫法一直沿袭了几十年。后来,楼房多了,才改为六号楼。再后来,六号楼作为危楼被拆掉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报社的大管家,秘书长鲁兮大手笔,一口气在宿舍修建了东西17排平房,解决了报社大部分人员的住房问题,编委楼就建在十一二排西边。楼房于1960年竣工,那时我才几岁,没见过楼房,施工期间,调皮的二姐给我梳了一根朝天小辫,脸上抹着红红,拉着我的手上楼去玩。那是一栋尖顶四层青砖红瓦的楼房,一共两个单元,东单元8户,西单元11户。每户近百十平米,房间很高大,有卫生间座式抽水马桶浴缸热水和暖气,每个卧室都有顶到天花板的壁柜,厨房有橱柜,地板听说是苏联进口的红砖地,越擦越红。尽管房间较高级,但是每家每户陈设都很简单。机关给每户都配备了大人和孩子的床铺,一张饭桌,几把椅子,案板、擀面杖和水缸等,属于各家的私有财产,就是几口锅两三只箱子而已。楼房四面围花栏墙,有个大门。大概就是这个院墙,让编委楼的孩子们普遍有种优越感,和墙外面平房的孩子们接触很少。楼房后院是各家的菜地,前院是各家的煤池。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我家住到了1970年,下放大同8年后,1978年又搬回了这栋楼房的东单元四层东面。直到1991年报社盖新楼房,才搬离。前前后后,我家在编委宿舍楼住了23年。
发小成群
那时候,都市里能闻到田野里飘来的青草味道,穿着白衣红裙的女孩在编委楼的院子里跑来跑去,塑料凉鞋叩击出轻快的响声,一群呼啸而来的男孩子,把自行车铃铛摁得有如冰雹落地,那会儿的冰雹都是透明的。
编委楼每家每户孩子都很多,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出生的到五十年代的,年龄不等,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不算多。19户人家一共有七十多个孩子,院子里总是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就是这样一群孩子,在那段青涩而淳朴的岁月里开始了一场混沌与成长的挣扎。
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名,比如陈墨章家中的小蛋,大块;鲁兮家的薇薇,小二,三娃;刘山家的小米儿,二米,小闺女。有些除了小名还有外号,甚至有些外号大人也跟着叫,比如郭允昌家的郭亦敏,人们都叫他老一胖;张春旬家的张效铮,外号居然叫耗子;左录家的左小青外号叫老左,因为那时候不时兴称呼职务,孩子们在楼下喊“老左”,左录老伴就从阳台上伸出头看,以为是喊左录。马明家的马小勇经常提着一把斧头下楼劈柴,他长得魁梧高大,像《水浒》里的黑旋风李逵,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马奎。
因为提倡节俭和孩子多,许多男孩子的衣服是大的穿过小的再穿,裤腿补了一截又一截,但是女孩子们穿得却都很时髦。每逢过年,母亲都会在我的床头放一身新衣服,初一早晨起来总让我十分开心。长大成人后,我惊诧地发现:昔日的邋遢鬼、丑小鸭们都变成了帅哥靓女,就连当年的鼻涕虫樊小慧,居然成了省歌舞团的合唱演员。
几十年过去了,昔日的伙伴大都不见踪影,四散在全国各地,有的甚至在海外,大部分人也年过半百了,相见不一定能认出了,但是我想,如果他们回忆起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不会忘记在编委楼的岁月的。
读书成风
我们这群报人子弟,可以称为书香门第。阅读各类书籍,是编委楼孩子们的一大乐事。每个大人都喜欢读书,许多人藏书颇丰,包括我的父亲康溥泉,唯一的嗜好就是淘书,购书,读书。耳濡目染,我也从小喜欢看书,家里有个一堵墙的大壁柜,上面堆满了各类书籍,我总是顺着暖气管爬上去,然后钻进去趴在里面,柜子留一条缝隙透光,然后在里面看书,许多书是看不懂的,但是也翻了不少中外名著。小伙伴们经常交换看书。那时家家户户白天都不锁门,我们推开门就能进去,看人家的书架上有啥好书,然后提出来交换着看。我记得小米儿借了我一本《红岩》,后来找不见了,怕我家长骂我,就郑重其事的给我赔了一本《野火春风斗古城》。我二姐曾经听见鲁对她爸爸说,“你上街去呀?你给我买书啊,买不回来小心点!”父亲看我们姊妹几个好看书,经常给我们买儿童读物,我看过后就捐给班里了。没少落老师表扬。我们家的孩子吃饭时看书,睡觉时看书,上课时也看书,不管家长和老师怎么呵斥,我们欲罢不能,看书绝对上瘾了。
那时,除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我们主要是看前苏联的文学作品。虽然那时中苏关系日益恶化,收音机里一评二评加重着抨击的力度,但是毛主席说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所以,列宁,斯大林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在中国仍处于肯定地位。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前苏联文学作品是《盖达尔选集》,里面的儿童故事让我十分向往,铁木尔成了我心中的偶像,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文革”期间,编委楼的孩子们都失学了,是各种名著陪伴着我们度过了那段特殊的时期。1970年,我家去大同下放,规定带的行李有限,清理最多的就是书籍,家家户户亦如此。我记得父亲左挑右拣,还是按废品价卖掉了两平车书,我想当时父亲的心里一定很悲伤。长期的家庭熏陶,使编委楼的男孩女孩都多了几分书卷气,也多了几分书生气,都有较深的文化底蕴,后来子承父业,在新闻单位工作的人较多,在其他行业的人也都很有成就,有人当了省级干部,厅级干部,处级干部,更多的人是当了各类专家,学者。
编委成谜
有这么多年纪相近的孩子在一起,星期天串在一起,院子里就动静大了,由于总有大人或读书或写作或上夜班睡觉,家长们总是一再叮咛孩子们不要在窗户底下嬉戏折腾。
其实那时候我们是不了解长辈们的。长大以后才知道,他们是一群来自太行,太岳,晋绥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报人,是山西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在中国的新闻史中留下了英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日报》成为全国的红旗报,毛主席,刘少奇都多次表扬山西日报,亲笔为报纸题写报头。我对毛联珏印象很淡,只记得他家条件最好,有黑白电视机,孩子玩的是很大的一辆电动遥控汽车。“文革”前夕他就调任北京,后来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对吴象的印象,只记得人们常调侃的一句话:“山西文章属吴象,吴象给我改文章。”后来他家也搬迁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刘山很有伟人的形象,发型很像毛主席。而陈墨章,张春旬,郭允昌永远是笑眯眯的。我印象中赵宪斌就是个老爷爷,拄着拐杖或者坐着轮椅,一直到现在,他依然是我儿时记忆中的形象。老虎的奶奶是个老烈属,脾气暴躁,经常拄着拐杖骂我们,孩子们都有几分怕她。后来她是拄着拐杖骂造反派。小蛋的爷爷说着一口河北话,一到天快黑时就对着他家养的鸡说:“窝里去!”那些鸡就乖乖回窝了。印象最深的是陈铿,他是报社专门负责给来晋的中央领导拍摄照片,后来他调任省外事办副主任,每次见他都是出国回来,在宿舍门口下了小汽车,气宇轩昂,风度翩翩。
鲁兮是报社的大管家,后来调任省广播局局长,他家里的后阳台通着后院。有一次,他出来乘凉,把一杯茶水放在阳台上,然后就回家去了。我们一大堆孩子看见了,不知是谁提议:我们给他换成尿吧,于是几个孩子争先恐后,扑过去倒掉茶水,尿了一茶杯尿,迅速躲在暗处,看见鲁兮出来喝了一口然后就倒掉了。我们都偷偷乐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见面常常开心的重复着这个故事:“鲁兮喝尿”。现在,德高望重的鲁老已经九十多岁了,身体非常好,他的长寿可能有我们一份功劳,因为喝了童子尿。鲁老大量,恕我们年幼无罪。
1966年,“文革”来临了,许多大人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我们惶惑,不解,编委楼的围墙被推倒了,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造反派抄我家时,翻出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书里夹着一张刘少奇的照片,第二天,报社院子里就贴出大标语,说我父亲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那时我们也做了不少傻事,我记得张春旬在报社院子里劳动改造,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孩子把他的草帽扔到树上,他乐呵呵地手脚非常麻利地就爬上去摘了下来,他的爬树本领着实让我们吃惊。岁月无情,几十年过去了,昔日的许多大人毛联珏,刘山、张春旬、郭允昌、樊显正,牛项良,李玉秀,杨尚枫,武蕴,王西一,张柯南,王士元,包括我的父亲等都已经作古,而我才对他们熟悉起来,才了解理解了我们的父辈。我怀念父亲,也深深地怀念着父亲当年的同人,我深深地敬重他们,我知道,他们是一群好人,一群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一群深深爱着我们的父亲。
苦难成甜
1960年到1962年,是我们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可是我却对那段历史印象很模糊,因为大人们努力让我们吃得饱点。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家家户户开始在后院种小块地。我们也经常在地里帮助家长干活,后院的地过去是坟场,我们经常在地里刨出死人骨头,然后拣小块的骨头摩擦手上的瘊子,确实很有效果。
那时候的我们,普遍偏瘦,豆芽菜居多,只有孩子少的家庭孩子能吃胖。比如王西一家的和平和东风,小时候胖乎乎的照片居然登上《山西画报》的封面,我们看了十分羡慕。
家里整天吃的是豆腐渣饼子、玉米面糊糊煮野菜,喝糊糊时,家里其他孩子喝稀的,让我捞干的野菜,因为那时我是家里最小的。我记得母亲经常领着我们去双塔寺挖野菜、挖甜草根、捋“榆钱儿”和槐花。还去过黄陵的菜地拣菜叶子。有一段时间,吴象家的小象吃坏了肚子,院子里的孩子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猴拉稀”。去食堂吃饭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预先订好菜谱,然后用饭票去排队打饭,许多要好的孩子挤在一起,窝头,熬白菜也吃得津津有味。其实不在乎吃什么,而在乎没有大人,自由自在聚餐的那种感觉。
编委们虽然吃的是小灶,但是困难时期,大人们都把小灶的饭菜打回家让全家人吃。星期天休息,就可以看见许多大人出门,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边晒一边说话,看谁的腿浮肿了,互相按着,看谁的坑深,复原得慢。就说明谁浮肿得厉害,报社就会给浮肿严重的编委批点黄豆。我记得最好吃的一种零食就是“伊拉克蜜枣”。那一时期。为了支援中东地区国家的独立斗争,中国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用外汇从这些国家进口了一些产品,“伊拉克蜜枣”就属于这种性质。可是过了一阵子,传说这种蜜枣带有肝炎病毒,也不知道真假,反正市场上这种枣渐渐绝迹了。
我第一次进饭店是在“文革”期间,有一天哥哥领着我们几个小伙伴出去玩,走到了并西商场对面的一家饭店,我们几个走进去,专门挑了一张靠近大玻璃窗户的桌子,让外面的路人看见我们几个能吃起饭,其实我们几个只是一人要了一碗开水,拿着筷子在里面搅来搅去,好像我们真的在吃饭店。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十分滑稽。
玩耍成瘾
少年不知愁滋味,尽管我们赶上了困难时期,赶上了“文革”,尽管那时没有现在的玩具高级,但是我觉得我们远远比现在的孩子幸福百倍,因为我们小时候玩疯了,玩够了。1963年到1970年,是最阳光明媚的时光。
1963年后的我们吃饱了肚子,精力格外旺盛。男孩子喜欢玩捉迷藏,打篮球,乒乓球,弹蛋蛋,叠元宝,打弹弓,玩打仗游戏,自制弹弓枪,或者木制手枪。孩子们因为玩耍受伤的事情时有发生。我曾在院子里的晾衣服钢丝上面,因为打秋千摔断一次胳膊;在院子里的墙头上,又摔断一次胳膊。那时候楼上楼下的孩子联系,就敲暖气管子联络。
我们玩得乐器是口琴,笛子,箫和一种有按键的不知道名字的琴。到了冬天,我们拿着自制的冰车去迎泽公园的湖面上滑冰,夏天,我们去公园湖里或者游泳场游泳,春天,我们偷来平房住的人家的竹门帘上的竹条自制风筝,去野外一比高低。女孩子喜欢跳皮筋,跳方格。那时我们还喜欢集邮和在院子里下军棋和玩飞行棋。我们很着迷下棋,相约到谁家去,几个人一下就是半天时间。选择的家庭,一般是自由度大,大人不怎么干涉,而且家里有点好吃的。一到饭点,院子里总会响起许多家长的呼喊声:××,回家吃饭!学骑自行车也是我们当时的一大乐趣。一辆自行车能乘坐四五个孩子,好在那时的车子结实。我们的另一大乐趣就是去报社礼堂看电影,我记得是五分钱一张票,因为家长有时候不给钱,我们只好趴到礼堂窗户上往里看,等到后半场不收票了,我们就冲了进去。那个年代,我们看了不少后半场的电影。
劳动成习
由于家长们的教育,编委楼的孩子们劳动观念都很强。大孩子照看小孩子就不用说了,比如,打煤糕,就是一件很重的活。那时烧土一块五一车,为了省钱,孩子们亲自去烧土场挖烧土,然后买回煤,把煤面和烧土掺和起来,用模具打成煤糕,晾干了储存起来。在家里也要每天活煤泥或者下楼搬炭和煤糕。楼道是每家每户轮流值日打扫,卫生红旗挂在谁家门口,谁家就负责清扫整个楼道。读小学时,我常常跟着邮局来报社拉报纸的汽车到火车站义务装卸报纸。初中时,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农劳动,学工劳动和野营拉练,后来又在学校挖防空洞,到汾河拉沙子,到东太堡砖厂拉砖。毛联珏是个九级干部,他家大孩子小矛小学时一到假期就去机关做临时工,扫院子,倒垃圾,所得报酬付学费。1964年暑假家长又让他去大寨劳动锻炼,1965年毛小瑞又去他父亲四清的河北永年县劳动锻炼。大概正是由于这些磨炼,使编委楼的孩子们后来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苦都能应对自如。
我在家里先后养过鸡,鸭,鸟,猫和兔子,那时最时兴的是养蚕。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当时觉得看着蚕吐丝做茧很有意思。许多人家把蚕放到大床板上吐丝,吐出了一个床板那么大的长方形的丝垫,揭下来之后,可以做一个丝绵背心。那时报社院子里种了许多桑树,但是也不够人们采摘,有时只好给蚕吃榆树叶子。1969年,编委楼的家长全部进了中央学习班,工厂停工,学校停学,社会极度混乱动荡,孩子们成了一群自由自在的羊,失控了,出格了。那时候都是大孩子给小孩子做饭。到了晚上,一群群的孩子围在煤池边上讲鬼故事,胡侃瞎聊。年龄大些的孩子就参加红卫兵,到社会上串联、造反去了。
1970年7月,中央办的山西干部学习班结束了,编委楼的大人们全部被重新分配工作,大部分人被发配到全省各地或者工作或者插队,年龄较小的孩子也随着家长各奔东西。年龄大些的孩子就到了内蒙兵团、铁建兵团、农村插队或参军。在北上大同市的火车上,15岁的我开始伤感: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但我知道,编委楼再不能为我们的少年时代遮风挡雨了。8年之后,我家再次从大同搬回编委楼,物是人非,那栋风雨飘摇中的旧楼已经没有昔日的欢声笑语,没有昔日的风采了。岁月流逝,许多事情已经很模糊了,但是那栋后来被拆掉的编委楼,以及童年的故事却在我的记忆深处愈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