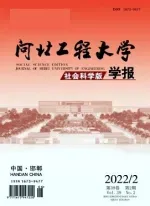信于本,传以真——论理雅各的儒经翻译观
陆振慧,崔 卉
(1.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2. 扬州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世人对其一以贯之的“信本”原则却褒贬不一。贬者常以“呆板”、“古拙”、“冗长”、“僵硬”等字眼(王辉,2004;魏望东,2005)抨击理氏译风,褒者却盛赞理译“准确”、“精炼”、“严谨”、“雅致”、“理通文顺”、“保留形象”、“切合风格”等。(王辉,2003c,2004,林煌天 1997,刘重德,1994)截然相反的评价折射出学界对待“信本”原则的不同态度,也反映了理氏儒经翻译观尚未被充分理解。理氏未留下多少翻译理论的阐述,但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更不能说他没有自己的翻译观。透过理氏译经的动机、目的、过程和方法,我们可以看到,理氏翻译观内涵丰富而深刻,对我国典籍英译工作亦有重要启示。
一、理雅各翻译儒经的动机和目的
许钧先生(2004)曾说: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涉及到“为什么翻译”的根本问题。对具有历史使命感的翻译家来说,只有明确了“为什么翻译”这一根本问题,才能作出“翻译什么”的选择;这两个问题一旦找到明确答案,如何翻译的问题便能在原则上得到解决。因此,翻译动机对翻译家选择什么文本译,采取怎样的策略译,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理雅各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翻译家。他译儒家经典出于责任与爱,翻译的目的,则是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东西交流。
(一)崇高的动机:责任与爱
与其它传教士一样,理氏最初来到中国(香港),最希望看到的是耶稣取代孔子。但此时的传教工作笼罩在侵略的阴影之下,遭到儒家学说的强烈抵制;而且与那些“更为本地化的天主教同行们”相比,新教传教士们在文化上的不敏感以及与本地文化的隔阂显得更为突出。在《中国的宗教》后序中,理氏直言:基督教当时在中国难以盛行,“基督教神职人员的矛盾与非正义态度,英国贸易的自私与贪婪,和所谓基督教国家的野心与自利”是一重要原因。(张西平、费乐仁,2011:15)另一方面,他发现“儒家思想既不像佛教主张无神,也不像婆罗门教信奉多神,因此和基督教并不对立”,可以“利用”而不可“肆意诋毁”。(Ride,1998:10)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中华民族是“早已经摆脱了野蛮愚昧”、有着“更高品性的”民族,其他帝国如亚述、波斯、希腊、罗马等皆兴而复衰,唯有“中华帝国连同它四万万国民依然耸立”,其中必有某种“最伟大的德性和力量”在起作用;他还发现中国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热爱和崇敬学术”,而中国“国民的礼貌风俗和习惯,来自于古代经典中的思想规范”,所以“任何人想要弄懂中华民族,就必须了解他们的古典文学”。(段怀清, 2005)他规劝传教士不可“驾着马车在孔夫子墓地里横冲直撞”,感到“只有透彻掌握中国人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石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认为与自己担负的职责相称。”(Ride,1998:10)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理氏决定系统译介儒家经典,坚信“此项工作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世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了解这个伟大的帝国,我们的传教士也才能有充分的智慧获得长久可靠的结果。”(Legge,1905:32,38,95)
(二)明确的目的: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东西交流
理氏虽最初以传教士身份东来,肩负着神圣的传教使命,然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让他倾心仰慕,逐渐产生了让中国经典为我所用、为他人所用的想法。(陈先芝, 2011)他深刻认识到“十三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必经之路,于是在布道传教的同时,开始了刻苦研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工程。理氏以儒学为中心,兼顾道家,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力度最强劲,影响最广泛的原动力,选择了深入中国文化中心地带的最佳路径。这种选择不再是早期传教士零星、临时的翻译,其预期效果也不再仅仅是对中国文化的习得。甚至在完成了全部儒经翻译计划之后,理氏仍继续研究、宣扬中国文化,可谓“将自己整个生命用来发现、理解和评价这个古老的中国世界。”(张西平、费乐仁,2011:18-19)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理氏译中国经典持的是“翻译交流观”,即把翻译看作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通有无,强调在翻译中持平等态度,要求译者充分认识原文所表现出的文化差异,并尽可能将之溶入到目的语的大语境中去,以真正达到吸收出发语文化与丰富目的语文化之目的,为此,在翻译上尽可能保持原作的“原汁原味”成了一种必然追求。(许钧,2004)
二、理雅各的儒经翻译观内涵
若用一句话总结理氏儒经翻译观,似可概括为:信于本,传以真。此“本”自然是原作文本。但理氏所信之“本”并非仅是文本字面之义或文本表面之形(尽管他十分注重“形似”),而是要透过文本表面探寻原文“本义”,也即“勿失厥义”之“义”。而“传以真”之“真”则包括译者对作者、读者和译事之“真诚”,以及实现文化之“传真”。需要说明的是,理氏翻译思想,他本人说了一些,但更多地反映在其翻译行为中,体现在其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信于本”既是原则也是手段,“传以真”既是目的也是行为。
(一)信于本:立足文本,探求本义,揭示本真
立足文本。先看理氏自述:
(1) … his object having always been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 Chineserather thangraceof composition.Not that he is indifferent to the value of anelegantandidiomaticrendering in the language of the translation,and he hopes that he was able to combine in a considerable degreecorrectnessof interpretation andacceptablenessof style.
(2) The Author ventures to hope that the translation now offeredrepresents the Chinese originalmuch more faithfullythan either of those previous ones.①
(3) My object has been to give a version of the text which shouldrepresent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without addition or paraphrase , as nearly as I could attain to it. The collection as a whole is not worth the trouble of versifying. But with my labours before him any one who is willing to undertake the labour may present the pieces in “afaithfulmetrical version.” My own opinion inclines in favour of such a version being as nearlyliteralas possible.
(4) His object has always been to translatefaithfully, without resorting toparaphrase, which he considers a slovenly and unscholarly practice; yet he hopes that his versions are not in language that can be represented as uncouth, or unpleasant to read.
以上(1) (2) (4)分别引自《中国经典》卷一(p.x)、三(p.vi)、五(p.vi)序言,(3) 取自卷四绪论(p.116),虽只寥寥数语,“信本”原则却是说得很明白:
第一,任何情况下,信(faithfulness)居首位;“信”主要指“信于义”(represent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坚决杜绝据己意释义(paraphrase)。第二,从不否认地道(idiomatic)、雅致(elegant; grace of composition)之价值,尽量做到准确性(correctness)与可读性(acceptableness)相结合。换言之,“信”必须保证,“达”、“雅”尽量兼顾。第三,宁可执“信”(直译 literal是为了“信”)而弃“雅”,决不因“雅”(metrical, versifying可视为一种“雅”)而失“信”。
不难看出,这几条主张与我国传统译论或文论多有契合。严复“信、达、雅”标准中“信”居第一,说明“信”为首要。三者兼备固然最佳,不能得兼则须取舍。理氏取“信”舍“雅”,恰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古文十弊》所云:“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或者西汉董仲舒所曰:“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
探求本义。译者翻译,面对的是文本,探求的是本意/义。“意义是翻译的根本。”翻译亦可定义为“意义的理解、阐释与再生的活动”(许钧, 2003:132-133)。然而,由于文本具有“内在矛盾和不确定性”、“非整体性”、“期待性”、“语义隐含”等本质特征,译者的阐释行为必然受到限制,或曰文本有“拒绝僭释的权力”。(刘宓庆, 2001: 81-88)因此欲获文本意义,须回到文本初始之源——作者,因为“在本文中,是作者在言说,而不是语言在代替作者言说”(刘全福, 2005),“文本作者是诠释文本极重要的参考系”(刘宓庆, 2001: 88),所谓“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翻译大家傅雷对“译文先知人”深有体会,强调译者只有深人原作者的时代背景,体验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才能超越文化障碍、心理障碍、时空障碍,和原作者实现心灵上的契合;只有将原作“化为我有”,才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在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体验中产生共鸣,“忘记了自我,化为故事中的角色,陪着他们作身心的探险”。(肖红、许钧, 2002)理氏译中国经典,花在“知人”方面的功夫可谓多矣。以《中国经典》卷一为例,“绪论”中涉及作者的内容就有:汉代学者与《论语》文本之形成、《论语》为何时何人所书及其旨趣、《大学》作者考、《中庸》作者行迹考、孔子生平考、孔子及其直接弟子、孔子影响及其主张等②。
揭示本真。《中国经典》中,“绪论”占译本篇幅三分之一强,“注释”又为“译文”的十数甚至数十倍,而前两个部分中,有相当多的内容属于考辨。以《尚书》“绪论”为例,总共6章却有5章为“考”:《尚书》历史考、《尚书》内容可信度考、《尚书》中主要年代始末考、《竹书纪年》翻译(为辨《尚书》真伪而译)和中华古帝国考。如此之多的“考”,目的显然是为了“求真”和“传真”。
“语义诠释任务的圆满解决取决于译者对客体文化内涵的多维观照,旨在质疑而求证,求证以定义”。文化历史观照便是求证的一个重要方面。翻译中国古代典籍,离不开参考历代注疏著作,然而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必须进行析义和析理,才能避免臆断与传讹。所以,“译者不是消极的‘传话人’,而是积极参与决嫌疑、明讹夺的‘真理裁判员’”(刘宓庆,1999: 133);译者甚至应作“把关人”——发现源文本中有谬误、错漏或不妥之处,在目标文本中须予以删除或“纠正”。(谭载喜, 2011)凡细读过理译经典的人都发现,理氏对评论性文本尤感兴趣。在其参考的300多位学者及其作品中,“通常会为了某个儒教经文的翻译和注释又回到那一堆的评论中去。在绪论中,他引用的内容更注重历史性的作品,而不是在《中国经典》的主要文本和英译本中找注释。”(张西平、费乐仁, 2011: 21-22)这么做,是因为他“从来不把自己仅限于学术传统的局外者,而是非常真诚地试图作为一位中国学者融入到学习古典中国儒家传统中去。”(张西平、费乐仁, 2011: 9)
(二)传以真:诚待作者、读者和译事,以实现文化传真
理氏之“信于本”,换个角度看即是“译以诚”。“信”、“真”、“诚”,据周领顺(2006)考证,当属同义词:“信”即“修辞立诚”之“诚”、孔子“情欲信,辞欲巧”之“信”、老子“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之“真”。
诚待作者。作者通过作品将真挚的思想感情示人,以示“赤子之心”(袁枚语)。译者在翻译作者的作品时,透过作品表现作者真情。与其说译者之“信”是信于原文,不如说是信于作者。
诚待读者。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力为其扫除阅读障碍,二是尽量让其领略“原汁原味”。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欲达预期交际目的,须有共同的背景知识/语用前提,为了语言的“经济”,交流时可略去双方不言自明的东西,叫做“情境缺省”。有些可在语篇内找到答案,称为“语境缺省”;有些无法在语篇内找到答案,称为“文化缺省”。遇到后者有可能出现意义真空(vacuum of sense),即无法将语篇内信息与语篇外知识、经验相联系,从而难以建立理解话语所必须的语义连贯和情境连贯。由于原作者意向读者一般不包括外族语者,因此本族语交际双方觉得不言而喻的地方,在他文化读者读来则可能不知所云。这就要求译者不但有双语能力(bilingual competence),而且有双文化能力(bicultural competence),以免将自己的意义真空转嫁给译文读者。(王东风, 1997)理氏深知“文化缺省”对理解的影响,故利用长篇绪论和详细注释为读者补上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为“保存原作的丰姿”以及满足读者对“洋化”的期待,理氏尽量采用“异化”手法。
诚待译事。体现在理氏自始至终的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上。他精推细敲,数易其稿,一经数译。无论书名篇名、专名术语,或是一词一句,一律认真对待,在准确把握意义的基础上,找寻最佳表达法。纵观1841-1897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理氏不仅翻译了大量作品,而且重译和再版了部分重要典籍,比如《尚书》至少经过两次修订,《诗经》分别有非韵文版和韵文版(前者再版时亦经修订)。
正是凭着这份真诚,理氏为自己赢得了“不朽”的声誉。吉拉多特评价说:“众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儒经译本,包括一些名家名译在内,均不能摆脱遭时间淘汰之命运,如麦氏(W. Medhurst)之《书经》、詹氏(W. Jennings)之《诗经》、孙氏(J. Charmers)之《道德经》、翟氏(H. Giles)之《庄子》,以及法国汉学大师儒莲(S. Julien)、毕欧(E. Biot)之译作;唯理氏《中国经典》和《东方圣书》,一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稳居‘标准译本’地位。”(Girardot, 2002: 355)
三、理氏儒经翻译的策略和效果
翻译观的确立不仅对拟译文本与翻译策略有重大影响,对译者具体的翻译方法和处理原则也有着直接影响。(许钧, 2004)理氏翻译儒经的目的是促进文化交流,因此他要在翻译中着重处理好两个问题:尽量展现中国文化的真实面貌,尽力帮助译文读者扫除理解障碍。这一理念反映到翻译策略上便是:一,导读;二,传真。
(一)翻译策略:绪论、注释文外导读,显化、异化文内传真
《中国经典》绪论因其浓厚的学术性常被称为“学术绪论”。费乐仁教授(2011: 5-7)评论理译《诗经》“绪论”道:“为了达到学术型与完整性,理雅各不但介绍《诗经》的历史渊源及其复杂性,还增加一系列特别附录与补充翻译,让读者了解更多知识”;“理雅各的绪论总能引起读者持续感兴趣的是他固定穿插相关资料的其他汉英双语译本,我们可以从中了解理雅各的翻译艺术及他为在英译本中带来更多儒家经典文献知识所做的额外努力。”在为华东师大版《中国经典》(此为中国大陆推出的首套完整的理译《中国经典》)卷一撰写的绪论中,他和张西平先生(2011: 8)总结了理氏绪论的十大特点,称之为“大量智慧的结晶”,认为理氏“通过这些方式,在更加准确和全面的要求上,追求远超过他之前的那些传教士以及现代欧洲汉学家出版的作品”。“学术绪论”之外,理氏“详注”亦让读者大受裨益。该策略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语言文化环境中,用多于译文十数乃至数十倍的详释解决了因文化隔阂导致的传播阻断,这种“厚译(thick translation)”方式,不但为儒经西译体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更丰富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诠释模式。
如果说“绪论”和“注释”是在译文之外所做的努力,“显化(explicitness/explicitation)”③和“异化”则属于文内策略了。“显化”着眼于译本的接受者,“异化”关注原著的文化特色;前者旨在消解双语隔阂,在准确传达原意的基础上,努力使译文更合乎译语规范,使原文隐晦/隐含的意义变得明晰易懂;后者旨在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的原汁原味。二者互相制约、互为补充。这种文化的二度编码,使理氏译本成为“另一个经典”。异化翻译尊重异域文化,紧跟原文形式,努力复现原作的行文特色。这一译法受到很多译者(包括汉学家)的青睐。然而“异化”过度,易使译文失之畅达。王辉(2004)比较理氏与庞德的《论语》译本,发现二者均喜用“异化”法,但“理译尚能兼顾英语文法的正确性,而庞译则常常以汉语文法改造英文,暴力倾向明显。”说明理氏“度”把握得较好。
(二)翻译效果:译内、译外均获认可,轰动之后再铸不朽
这里“译内”、“译外”④分别指“译界学者”和“非译界学者”。
“译内”评价举例:“理氏所译理解原作基本正确,译笔严谨细腻,简洁雅致,大量的注释反映出他对我国经典翻译的严肃认真态度,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林煌天,1997: 399)“理雅各的译文内容或有值得推敲之处,但他旨在摆脱或力图摆脱中国典籍翻译初期的表层翻译幼稚病是毋庸置疑的。这种以解释指称为主旨的翻译,基本上保持了原文的‘机理’(组织层次)。”“理氏的译文不仅工于涤除翻译中的浅表之见……而且对原语做了恰如其分的意向性释义……重视超指称意义。”“这样的翻译可以称为‘深层翻译’或者‘深层涵养翻译’,重在发掘‘言下之意’和‘言外之意’,总之是‘超指称’成了译者的关注中心。”“对于深层意向把握,理氏非常慎重,不轻易以音译了事。”(刘宓庆, 2001: 339-340)
“译外”评价举例:《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理雅各的翻译是汉学史上一个里程碑。”(Legge,1905: 38)“理雅各译注《书经》,乃是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和融合了许多前人的严谨成果之后所做出的一想重要学术成就,确为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注释开辟了不少新的途径。”“从现代学术眼光看,尽管理氏的英译之中存在着一些误解和误译,然而他所译《书经》《竹书纪年》迄今仍是惟一的英文全译本,一直是西方汉学家从事研究的不可缺少的参考著作。并且他所提出的若干深思卓见,作为思想史之宝贵资料,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刘家和, 2005: 104-105,141)“在1897年理雅各去世之前,几乎所有居住在中国以外和学习过中文作品的人都知道至少一本或多本理雅各的权威性翻译版本。在1893-1895年第二版出版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经典》的一再重版展现了理雅各作品既对读者有吸引力,也是世界各方面对他在古代中国学术认知的一个充分见证。”(张西平、费乐仁,2011: 18-19)
理氏于1873年成为“儒莲奖”首位获得者,标志着其翻译成就获得了欧洲最高学术殿堂的认可(张西平、费乐仁, 2011: 9-10);而《中国经典》时隔一个多世纪仍被公认为中国古代经典“标准译本”在世界各地一版再版的事实更证明:理译儒经,轰动之后再铸了不朽。
四、理氏译经成就对我国典籍英译的启示
(一)翻译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信本”“传真”观念或未过时
所谓“经典”,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著作,且其意义和价值具有永久性。“经”即恒常、经常,“典”即模范、典范,经典即“恒久的模范”。中国古代经典凝聚了华夏文明精华,充满了先贤哲理智慧,理所当然属纽马克所谓“权威/哲学作品”,因此宜采用语义翻译法(semantic translation),即“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Newmark, 2001:39)。理译儒经,基本属于语义翻译。理译的成功,证明“信本”“传真”观念用于文化经典翻译是恰当的,也是值得坚持和推广的。
(二)译经须先解经
“误译多源自误解。”(Nida, 2001: 1)翻译古籍,理解尤难。因为古籍“成书时间早,文词古奥晦涩”,所述史实既“简赅不详”又“真伪参半”,“加上后人注疏汗牛充栋,观点千变万化”,令人莫衷一是;“非学贯中西、大才大识者几乎无从下手”。襄助理氏翻译《书经》、《诗经》和《春秋》、《左传》的王韬(1828-1897),自述“少承庭训,自九岁以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一生学业悉基于此”,经学造诣远非一般儒生能及,却仍在为理氏准备资料期间每日“凌晨辨色以兴,入夜尽漏而息”,写就研究性笔记“《皇清经解校勘记》24卷、《国朝经籍志》8卷、《毛诗集释》30卷、《春秋左氏传集释》60卷、《春秋朔闰日至考》3卷、《春秋日食辨正》1卷、《春秋朔至表》1卷、《礼记集释》和《周易注释》等”。(张海林, 1998: 4, 102)而理氏亦是“每天早晨3点起床,工作到7点或8点才吃早餐,然后是一整天的传教服侍工作。在凌晨靠着烛光学习,视力逐渐下降……”。(费乐仁, 2011: 2-3)为此,王韬(2002: 181)在《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中颂其:“先生独不惮其难,注全力于十三经,贯穿考核,讨流溯源,别具见解,不随凡俗。其言经也,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务极其通,大抵取材于孔、郑而折中于程、朱,于汉、宋之学两无偏袒。”作为一位外籍学者,理氏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普遍尊敬,而其许多关于中国经典的精辟见解,正是基于他大量阅读各种评论和仔细揣摩文本内容的结果。(张西平、费乐仁, 2011: 9)事实上,除研读原作和王韬笔记外,理氏还广泛参考了传教士、汉学家们已刊行的儒经译本及其他中国文化研究文献。费乐仁曾惊叹:理氏译文中能挑出的问题的数目少得令人惊讶!(岳峰,2004: 171)
相比于理氏或他优秀汉学家,国内(大陆)学者在近二十年“典籍英(复)译热”背景下推出的一些译本则大为逊色。有的仅“根据某一白话文转译,于经文的义理、训诂、考据略无涉及”,更有的“英译文错误百出、文理不通”。自己都未曾消化,又如何为读者指点迷津?“这样的译作自然难以在国际汉学研究和汉文化的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王辉, 2003a,b)。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三)了解读者需求,选择适当策略
理氏译本中的“绪论”、“注释”尽管因篇幅较长遭受过不少批评,但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学者从中受益。刘家和(2005: 104-105)指出,理氏为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注释开辟了不少新的途径。王辉(2003c)认为,理氏“语义翻译”加“详尽注释”的模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经义的传达,较好地反映出经文的语言特色”,“堪称经籍翻译的典范”。国内推出的一些经典译本往往只有译文,没有绪论、注释等,对译者不尽“导读”、“释惑”之责,倒是以“照顾读者”为名,一味简化或归化,使原文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文化个性消失殆尽。难怪郭尚兴教授(2008)大声疾呼:英译中国文化典籍须以“保持文化个性,力求形神兼备,减少文化亏损,平衡语用效果”为原则。
五、结语
通过回顾理译《中国经典》的动机、目的、策略和效果,我们看到“信于本,传以真”是理氏自始至终贯彻的翻译思想。在这一翻译观指导下确立的“绪论、详注文外导读,显化、异化文内传真”的翻译策略,较好地帮助他实现了预期目标,因此译本推出大获成功,广受欢迎,经久不衰。然而,理氏儒经译本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奉为“标准译本”是欣慰,也是忧虑。欣慰的是,理雅各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跨界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忧虑的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在经典(特别是儒经)翻译方面仍无多少超越之举。理氏译本并非十全十美,随着学术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理氏译本中还会有更多偏颇之处显现出来。这一现实不断提醒我们:金无足赤,译无定译,经典永远呼唤新译本。但要牢记的是:经典翻译,重在质量;经典复译,重在超越。动笔之前我们或许应认真地自问一声:翻(复)译经典,我准备好了吗?
注释:
①指宋君荣(A. Gaubil)《书经》(1770)法译本和麦都思(W.H. Medhurst)《书经》(1846)英译本.
②详见理雅各《中国经典》卷一, 华东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2011:12-127.
③又称“外显化、明晰化、明示”等。出自柯飞《翻译中隐和显》,见《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4):303-307.
④二术语借自周领顺《“译内效果”和“译外效果”:译文与译者行为的双向评价—— 译者行为研究(其六)》,详见《外语教学》, 2011(2):86-91.
[1]Girardot, N. The Victorian’s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355.
[2]Legge 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M], 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32, 38, 95.
[3]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9.
[4]Nida 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
[5]Ride L. Biographical Note.In: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I.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8: 10.
[6]陈先芝. 从言语行为理论看理雅各《道德经》的英译及影响[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 15-17.
[7]段怀清.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缘起及体例考略[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3):106-108.
[8]费乐仁. 引言. 理雅各《中国经典》(卷四)[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2-3, 5-7.
[9]郭尚兴. 论中国典籍英译与全球文化和谐共处[C]//中国翻译协会.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08: 105-108.
[10]林煌天. 中国翻译词典[Z].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103, 399.
[11]刘家和. 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04-105, 141.
[12]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81-88, 339-340.
[13]刘宓庆. 文化翻译论纲[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88-133.
[14]刘全福. 意义的回归: 阅读中的本文神秘主义批判[J]. 文艺理论研究, 2005 (4): 40-43.
[15]刘重德. 校注《汉英四书》杂记[C]// 刘重德,英汉语比较研究.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87-93.
[16]谭载喜. 译者比喻与译者身份[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 46-50.
[17]王东风. 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J]. 外国语,1997(6): 38-40.
[18]王辉. 从《论语》三个译本看古籍英译的出版工作——兼与刘重德教授商榷[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3(3):77-82.
[19]王辉. 理雅各、庞德《论语》比较[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 (5): 15-19.
[20]王辉. 理雅各英译儒经的特色与得失[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4): 45-48.
[21]王辉. 盛名之下, 其实难副——《大中华文库·论语》编辑出版中的若干问题[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29-31.
[22]王韬. 园文录外编[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181.
[23]魏望东. 跨世纪《论语》三译本的多视角研究: 从理雅各、庞德到斯林哲兰德——兼译典籍复译的必要性[J]. 中国翻译, 2005 (5): 27-31.
[24]肖红,许钧. 试论傅雷的翻译观[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 (3): 22-25.
[25]许钧. 翻译动机、翻译观念与翻译活动[J]. 外语研究,2004 (1): 101-105.
[26]许钧. 翻译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132-133.
[27]岳峰. 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M].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171.
[28]张海林. 王韬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102.
[29]张西平、费乐仁. 绪论. 理雅各《中国经典》(卷一)[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8-10, 15,18-19,21-22.
[30]周领顺. 新史料求证严复的翻译思想——从发展的角度看“信达雅”的包容性和解释力[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 (3):6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