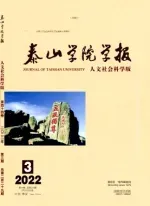“刺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潘松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241)
一、刺激的理论负载
蒯因反驳传统认识论中的意义观念论与意义指称论,主张抛弃作为实体的意义概念,转而谈论语词或句子是有意思(significant)的、意义相同的或具有同义性(synonymy)。他结合行为主义和语义上行提出句子的刺激意义(stimulus meaning)来讨论意义相同或同义性。行为主义语言观和意义观在其著作中随处可见:“以某种程度的清晰性和严格性来解释‘有意义的’和‘同义的’这些形容词的问题——最好根据行为来解释”[1](P12)。“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的技能,为了获得这种技能,我们不能不完全依赖于从主体间可资利用的关于我们要说什么和什么时候说的线索(cue)。①因此,除非意义说的是人们公开应对公共社会中可观察的刺激所具有的种种倾向,否则就没有任何道理为语言表达配置意义”[2](P1)。此行为主义有两个特征:公共可观察;对刺激进行反应。蒯因自己就说:“对我来说,行为主义仅仅是一种主体间的经验主义。”[3]但是观察并不一定就是公共的,例如,从私有的感觉来谈论观察。通过语义上行,我们谈论关于观察的语词与句子。它们是公共的,从而排除了私人性。“探索清晰而实际的意义概念应该首先检验句子。一种语言中一个句子的意义是这个句子与它的另一种语言译句共同分享的东西。”[4](P495)蒯因在原始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的思想实验中就检验了场合句(occasion sentence)、观察句(observation sentence),观察句所共享的刺激意义。这些句子“作为初始联系的东西,是一些与我们的刺激直接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句子”[4](P472)。蒯因对语义的追溯最终越过观察句延伸到并停止在了刺激。
刺激也是自然化认识论(Epistemology Naturalized)的基本概念。蒯因最后一本重要著作就命名为《从刺激到科学》。他认为认识论最基础的问题就是要知道我们如何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如何从贫乏的刺激输入得到汹涌的理论输出,即“我们,物理世界的物理的子嗣,从我们与整个世界的贫乏的接触出发,从光线和粒子对我们的感官的单纯冲击以及像努力爬山这一类的零星事件出发,如何能够构想出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科学理论呢?”[5](P566)。通过语义上行,蒯因将我们习得科学理论的知识转变为习得科学理论的句子。在习得理论句的过程中,“观察句发挥着特殊作用。它们是连接我们的感官激发和我们理论之间的纽带。因此蒯因想将它们定义为一方面:[从独词句地解释上(holophrastically construed)]它是我们的句子中与刺激最紧密相连的句子,另一方面[从分析地解释上(analytically construed)]它是与我们关于世界理论的其余部分逻辑上相联”[6]。理论句需要其他句子作为证据来进行支撑,观察句却不需要。观察句独立具有意义,“它已经是主体间一致同意的、主体间可观察的。所以,对于观察句来说,问题不在于证实,而主要在于观察句如何获得它们的意义”[7]。不同于在原始翻译中诉诸共享的刺激意义来作为观察句的意义,并保证其公共性;在自然化认识论中,蒯因诉诸“知觉类似标准的先定的和谐(preestablished harmony of perceptual similarity standards)”以及自由利用科学本身的成果来保证观察句的公共性特征,并从这两者进而追溯到我们贫乏的总体刺激(global stimulus)。蒯因的认识论追溯最终也通过观察句延伸到了刺激。
原始翻译和自然化认识论都通过观察句联系到刺激。观察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蒯因的其他概念怎样变化,不变的是其预设的观察句的公共性特征,其他概念的变化只是为了改变通达此公共性的不同方式而已。原始翻译与自然化认识论在观察句之后从各自的途径得到了刺激。在下文中,我将表明这两条进路所阐述的刺激都不能完成蒯因预设的理论目的。
二、原始翻译中的刺激
蒯因认为,原始翻译首要关注的是观察句。他设想一语言学家来到一从未被发现过的原始部落,观察到土族在看到兔子出现时,叫出”Gavagai”。语言学家研究了促使土著说出“Gavagai”时的刺激,尝试将其翻译为“兔子”,并在下次同样的刺激出现时说出“Gavagai?”观察土著是否认可。通过搜集归纳,当“土著居民对‘Gavagai?’作肯定回答的刺激条件恰恰是我们被问道‘兔子?’时会作肯定回答的刺激条件”[2](P31),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兔子”来翻译“Gavagai”。此思想实验中一目了然的“Gavagai”和“兔子”就是公共的观察句。但什么是刺激和相同的刺激条件却并不是很清晰。蒯因在《语词与对象》中按顺序逐步谈到了刺激,刺激意义,场合句,观察句,并且在定义后面的概念时要用到前面的概念,表面上是从前往后逐渐论证的。但我认为他实际的推演顺序却完全相反,出发点是在观察句。蒯因对后面三个概念都有很好的定义,而对刺激只有侧面的描述。
Dagfinn(2011)发现了《语词与对象》(1960)中刺激的不一致。“蒯因先是提示了关于刺激的神经学概念,他说‘其视网膜受到红色光线刺激而产生的光化学作用’”[3](P6)。这是将刺激看做了受激发的神经末梢(triggered nerve endings)。“然而,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蒯因将视觉刺激定义成了眼睛的有色光射模式(light patterns)”[3](P31)。前者是私有的,惟一的;后者是公开的,可以复制的。Dagfinn在蒯因出版此书时正好是他学生,经其询问,蒯因当时的刺激是指受激发的神经末梢。但是私有的刺激不能为公共的观察句所共享,这违反了前面提到的行为主义语言观,损害了观察句的公开性。“受激发的神经末梢不是公开的可获得的(publicly available)证据,而这对行为主义是至关重要的。”[3]如此一来,刺激就切断了与刺激意义、观察句之间的联系。因此,从刺激到观察句的正面论证的途径就发生了困难。蒯因在后来的《三种不确定性》(1990)中修改了原始翻译中的刺激意义、观察句的定义,但是观察句的公开性仍未改变。他在原始翻译中将刺激限定在我们的感觉输入上是受到他的自然化认识论立场的影响。尽管在出版《语词与对象》时未有明确的论述,但九年后他就正式发表了《自然化的认识论》。
观察句在《三种不确定性》中被重新定义,不再由主体间共享的神经末梢的激发来达到。“在我最初的定义中,我曾诉诸说话者之间刺激意义的同一性”,“既然语言学家和土著不共享任何接受器(receptors),他们怎么能被说成共享刺激呢?”“至1981年,它促使我重新调整我的观察句定义”[8]。蒯因转而从单个说话者(a single speaker)来定义观察句,“如果在一场合,询问该语句得到来自给定说话者的赞成,那么在任何其他场合,当那同样的一整套接受器被激发时,也将同样得到赞成;而对于不赞成也是类似的。”“于是,当一个语句对于每个成员都是观察性的时候,我就认为对于整个共同体它是观察性的。”这样的观察句在原始翻译中就表现为“观察句‘兔子’对于语言学家有其刺激意义,而观察句‘Gavagai’对于土著也有其刺激意义。语言学家注意到土著人对‘Gavagai’表示赞成,而此时他如果处在他们土著人的位置,也会对“兔子”表示赞成”[8]。其中,单个给定的说话者不需要与别人共享接受器的激发,但此激发对他自己而言却可以是相似的,不存在共享的困难。观察句的新定义虽然避开了私有的刺激不能在主体间共享的困难,却同时也失去了观察句的旧定义中由共享的刺激意义带来的公共性特征。为此,蒯因引入了移情(empathy)来保证新定义对整个共同体的公共性:“对语言学家而言,是他自己的移情作用使得他从土著人的发音和取向作出关于‘Gavagai’的第一次推测,又使得他在有把握的后继场合询问‘Gavagai’来征得土著人的赞成。”[8]
如果说在旧定义中蒯因还试图从刺激、刺激意义的相同来论证观察句的公共性,那么在新定义中几乎放弃了这种企图。“关于主体间刺激的相似性,我已得出的观点更确切地说就是:没有它,我们也完全可行。”[8]蒯因的论证立场在此转变,他不再要求阐明观察句的公共性来源于何处,而是对其既有存在进行说明与描述。这种转变也印证了我对他推演顺序的判断。只要观察句在我们的原始翻译中能够达到交流顺畅、融贯、能预测反应,那么它就可以为语言学家和土著共享,就是公共的。从多个说话者之间的刺激共享,转到单个说话者自身的刺激同一,表面上看是一种从主体间到私人的倒退,但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既然从神经末梢的触发来讨论观察句的公共性不可行,那么我们可将公共性从刺激相同上剥离开来,从其他角度来讨论观察句的公共性。剥离的结果就是蒯因的刺激在原始翻译中成了毫无理论价值的死概念,不仅不能为原始翻译中的其他概念——观察句的公共性——提供解释,反而成了需要被解释的概念。但是蒯因并不打算就此放弃刺激。他试图在自然化认识论中将刺激拉回来。至于观察句的公共性是如何得到的——也不是由移情得到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本文末尾将予以提示。
三、自然化认识论中的刺激
由前文可知,观察句的新定义切断了刺激与观察句公共性之间的联系,使得刺激面临被抛弃的危险。戴维森建议修改刺激的定义,将其从身体表面(bodily surface)向外移到两个主体之间相干行为最近似的原因之中(in the nearest shared cause of the pertinent behavior of the two subjects)以适应新的观察句。②在强调观察句公共性的特点时,蒯因也会说:“流动在露天中的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我们每个人都自由地以他独特的神经方式将其内在化。语言是产生主体间性的场所。交流(communication),这个命名很贴切。”[8]他把交流比喻为被修剪过的灌木丛,在外形上相似,而内部的枝节却不一样。换言之,蒯因承认我们的交流能够顺畅融贯地进行,即使每个人内部的刺激可能差异巨大。但在论及戴维森的建议时,他却不同意:“在将刺激确定在神经输入上我仍然是坚定不移的,因为无论如何自然化,我的兴趣都是认识论上的。我对从感官的激发到科学见解中证据的流变感兴趣。”[8]
从原始翻译过渡到认识论,蒯因继续讨论刺激。他认为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中对世界的理性重构是传统认识论发展的顶点。它不是对确定性的追求,而是对我们关于心灵和自然的科学概念的系统整合。这对蒯因非常具有启发,自然化认识论的目标也是要放弃传统认识论对先于经验科学的制高点(vantage point)的追求,并且系统整合从刺激输入到理论句输出。但在蒯因看来,卡尔纳普采用基本经验(elementary experience)作为重构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对基本经验的定义已经是一种科学设定的理论对象,它们是学习理论句的结果,而不是出发点。与卡尔纳普的现象主义不同,蒯因选择了物理主义的进路,从基本经验的物理对应物:“总体刺激”(global stimulus)出发,一步一步地,通过观察句构建出科学的理论句子。
蒯因对总体刺激的刻画带有很浓的准科学(quasi-science)理论的气息。总体刺激就是“在那个时刻被触发的所有感觉接受器(the class of all sensory receptors)的类……是属于某个时刻的总体感觉经验的一种的合适的物理关联物。”[5](P566)总体刺激在大脑中得到处理,“把一个未经处理的输入与另一个输入区别开来的,仅仅是何种接受器被触发,以何种次序被触发”[5](P566)。“于是,总体刺激——接受器的有序集——就是我提出作为卡尔纳普的基本经验的物理关联物的东西。”[5](P566)。不同的总体刺激之间有两种关系:接受器类似性(receptual similarity)与知觉类似性(perceptual similarity)。“每一个总体刺激都是主体的神经末端的有序子集,两个这样的子集以或多或少的次序包含着或多或少同样的神经末端”[5](P566),这是接受器类似性。总体刺激和接受器类似性都是以接受器为对象,是对它们的激发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描述。这体现出了物理主义的要求。但是从总体刺激和接受器类似性还远远得不出具有公共性的观察句的定义。为此,蒯因引入了个体的知觉类似性和不同个体知觉类似性之间的先定和谐。“在个体范围内,观察句对应于某个范围的知觉上相当类似的总体刺激……由于先定的和谐,它们有资格成为整个共同体内的观察句”[5](P570)。延续原始翻译中从单个说话者出发来定义观察句的办法,他采用知觉相似来定义对单个说话者的观察句,然后用先定和谐来说明观察句在群体中的公共性。但是这两者却不具有明显的物理主义的和准科学的特点。
蒯因没有像定义总体刺激一样,给出知觉类似性标准明确的准科学的定义;相反,只是给出了一个现象描述,而不是机制刻画。③P.Hylton认为知觉类似性最重要的特征是行为主义的,它避免了论及到关于经验与意识的观念:“大致说来,两个刺激模式可以被看做类似的(对于某一时刻的一个动物而言),只要它们能够导致相同的反应。”[9]我认为Hylton的理解不准确。如前所述,行为主义的典型特征是主体间性和公共性,是“一种主体间的经验主义”;知觉相似性却是对个体的总体刺激之间关系的描述,而非公共性。
直观地看,接受器类似性的确是总体刺激(接受器的有序集)之间的关系;而知觉类似则不是对接受器之间物理关系的直接描述,而是一个现象描述,与总体刺激之间的物理关系有差异。这是因为知觉类似作为一座桥梁,要将共同体内的观察句通过个体的知觉类似与总体刺激相联系。从知觉类似得到的只是失去了公共性特征的个体的观察句。公共性是观察句的根本特征,因此必须将共同体内观察句的公共性传递给个体的观察句。所以,知觉类似就不能像接受器类似性一样,仅仅只是总体刺激之间的物理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必须具有超越总体刺激之间的关系,而与共同体内的观察句的公共性相联系。
在原始翻译中刺激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在自然化认识论中知觉相似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共同体内观察句的公共性来自先定和谐的知觉类似性,此知觉类似是现象描述的知觉类似,而不是作为总体刺激的物理关系的知觉类似。因此,观察句的公共性只能传递到作为现象描述的个体的知觉类似性;而不能传递到作为总体刺激之间的物理关系。换言之,不能传递到总体刺激。由于知觉相似自身存在的跨越,蒯因试图在自然化认识论中得出从总体刺激到观察句的公共性之间的必然联系也是不成功的。
四、结论
我们已经看到,在原始翻译中对观察句公共性的解释不需要预设刺激。作为原始翻译更进一步的发展,自然化认识论中对总体刺激与观察句之间的联系仍然不成功。
移情违反了行为主义的公开性、主体间性原则,并不是一个比刺激相似更具优势的概念。总体刺激也并不比卡尔纳普的基本经验更具有优势,因为它比后者更接近于科学设定的理论对象,是一个需要在理论框架内习得的理论句。卡尔纳普的理性重构不是传统认识论发展的顶点,它只是传统认识论中基础主义的一支。“除了卡尔纳普的还原主义外,基础主义还有许多变种,而且除了基础主义之外,传统认识论还有许多其他学说。”[10]蒯因对总体刺激的追求仍然是一种基础主义的还原论。还原论传统认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是有赖于我们自己主观经验的知识……而这种对外部世界的辩护预设了私人语言的可理解性。”[10]这一进路是“对我们关于感觉、知觉、观察,以及它们的多种同族概念的误用”[10]。
观察句的公共性并不需要在自然化认识论中,自由地利用已有的科学成果,通过联系到总体刺激、知觉相似和先定和谐来解释。观察句的公共性存在于我们在公开的言语行为中的语词约定和用法的实践中。例如,颜色词汇的设定并不是为了与自然事实相对应,而是为了颜色词能够言说颜色以及一般言说服务。[11](P90)观察句的公共性就体现在为我们的一般言说服务上,而与刺激这类自然事实没有太多关系。
[注 释]
①此处由陈启伟组织的翻译为“主体间通用的信号”,容易引起误解。参考陈嘉映的《语言哲学》,将其翻译为“可资利用的线索”。
②戴维森认为蒯因的刺激有近端(proximal view)与远端(distal view)的区别,蒯因倾向于从前一种,而他建议从后一种来讨论刺激。
③对知觉相似的描述,参见蒯因的《从刺激到科学》第567页。
[1]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蒯因.语词与对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Follesdal,D.(2011).“Development in Quine's Behaviorism.”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48(3).
[4]蒯因.蒯因著作集(第6卷)·真之追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蒯因.蒯因著作集(第6卷)·从刺激到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F.Tersman,(1998).“Stimulus Meaning Debunked”.Erkenntnis 49.
[7]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Quine,“Three Indeterminacy”.in R.B.Rarrett,et al.(1990).Perspective on Quine.Cambridge,Mass.,USA,B.Blackwell.
[9]P.Hylton: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 quine/.
[10]P.M.S.Hacker(2006).Passing by the Naturalistic Turn:On Quine's Cul-de-Sac.Philosophy 81(2): 231-253.
[11]陈嘉映.说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