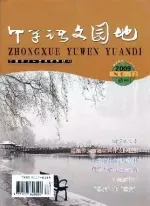背景:标签或者补丁
周晓冬
“时代背景”或说“写作背景”,向来在语文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分析文学作品,“背景介绍”更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翻翻各种版本的教材,每篇课文不论现代文古文还是诗歌,正文前的 “阅读提示”或“预习提示”,都毫无例外的有一块背景介绍;在“教参”或“教师用书”里,必定有相当的篇幅是用于提供更为详尽的背景资料的,在“教学建议”一栏,往往不忘“建议”老师:“为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准确把握作品主旨,宜先将该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思想状况向学生作简要介绍。”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会时时告诫学生:“只有了解了时代背景及作者的情况,才能真正理解作品”。“背景”是理解阐释一切作品的前提和基础,并决定着作品的意义,这地位、权力似乎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它真的有这么大能耐么?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一直被恭恭敬敬奉在卷首的“背景”,有时的确是一把打开意义大门的钥匙,而有时则不过是一张大而无当随处可贴的标签,有时甚至是成了一块破坏作品整体美感,消解读者审美愉悦的补丁。
以文中标明的写作日期为线索,去查找到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及政治气候,再依照作者的生平行状和政治倾向,来推求作者当时的写作意图,进而索解作品的意义,在中学课堂里讲解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用的就是这种最为常见的鉴赏文学作品的方法和流程。教材里通常有这样一段提示:“《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或“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白色恐怖的气氛笼罩全国”)。作者在文章里描述了一幅清幽美妙的图画:曲曲折折的荷塘,密密田田的荷叶,星星点点的荷花,淡淡的月色,脉脉的荷香……这一切又交融着作者那隐隐的,却又是深沉的孤独与苦闷的心绪。这正是那个黑暗时代在作者心灵上的折射。”这还不算完,编者生怕广大中学生不能清楚而准确的感受到这种时代特征的“折射”,便进一步点明:“阅读时,要重点抓住‘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令我到底惦记着江南了’等语句的深刻含义。这样,就不难理解文章的主旨了”。本来一篇结构并不复杂篇幅也不长的写景抒情散文,理解起来的确不难的,但经这么一“提示”倒真的让人为“难”了,仿佛处处隐藏着以“春秋笔法”写就的微言大义,比如“颇不宁静”是某政治事件的折射,“江南”实指发生了反革命政变的“上海”,如此索隐下去,连天上那轮“今夜不能朗照”的月亮,也大为可疑,恐另有所指。当然,这一番喋喋不休的耳提面命也并非全无意义,起码能将这篇带几分古典意境的婉约小品升格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朱自清先生也由一位月夜漫步荷塘“受用无边的荷香月色”的颇富雅趣的文人,变身为时刻在观测政治形势的时事评论员。贴上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标签,也许有助于凸显朱自清先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但同时也带来不少尴尬,例如,若说文中的“苦闷哀愁”是当时黑暗与恐怖的“折射”,那么,通篇如荷香似月色的“淡淡的喜悦”又是什么社会情状的折射呢?如此严峻的时局下他的“喜”从何来?再者,文后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927年7月”,也就是说,朱自清先生面对这起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时隔三个月,才在一篇赏月品荷的散文抒发一缕融合在“淡淡的喜悦”里的“淡淡的哀愁”?如此这般的“介绍”、“提示”究竟是要突出“有骨气”、“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粉”的朱教授的正直义愤还是冷漠麻木?
另外,近有爱抬杠较真者,说查阅朱先生的日记,发现那天先生与太太吵了架赌了气,因而“心里颇不宁静”,于是走出家门到荷塘边散步散心!若确有此记录的话,就更表明“时代背景”这块标签实在大而无当,且贴得不是地方。再者,即使那天夫妇俩相安无事一如往常的和睦,恐也不能断定朱先生夜游荷塘的动机就是有感于那起政治事件。试想,仅以中国而论,地域之广、人口之众、事发之频,一年一月一日之内发生的可致人心绪不宁的事不知凡几!而况,作为文学家的朱自清本就是敏感善感之人,能引发他情绪波动的人、事、物,更不知凡几!一个宽泛无边的“时代背景”,又怎能框得住对得准?
我们不能说一切背景对于作品意义的理解都是毫无作用的,但是,若把它当成万能钥匙,逢锁即开,且是理解作品的唯一可靠的途径,就像浦起龙认准的那样:“缵年不的则徵事错,事错则义不可解,义不可解则作者之志与其词俱隐而诗坏。”(《读杜心解》),则不可避免的陷入一连串的困境。
首先,作品的写作背景并不都能考证清楚。能像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这样在文后清楚标明年月日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当然,因是现代作品即使无准确日期,要确定一个大致不差的写作时间段也不难,况且作者还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是,那些年代久远的作品呢?且不说史料“代远多伪”,也不说我们看到的所谓“历史”不过是历史学家的一种历史叙述,而“历史叙述早诗歌及文学作品本来是要给人们以艺术美感享受的,而这种精确到有些残酷的背景批评却常常破坏这种乐趣,好像用Ⅹ光透视机把美人看成肺腑骨骼,用化学分析把一朵花分解为碳、氢、氧。堪称集古典文学研究之大成的“鉴赏辞典”系列,就为我们提供了每一篇作品的当算是最详尽准确的背景资料,可是这又能带来什么呢?是锦上添花还是佛头着粪?唐代宋之问诗《渡汉江》“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无须解释,人们即能感受到久离家乡的归乡者的惴惴不安,这惴惴不安里有对家乡故人生死存亡的惦念,有对故乡是否拥抱游子的忧虑,还有若惊若喜的回乡之情,这是一种人人心中都有的普遍情感,读到它就勾起人对故乡的一分眷念。可是,《鉴赏辞典》本着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给这份动人的乡愁贴上一块经严密考据的“背景”:“这是宋之问从泷州(今广东罗定县)贬所逃归,途经汉江(指襄阳附近的一段汉水)时写的一首诗……宋之问这次被贬泷州,是因为他媚附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可以说罪有应得。”那份美好的情感就顿时烟消云散,在这个铁案如山的背景下,“近乡情更怯”成了被通缉的逃犯潜逃时的心理报告,“不敢问来人”则成了逃犯昼伏夜行鬼鬼祟祟的自我坦白,一首诗就这样被“背景”勾销了它作为“诗”的资格。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写得很美,是教材里的固定篇目,在课堂上由稚嫩的童声读来,尤自晶莹透彻,而一贴上背景就反而变得浑浊暧昧,“据《唐才子传》和《河岳英灵集》载,王昌龄曾因不拘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开元二十七年被贬岭南即是第一次,从岭南归来后,他被任为江宁丞,几年后再次被贬谪到更远的龙标,可见当时他正处于众口交毁的恶劣环境之中。”所以要辛渐到洛阳为他表白心迹,这当然很可能,但是,这首诗的意义被背景框架限定后,“一片冰心在玉壶”不仅成了不太谦虚的自我标榜还可能成了强词夺理的自我辩白,这首诗便不成为“诗”却成了押韵的“申述状”或“上告书”,未免大刹风景倒人胃口。
历来的文学批评那么执著于对背景的重视和依赖,是因为文学作品总是面目模糊,不贴上背景的标签便无法辨认,还是因为文学作品不过是件百孔千疮的破衣裳,非打上背景的补丁不成体统?显然,我们应当承认文学作品本身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本,它是由文学的特殊语言构成的传情达意的艺术品,而不是由背景限定的或离开了背景就不可理解的历史文本。文学上相当多的作品并不需要依赖背景的支撑为靠山就可以拥有完足的意义。特别是那些历久弥新、传颂不绝的抒情类作品,且严格地说,凡艺术都是抒情的,它并不传达某一历史事件、某一时代风尚而只是传递一种人类共有的“永久不变”的人性和情感,像自由、像生存、像自然、像爱情亲情等,它的语言文本只须涉及种种情感与故事便可为人心领神会。一旦背景羼入,它的共通情感被个人情感所替代,反而破坏了意义理解的可能。正像尼采说的,有时人们不得不学会忘却,因为有时过多的记忆损害了人的自身创造力,而在文学里,过多的背景记忆正妨碍了作品欣赏的自由使阅读者在历史专制下不得不被背景耳提面命,也把文学降格为历史学的附庸而忽略了文学的个性存在,只有历史赋予的意义,而没有语言技巧与审美经验赋予的意义。
既然文学创作包容了 “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那么,作为诠释手段之一的“背景”就不必指望独揽意义的解释权。毫无疑问,背景批评应当允许存在并作为探寻意义的一条途径,尤其是作品主题与历史背景相关密切的时候。但是,意义毕竟是作品本身的语言文本提供的,我们不应让背景替代人们的阅读与理解,当代学者扬之水说得好,“我们与其观世,不如观思;与其感受历史,何如感受生命”(《君子于役》篇),更不应让背景越俎代庖地取代审美主体的感悟,。在今天强调主体意识、倡导自主探索的课堂上,在一群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的学生面前,文学作品是一个开放的国度,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这里没有上锁,甚至连大门也没有,把历史背景当作标签当作补丁,当作阅读与理解的唯一钥匙,都会阻塞其他通向“意义”的途径,破坏学生有活力的感悟,使他们领会不到文学作品的整体魅力和多彩的丰富性。语文教师与其不厌其详地介绍 “时代背景”、“写作背景”,倒不如告诉学生那句虽然令人尴尬但也令人轻松更能激发学生创造力的古老箴言:“诗无达诂”,即使作者的日记摊在我们眼前,或者作者直接已将历史事实剪裁过了,所以它并非事实。”(怀特《叙述的热门话题》),就是不伪,确是事实,正统的纪传、编年、本末体史书又有多少篇幅来记载文学家?耗费了数辈学者心血修撰的那些古代文学家的生平、年谱、编年诗集,有相当多还是依靠作品的提示,标题的线索,语词的象征来推断的,可那些提示、线索、象征又有几分可靠?再拿这些猜测来作背景去评判作品,这种“循环论证”还能真切地阐释作品意义?就算能,那些文学史上为数不少的无确切年代的,无明确抒写对象的,连作者也无的“三无”作品,是否就永不可解,或毫无意义呢?比如《诗经》,比如《古诗十九首》。
其次,所谓的“作者之志”如何得知?我们如此看重“背景”,努力搜寻查找作者作品的相关资料,无非是想透过作者所生活的时代风貌,看出作者的模样,因为“一个艺术家总是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是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了解了作者的生平事迹与思想状况,进而揣摩出该作品的创作意图(即“作者之志”),作品之义便自然凸现。可是,“背景”与“意义”都有这么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么?虽说一定的社会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但“从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因为,实际上文学家与文学作品总是多彩多姿的,“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但是它反映这些情况和表示这个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样。”(钱钟书《宋诗选注序》),就像同是盛唐的王维、李白、杜甫,承受同一背景而各自风格迥异。既然文学作品是“特殊语言构成的一个传情达意的艺术品”,那么,它在写作时就包容了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当然受到历史环境、个人经历的种种影响,政治形势、学术思潮、地理民俗、民族心态、经济环境,即整个文化都会在作者心里留下痕迹,但是,这一切都必须经由一连串的“移位”才能渗入创作,并受到作者个人的禀赋、气质、性格这一磁场的扭曲,受到具体创作时极微妙的心境变形,往往迂回曲折,才在文本中留下极其含糊的“印迹”,要想从一块砖里看出万里长城的雄伟气势来,或只是眺望大海便能分辨出一滴海水的各种成分,不亦难乎?
再说,无论怎样齐备、怎样精确的背景资料,也不过是批评家阐释者视野里重构的历史,是按照他们各自的理解与分析对一系列事件材料的排列组合与解释,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本身,属于历史的那些事件早已逝去,属于历史的文学家也早已死亡,时间带走了他们复杂的精神与微妙的心灵,尽管通过种种努力,靠近了作者,依然无法重现历史的血色和心灵的生命,更何况艺术家、文学家、诗人正属于最复杂多变的那一类心灵,文艺作品正是拥有最微妙难测的那一类情感的“精神产品”,把“背景”之因与“意义”之果硬叠合在一起难免犯刻舟求剑的错误。
生活的真实不对于艺术的真实,“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钱钟书《宋诗选注序》),常言也说,生活是米,小说散文是米煮成的饭,而诗歌则是米酿造的酒。两者固然有联系,但差异更是显而易见。把诗人复杂的写作心理简化为背景到意义的机械过程,把诗歌广泛的表现领域缩小为政治或时事的专门栏目,这对诗人与诗歌是“充分的理解与尊重”还是画地为牢对他们的贬抑?当这些背景、“史料”直接参与对诗人或诗歌的诠释时,它那种大而无当常常就会泯灭诗人或诗歌的个性特征。例如,南宋词人辛弃疾被不由分说地牢牢钉上了“主战、抗金、力图恢复”这块背景之后,就把他所有的休息时间都一概取消,不让他有半刻的喘息偷懒,他的每一句话都被挤榨出“金戈铁马”的背景来。《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这首清新明丽的农村词,因为事先知晓“辛弃疾是一位忠义之士,处在南宋偏安杭州,北方金兵虏去了徽、钦二帝,还在节节进逼的情势之下,他想图恢复,而朝中大半是些昏聩无能,苟且偷安者,叫他一筹莫展,心里十分痛恨。就是这种心情成了他的许多词的基本情调。”就理所当然的认定“这首词实际上也还是愁苦之音”。词中所有句子便笼罩在这块大背景下了:上阕描绘的生机盎然的早春美景不妨当作是反衬“愁苦”的,“斜日寒林点暮鸦”句则已正面透露了一点消息,“到了‘桃李愁风雨’句便把大好锦绣河山竟然如此残缺不全的感慨完全表现出来了”。可末句“春在溪头荠菜花”无论如何也读不出“愁苦”来呀,也不碍事,罩得住。用个转折词“但是”就圆过去了:“沉痛不等于失望,‘春’句可以见出辛弃疾对南宋偏安局面还寄托很大的希望。”而“这希望是由作者在乡村中看到的劳动人民从事农桑的景象所引起的”(朱光潜《谈白居易和辛弃疾的词四首》)。读着这样的“知人论世”的评论,真让人捏一把汗,幸好没说辛弃疾充分意识到发动广大农民的重要性,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设想,不然,辛弃疾就该跟毛泽东发生知识产权纠纷了。
如果诗人(艺术家、文学家)写诗真的是都为时事而作倒也罢了,可是中国到底有多少“史诗”或“诗史”呢?很多诗人写作只是“兴会偶发”,不少诗人写作又是“因题凑韵”,当诗人见月伤心闻铃断肠写抒情诗,当诗人倚马立就即席咏哦写应酬诗时,他与他周围的那些“背景”有什么关系?况且,我们还不得不时时提防那类“为文造情”“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伪作”。
再次,我们暂且不论背景与作品关系的亲疏远近,承认专家们挖掘史料的努力没有白费,的确为作品找到了最为精确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动机,可这又如何呢?作者可以站出来宣讲他的创作体会,我们也同样保持着作为读者作为审美主体应有的自由和权力: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