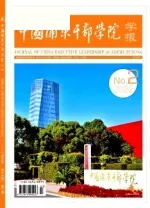从忠诚到利益:革命后社会的公务员激励机制
王向民
从某种角度说,公务员的行动效率取决于激励机制的选择与执行,而公务员激励机制的选择取决于公务员所有的公权力的性质与功能。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具有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双重职能,相应地,公权力也分作政治统治权力与社会管理权力。公务员所掌握的公权力应当是社会管理权力而不是政治统治权力,因为公务员队伍并不是暴力机构,在性质上,它不同于军队、警察与监狱等强制与制裁性机构。
不同性质的权力需要不同的激励机制。政治统治权力的激励机制在于意识形态,并以态度与忠诚为其标志,而社会管理权力的激励机制在于理性的物质利益分配。意识形态激励机制通常表述的是对某种理想与道德价值(生存意义与终极价值)的追求,它排斥或忽略行动者个体的物质利益诉求,强调价值信仰对个体行动的引导与规范作用,政治立场与政治忠诚是个体行动的行动逻辑与考核标准。换言之,政治统治权力的激励机制更多是通过意识形态控制而对组织内个体实现规制的。而物质利益分配形成的利益激励则表明个体行动者承认个人的世俗生活诉求,遵从制度价值与规范而不是组织的强制,期望服务性行动与利益薪酬的理性交换,亦即以完成制度规定的既定任务换取固定的利益薪酬。
一般而言,个体行动者的激励机制受制于政治社会进程及其结构。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主题是革命与建设,后者又分为1978年前后建设道路的不同探索。为了抵制外国列强的侵略并统一国内政治权力,中国的国家建设必须将低组织化社会转化为高组织化的状态,克服社会领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对付传统专制权力是权力重构的一体两面。因而,革命中国的关键词是“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在干部队伍建设上体现为建立高度集权化、政治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同时悬置公民的政治自主权,限制个人的财产权利与利益诉求。
应当说,通过意识形态整合与激励干部队伍的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了解释和论证阶级动员、政治集权、赶超战略、经济社会权利平等而形成了一套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有其完整的对象与层次,在结构上,它覆盖了意识形态的三个层面,即信仰层面(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全面自由的终极价值)、世界观与方法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具体策略(如何生产、如何营销、如何管理、如何评估)。在形态上,它以“学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面目,既满足形式逻辑的要求,又符合来自基本事实经验的判断;既能够解释现实的变化与变迁,又和其他知识体系保持灵活良好的互动。这套精致而非粗陋的意识形态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两种特征,具有解释的雄辩性和论证的自洽性两种品格。在功能上,革命动员的需要,使它假设了干部的非趋利性以及意识形态的强规制性,态度忠诚与排除私念是信仰性干部的行动逻辑。因此,建国前后的意识形态激励机制是政治性的,公务员的公权力作为政治统治权的分支,其国家干部的个体地位及其行动也是政治性的。应当承认,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激励取得了干部行动的极大效率。
但是,新中国的某些革命政治运动却又破坏了既有的意识形态。为重建社会秩序清理地基,而改造旧时代的思想文化遗产(思想教育批判运动);为确立全能政治体制,而铲除旧时代的思想文化精英(反右运动);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开辟道路,而批判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时,“实践的意识形态”已千疮百孔,意识形态的生产、营销、管理和评估系统都发生了重大问题,严重影响到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突出表现为 “信仰危机”——生存意义和终极价值受到质疑,从而导致“纯粹的意识形态”陷入困境。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工作中心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政治调控战略由一元统治向多中心治理的转变,个体自主、分权、自由、竞争和社会分层这些内部治理问题,使原有意识形态的内部充满紧张。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也做了尽可能的调整,尤其在策略方面(包括如何生产(制造概念、提出思想、引领话题)、如何营销(论证、解释和灌输)、如何管理(调控舆论、意见、民意)以及如何评估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灵活的应对,信仰层面(生存意义和终极价值的关怀和主张)也在与时俱进的口号下也缓慢进行了调整(如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道德建设的决议),然而在世界观与方法论则相对稳定。这导致信仰层面、认识层面与策略层面的彼此脱节,集中表现为解释力的贫乏与论证的非自洽性。
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在困境导致原有的干部激励机制发生困难。例如政府官员放言“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使党政关系以及人民主权的宪法宪政充满内在紧张;再如腐败多发于掌握政治权力与行政资源的国家干部,官民冲突大多是由于利益分配的腐败所引起,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这些观念难以说服民众;最后,干部实践中的“对上级负责”而不实事求是或罔顾百姓,使干部制度或公务员制度的制度规范形同虚设。因此,需要重塑公务员队伍的激励机制。
革命后社会意味着革命理想的褪色,完美计划的破碎,世俗利益的诱惑,在市场经济的利益蛊惑下进而形成个体化与利益化的政治社会结构。个体消解了组织,利益消解了忠诚,干部队伍中公务员的行动越来越被利益逻辑所吸引。因此,需要建构一套不同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公务员激励机制,亦即需要建构一套以制度与利益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它以制度规范的信仰替代价值忠诚的信仰,以职业道德的绩效评估替代政治忠诚的态度评估。
整体来说,以制度与利益为核心的公务员激励建设包括公务员的人性假设、利益结构、制度信仰以及行动皈依等内容。
首先,承认公务员的逐利性个体假设。“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构成的”,这样的“特殊质料论”不应当成为公务员激励建设的假设前提。权力的滥用与寻租是人的本性使然,我们可以用伦理道德对其加以规范,但是并不能由此否认制度规制的矫正功能。尤其是在革命日远的世俗化时代,克里斯玛的魅力人物更难形成,因此,我们只能用制度设置限制个体的逐利性行动。
其次,界分公务员的应得利益与寻租利益。作为一份社会职业,公务员的劳动应当获得相应的利益报酬,既不能使其陷入“大公无私”的赤贫状态,也不能使其成为特权阶层。当前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务员的高回报率。同时,作为公权力,应当防范公务员滥用权力或者权力寻租,从而导致官民紧张的腐败根源。当前公务员制度建设中并未堵塞公务员的寻租机会,制度漏洞与个体寻租交相呼应。例如派出所民警故意把新生儿名字写错,为的就是要让新生儿父母要派出所改正名字时送礼行贿。
再次,建立公务员的制度信仰。制度信仰意指两者,其一,公务员的行动守规,不得滥用权力或权力寻租,把公务员行动归纳到制度规定上来;其二,以制度信仰替代组织信仰与政治信仰。公务员的权力的社会管理权力,以公平效率为标准,有其独立于政治统治的制度价值,故而,首先需要建立制度的公正基础,制度的功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服务形态;其次,制度信仰必须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过程控制加以实现;再次,制度必须有其利益薪酬作为公权力行动的利益交换。
最后,建立公务员的法治信仰。法律是革命后社会的秩序准绳,没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社会组织与行动个体,只有在法律面前才能保证人人平等。因此,作为法律法规的执行者,公务员的行动必须建立在守法逻辑上,只有坚持程序政治、透明政治与法治政治,才能真正实现责任政府、服务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