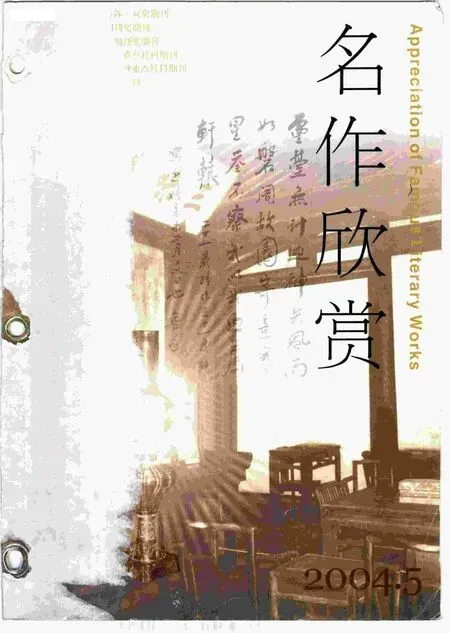李佩甫小说创作与道家文化
⊙李中华[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 郑州 451191]
一、道家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根底
李佩甫是河南作家群中的一员大将,这位不务张扬、沉默勤奋的作家以其厚实的作品令评论界刮目相看,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对于这个作家的研究,正在日益升温。而关于李佩甫创作的道家文化底蕴,却鲜有发现。实际上,中原文化的根底,即是道家文化。作为一个深受地域文化影响,并把其创作的根据地放在豫中平原的一位作家,李佩甫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浓厚的道家色彩,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的。
中国道家,黄帝是其最早的始祖。黄帝所居之地,就是今天的河南新郑。列御寇也是新郑人。作为黄帝之邑人,列御寇在其著作《列子》中对黄帝经过苦苦探求,最后终于悟到了道家哲理的过程,描写得极为生动细致(参见《列子·黄帝第二》)。列子自己,也是道家哲学的一位代表人物。道家的另外两位代表——老子和庄子,也是河南人。老子是陈国人,老子活着的时候,陈虽被楚攻伐,但仍然存在,并没有最后灭亡。司马迁之所以说老子是楚国人,是因为陈最终亡于楚。庄子是宋人,其故里位于现在的河南商丘。如果把老子、庄子和列子的故里用直线连成图形的话,就成为一个锐角三角形,而且三点相距不远,都在河南,属于典型的中原文化地区。①
黄帝的思想经过老子、庄子和列子的阐释,成为一种弱者的哲学。它之所以在中原地区首先产生,是与中原的地理、社会、文化的因素密切相关的。老子出身于陈国贵族,在老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晋国、齐国、秦国等大国利用其实力,疯狂地向外扩张,特别是楚国,在灭亡了申、息、吕、弦、江、黄、道、柏等小国之后,把矛头对准陈、蔡、郑、宋诸国。陈国曾两次被楚所灭,最后在公元479年终于被纳入了楚国的版图。庄子为宋国贵族,而宋又是商族的封国。商被西周灭亡,其遗民被封为宋国。宋国在宋襄公时曾一度强盛,而最终在兼并战争中成为牺牲者。所以老子庄子的哲学在河南地区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是失败主义情绪和弱者智慧在哲学上的反映。老子看到“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强”,“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因此,要求人们“无欲”“守雌”。如果说,老子哲学中还包含着一些刚健的成分(兵家、法家亦出于黄老),那么庄子思想中,悲观消极的失败主义情绪就处处笼罩,成为主导情绪。
有学者认为老子可能是在对水性潜心研究把玩的过程中悟到了深刻的道理,发之为文,即成为《道德经》一书。其实,老子哲学的产生,与水无关,而与中原地区的老百姓的心理、性情倒有极大的联系。直到现在,河南的民风民性还保持有极浓的道家风貌。李佩甫的创作,执著地把关注范围限定在豫中平原一带,他在作品中就自然表现出老庄风味,成为河南作家群中最具老庄色彩的一位。可能有人会怀疑,一个现代作家是否会研究完老庄哲学之后,再以自己的研究心得在农村中找人物、找情节,来完成他的小说创作?这个怀疑是稍具创作经验的人都可以轻易否定的。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必是失败之作。李佩甫的创作的确具有很强的理念色彩,然而这些理念和作品结合得天衣无缝,完美无缺,正如水中盐味。李佩甫对河南民风民情的解读,其实正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出许多老庄的哲学理念。这一点,的确令人惊叹:何以时间流逝了二千多年,而中原民风民情变化竟如此之少呢?
二、李佩甫笔下的下层百姓和基层统治者体现着道家哲理
《金屋》以豫中平原的一个小村——扁担杨为描写对象。村中有两个强者,一是杨书印,二是杨如意。杨书印是村里的村长,“他不仅是一村之长,三十八年来也始终是扁担杨的第一人。他先后熬去了六任支书,却依旧岿然不动,这就是极好的说明”。这样的一个强者,却败在新崛起的年轻人——“带肚儿”杨如意手里。杨如意的暴富,形成了对村长杨书印的巨大威胁,二人以扁担杨村为舞台,展开了斗争,最后,村长杨书印被斗败了,而杨如意也并没有胜利。杨如意最终的感悟是:“扁担杨村最厉害的人不是杨书印,是这块土地,还有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他们才是最最厉害的,再强硬的人在他们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这群常常受人欺负,吃苦受罪的人比城里人有更可怕的地方……”默默无闻的大地,受苦受难的村人是柔弱的,然而,柔胜刚,弱胜强,最后胜利的还是他们。杨守印象征着政治权力,杨如意象征着财富金钱,二者都曾在扁担杨这块土地上炫耀一时,然而最终还要在卑贱忍辱的土地和老百姓面前表示臣服。中原百姓正和这些平原的草类一样,“在败处求生,在小处求活”,显示出阴柔的道家风貌。然而立于不败之地的正是他们,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他们。
下层百姓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柔弱而强大的性质,这还只是道家思想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底层乡村中的统治者,也即熟谙乡村治术的基层官僚,其统治手段也非常合乎道家哲学的基本原理。司马迁的《史记》有《老庄申韩列传》,把老、庄这些道家人物和申、韩这些法家人物并列在一起,认为法家思想的本源还在于黄老。老、庄、申、韩这四位人物,都是河南人。老子、庄子我们前面已提及。申不害是郑国京人(今河南荥阳人),曾任韩昭侯相国,执政十五年,是法家学派的开创者。其继承者韩非也是河南人(河南新郑),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另一个有名的法家人物商鞅是卫国人,又称卫鞅。卫国在今天的河南濮阳一带。可见,道家哲学在人生世态上的表现,不单单是那些出家做道士的人,那些消极避世的人,也在那些志于事功,精于人治的统治者身上。古代河南出现了为数极多的政治家,他们的统治手段在20世纪并没有寿终正寝,而是以其他种种名义继续通行无阻,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羊的门》中,呼家堡的主人呼天成,就是深谙以至弱胜至强这一传统治术的乡村政治家。呼天成对中原地区“人是活小的”这一做人原则深有研究体会。呼天成固守着呼家堡这一方小天地,生活极其简单,他最爱吃的,只是一种手工的擀面,加上一些霜打的红薯叶。这都是“人是活小的”这一理念支配的结果。
呼天成深知欲先取之,必先与之的道家哲理。这个哲理表现在呼天成的为人处世上,就是对“人场”的经营。呼家堡的暴富,看起来在一夜之间,其实却是呼天成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呼天成几十年如一日,对可能有用的人才不惜血本,进行感情投资。河南大饥荒的时代,到呼家堡驻村的下派干部老秋已经浮肿,呼天成认为老秋是个人才,找遍全村弄到五个鸡蛋送给老秋,救了老秋的命。呼天成经营的“人场”中,除了老秋这样的老干部之外,还有很多的年轻干部。在这个名单中,有许田市常务副市长孙全林,省委组织部干部调配处处长邱建伟,省报副总编辑冯云山,省银行行长范炳臣,颖平县县委书记呼国庆,市工商局副局长刘海程,市税务局局长彭大鹏……呼天成靠他多年培养的“人才”,在一个人治社会里如鱼得水。一个小小的呼家堡能够把其影响力延伸到全县、全省、乃至全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呼天成把自己的人情“债权”放到了最可能广阔的地方。到必需的时候,他就要去收获利息。他对呼家堡人的压迫、奴役和愚化,也和他对外部“人场”的经营互为条件,互相促进。这样,他在呼家堡树立了最高最严厉的权威。
呼天成处心积虑建立的关系网,发放的“人情债”,他使用起来是极为节俭的。有一次,呼天成坐车去省城的路上出了撞车事故,村秘书徐根宝打了八个电话,三个县的交警开着警车赶来,“于是,整个300国道全被封锁了!那个场面极为壮观……”可是,根宝受到了呼天成的严厉批评,被勒令站在院里一天进行反省。根宝终于悟出,“人是活小的”这一原则对呼天成来说是至高无上、绝对不可违背的。
对《羊的门》中的呼天成,有两种评论:一种是把他看成村中的专制独裁者,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李佩甫“国民性批判”的指向;另一种是把他看成一个“主”的形象。“尽管他扼杀了村民的精神自由,但的确是他,用肩膀撑起了呼家堡这一方净土,主体在批判呼天成负面因素的同时,亦默认、强化了某种统治(神性)的序列。”②这两种意见中,第二种意见更合理更全面也更有说服力。呼天成为什么能用肩膀撑起呼家堡这一方净土呢?压抑欲望从而使自己具有道德优越性和神圣性,使自己在呼家堡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成为实际上的“土皇帝”,这是他“事业”成功的基础。尽管呼天成可以有好多次机会到大城市去做官,他却固守着呼家堡这一片弹丸之地;尽管他可以调动很多关系为个人、为集体(呼家堡)带来方便,他却轻易不动用这些宝贵的资源,除非是不得已。尤为符合道家理念的是,尽管呼家堡最美的女人秀丫和她的女儿自愿献身,呼天成却对着献身者美丽的胴体开始练功,直到自己的性欲望完全消失。作为性欲消失的补偿,秀丫的丈夫对呼天成权威的挑战也彻底失败。这里,无疑表现了一种“无欲则刚”的理念。
三、老、庄式批判精神和对自由人性的渴望、追求
贯穿于老子、庄子思想的一个主导方面,是对主流价值观的批判和对自由人性的向往。李佩甫创作的总主题,和老子、庄子一致。
一些研究者认为《羊的门》中的呼天成是一个“卡里马斯型”的典型人物③。这是有道理的。呼天成是一个“成功”的乡村统治者,其成功的根本,在于顺应时代潮流,永远和时代保持同步。“大跃进”时期,呼天成就靠着工作积极从副支书提拔为支书,成为呼家堡的“主人”。在饥荒肆虐的1960年,呼天成用残酷的手段,把孙布袋当成“贼”的典型任意羞辱,扼制了村人偷盗集体庄稼的潮流。改革开放以后,他费尽千辛万苦大力发展村办企业,让呼家堡村民过上了小康生活。呼家堡集体资产过亿,可是作为创业者的呼天成却住在一个小茅屋里,屋内的摆设是“破旧的洗脸盆架”,“一张旧办公桌,还有几张简单的床铺,一些木椅之类”,更令人惊异的是,呼天成睡的竟然是一张“已有四十年历史”的“绳床”,“它是那样的破旧,床帮仅是几块粗糙的,黑污污的木头,木头上泛着一股腥叽叽的气味,那气味是人的油汗和蚊虫的尸体喂出来的”。对于这样一个体现主流价值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人物,李佩甫并没有放过他。作家用老子、庄子一样的犀利目光,穿透笼罩在呼天成身上华美的神性光圈,把其虚伪的本质残酷地暴露出来。大饥荒时期,呼天成之所以能镇住人心,使人们宁愿挨饿也放弃偷窃来的红薯、玉米,成为呼天成驯服的羔羊,完全是呼天成玩弄权术、残酷镇压的结果。孙布袋心甘情愿地被树为“贼”的典型,任村人唾骂,是因为呼天成把自己救活的逃荒女子秀丫送给孙布袋当老婆,以此作为交换。呼天成的“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的权术背后,隐藏着把人当畜生的残酷心肠。正因此,孙布袋悲哀地总结:“我放了三十年羊,你放了三十年我,人也是畜生。”当年老子、庄子看清了孔孟之道的虚伪本质,喊出了“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而今李佩甫看透了主流价值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虚伪,其批判精神和古代道家是一脉相承的。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人物所热烈追求和热情讴歌的,是人的本真的自由人性,李佩甫同样也是如此。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李佩甫有着深深的乡土情结,乡土是他所有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李佩甫不过是借乡土表达着他对自由人性的渴望与向往罢了。他对乡土,除了深深的眷恋与赞美,也有无情的批判与鞭挞,正如有论者所说:“佩甫一方面俨然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审判官……另一方面又是一位深情的歌者。”④呼天成作为乡土的精灵,李佩甫对他的态度我们很难用“批判”或“厌恶”这些简单的字眼来全部概括。
研读《羊的门》,我们可以清楚地体悟到,李佩甫对呼天成,除了批判之外,还有深深的同情和悲悯。在四十年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呼天成已经完全被政治权力俘获,异化为一个政治动物。他身上的自由人性已经丧失殆尽,成为“心如枯井,形如槁木”的空壳。正常的爱情、婚姻,人生的天伦之乐,喜怒哀乐,这些人之常情,在他身上都已经消失了。对于这个政治权力的牺牲品的同情与悲悯弥漫于《羊的门》的字里行间。对自由人性的讴歌、赞美不但是《羊的门》的主题,也是李佩甫所有创作的总主题。因为在人间社会特别是都市,自由人性被物欲、权欲所遮蔽,成为稀缺物,李佩甫甚至把自由人性转移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上去,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万物有灵论者。在李佩甫的小说中,大地万物都有生命和灵魂。小草、麦浪、庄稼、草帽、房屋都有灵性。《黑蜻蜓》甚至说:“土坯是活的灵魂。”对自由人性的追求也是李佩甫创作“二元对立”结构的根本原因。都市和乡村比较,李佩甫热爱权欲、物欲相对稀薄的乡村;乡村中的权势者和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比较,李佩甫的价值天平又剧烈地倾斜于养育过李治国等城里人的三叔、梅姑、七爷,以及吃玉米面糊糊长大、丧失父母、耳聋的二姐等苦难百姓一边。李佩甫的二元对立结构是双重的,既有城乡二元,也有善恶二元。研究者们大都注意到了城乡对立,而没有注意到善恶二元对立,这是李佩甫研究的一个缺陷。
① 张松辉.老庄文化应属于中原文化[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4).
②李丹梦.卑贱的神圣之旅——李佩甫论[J].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07(2).
③ 陈昭明.永远的乡土情结[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5).
④ 陈继会.永恒的诱惑:李佩甫与乡土情结[J].文学评论,19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