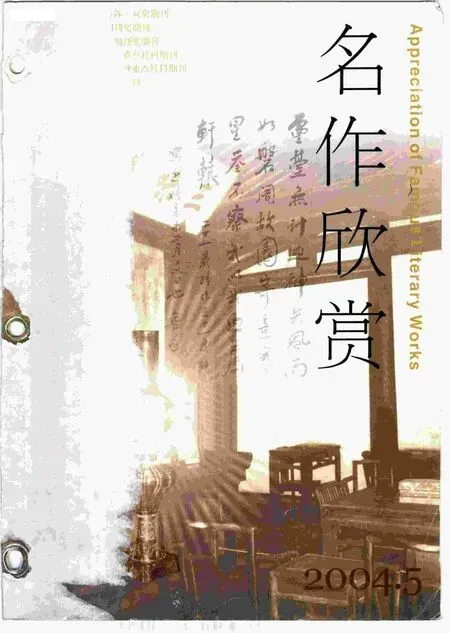浮生若梦:读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
⊙郁 梅[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上海 201306]
春夜宴桃李园序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一、生命的悲歌
一切哲学思索的焦点,都是以人类生存的方式为本元的。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更是始终表达着对人生的认识和要求。且看一代诗仙李白是如何表达对人生的思考:“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生命的短暂与自然的永恒相对照,使个体逃脱不了“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前赤壁赋》)的那种今古茫茫之感。李白也同样呼吸着这生命的无奈。生命所经历的片段式的悲欢离合似乎引人入胜,然而在永恒的时间面前,个体的朝生暮死不过是一出出悲剧。庄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庄子·刻意》)说尽其中的道理。个体在的永恒的天地面前,有实质感而无把握感:“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荣枯不定的命运使汲汲营营所追求的功名利禄如梦如幻,这种身不由己的漂浮感和流动性使生命无法超越自我而失落。李白洞悉这生命的原貌,所以有“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自问和自答。对着“逝者如斯”的人生发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的诠释,饱含着虚空与感伤。
二、生命的超越
陆机《文赋》云:“遵四时而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李白《古风》云:“逝水与流光,飘忽不相待。”中国文人凭借时间,领略生命的诗情与存在的真谛。其中所引起的时间体验,不仅仅是怀旧和伤逝,更有直面和珍视生命的感触:“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离骚》)。在“朝”“夕”时间的张力场中,去日苦多的“坠露”以及那还没有来得及开放即凋落的花蕾“落英”,表现的是生命中美在最美的那一瞬的流逝和沉暮。而“饮”和“餐”是怎样的一种无力的挽回,然而正是这无力的挽回照耀出屈原对生命的自我提举,对美好人格和生命的无限珍爱和追求。因而,屈原的体验是勉励生命的,是一种觉悟了自身的有限,却敢于直面永恒的悲壮之美。
勉励生命的意识还来源于《易》的智慧。《易》的盈亏循环转化使生命不再胶着于一时一事,所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风水轮流转”,使生命中之不能“承受之重”变得易于接受。时光和世事的流转是生命对生命的慰藉,命运对命运的宽勉。《易》是中国古代先哲在长久观察自然界中日往月来、寒暑易节、花开花落总结而成的智慧,是人生对时光流逝冷静的承受与解脱,使生命超越了自我,融入宇宙大化。
生命的悲欢在于不能超越一己之渺小,在于人所无法突破的时空限制,李白所谓之“万古愁”。庄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内篇·逍遥游》)彻底放弃了“我”的存在,从而进入一个纵浪大化、心理自由的世界。同时它也消解了勉励生命的人文品性,并掺入了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勘破知性时间,进入无时空的逍遥,李白对此给以遥远的回响:“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大鹏赋并序》)时间流逝所引起的生命痛苦与心灵焦虑到了陶渊明宁静安谧的田园世界里,才得到真正的安顿与止泊。陶渊明淳朴淡泊的睿智使庄子的深层底蕴诗化于如画的田园之中。“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归园田居》之三)这洗尽铅华的悠然和从容是对失落了的自然,失落了的生命自由最根本的寻找。陶渊明之浑朴天然,乃来自于充满自然本色情趣的真美。
李白继承了以屈原、庄学、陶诗为主体的人文精神之至高境界,将生命的长度转化为时间的密度:“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由此得以品尝、消受这“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外篇·知北游)的人生。同时,身处盛唐、遍历名山大川求仙学道的经历使诗人拥有了非凡的自然审美能力。“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式的物我合一则使诗人在自然中看到无限舒展的空间。“云从石上起,客到花间迷。淹留未尽兴,日落群峰西。”(李白《春日游罗敷潭》)所表现出的飞扬的意趣、缥缈的轻快、旺健的精力使生命的自由感得到最大的满足。凭着对大自然强烈的感受力,诗人把天地山川的美感与自我的情绪自然地相交融会,并超越个体的局限:“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尽管“召”和“假”隐隐透露着怀才不遇、渴望入世的心情,诗人已然把个体融于自然的生命之中,忘我地游乎四海之外,以其特有的浪漫飘逸实现了对永恒的把握和对现实生活中自我价值失落的超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人生态度使及时行乐成为理所当然,体现出一种浓烈的感性生命精神,同时也找到了生命存在的理由与意义。这或许是消极和放纵的,然而却体现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怀,是魏晋以来重视个体价值的传承。“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燃烧着对生命的热爱。至此,序文一扫开篇宿命的虚空,呈现出豁然开朗的潇洒飘逸之感。
诗人执著追求个性的自由体现于其作品中奇特的想象和自由豪放的文风,这样的生命情调使李白得以在仙凡间自在流转。他以胸中之豪气赋予山水以崇高的美感,是他对自然伟力的讴歌,也是对奋斗不息、飞扬的人生的礼赞。“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所体现出的豪迈自信足以超越短暂人生所引起的时间敏感。遨游于神话世界中的诗人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天姥吟留别》)的呼声,更是其独立自由人格最好的概括。忙忙碌碌,虚幻不定的人生所带来的无奈悲苦在诗中一一得以解脱。这种自由意义的象征手法造就了诗人行云流水般舒卷自如的洒脱与飘逸。这正是李白在生命中所追求的得意,是心灵自由的欢歌。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诗歌语言更是保持了清新流利,意在言外的魏晋清俊自由的文风。因此,李白时以谢灵运自比:“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
三、生命的意义
然而,李白所处的盛唐时代与谢灵运的时代大不相同。李白诗中绮丽的自然风光不自觉地带有时代的精神烙印。盛唐时代是极富英雄色彩、浪漫情怀的时代,是充满自信,对世俗价值如功业、金钱、地位充分肯定的时代。因此,李白热爱自然山水的无限丽质,却没有魏晋六朝的自然与社会对立的心态。正如李白《宣州谢 楼饯别校书叔云》中情感活动的几度跌宕起落,生命存在的意义在于直面人世流年之忧而又不被其所淹没或吞噬。一切往日的枯荣只同于梦境,个体需要挣脱这内心深沉的苦痛,才能飞向自由的空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正如杜甫诗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对李白来说,诗歌是生命得以永恒的一种赎救。在即兴抒情的创作中,生命的意义不断地得以继承和创新:“不有佳作,何伸雅怀?”阳春烟景已令人陶醉,更何况此时此刻,诸弟相聚:“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朦胧淡月云来去,桃杏依稀香暗度”(李冠【蝶恋花】)的桃李芳园中,如梦如幻的浮生与无穷无尽的天地美景相遇,人生借而获得全新的感受:“浮生速流电,倏忽变光彩。天地无凋换,容颜有迁改。对酒不肯饮,含情欲谁待?”(李白《对酒行》)“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这诗化的美酒使意兴倍增:“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李白《梁园吟》)李白的生命中,须臾与永恒是如此巧妙的结合。在李白的心灵境界中,人与自然不再孤悬隔绝,自然不再是异己的存在;而人的生命情感也不再孤独、有限,不再与自然本体相乖离而存在。李白的这种自然之美与他遍游名山大川、长期生活于大自然的美中有关。诗人沉醉于大自然,自然之美又熏陶了他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反映在李白的文艺思想上就是:真诚率真、质朴自然。
《中庸》云:“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通过皈依自然来认识、陶冶和提高自己,这个过程本身就参与了自然宇宙生命的创化。这正是中国先哲“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深思。
四、结语
李白对生命有着深沉的悲剧知觉。然而,诗人忧乐互济、悲智双修,以其特有的生命诗情追求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用物我合一、流动飘逸的哲学境界把自我融于自然,把瞬息之当下化作未来之永恒,从而超越这生命的悲歌。
[1]胡晓明.万川之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2]罗宗强.李杜论略[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
[3]萧涤非等编.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4]袁行霈主编.历代名篇鉴赏集成[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