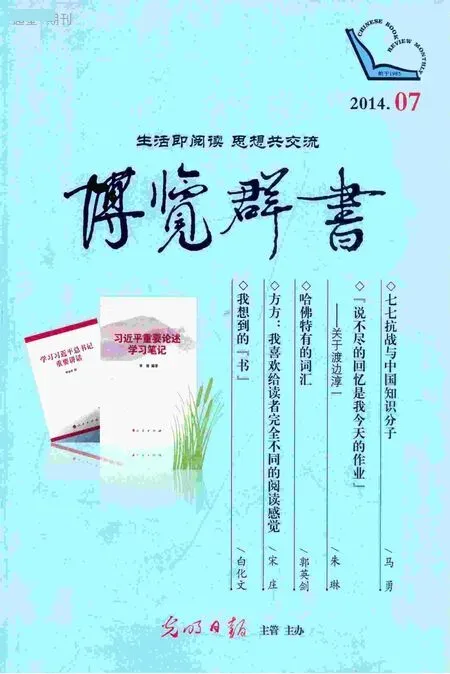“儒家宪政”之说成立吗
○伊卫风
“儒家宪政”之说成立吗
○伊卫风
秋风认为,古代政治中存在两种传统,即周制传统与秦制传统。前者以封建制为构架,强调君臣之间的契约关系,所谓“君臣以义而合”,君臣之间不是上下尊卑关系,有伙伴、朋友关系的含义;每一个君与他的臣组成一个共同体,在重大事务上共同决策,而规范彼此行为的就是“礼”,所以周代的治理秩序是礼治秩序,具有贵族共和的性质;在这样的秩序下,君臣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礼”保证了平等,也保证人们的自由。后者是大一统以来的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换言之,皇帝的权力要受到来自儒生的限制,即以道统制约政统,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宪政性质。因此,“儒家向来就具有限制绝对权力的意向和精神”,它的思想中自然就蕴含着宪政的踪迹。本文作者对秋风的观点持不同意见。
秋风先生曾连续撰文讨论“儒家宪政”,引起很大的争议。为了论证这个命题,秋风旁征博引,显示出扎实的学术修养,令我辈敬佩。在他看来,宪政“主要关心宪制(constitution),也即权力的安排”。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宪政不只处理这个问题,还有“保障权利”的问题。作为宪政的经典样本,美国宪法不仅有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更强调这种安排的目的——“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相应的宪政理论更是明确提到:基于公民同意的政治权力就是要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政治契约的基本宗旨。因为没有权利的权力安排是独裁的表现,只注重权利的后果是人人都成了立法者,故而约束权力和保障权利并举,宪政才能实现。从这个思路来看,所谓的“儒家宪政”不过是“直把杭州作汴州”的错觉。
秋风认为儒家宪政两种形态,一种是封建制,另一种是共治体制。在封建制下,“君臣以义而合”,说明君与臣是一种契约式的结合。他引用孔孟的话作为论据,“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语),“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语)。孔孟的话能否证明封建制的儒家宪政存在呢?
一
先说封建制的问题。瞿同祖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中指出,大一统之后的中国很难称之为“封建社会”(我们现在仍把秦汉以来的中国称为“封建社会”,其贡献要归功于郭沫若,并深受毛泽东的推崇,然顾准早就指出此中的牵强附会),而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夏商周为主,西周最为典型,在宗法、阶级和政治三个方面表现极为明显。“分封而建”是授予封臣采邑,但这种封建关系的形成不是契约,而是靠血缘,即血缘宗法制。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不过是家族的扩大而已,从而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也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政治身份,所谓“血而优则仕”,贵族恒为贵族,平民恒为平民,两个阶级是泾渭分明的。一旦有人破坏这种界限将是严重的僭越,所以孔子才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同的阶级地位当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政治前途。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与庶人在政治上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在经济上是“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由此看来,中国的封建主义是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当礼崩乐坏之后,“道术为天下裂”,王官之学失守,稷下私学兴起,先秦的封建社会随着秦始皇的统一创造性地转化为新型帝国,原有的制度也就随之而解体。原来的“分封而建”为新的“郡县制”取代;“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采邑制也由官员的俸禄制来承担;官僚的血缘世袭制也被后世的科举取士制所替代。何怀宏认为这是一种“选举社会”,因为官员的产生不是世袭而是选举,成了区别于先秦封建制有的根本所在。
事实上封建制的概念并非中国的概念,而是源于西欧中世纪,瞿同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导言中就明确指出。通常所说的封建制度主要是指西欧中世纪的一种非常典型的社会形态。法国年鉴学派的布洛赫《封建社会》一书专门讨论了“什么是封建制”。他指出西欧封建制所强调的“封疆建土”涉及的也是土地问题。一般来说,领主授予封臣采邑,封臣又把采邑再次分封给自己的附庸,但领主与附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所以才有“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而封臣接受领主的采邑,要合掌置于领主的双手之中,主仆双方以唇相吻,表示双方的和谐和友谊。后来因基督教对世俗生活的干预,封臣则要手按圣经或圣物,甚至跪拜以表示效忠。经过这样的仪式,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就形成:领主授予封臣采邑,封臣也要向领主履行相应的义务,主要是打仗(这里的打仗经常指的是不同领主之间的利益争夺)。当封臣履行了义务之后,若没有宣誓继续效忠的话,那么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就随之而结束,封臣也就可以寻找新的领主宣布效忠,从而形成新的封建关系;当然他也可以继续效忠旧主,同样的仪式还需履行。由此可知,领主与封臣之间关系的基础是契约而不是血缘,这可以说是欧洲封建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布洛赫也明确地指出,“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关系纽带正是在血族关系不能发挥有效作用的时候才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2004版,P700)
另外,封臣在战争中获胜的话就可以获得贵族称号,有点像商鞅时代“军功立国”,故而尚武又勇于冒险的骑士阶层迅速崛起,一度武化之风甚盛;在采邑之内,领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掌管该疆域内的法律、行政和宗教事务。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是中世纪苏格兰流行的一项社会习俗——领主对其附庸的新娘享有“初夜权”。尽管这些弊端遭人诟病,然而封建制也为后世留下了不少的思想遗产: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契约精神也成为近代政治思潮中“社会契约”的渊源之一,尤其是近代宪政中的“国家的形成就是一种政治契约”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各自为政的领主彼此之间的力量角逐更为近代以来的欧洲社会民主进程早早埋下了伏笔,这些特征都与中国的封建制完全不同。虽然我们借用了西方封建制这样一个概念,但必须清楚两者的区别之所在。不幸的是,秋风先生认为中国的封建制与西方的封建制一样,体现着一种契约精神。
二
退一步讲,姑且认为“君臣以义而合”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但这种契约关系的双方是“君与臣”。君是统治者毋庸置疑,而臣是统治者的助手,权力的执行者,归根结底还是属于统治者,所以最终的契约不过是权力占有者之间分享权力的契约。孔孟确实说了君臣之间的相互尊重,可实际上君臣在权力问题上都是一家人,相互体谅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关键是权力所指向的对象——被统治者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并不存在,与宪政的基本精神也完全不符。
宪政的形成是“公民为了保障基本权利而达成的政治契约”。换言之,公民才是契约的主体,可是在秋风封建制的儒家宪政关系中,统治者成了契约的主体,与宪政的宗旨截然相悖,这还能是一种宪政关系吗?更进一步说,在秋风的儒家宪政框架下,被统治者——普通百姓——的权利在何处得到体现?宪政要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问题,这在封建制的语境下,就是“君与民”或者“官与民”的关系,可是在秋风的论证中,“权利”完全被忽略。这么要害的问题只字不提,又怎么能说是一种宪政关系呢?

《中国封建社会》,瞿同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秋风认为“士大夫与皇权共治则是另外一种儒家宪政”,更是令人费解。他明确指出,士大夫通过教育考试而进入政府;获得资源的控制权,形成了“士人政府”;提倡“道”或“天命”的观念等,这些对皇权都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和约束,所以也体现出一种宪政的倾向。如前所述,宪政不但处理“权力的安排”,也负责“权利的保障”问题。在共治体制上,士人对权力的约束体现在秋风所说的“道”以及“天命”上,他还特别引用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学说,来证明“道”对现实统治者的制约,使得统治者不敢胡作非为。可是在现实社会中,“道”或“天命”如何能够制约皇权,具体怎样操作,儒家没有说法,秋风更是没有说法。事实上,通过观念对权力的限制往往是士人的一厢情愿,除非所有统治者都是上古圣贤,敬天明神,否则用观念来制约权力,无异于画饼充饥。现实中依靠制度制约权力的典型是美国宪政。三权分立作为一种切切实实的制度,把权力的界限确定在一个明确的范围内,同时各种权力之间相互制约以防止专制的可能。可是共治体制依靠士人的“道”来制约权力的办法,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于是士人就从相反的方向入手——寄希望于德行高尚的圣王出现,他定然不会滥用权力,也会爱民如子。虽然这样完美的人物符合士人的道德期许,可毕竟是百年不遇、千年难求的。即使有这样的人,谁能保证他永远不会腐败呢?所以士人通过“天命”或者“道”制约权力,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乌托邦设想,但并不是所有士人的理想。
对于多数士人而言,按照社会既定的逻辑行动才是正道。学而优则仕是社会主流方向,士人通过教育科举而入朝为官,他们就变成了统治集团的一分子,权力的附属者,既得利益的获得者,让他们再去批判权力本身,无异于自毁前程,故而通过官僚儒生来约束权力基本上也落空了。当然秋风或许会反驳,还有追求精神独立的儒生会“为民请命”。这一点当然不可否认,历史上究竟有几个读书人纯粹追求知识而拒绝科举?纵然有也是个案,总不能把历史中的偶然当作常态吧。因此共治体制中通过士人的“道”来制约权力在实践中无法操作,往往变成了道德评价,无法制约权力滥用的问题;就士人自身来说,更是缺乏制约权力的动力,而且官僚儒生还是权力的受益者。
权力问题尚且如此,那么权利问题又会是何种命运呢?普通百姓的权利是否会得到保护?如前所述,皇帝和官僚儒生持有权力,难以制约的情形已经毋庸置疑,而普通百姓在共治体制中有何权利,又如何被保护呢?现代社会中公民可以选举代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代议制民主或直接民主是体现民权的主要途径,那么在共治体制下的民意体现、民权表达如何体现呢?有没有一个正式的制度来保证普通百姓的权利?秋风对此语焉不详。事实上普通百姓在“共治体制”下几乎成了“历史上的失踪者”,很难见到关于百姓权利的历史记录,反而经常看到为了权利而“拦轿喊冤或赴京告御状”,这正好说明了古代缺乏保护民权的有效途径,百姓才冒着杀头的风险采取上述的举动。由此可以看出,依靠儒生所谓的“道或天命”观念,要么完全落,要么空陷入了道德批判;作为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官僚士人也没有动力去制约它;普通百姓的权利保障制度更是无从说起。试问,作为宪政基石的两个要旨——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在共治体制下都无法实现,儒家宪政还能成立吗?
三
当然宪政本身也有历史,存在古典宪政和现代宪政之分。古典宪政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好生活”,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专门讨论“幸福的城邦”问题,它不仅涉及权力和权利的问题,更包含美德教化等问题;现代宪政则主要约束权力以防止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后一个问题完全放弃了,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姑且不论。从秋风的论证来看,他所界定的宪政显然是属于后者。要论证古代中国就有现代宪政的因素,且不说这里的时空错位,只着眼于宪政本身就会发现,所谓儒家宪政的说法不过是“直把杭州作汴州”。
若“用观念制约权力”在现实中真能发挥作用的话,那么人类所有的乌托邦都可以变成现实,理想国中的哲学王或儒家的“内圣外王”早都把人类带入了美好的社会。然而现实告诉我们,那些都是乌托邦,因为现实有现实的逻辑。仅就“权力制约”而言,历史上确实存在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自从大一统之后,中国政治的架构发生了变化,原本属于服务于皇帝私人生活的人员经历了“外部化”过程,从皇帝的私人随从变成了具有公共职能的官员,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组织结构,也就有了“皇权与相权”的权力格局。皇帝统领王室,而宰相领导政府;皇权与相权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赖。皇帝要依靠宰相来治理天下,而宰相则借助皇帝表达政令的正当性。皇帝不能为所欲为,宰相也不是有恃无恐,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皇帝发布命令,须先由中书省起草,然后交由门下省审议,通过之后交给皇帝,用红笔横批,最后由尚书省按照兵、刑、礼、吏、户、工各部门的具体分工执行。皇帝如果想要走后门给某人封官,即没有经过中书门下两省,自行起草命令,然后直接交给尚书省执行。自知没有经过合法程序,所以皇帝不敢用“红笔横批”,而改用墨笔斜批,意思是让尚书省马虎执行,这样得来的官因没有经过正常的途径,所以被称为“斜封官”,在官场中是受到轻视的。从这套权力的运行规则来看,皇权与相权的相互制约有制度性保障的。不幸的是,明代废除了宰相,政府失去了领导,那么对皇权的制约也就不存在了,相应的制度基础也就没有了。要说古代社会是专制权力不受制约,那么明代则是典型。由此可以看出,制约权力的制度性安排比起儒家的观念约束更为切实可行,然而传统对百姓权利的保护方面一直处于缺失的状态,故而与现代宪政的含义相差甚远,更与儒家宪政扯不上关系。
北京大学法学院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