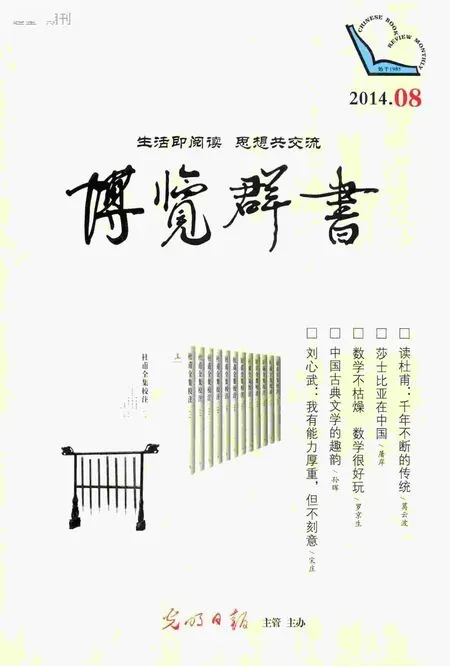《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勘误纠谬
○胡学常

《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昔杨遇夫有致陈寅恪函,盛称《元白诗笺证》之美,以为“自有诗注以来,未有美富卓绝如此书者”,复叹诗注之难,有谓:“古来大诗人,其学博,其识卓,彼以其丰富卓绝之学识发为文章,为其注者必有与彼同等之学识而后其注始可读,始可信。否则郢书燕说,以白为黑,其唐突大家已甚矣。”(《积微居小学述林》,P308,中华书局1983年版)杨氏所言者在注诗,然可推及历史人物研究之一切科目。义宁陈氏,巍巍荡荡,几无能名焉。况陈氏分明夫子自道,“吾侪所学关天意。”“天意”者,从来高远难问也。故而陈氏之学,难于屈子之“天问”。今有“劝君免谈陈寅恪”之警诫,良有以也。
然则陈氏不可不谈,世间谈陈氏者,事实上亦不可断绝。前两年,陈氏诞辰百二十周年之际,谈陈忽而转成小热潮。坊间所见,两种最受关注,一是《也同欢乐也同愁》,一是《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前者三联出品,系陈氏哲嗣之回忆,不属研究性质;后者是陈门弟子卞僧慧先生之研究著述,由中华书局推出。卞氏以老迈之身担负使命,孜孜矻矻,呕心沥血,垂二十余年,不能不令人感佩。书出,座谈会开过,专家称善,媒体叫好,据称是陈氏后人与陈门弟子“惟一认可的《年谱长编》著作”。
早在1980年代,陈门弟子蒋天枢先生即有《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氏以“粗疏缺略”,谦而不敢自命“年谱”。尔后复搜罗史料,时加增补,冀成完整翔实之年谱。惜乎年高体弱,无力遂其心愿。卞先生承蒋氏嘱托,继而有作,终成完璧。卞氏亦自谦不敢当,于“年谱长编”下复缀“初稿”二字。老辈美德,于此可见一斑。
“初稿”云云,固是谦德,然细读一过,发现未尝不可谓之实情。卞氏受蒋先生之托,已过古稀之年,书出之日,则已近百龄。新材料愈益涌现,如此老弱之身,自是难以应付。许多后期工作,显系卞先生哲嗣卞学洛帮助完成(署有“卞学洛整理”)。据云,卞学洛不习文史之学,所业者在地下水资源利用,虽勉力从事,亦力图臻于完善,毕竟力不从心。便是卞氏,专攻亦不在晚近百余年之历史,虽有亲历之得天独厚处,却也不能不于晚近文献颇生隔膜。而且出版方,贵为学术著作出版之重镇,却不思爱惜羽毛,其态度之轻忽,编校之粗疏,实属罕见。故而综观斯编,失误多多,几不遑枚举。如不惮非礼,直呼曰“半成品”可也。可叹学人不读书,媒体甚至无力读书,一时充于耳者,皆是人云亦云的叫好之声。笔者不学,尚能读书,于叫好声大惑不解,遂草此小文,专事勘误纠谬,其好处美处,皆不欲及之。
一
大凡年谱,必立例言。此编竟然无之,“半成品”气象,触目即得实感。翻检此编之“按语”“慧按”“慧又按”之外,间有“经富按”“求会按”“小如按”诸名目,一般读者见此,实不可解,便是专门家,亦平添突兀。如标立例言,略作说明,此病即可避免。
此编征引文献,多方搜罗,堪称繁富。然繁富之文献,尚需作精当之处理。其首要者,当尽力征引第一手文献。衡诸此编,二手乃至三手文献,在在多有。此不惟观出搜罗之功尚阙,亦可见于相关文献颇有隔膜。如征引“吴宓日记”,舍《吴宓日记》不用,转引《吴宓与陈寅恪》。又如谱主信函,多辗转辑录,似不及见识三联版《陈寅恪集》之《书信集》。梁漱溟与毛泽东冲突事,已是众所周知,汪东林、艾恺诸人之相关著述,亦不难觅得。此编述及此事,竟转录某刊一篇平庸之作,则史料已沦为二手之下(见原书P281,下引此书仅注页码)。一些写家(远非研究者)之书,亦不惮繁引,取而用作二手、三手料。像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不惟不惮征引,而且征引得莫名其妙。陈明远书录有中共中央办公厅1956年初印发之《关于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人数的调查报告》,转录中竟然多出一大段文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段)。此段文字,既不见诸原书,亦非“调查报告”原有。注明此段文字之出处,出版时间误作“2006年1月”(当作“2006年2月”),且不注明页码(P298)。如此怪现状,足以表明编撰者甚至不曾见识陈明远原书。尤令人费解者,在《论再生缘》公案之文献运用。此公案由余英时引发,则余氏相关文字,当是非征引不可者。然检点此编,仅见征引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一文。徐文披露之新材料自可征用,而关涉余英时者,本源自余氏文字。余氏乃研究义宁陈氏之一大重镇,文字俱在,当径引才是。否则,悉从徐文出,则史料沦为二手,且势必见笑于大方之家。
二
名曰“年谱长编”,非仅以铺排宏富之史料为能事,更当具备眼光,精于剔抉。史料之爬罗功夫,此编尚有可称道处,剔抉之识力,则或有为人所诟病者。此病一方面在疏于剪裁,芜而不精,另一方面则在畸轻畸重,谱主一生之大关节处,史料或反有阙漏。
此编多处引《竺可桢日记》,以间接传达谱主之信息。1950年8月7日竺氏日记,记“姜立夫来”,且谈及“陈寅恪在彼尚好”,此编录此,并无不可。然接下复引8月8日、8月15日两条,语间却无一字涉及谱主(P264)。又,此编转抄吴宓日记(1937年6月22日),点明谱主于熊十力、欧阳竟无两家之唯识学均有微词,尔后复引文献达四条之多,皆仅及熊十力、欧阳竟无之学,而与谱主了无干系(P111-112)。枝蔓过甚,不知剪裁之病,于此可以概见。至于详略失当之病,仅举典型一例。谱主自清华园出走,卜居岭南,此事无疑是其一生之重大关节。其间殊费心思,亦多故事,近年新料愈出,真相渐明,大可囊括殆尽,一一罗列。《陈君葆日记》及《陈君葆书信集》系新出文献,编撰者未及见原书,却也伪装引作亲见之一手材料。虽如是,毕竟避免一件重大史料之遗漏,可堪肯定。陈君葆材料之外,尚有多种可资利用。冯友兰晚年撰《怀念陈寅恪先生》(1988年版),以陈氏之“突走”媲美王国维之“自沉”,称誉二氏乃“当代文化上之夷齐”。其解析陈氏之“突走”曰:“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三松堂全集》第1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余英时用心探究陈氏之“晚年心境”及陈诗之“暗码系统”,断定陈氏曾萌生“避地海外的念头”(《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P97,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且透露陈氏夫妇因去留而生争执(同上,P6)。吴宓日记1961年9月3日有记,陈夫人力主避地欧美或台湾,约于1950年1月或2月,竟只身出走香港,陈序经校长亲赴港访寻方归。(《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P166,三联书店2006年版)钱穆回忆亦称:“后闻其夫人意欲避去台北,寅恪欲留粤,言辞争执,其夫人即一人独自去香港。”(《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P245,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搜罗极勤,上列种种,均有涉及。(详见胡著上册,P469—470,473—474、490—494,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此编所引陈君葆书信,实已证陈氏不惟有避居香港之想,甚至业已付诸行动。加之上述种种史料,则结论更无疑义。编撰者有心遗漏上列材料,亦未可知,盖不如此,不能维护陈氏所谓“爱国”、“爱文化”之成见。果如是,则编撰者头脑冬烘,思想僵化,比之陈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啻霄壤之别。
三
处理史料之外,此书“按语”更能凸显编撰者思想之鄙陋,以致“唐突大家”而不自知。
1951年夏,陈氏有《文章》一绝,诗云:“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此是陈氏略施小技之“暗码系统”,诗旨不难破解,大抵讥讽彼时颂圣之新式八股文章。此编引周一良一文,文中透露,邓文如读过此诗,评曰:“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既引周一良文,则诗意已出,按语可下,亦可不下。此编下了一段按语:“旧制,八股立论必用朱熹说,试帖诗必有称颂熙朝圣皇语。举子应试,不得违制。在极个别例子中亦有利用朱子之说以攻击清朝者。”(P269)后一句似在暗示,彼时八股文章藉八股成规以行攻击时政之实。此论颇不得要领,与彼时情形颇不相符,亦有乖于陈氏之沉痛心思。陈氏之深哀钜痛,方彰显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此编多反其道而行之,设法消解陈氏之沉痛。1954年1月16日条下,转录陈氏《第一次交待底稿》,复征引黄萱《悼念陈寅恪教授》,均事关陈氏拒任历史所所长。尔后下按语云:“辛亥革命时期,先生为了解革命问题,曾认真阅读《资本论》。民国十六年论史,即重视经济制度之重要。解放以来,知识分子学习成绩卓著者,不胜枚举。”(P287)按语下的陈氏,了无沉痛,经由思想改造,已然变身为温良驯服之一代大儒。果如是,且不论陈氏系列“谤诗”当作何解,便是陈氏自身,亦曾称不应北京之召,乃在“畏人畏寒”(见1954年7月10日答杨树达书,此编已引)。其实,“畏寒”显系冠冕堂皇之辞,“畏人”方是真相。又,1954年3月28日条,记杨树达得姚薇元书,姚书言及陈氏不满于科学院,以为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至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抄录杨氏书后,编撰者又附按语,谓姚氏所云,“颇疑出自辗转传闻,恐非先生原语”。进而强作解人曰:“先生1931年尝有‘国史已失其正统’之叹,前此1929年即有‘神州士夫羞欲死’之恨。所谓‘接气不上’实已五十余年。而此时解放不过五年,何致造成如此严重后果!近年先生关注者厥在学风上。”(P289)以陈氏法眼,昔日之“接气不上”是真,五年来之“接气不上”亦是真,各生各病,各有各账。甚至两相比较,陈氏犹痛感于五年来之怪现状,此无他,盖五年来之所作所为,愈益威胁其高自标持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本浅显之理,且史料俱在,毋庸空耗笔墨,遽下不三不四之“按语”。
四
编撰者粗疏如此,编校者之作为更形不堪。编撰者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无力作为处,正是编校者理应用功处。翻检此编,重复错乱之病,偶有所见,此即编校者不作为所致。
页235有载:“先生乘船抵上海,转赴南京,暂住俞宅”。页236复有“先生乘船抵上海,转赴南京”之语。又,页289转录吴宓和朱光潜之思想改造事,与上下文无涉,颇显突兀,似是页287按语之所谓思想改造“态度极为认真者二例”,而误植于页289。
编校者之不作为,见于校对者更甚,其粗放潦草,真令人不敢信也。兹略作举证,罗列如次。页34:“構釁”当作“搆釁”。页35:“既渐罢防守兵,民得安枕”,断句或有误,“兵”属下读为是。页38:“王益梧祭酒”,“王益梧”系“王益吾”之误。王益吾即王先谦,“益吾”其字也。页39:引陈宝箴札,多有讹误,几不可读。如“非咫闻目论之儒,所能臆度也”,“目”似是古“以”字(“苢”去草字头)形近而讹。页46:“南洋陆师学堂”当作“江南陆师学堂”。又页52:“从江南陆师学堂考入三江师范学堂”,此处“江南陆师学堂”,是。页79:“年七十九岁”,当是“年九十七岁”。李璜,生于1895年,卒于1991年,享年97岁。页102:“槁葬”当作“蒿葬”。页102:“二十几同学生”当作“二十几位同学”。 页 110:“此经全真音”,“音”当作“者”。页 121:“送其入验”,“入验”当作“入殓”。页121:“周怡春”,当是“周诒春”。周诒春(1883—1958),安徽休宁人,曾任清华学校校长和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此引自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查原书,确系“周怡春”。胡颂平书误,著者不察。页 121:“送他入捡”,“入捡“当作“入殓”。页 121:“浦江请”,当作“浦江清”。页122:“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作”,句中逗号误用,当作句号或冒号。此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查三联书店版原书,果是句号。坊间所见录此铭之书,多作逗号,不可从。页 170:“What(何时)”,当作“What(何事)”。页185:“倾接到”,当作“顷接到”。查三联版《陈寅恪集》之《书信集》,亦作“倾接到”,误。页185:“北大达羽”,“达羽”当作“逵羽”。逵羽即樊际昌,曾任北大教务主任。页186作“逵羽”,是。页187:“土地粗窑”,当作“土粗窑”。页205:“潭第吉羊”大不通,似“阖第吉祥”之误。页214:“先生在桂林良丰适值红豆开花”,句中有逗,即“先生在桂林良丰,适值红豆开花”。页227:“原来陈公左眼视网膜脱落已有数年,屡治不愈。在成都忽然右眼视网膜亦不幸脱落。”此处“左眼”和“右眼”,适与陈氏之真实情状相反,当先是右眼视网膜脱落,后左眼同此。或是所引原文如此,但著者当下一按语以修正之。页256:“曾昭伦”,当作“曾昭抡”。页268:“阖中肆外”,当作“闳中肆外”。语出韩愈《答李翊书》。页293:“始终有‘猧子吠声’”,当作“诗中有‘猧子吠声’”。页307:“1985年”当是“1958年”。页 308:“承俞允”,当作“承惠允”。页 347:“薄海同钦”,“薄海”当作“溥海”。页 349:“含恨齎志逝世”,“齎志”当作“赍志”。页410:“1988年 11月”,当是“1989年 12月”,查原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