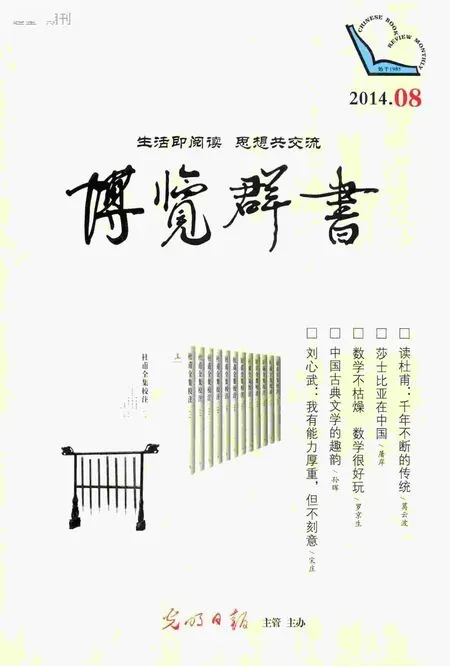《变男》:书写8080后生存真相
○徐鲁

《变男》,刘闻雯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
写作从来就是一桩孤独的工作。它意味着,写作者必须保持着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警惕,保持着对周围人们的一种疏离。当你进入写作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将独自穿越一片茫茫的、未知的沙漠,你既是沙漠,同时也是旅人和骆驼。你将在孤独中去创造新的孤独。当然,孤独中会有星光、黎明和泉水,把你自己,也把你的读者从黑暗和干渴中拯救出来。杜拉斯说:“只有写作能够救你。”而圣埃克絮佩里告诉我们:拯救一个人,就是要教给他口渴的感受,然后再给他一条通往泉水的道路。他借小王子之口说:“沙漠所以美,是因为在某个地方,藏着一口水井。”
刘闻雯的文字里,有一种杜拉斯式的疏离感和孤独感。一个写作者还在继续坚持写作的唯一理由,就只能是为了自己的内心。或者说,只能是对每个人都必须为之做出某种归属和选择的这个社会现实的一种无声的“抵抗”。小说《变男》,就是刘闻雯假借梅悠这个人物,向现实世界呈现的一种不屈服、不盲从、不放弃的反抗姿态。这种姿态是小说的女主人公、一位正处在奋斗状态的青年作家梅悠的,也是年轻的刘闻雯的。
一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惊出一身冷汗。我问自己,我在哪里?我什么时候死去?我都干了些什么?无论头一天我是痛哭流涕还是醉生梦死,第二天早上醒来我都会诚惶诚恐。我去看了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告诉我……我很正常。而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看上去似乎都是正常人。他们四肢健全,可在我眼里,他们全有残疾,都受了内伤。”小说一开始就呈现了主人公对这个世界和周围的人们的疏离与紧张感。
这是一部关涉“80后”这一代人的生存困境、价值观念和精神取向,书写这一代人的怕与爱、疲惫和无奈、丧失和凋零、悲欢与疼痛的现实主义小说。大多数人会认为,“80后”这一代人的成长路径未免过于简单和顺畅,他们不曾经历什么社会动荡,不曾有过青春的劫难,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饥饿、悲苦和寒冷。其实不然。他们的成长过程和精神世界里也有痛楚和恐惧,有挣扎、纠结与反抗,乃至不得不付出的生命祭献。当然,还有谎言、欺骗、沉沦和背叛。《变男》这部小说所书写的,正是他们这一代人所见证的生活真相、所承受的生活重量。
小说的主人公梅悠是一个过着“北漂”生活的漂亮女孩、青年作家。以小说里那个“富二代”张小楠的目光看来,这个女孩“不拜金,漂亮,有思想”。然而,她能够按照自己的内心去写作,却无法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这正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也是每个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困境。
生活是艰辛的。她一心想好好地、堂堂正正地凭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去工作,去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去热爱这个世界,去友好地对待每一个人,可是,她又必须去直面眼前的种种残酷和卑鄙的现实:阴险的竞争、无处不在的拜金主义、尔虞我诈、世态炎凉、性骚扰、潜规则,以及恋爱中的谎言、欺骗、游戏和背叛。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每每乐观地去对待这个世界,世界却总要呈现出灰暗的一面来打击我。”
一个纯净灵魂的获得必须经历血水的浸泡和沸泉的洗涤,一个年轻生命的成长,也必须经受现实生活的百般磨练和挤压。她看清了一切,知道自己不能这样活着,但是只能无力地挣扎、反抗,在心里拼命呐喊。她不断地恋爱,却一次次地失败,不是遇人不淑,被人伤害,就是因为自己太清醒,反而无法投入地去爱。
从南京到北京,从成都到云南……生活不停地驱赶着她、磨练着她、考验着她,同时逼迫着她在深夜里用文字去说出它的重量。
“你生活在车子里,而我生活在世界里;你生活在天花板下,而我生活在蓝天下。”“人生仅仅两万天,而青春更加短暂,我不希望自己每天都在重复着昨天……我渴望经历不同的生活,哪怕是痛苦。”正是这种带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甚至还有一点英雄主义色彩的情结,成了支撑梅悠不折不从、自尊自信的最后的支柱。
一方面是隐忍、坚强和不屈,是内心的抵抗和挣扎;另一方面是率性、开朗和单纯,是真诚的宽容和原谅。而后者往往是外表,前者包含在后者之中。梅悠觉得自己就像艺术家罗丹的情人克洛岱尔·卡米尔,“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有眼泪,也有欢欣。“我知道泪水里包含的不仅是伤感,更多的是一种蜕变,就好像桑蚕破茧的热烈。……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变得更加的坚强。”这就是这一代人的成长。
二
张爱玲曾经这样发问:你还年轻么?不要紧,很快就会老了。梅悠这一代人,也就在这样的挣扎和突破里,从最初告别了各自的校园,而匆匆走到了奔向三十岁的路途上。谁说时间没有重量?谁说他们所经历的只是生活的“不能承受之轻”?不,他们也同样是在承受着生活的“不能承受之重”。
小说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当畸形的家庭和社会使得彭韦熙这个男孩随波逐流、几经折腾而欲罢不能的时候,梅悠这样看着这个熟睡中的男孩:“他喜欢把身体蜷缩起来睡,像一只没有安全感的猫,更像一个躺在母体里的胚胎。他的眼角已经浮现一丝皱纹,好像才刚刚开始长大就已经老去。我把他拥入怀中,此时此刻,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孩子,一个没有发育健全的孩子。”
这样的细节,呈现出了一种温暖的成长关怀和人生悲悯情怀。显然,作者并非在书写她的同龄人的“生活秀”,而是在写着这一代人的“青春劫”。沉痛的叙事背后,是对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的无声控诉和抗议。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把社会批判的触角伸到了主人公目光和心灵所及的许多阶层,甚至是那些弱势群体和非主流人群。
作者借梅悠之口说:“我认为最好的小说应该接近真实的生活。”这是对的。且看她写梅悠和另一个北漂男孩夏风一起晚餐:“我们把灯关掉,点着蜡烛,倒上红酒,开始了简陋的烛光晚餐。这种氛围一点也不小资,因为我们都是一群北漂的穷孩子,因为相似的经历让我们坐到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们是故作情调的无产阶级,正因为如此我们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做。而我偏偏又爱上了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我们喜欢摆弄出那么一副品位和情调,喜欢奢侈那么一把,实际上那都是平时省吃俭用出来的。”作者自己有着“北漂”生活的真切经历和感受,因此写到这个群体的生活尤其感同身受。
小说里也对这一代人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失败的教育提出了质疑和批判,用一种近乎恶作剧的方式作出了解构和讽刺。例如梅悠的成长:“我的成长有点离经叛道,母亲是做教育的,所以对我的管教十分严厉,父母和所有的家长一样望女成凤,儿时带我去学钢琴,我却把乐器室的架子鼓给敲破了;他们带我去学画画,我却把老师家鱼缸里的金鱼给弄死了;把我丢在家里,我溜出门自学学会了游泳……我是阎王不要的小孩。”极端功利化和畸形的、失败的教育方式,养成了这一代人叛逆、抗争和怀疑的性格,也使这一代人从小就对世界失去了信任感和安全感。
如果说,性格坚忍、誓不与卑鄙的现实妥协的梅悠是这一代人中的理想主义者,那么,小说里的另一个人物——梅悠的闺友孔灵,则是代表着这一代人中为金钱和功利所屈服,献出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而与严酷的现实生活达成了和解,心甘情愿地在现实生活的潜规则面前束手就范的一类人。
“这个世界上什么可以靠得住呢?感情?男人?那是扯淡,只有名与钱是可以被你牢牢抓住的。”“我只相信自己能抓住的东西。”这就是这个充满欲望的社会让孔灵得出的最后结论。生活很快就把她变成了一个非常实际的功利主义者。
在梅悠看来,孔灵的选择并非孔灵之过,真正的罪过仍然源自丑陋和卑鄙的现实生活。
三
这部小说给我们刻画了一系列“80后”的青春画像。除了梅悠、孔灵外,还有星星、夏风、张小楠、彭韦熙、林忆藤等。作者不惮以最冷酷、最尖锐的文字,来揭开遮蔽着这些同龄人的温情脉脉的青春面纱,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更真实、更凌厉、更残酷的生存真相,看到了他们的改变、失去、离散、悲伤和哀愁,也看到了他们的“少年劫”和“青春祭”,他们的屈服、利己和被世俗社会迅速异化。就像梅悠对孔灵所说的那样:纵然你已经过上了所谓“上流社会的生活”,我却看不到你肆无忌惮的笑,看不到你发自内心的快乐了。
当然,一本书无论有多么沉重有多少痛,也永远不会像生活一样沉重和使人痛苦。这个世界的痛楚还在加深,但生活还在继续。甚至当你对这个世界失望的时候,生活依然在继续。纵然生活一次次捉弄和欺骗了年轻的梅悠,让她一次次从爱情中失望地离去,但是,她对未来的热情之火还在燃烧。她仍然会一次次地擦干眼泪,拖起自己小小的行李箱,去赶下一列火车和下一个航班。
她也知道,一切试图与这种现实达成和解的想法都可能是不道德的,是天真和徒劳的。也许,对于一个能够用自己的思想和文字来反抗这个欲壑难填、功利十足的世界的年轻人来说,写作,就是一种最好的存在方式。只要是思想家和智者,就会是痛苦的。在梅悠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贵的“怀疑精神”。她用自己的经历和小说,在不断地探讨这样一个命题:如果说,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那么,它真的会终止吗?如果说,它会终止,那么,它当初真的是爱吗?也因此,她的纠结和痛苦从未间断过。她是一只渴望突破而不断挣扎的蚕蛹。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小说始终在传达着一种积极向上和坚忍不屈的励志精神,是一部真实呈现“80后”一代人成长轨迹的“奋斗小说”。
作者曾借书中人物之口,评价梅悠的小说风格:“他们说,我的小说和一般小说的写法不一样……把小说当电影写……太追求创新和自由。这大概是一本没有文体的书,似杂文,似小说,似传记。”用这几句话来看待《变男》,倒不失为一种既省事又贴切的方式。
具体说来,小说里大段大段的思辨和议论,颇具凌厉的杂文风;而在主人公梅悠身上,又分明带着刘闻雯自己的色彩;同时,刘闻雯在这部小说的语言上,也尽情地呈现了她那种独特的充满张力的“语感”。例如她写梅悠在经历了又一次失恋的痛苦之后重新振作起来的感受:“……阳光在黑云里散发着黑色光芒,用力,用力,终于它将两片黑云推开,仿佛打开了那扇即将关闭的万恶之门。我看着它,微笑。眼泪滑过我的眼角。成长在每一次绚烂里,自由在每一分独自里。我失去了吗?没有。我得到了吗?是的。”这样的叙事语言,不仅有几分杜拉斯电影小说的飘忽和疏离,也带着点米兰·昆德拉式的思辨和冷峻的意味。
“你害怕死亡吗?……几十年后我们都会变成灰烬。”在《变男》的尾声,作者借小说里的人物之口如此发问。这使我想到了杜拉斯的预言:“写作可以使人走得很远……直至最后的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