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萨拉蒙诗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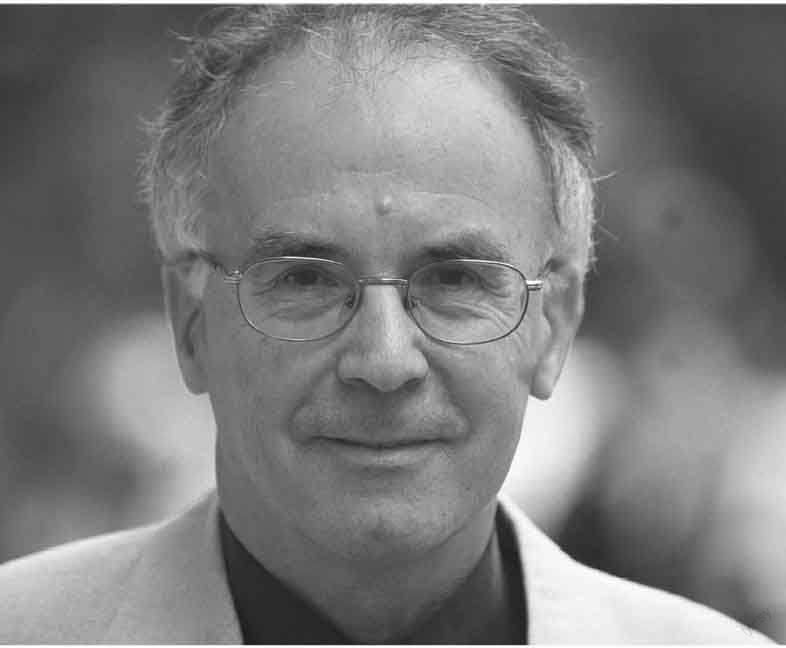
民歌
每个真正的诗人都是怪兽。
他摧毁人民和他们的语言。
他的歌唱提升一种技术,抹去
尘世,使我们免于被蠕虫吞噬。
醉鬼卖掉衣衫。
小偷出售母亲。
只有诗人叫卖灵魂,以将它
从他所爱的躯体中分离。
历史
托马斯·萨拉蒙是头怪兽。
托马斯·萨拉蒙是掠过天空的星体
他在曙光中躺下,在暮色里游泳。
人民和我,我们都惊奇地看着他,
我们祝愿他运行良好,也许他是颗彗星。
也许他是来自诸神的惩罚,
世界的界石。
也许他是宇宙中的一块肥肉
当石油、钢铁、粮食短缺
他将给这颗行星提供能量。
他也许只是一个驼峰,他的头
应当像一只蜘蛛的那样被拿掉。
但是那样的话某物接下来就会吮吸
托马斯·萨拉蒙,也许是领袖。
也许他应该被夹在
玻璃中,他的照片该被拿走。
他应当浸在甲醛里,这样孩子们
就能够看着他,像他们看胎儿,
变形虫,美人鱼。
明年,他可能会在夏威夷
或卢布尔雅那。门房会倒卖
门票。人们赤脚走进
那儿的大学。浪头能有
一百英尺高。这城市神奇,
突然感动于正在建设它的人们,
轻风和煦。
但是在卢布尔雅那人民说:看!
这是托马斯·萨拉蒙,他去商店
和他的妻子马鲁什卡一起买牛奶。
他会喝它而这就是历史。
我是石匠
我是石匠,尘土的祭司
强固如怪兽,面包的痂壳
我是睡莲,圣树的士兵
圣梦的护卫,和天使们一道我大叫
我是城池,一道死去的石墙
我运送舟船,津口摆渡
噢,木头!木头!
来此,小小苍鹭们,一粒种子
来吧,园丁们!光,现身!
来吧,伸长手臂,一块窗玻璃
蓝色旋风,平静的原野
诸层面之生命流动的风息
牧场燃烧,岩浆沸腾
牧羊人等待,不眠不休,以翼践履
狗群,嗅闻自己,狼狗
这里记忆站定,秩序,未来的标记
再次,道路沉默
再次,道路沉默,安宁静黑
再次,蜜蜂,甘美,沉默的绿地
河沿垂柳,谷底矿石
眼中的山岭,动物体内的安眠
再次,儿童躁动,汽笛中血涌
再次,钟里青铜,舌中的香息
旅人们互致问候,瘟疫强固关联
野鹿行在掌中,雪在闪烁
我看见了清晨,我行色匆匆
我看见虔敬尘土里的皮肤
看见欢乐的尖叫,我们怎样一头扎向南方
托莱多男子,两个小小的搭车人
景象清晰,花朵羞怯
黑暗铅封的天空,我听见一声尖啸
爱的时刻将临,高大雕像的时光
沉默洁净的雌鹿,梦幻的菩提树
时间的颜色
从这里世界的
苹果弹出,滚过
一代又一代。
你和我
塞满我们眼睛的口袋。
我们砍倒松树林。
我们刮去捕鼠器上的锈迹。
我们拔除黑血浆的牙。
我两次攻击
一块厚土,用我的大镰刀
把它劈开。
我使羔羊、牛犊翻转向
使者,他们深深感动。
他们交出自己。他们绘彩的嘴,
痛苦的酒,溢出。然后我向着
强壮的月亮投出长矛所以我会知道
准确的时间。
那就是我如何知道的。
时间是个高个子,黄灿灿的,
是太阳的孩子,是太阳自己。
红色花朵
红色花朵长在天空,花园中有簇影子。
光弥漫,光不可见。
那么影子如何可见,花园中有簇影子,
大块的白石散落四周,我们可以坐在上面。
周围山岭一如地球上的山丘,只是低些。
它们看似极为温柔。我想我们也是,极其轻盈,
几乎足不沾地。我踏出一步,
红色花朵似乎缩回了一点儿。
空气芬芳,清凉又火热。新生命
靠得更近,某只看不见的手平稳地将它们放在草地上
它们美丽,安静。我们全都汇聚于此。
它们中的一些,游向此地时
在空中被推转,切除。
它们消失,再不为我们所见,它们叹息。
现在我的身体感觉自己如在一个火焰的坑道里,
它面团般起身,细雨洒落散入星辰。
天堂里没有性,我感觉不到手,
但是所有事物和生命完美合流。
它们奔突离散,只为变得甚至更为一体。
色彩蒸发,一切声响都像是眼中的海绵。
现在我知道,有时我是雄鸡,有时又是牝鹿。
我知道有子弹留在了我体内,它们正在瓦解消散。
我呼吸,多么美好。
我感觉自己正被熨烫,但全然没有灼伤。
读:爱
我一边读你,一边游泳。像只熊——带爪的熊
你将我推入极乐。你躺在我身上,
撕裂我的人。你让我爱到至死,第一次
成为新生者。只用了片刻,我已是你的篝火。
我前所未有的安全。你是终极的
完满感:让我知晓渴望来自何处。
无论何时在你之内,我便身在温柔墓穴。你砍斫,照亮,
每一层。时间迸出火焰,又消失无踪。我耳闻圣咏
凝望你时。你严格,苛刻,具体。我
无能言说。我知道我渴求你,坚硬的灰钢。为你的一次
触摸,我放弃所有。看,傍晚的太阳
正撞着乌尔比诺庭院的围墙。我已为你而死。
我感觉你,使用你。折磨者。你连根拔起我,把我举为火炬,
永远。至福涌流,进入已被你摧毁之地。
鹿
令人敬畏的悬崖,白色欲望。
水自血中涌出。
让我的形质变窄,让它粉碎我的身体
以致万物归一:矿渣和骷髅,一抔泥土。
你喝下我。排干我灵魂的色彩
你舔食我,似微小舟船里的一只苍蝇。
我的头被涂抹,我看见
山如何被造,星辰怎样生出。
你从我身下拽出你的山顶。看,我站在
空中。在你之内,排干,我的
一切。在我们下面,金色房顶向上弯曲,
小宝塔长叶。我在丝滑的糖果中
轻柔,强韧。我聚拢雾送入你的
呼吸,你的呼吸又进入我花园的神性——鹿中。
兔子
群蛇背上长着聚乙烯质的肩
体内携着绿莹莹青杏。
他们日夜给佛罗伦萨的银行写信。
兔子们前仆后继穿越尼罗河
大量溺毙,这样一只兔子终得越过。
他们中的一只用力吸气说道:“我在吸气。”
他们中的一只喝着水说道:“我在喝水。”
他们中的一只跳到鼓上像头圣牛
说道:“我的鹿角在哪儿?
即使我是只兔子也该长它们吗?”
一个兔妈妈扔了株迷迭香
幼芽在他头上,谁能说清
这是愤怒中所为还是出于爱?
他可以照此理解:
从那鼓上下来,你这兔子,我们会爱抚你的。
但是兔子待得太远。
兔子吃着他浸在番茄酱中的爪子
舞蹈得像只老虎。
他的眼睛上蒙着“绷带”,
耳朵上打着耳钉还有蠕虫,鼹鼠,星星们
被用绳子系在鼹鼠的腿上叮当作响。
他在鼓面上蹦跳,滚落下来,砰!
他去到天堂说:“这里不够温暖。”
他跳了出来,砰!他开发出污点
他通过他们喷射像一把水枪,
因此所有的书都湿了,翘弯,
被浸泡,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了。
兔子生出苍天,可怕的分娩痛苦,
太糟了,他们把亚历山大图书馆置于
火上。少数人系紧他们的驴子
嚷道:“该死的蠢兔子。”
乌龟
处在有毒的地理位置,带着
坚硬的壳,乌龟能独自养育
星星。
星星,那里有大豆平行
生长出,绿色天空,
而全世界的士兵们
都想咽口水
却未能。
带着他的可怕精力
和新娘面纱,乌龟像
一对夫妻!一对夫妻!
复活妈妈
从被坦克压毁的
牛奶中。
带着他机灵的
脑袋和水汪汪的声音
——大地的背正翻转——
乌龟杀死,阻止死亡,
还有口中的甜蜜
摇晃自己生出自己。
你可以不戴十字架
而他不会意识到它。
只有乌龟喷涌记忆。
死者
死者,死者
那里在大草原上鸟群掠过,白天被劈成两半
那里骰子顶部是窃窃私语的航船和载着船板的马车从悬崖弹回
那里清晨闪烁如同斯拉夫人的眼睛
那里在北方海狸们互相拍击,再听仿佛死亡的邀请
那里孩子们指着他们青黑色的眼,狂暴地在木头上跳脚
那里,用他们被扯掉的胳膊,他们恐吓邻居们的公牛
那里他们因寒冷而站立成行
那里面包散发醋的酸臭,野生动物的女人们
死者,死者
那里象牙闪亮,童话沙沙作响
那里最高艺术是将奴隶钉在半空中
那里谷物燃烧在广阔平原上以便上帝能够闻到
死者,死者
那里有为鸟类而建的特别教堂教它们如何承受灵魂的负担
那里居民们每一餐都折断他们的桌腿并踏步在桌下的圣书上
那里小小眼球是橘色的,妈妈们被一个个钉成方形
那里马儿被烟炱熏黑
死者,死者
那里九柱戏是巨人们的工具在圆木上擦伤他们油腻腻的手
那里萨拉蒙将被尖叫致意
死者,死者
那里所有的门房都是黄种人因为他们眨眼更快
那里肉贩子被用球拍打死并被曝尸
那里多瑙河流淌进银幕,从电影里进入大海
那里士兵的号角是春天的信号
那里灵魂们高高跃起低声合唱
死者,死者
那里朗读被砾石加强,当我们击打它,便能听到它的隆隆声
那里树木有圈圈螺纹,林荫大道的膝关节
那里他们将出生后的第一天切进孩子们的皮肤,就像切进轻木中
那里他们把酒卖给老女人
那里青年刮擦他的嘴就像挖泥船刮擦河底
死者,死者
那里母亲们自豪,从儿子们身上抽出细丝
那里机车上覆盖着麋鹿的血
那里光腐烂,破碎
那里部长们身穿花岗岩
那里巫术使动物们落进篮中,胡狼践踏在水獭们的眼睛上
死者,死者
那里一个人用十字架标记天空的每一边
那里小麦粗壮,双颊被火吹得鼓胀
那里群群飞鸟有着皮革的眼睛
那里所有瀑布都是生面团的,他们用年轻生命的黑丝带系紧它们
那里他们用木钩打断天才人物的足弓骨
死者,死者
那里摄影术限用于长爆成纸的植物们
那里李子在阁楼晾干,然后落在老歌里
那里士兵们的母亲推车运食品包裹上架
那里苍鹭建造得如同运动家型阿尔戈英雄
死者,死者
那里水手们来访
那里在豪华府邸马儿嘶鸣,旅行者嗅闻
那里小小浴室的瓷砖覆盖着鸢尾花种子图案
那里食人魔被喂以木制墙面板
那里藤蔓的枝条被灰色面纱裹住因而嫉妒的眼被覆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