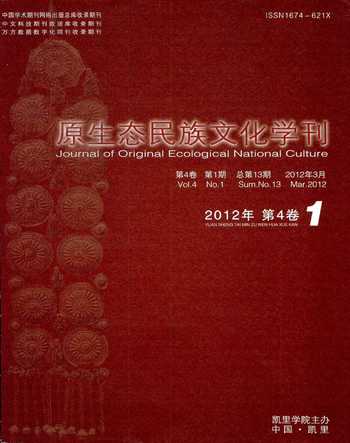从阿拉善生态移民政策看荒漠化治理
夏循祥
摘 要:阿拉善地区生态环境严重退化的原因是综合性的,但最主要的是宏观调控政策失当和市场经济过分掠夺。而目前的生态移民政策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原因,而是简单地以农业代替牧业,但该地区的极端干旱气候根本不能承受耗水量远远超出牧业的农业生产方式,而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则会导致地下水水位的迅速下降,从而引发无法弥补的绝对干旱和盐碱化、沙漠化。最有效而也是最难实施的举措就是宏观调控下的黑河流域水资源合理再分布,使有限的水资源得到平均而最优使用。蒙古族游牧文明的生态善恶观、生态伦理观和宗教信仰,以及传统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能够保持当地脆弱的生态平衡,并且不断再生产再发展,也将是阿拉善地区恢复生态环境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生态移民;荒漠化治理;阿拉善
中图分类号:S8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1-0134-08
2005年8月至9月,受阿拉善SEE生态保护协会的资助,我们项目组①(①本次项目受阿拉善see生态保护协会资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本课题负责人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高丙中。当时参加本次调研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王立阳、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章邵增、马强、仲林、宝花、乌日吉木斯及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乌云其其格,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翔实的研究资料表示衷心的感谢。)在阿拉善地区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调研,主要调查阿拉善地区蒙古族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选取的5个调查点②(②这5个项目点,分别是纯牧区的阿拉善左旗的苏海图嘎查(村)、巴音朝格图嘎查、阿拉善右旗伊和呼都格嘎查;亦农亦牧的额济纳旗赛汉桃来嘎查、阿拉善左旗沙日霍德嘎查,同时项目组还走访了已经建好和正在兴建的额旗移民村和赛汉桃来移民村。在此对接受我们调查并给予帮助的人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其生产方式正处在牧业、亦农亦牧、农业几种类型,生活方式包括游牧、定居、聚居这三种类型转变中的不同阶段。空间的差异性与时序上的纵深感能够帮助我们对其现有政策的实施过程进行思考与评估。
虽然本次调查的重点不是针对生态移民问题,但由于生态移民政策在阿拉善地区的普遍采用及推广,我们在调查中也取得了很多关于生态移民的第一手资料。在为期1个月的调研中,项目组兵分三路走访了5个项目点的大多数农、牧民以及当地官员,获得了丰富、翔实的访谈和文字资料。在生态移民政策已经成为阿拉善地方政府改善生态环境的一种主导性实践行为时,本文通过深度访谈与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1]出发,通过对现有生态移民政策本身的出发点及政策手段提出质疑,而且针对移民之后所产生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在此基础之上,对生态移民政策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并希望能为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有益的建议。
一、阿拉善生态移民政策管窥
调查表明,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阿拉善的生态环境还基本保持着比较良好的状态,人们还保留着对80年代河流、植被、草场的美好记忆,沙尘暴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词。目前的阿拉善则面临着五大生态危机:河道断流加剧,湖泊干涸,湿地消失,绿洲萎缩;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水质逐渐恶化;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草原生态系统退化;沙漠化加剧,沙尘暴频繁发生,阿拉善成为沙尘暴的策源地之一。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给阿拉善地区经济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并且也波及到西北、华北及海外一些地区。阿拉善的生态危机已经引起各级政府、群众、各类民间环保组织甚至国际社会的重视,并已经采取一些措施、启动一些保护项目以缓解生态危机以期达到保护和恢复生态,比如生态移民政策的采用及推广也主要是基于这一目的。
阿拉善一直是蒙古族聚居的地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是以游牧为主。所以很多人都在猜想甚至断言:是蒙古族人的游牧,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给我们带来了沙尘暴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牧民在一直受到过度放牧的指责的同时,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生存也受到草地退化、盐碱化、沙漠化等生态系统严重恶化现象的直接威胁。调查时,我们看到的是寸草不生的戈壁、一望无垠的沙漠,骆驼和羊都瘦得让人心痛。绝大部分骆驼的驼峰都是干瘪地伏倒在背上,两边的肋骨清晰可数。羊群基本不能挤奶,一般成年公羊也只能产30-40斤肉。牧业在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似乎已经走到尽头。对牧民及畜牧业的这种归因与指责也直接导致了他们成为生态危机应对措施的主要┒韵蟆
在引进了棉花、哈密瓜等经济作物以后,阿拉善的农业收入已经远远高于牧业收入。在一些传统牧业地区,农业也成了主业。额济纳旗赛汉桃来,苏木赛汉桃来嘎查过去水草丰美,是一个传统的牧业区。黑河断流后, 1996年开始试种棉花;2000年开始种哈密瓜,到2004年底已有1500亩左右的耕地(不包括各家在自己的草场上开的地)。赛汉桃来的富裕村民几乎都种有数百亩地,每年的现金收入也基本在100000元以上。我们调查的阿拉善左旗的某个嘎查的书记、村长种地都在500亩左右,因此在巴音(阿盟首府)、银川都购买了地产。
因此,在当地政府看来,农业不仅成为了独立于牧业,更为赚钱的生产方式,而且成为最普遍的、最值得推崇的生产方式。因此,在以单纯的经济指标来衡量地区发展水平、以现金指标来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官员考核体系下,农业被地方政府用作了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途径。在生态保护的语境下,当地政府目前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农业解决贫困,移民解决生态”,即生态移民,并限制牧业的发展,用农业化生态移民政策来解决生态危机。具体措施就是退牧还草,让牧民从草场中退出来,使草场休养生息,而在土壤、水利条件允许的地方将牧民集中起来从事农业生产,使牧民转化为农民。①(①由于本次调查没有对该地生态移民政策进行全面收集,所以不能提供关于阿拉善生态移民的一般现状。该地生态移民状况可以参见【日】儿玉香菜子,“‘生态移民引起的地下水危机”,载新吉乐图主编《生态移民——来自中日两国学者对中国生态环境的考察》,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43页;杨炳禄编著:《额济纳河》,阿拉善盟黑河工程建设管理局、额济纳旗水务局出版,2002年,第130页。)
在调查中,额济纳旗赛汉桃来苏木(镇)党委王书记说:额旗已经建立了达来库布镇和赛汉桃来2个移民点。赛汉桃来下游三个嘎查都要搬到赛汉桃来移民点农业区去,人均分配10亩地进行农业生产。部分种饲草,部分种经济作物,向农牧结合的方向发展。户均房屋70平方米,配备暖气等设备,另留有100多平方米牲畜舍饲基地。牧业基本上要禁了,只能留下10-20户,适当地保留民族传统经济。但牲畜不能放多。除了移民村农业基地,还要开设电厂等工业基地,发展工业。上游两个嘎查到工业小区。部分牧民转作护林员,一部分移入达镇从事餐饮、出租等第三产业。牧民的子女可以劳务输出。通过多种分流方式,把牧民变成农民、工人、城镇人,彻底从胡杨林、草场中退出来享受和城人一样的待遇。目前执行社会保障制度有:(1)低收入的列入城镇低保;(2)新建农村合作医保,95%的人都可以享受;(3)养老统筹,达到55周岁的老人,从社保上发养老金,全旗统一平均算,具体金额还没定;(4)退耕还林,从耕地退出来,补钱补草料,按全旗农牧区人口的总数平均分;(5)退牧还草,按草场算,人均补大约5000元;扣除养老统筹和盖棚圈的钱后,户均4-5万块。在退牧还草政策下, 赛汉桃来嘎查于2005年开垦了2000亩耕地作为生态移民政策的配套耕地。
从牧业到农业,这一生产方式的转换在政府官员看来,是生态环境恶化必然的结果,也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但调查发现,这种转变对生态系统的恢复至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显示出优化的迹象:一是没有了牲畜的草场植被状况依然很糟糕,总体生态环境并没有好转;二是移民村成为养老村、儿童村、教育村,没有发挥政府期望的作用,青壮年依然在牧区、农区生活生产;三是移民的生活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并没有使移民看到脱贫或致富的宣传效果。
三、农业不是出路
历史地看阿拉善地区农业与牧业的发展关系,其中关键的一条是:农业并不是脱离牧业的纯农业,而是一种农牧结合型的新型农业,农业中包含着为牧业提供草料的饲草种植的重要内容。饲草种植和与牧区的交换构成了阿盟农牧一体的特殊格局。而且垦田较少,有政策制约。这种支援牧业的农业存在,使牧业生产有了可靠的后盾和依托[2]。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尤其是汉族人的不断涌入,在“吃饭政策”的压力下,农业所具有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人的相对优势,使大面积开垦土地成了必然。人口、农田、牲畜、草地载畜量都迅速地直线增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峰。1960年代初沙日霍德嘎查只在前滩有大约200亩耕地,主要是饲料田。1981年,该嘎查已有耕地2000余亩。2005年,根据腰坝镇政府三月的统计数字,该嘎查耕地总数为14182亩(实际数字应该还要大)。而1980年代之后的这段时间正是阿拉善生态状况急剧退化的时候。
一旦以往的农牧业格局被打破,强势的农业会进一步促使牧业的萎缩,从而使大量的草场转变为耕地。在降雨减少、黑河水量几乎没有的情况下,大肆开荒的后果之一是致使地下水位的急剧下降。1960年代之前,沙日霍德嘎查只需要人力挖几米深就可以见到水,1968年已经需要用柴油机挖涝坝。1970年代开始使用打机井,只需要打40-50米便可找到水源,而现在大部分的机井都已打到100米到120米深。后果之二便是地下水位的下降导致沙漠区域地下水向农耕区地下水倒灌。现在沙日霍德队的机井抽出来的水带有很大的碱性,村民饮用的自来水也带有咸味。根据阿左旗水利专家的检测,当地现在的食用水中矿物质严重超标。耕地耕种几年后也容易盐碱化。后果之三是对草场植被的破坏导致沙漠的推进。开垦耕地的过程中把草场原有的树木、饲草全部挖掉。沙尘暴一起,没有了防风固沙的植被,草场也就随之荒漠化了。没有遮挡的风沙便逐渐扩展,影响村民的生活,也威胁到他们未来的生存。沙日霍德嘎查有两个居民点距离沙漠只有1公里左右,另外一个居民点就在沙漠的包围之中。据村民说,沙漠在最近十几年中向村庄附近推进了1公里多。
阿拉善目前的农业强调的是土地开垦,而不是重点引进节水型和低耗水型的农业技术,以及采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技术带来的增产效果上。这种农业越是发展,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就越严重:对现金利润的追求与农业人口的不断增加,会引发对农田的更大需求;耕地的不断增多必然导致对地下水更大的、不断地汲取,必然更加加速地下水水位的下降和水质的恶化,使得本来就不适于农业生产的地区生态系统愈加难以负担。如果按照现有耕地用水和地表水、雨水补给之间巨大的差别,即使全面退牧,生态环境也会进一步恶化。如此往复,将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
不仅如此,现有的生产技术结构也不具有市场竞争力。对阿拉善来说,应该强调与生态保护有关的种植业或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的农业项目。如梭梭、苁蓉、锁阳、苦豆子等农产品的种植与培育,不仅不会破坏生态环境,相反还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这些产品既是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又是节水型和低耗水型农业项目,因此应给予大力发展。可是政府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目前,地下水采用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只需要打井的费用和电费。这让农业从业者及农业支持者一是以为地下水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二是对地下水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比较严重,根本没有相应的保护意识。赛汉桃来嘎查每天有1个小时向居民点排放自来水。有很多居民都在接满生活用水之后,把自来水管放到自家院子里,任其排放。
这样的后果其实更为严重。地下水资源需要循环,需要很长时间涵养。阿拉善地区虽然地下水丰富,但缺少补充的情况下涵养量必然持续减少。原来植被都靠河水漫灌,或者地下水来维持生命。但现在黑河工程变成了一条通向东居延海的“渠道”。其他的河道被工程堵死了,还加上了防渗工程。没了河水补给,农业用水必然使地下水位不断下降。一位水利专业人士对我们说,过去额旗的地下水位是3尺左右,如今的水位已经下降到5米左右。胡杨的根只能扎到3.3米,最耐旱的红柳根也只能扎到4米。如果水位再下降,这些最耐旱的植物也都得枯死。据观察,目前沿着原西河河床两岸,白刺、黑豆等极抗旱植物现在基本上都消失殆尽,胡杨也岌岌可危。赛汉桃来汉族农民李明远也证实这一片胡杨树每年的死亡率是10-15%。某位富裕村民说:“2005年9月份抽水时的出水量就比6月份的小很多,水位下降很明显。黑河工程修好了,上游给水也是象征性的,沿途也不渗水了,直接到居延海。如果两岸的胡杨都死了,把居延海灌满了又有什么用呢?”。
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土地的沙化日益严重,到了农业也难以为继的时候,阿拉善的出路在哪里?民勤信息网的主题词是“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①(①http://www.mqhg.com/)如果继续按照现有的模式,全面推广农业,阿拉善肯定会成为第二个民勤。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四、移民:移走什么人?
莱斯特·布朗在《环境经济革命》一书中,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认为人类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两大主要任务就是稳定人口规模和稳定气候变化[3]。从这个观点出发,解决阿拉善生态危机一定要严格控制本地区人口规模。但目前,生态移民的政策对象基本都是牧民,移居的目的地也在本地区。也就是说,阿拉善地区的人口规模并没有减小到现有生态环境可以承受的规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盟总人口仅有34110人,绝大部分是蒙古族人。到2000年,已增至196279人,人口共增加了162572人,增长了5.75倍,平均每年以3.51%的速度递增。全盟境内28个民族中,汉族人口最多,为140900人,占71.79%;其次为蒙古族人口,有44630人,占总人口的22.74%。在这样一个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却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汉族。②(②本次调查中人口资料来自于阿盟统计局内部资料《阿拉善盟人口现状及发展预测》,在此表示感谢。)据调查来看,阿拉善地区基本控制了人口的总体自然增长率,增长主要来自于外地移民。民国以来,宁夏、甘肃等地的汉族人开始陆续地进入阿拉善,尤其是战争年代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两次难民潮使得阿拉善人口的蒙汉比例急剧变化。1980年之后,与周边宁夏以及甘肃民勤、金塔一些县市相比之下稍显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及回乡探亲者显而易见的更为良好的物质生活水平,依然吸引着外来者。调查发现,沙日霍德、吉兰泰一队等一些村庄的当权者,近几年还引进了一大批新的汉族移民。
可能因为与草原没有太深的感情,也没有对自然的畏惧,汉族人在利益面前显示了他们比较自私而急功近利的一面。在生存经济及后来的市场经济刺激下,他们开始采取一些掠夺性的经济生产方式,对植被的破坏应该负有最大的责任,比如伐树建房、打家具;超载放牧;挖中药材和根雕等。有的人放养超过千头的牲畜,并首先到别人的草场放牧,来水的时候也偷偷抢水。当然后来很多蒙族人也开始超载放牧了。在草场上拉铁丝网也有汉人的原因。一方面因为汉族人不按草场的自然规律放牧,一方面汉族人比较爱占小便宜,总是把羊先赶到别人的草场上,然后才到自己的草场上放牧。比如苏海图嘎查的乌兰扣和潘竞泽家。潘家羊多,总是到乌兰扣的草场上吃草。乌兰扣的羊群小,撵不过潘家的羊群。乌兰扣只能拉上铁丝网。
为减少农业,减少地下水资源的消耗,也减轻目前生态危机的压力,政府应该考虑如1963年一样,不仅要坚决杜绝外地农民的迁入,而且要适当考虑将1990年之后或者1995年之后进入阿拉善的汉族移民进行遣返或移往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其他地区。③(③该思路可以参见方兵、彭志光:《生态移民:西部脱贫与生态环境保护新思路》,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31 —57、72、74 —76页;范红忠、赵晓东,“西部生态移民问题及中东部地区在其中的作用”,《农村经济》,2003年第7期。)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因生态移民而引起的民族恩怨,而且对祖辈都居住在阿拉善地区的蒙古族人民更为公平。
五、水才是关键问题
几乎所有接受过采访的人都认为,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才是恢复阿拉善地区生态的最关键因素。
黑河曾是阿拉善地区的生命线,它充足的水量使得蒸发量是降水量100多倍的阿拉善依然能够形成众多的绿洲,孕育灿烂的居延文化。1970年代后,上中游地区的农业与人口占用下游的原有的水资源份额,是阿拉善草场退化、牧群缩小的最主要原因。当前黑河上中游用水分别占用水总量的1.2%、93.3%、5.5%。水资源供求矛盾主要在中游,危害则在下游。1993年后,黑河下游基本长年断流,只有零星来水。④(④关于黑河水资源状况,参见杨炳禄编著:《额济纳河》,阿拉善盟黑河工程建设管理局、额济纳旗水务局出版,2002年,第130页。)赛汉桃来苏木王书记说:“黑河断流的主要原因是上流用水量剧增。黑河管理局作为黄河管理局的下一级,权威性不大。对此旗上跑了十几年,向盟、自治区以及中央汇报这里的情况,希望能解决水的问题。”目前阿拉善的水循环系统处于极其恶劣的状况:降雨量极小、地表水缺乏、地下水位不断下降,水质恶化等,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处于岌岌可危的状况。
中央曾发出指示,从2001年开始修建黑河工程,要最大限度地让东居延海实现“3年内看到波涛”的目标。到2005年工程已完工,干枯了14年的东居延海也确实重新见水。但生态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黑河工程使用的防渗材料影响了河水浇灌沿河草场,同时存在东西居延海分水不均的问题。黑河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面子工程,更需要水资源补充的广阔草场却只能处于更为饥渴的状态。王书记说:“这个地方的水是生态水、灌草场的水,所以只能满滩流。西河每年来水量应该有1.88亿立方米,但是实际上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来水的季节也不太合适。3月份的春水或冬水最重要,秋水的用途远远不如春水。现在的来水(2005年8月底)是修黑河两年以后最大的水,但都流进了东海。”
因此,即使黑河工程长年恢复水流,对流域的地下水补充、植被的灌溉作用也非常有限。除了原东居延海的一部分,阿拉善大部分地区沙化趋势根本没有缓解。没有河水、雨水的补充,地下水位会持续下降;农业要汲取地下水,只能打更深的井。如此循环往复,有限的地下水终有枯竭之日。而地下水浇灌的耕地碱性也会越来越大,最后只能寸草不生。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解决阿拉善生态问题的最大关键。如果黑河水域的行政区划问题、地方利益的分配问题不解决,要恢复阿拉善的生态也只能是神话。
没有水,再多的措施与方法也是空谈。几乎所有接受过调查的人都认为:只要来水,生态就会变好;也只要有来水,生态才会变好。据老百姓说,2002年,黑河上、中游地区降水充沛,5 月份就有水通过额济纳旗绿洲进入东居延海。有水经过的地方,到处生机一片。我们在调查中,也能够观察到河流(枯河)堤岸与河流流经地方、与远离河流地区植被状况之间明显而深刻的差别。而恢复了一定水面的东居延海,芦苇更是茂密,恢复了往昔状况。
本文认为:必须减少额济纳河上、中游对河水的利用,使下游的生产和生态系统得以良性运转;必须赋予黑河管理局更大的权力(清朝时期,年羹尧曾设置“均水制”,每年芒种前封闭上段各渠口10天,给下游放水,并借助强大的军事力量予以实施①(①参见杨炳禄编著:《额济纳河》,阿拉善盟黑河工程建设管理局、额济纳旗水务局出版,2002年,第57页。));不仅要加大下游河水量,还要停止河道的防渗工程;来水季节最好在春天,为植物的普遍生长提供水源;夏季也要补充地下水,使水质变好;使胡杨等沙漠植物能够在降水无法增加的情况下得到滋润。
六、移民之后的原有草场、耕地的保护和利用
生态移民政策的采用,目的是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但据调查得知,部分生态移民或承包户自主退牧之后的草场被政府或嘎查承包给企业或个人进行矿产开发。这符合经济学和市场规律,但不符合生态移民的目的,从而使移民做出的牺牲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一位嘎查长告诉我们:对于开矿,牧民都不愿意,但嘎查和镇里都愿意,因为可以增加经济收入。而且政府和嘎查认为迁移出去的牧民不能分享该项承包或租赁收益,这实际上剥夺了牧民对原有承包地收益的享用权。由于退牧的原因只限于生态恢复,牧民领到也不是矿产开发权的转让费用。同时,现有生态移民政策对5年之后或者生态环境恢复良好状态之后,退牧草场的承包权与所有权的归属没有进行明确规定。这必将埋下纷争隐患。本文认为必须减缓矿产开发步伐,一是这些矿产开发产生的价值没有付出的代价(沙尘暴、生态危机以及经济损失)大,二是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对草原破坏大。同时要对已经承包的矿主签订严格的环保合同并坚决执行,每年征收一定比例的环保费用用于生态建设,否则进行高额罚款甚至收回承包权。
一些嘎查还在不停开垦新的农田。而这些新开垦的农田,基本没有很好的收益。沙日霍德嘎查一家农户2005年初以每亩850元的代价买回40亩新开垦的土地,然后花1万多元买了含粪的沙土进行盐碱稀释。但秋天的收成是2袋半麦子,合250斤左右,连种子都没有收回。还不包括开采地下水的电费和农药、化肥等。这既不符合经济规律,更不符合生态要求。但这样的开田、卖田行为还在继续,使小范围生态移民的努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化为乌有。
内地汉人在禁牧无主草原上不负责任地挖掘或开采苁蓉、发菜、甘草、根雕等,在山上拣石头(阿拉善奇石目前是当地一个主要经济来源)等,导致生态的更直接破坏。赛汉桃来嘎查由于拥有大片的胡杨,四五年前就有人来挖树根。以前挖死树,现在开始挖活树的根了。外地商人雇三轮车到处挖。在他们带动下,本地有些人分地之后就把草场上的树都挖掉了。外地人挖药材、根雕,挖得特别深,挖完就不管了。这样特别破坏草根,沙子失去固定物,风一吹就起沙,还压坏别的草根。草场归个人时,承包人还能加以阻止。退牧还草之后,草原变成无主之物,也没人管。2003年起政府开始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但无法完全阻止这种非常直接的破坏行为。对内地汉人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无视生态环境的观念和行为更是需要采取足够有效的防范措施。
草场单纯地闲置,也容易导致草场的另一种破坏:鼠害和火灾隐患。没有人类活动和羊、骆驼的游牧,草原鼠害变得肆无忌惮。而部分毒草在夏季的疯狂生长,容易导致冬季火灾隐患。蒙族人认为“草长出来天生就是给羊吃的”。第一年不吃,第二年就败了——不适合放牧了。大多有经验牧民认为:闲置草场必须按照现有牧草科学计算,放养最小数量的牲畜,以减轻两类隐患。
七、移民之后生活方式、生活水平、聚居生活等问题
长期以来,牧民尤其是蒙古族牧民价值观、世界观、生活观念和方式都不同于农民。要其完全从游牧生活转变为农民,需要一个持续而艰难的过程。传统蒙古族观念认为“大地是母亲”,要其种地便是挖开“母亲”的身体,在宗教理念和传统观念上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从生态人类学观点出发,如果保护环境需要改变当地居民的经济活动,若不了解当地人的价值观念,就很容易作出错误的决策,也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现在政府宣传只讲生态移民和农业可以脱贫致富和恢复生态,而不提稳定牧业人口,对畜牧业这一传统的也是必需的生产方式构成了一定的伤害。生态环境恶化后,牧民们沦为生态难民,牧业也难以为继。嘎查里许多年轻人都到外地打工、上学,“不再回来”是他们在外边打拼的动力,也是家长们教育小孩的主要内容。从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肉、奶制品需要来说,畜牧业还是有着很好前景的。蒙牛、伊力等草原企业的蓬勃发展就是明证。盟畜牧局一位负责人担心地说,牧区现在是青黄不接,牧业后继无人。放牧只有老年人与中年人。年轻人不愿意放牧,也不安心放牧。城乡差别造成越来越多青年人弃牧进城,牧业再也吸引不了青年人。这样,不仅畜牧业处于萎缩状态,阿盟城镇本来就比较突出的待业问题随着牧区青年的涌入变得越发严重起来[4]。
而没有牲畜的蒙古族人,也在慢慢丧失自己独有的游牧文明和文化。一次在巴彦宝格德举行那达慕,总共才只有18匹马参加比赛。那场面小得实在不能看。赛汉桃来蒙古族退休医生萨日听收音机报道在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有800匹马参加那达慕,都伤心得流泪了:因为额旗也曾有上千匹马参加的那达慕,马曾是这块土地的装饰品。图克木苏木2002年那达慕上只能举行赛毛驴。很多牧民都特别伤心,说:“什么叫赛毛驴?”
市场经济以现金的多寡为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打破了蒙古族人以生活舒适度为评价标准的生活感,成为蒙古族人遭受经济性歧视的重要来源。对于长期以牧为生的牧民来说,农业生产经验、技术、机械的缺乏导致农田管理的不善,必然会导致农业收入无法达到政府宣传与本人预期的水平。而且对于移民来说,退牧改农后,由于分到的都是新开的地,土壤情况、肥力、灌溉条件等都不可预期,农业的前期投入肯定高于牧业投入。这必将导致部分原来量入为出、缺乏存款的移民家庭的收入受制于资金投入,可能会陷入贫困。
游牧以分散居住为主,农耕以聚居为主,而闲暇时光的增加和居住空间的邻近,使生活水平有明显下降的蒙古族,容易导致对政府的集体怨恨,从而培养了一大批“怨民”而违背初衷。文化生活和娱乐方式的不同,也容易导致民族之间的偏见和管理上的简单化。蒙古族人爱喝酒,农业给予了相对更为漫长的闲暇时间,而聚居生活可能导致酗酒事情的更多发生。因此,对于移民村的生活,大多数青壮年牧民虽然觉得对老人赡养、孩子教育来说起到很大的作用,但他们还是表示了一些担心:怕人多以后喝酒打架、怕是是非非,怕孩子在城里学坏。额旗县城里的移民村的住户大多是老人,整齐划一的砖木结构的院落里,有许多人家依然搭着蒙古包,飘着风马。还有一些老人则坚持住在蒙古包里,愿意守着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不愿搬回嘎查,更不愿意搬到移民村。
八、一些结论与讨论
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已经引起各级政府、包括境外机构在内的民间环保组织以及当地群众的重视,并已经启动一些保护项目,但目前人们总是习惯于单纯动用技术、法律、经济或行政的手段,去完成既定的维护目标。然而类似的手段只能在特定的时段内,解决某些局部的生态维护问题,这远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5]。本文认为生态问题决不简简单单就是生态的问题,而是社会、环境、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问题综合造成的,解决起来也不能单从生态二字着眼。生态环境的恶化固然与人有很大关系,但人的活动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且并非只有当地居民才对地区环境有影响。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地方资源的毁灭需要到更大的共同体中寻找原因,所造成的也是一个更大的有机体循环的破坏甚至毁灭,而不只是单纯寻找当地居民与环境的关系。把生态危机的全部责任归结到牧民群体不仅有失公允,而且无法解决问题。生态问题也不简简单单是阿拉善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大的体系、更大的区域的问题,是在全球化背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人类与资源、人类与地球的关系问题。
过去,蒙古族人成功地利用民俗建立了环境为核心的公共物品、公共利益的观念,并具有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让这种观念体系顺利运作,达成可持续的良性运行结果。后来 “公共”的范围变化了,外部世界(市场需求、国家建设、政府规划和政策)进入社区,成为了内部因素。而新加入的主体没有同样把生态作为核心公共物品的观念,因此导致环境的破坏。
本次调查认为:阿拉善生态环境的恶劣,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正确决策或没有起到良好引导所造成的人与环境原有和谐关系的毁灭,是老百姓自己不能参与决定,国家强力介入普通生活的后果。在全能化国家的控制下,阿拉善地区无论是社会、经济、文化,还是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他们与自然环境相处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对自然环境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非理性行为(砍树炼钢铁等)、自治区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造成对蒙古族人、牲畜以及草原等生存空间的无限挤压,尤其是在牧业地区大规模推行农业生产方式,使生态环境付出了沉重代价[6]。而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系的压力下,还大张旗鼓地宣传“大牧业”,到处鼓励“万峰驼苏木”“万峰驼嘎查”之类的“头数畜牧业”,以求得自己在官场上的更进一步。日渐狭小的放牧空间与日渐扩大的牲畜群,使本来就已经退化的草场加速了毁灭。据统计资料表明,40年代的39万只(头)牲畜,到了90年代变成了175万只(头),超过自然载畜量的3倍多[7]。调查表明,2005年6月末,牲畜头数已经达到218.51万只(头),比上年增长了15.91%,超过草场良好时自然载畜量的4倍以上!
而国家政策就全国范围内所作的论证和决断,对于阿拉善这样一个小社区而言,也缺乏足够的指导性,甚至是破坏性的。比如承包制破坏了原来的游牧和轮休制,使草场不能休养生息。后来拉铁丝网也阻止了动物粪便传播种籽这一传统播种方式。目前生态移民政策的禁牧、改农,使蒙古族人觉得汉族抢占了他们的草原,野蛮地破坏了他们的家园,而现在又要他们以民族文化和游牧文明的牺牲来承担这样的代价。正如我们批评美国人喜欢将他们所谓最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推广到全世界一样,汉族作为56个民族中的一个民族,也不能掉进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的陷阱。我们不仅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也应当尊重他者的文化。
我们的调查表明,蒙古族人以及蒙古族人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是阿拉善生态环境严重失衡的罪魁祸首。相反,蒙古族的生产方式(如牲畜的管理、草场的轮牧、狩猎的禁忌)、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皆取之于草原)、宗教信仰(无论古蒙古的萨满教还是黄教都有倡导崇尚自然,倡导“天人合一”的思想)都比现在以汉族为主导的农耕文化更具备环境保护的特质,对当地环境资源的利用方式及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蒙古族游牧文明发生发展的历史来说,蒙古族的游牧方式更适合于阿拉善干旱半干旱地理特征。阿拉善地区的核心价值观只能来自于传统的游牧文明。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耕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检讨,而决不能把游牧文明当作一种应该予以抛弃的“低级文明”。不仅要把蒙古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当成一种需要挽救的文化,而且要把它当作一种更高形态的、适合当前充满危机的阿拉善生态环境的文明形式来予以推崇。当然,在目前草场已经被基本破坏、完全不适合放牧的前提下,适当的退牧、禁牧也是必要的保护。引导和动员是一回事,循序渐进和引进更有效替代方式是更加迫切的一个需求。
虽然蒙古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在国家话语权、与汉族涵化、市场经济评价体系、环境恶化等多种情况下,发生了面向全球气候变化、面向市场、面向危机的系列变化,但宗教信仰、基本思维方式、游牧文明的内涵与本质,那种追求“天人合一”、生态系统与自然环境保护的理念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要国家与地方政府对自己的行为不断反思并予以纠正、改进,当初人与环境之间比较和谐的关系还是可以重现。
当然,新的价值观当然不可能再次全部建立在原来宗教信仰之上。它的重建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不仅需要阿拉善人对自身的文化传统重新挖掘、整理、研究、表述,也需要外界力量的鼎力相助——但是一定要注意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帮助他们发掘有益的地方性知识,充分利用当地人的知识传统和人力资源。生态危机的逆转和宜居环境的再生仍然取决于实际上属于“公共”这个范畴的全部主体建立观念的共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中,先从政府做起,从有能力的社会主体做起。
因此,为应对阿拉善生态危机,除了妥善而适当的移民,我们全社会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比如加强草原森林、植被的保护、培育和管理,减少农业对地下水的需求,减缓矿产开发的步伐等等。尤其是黑河水资源的合理调配,使地表水、地下水、水蒸气的循环趋于合理,而不是把移民禁牧当作万能药。
总之,本文对阿拉善现有的生态移民政策持有保留意见。阿拉善目前的生态危机并不是移民就可以变好,也不是移民就一定会变好。当然,在移民成为一种既成事实之后,除了要继续对移民政策的推广进行事前论证和事中检验,移民之后的评估和调研也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这样才能有助于生态危机的最终克服。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希望能够为这一政策提供另一种观察角度。
げ慰嘉南祝邯
[1]克利福德·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A].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2]刘援朝.历史与现实:阿拉善盟的汉族与蒙古族——阿拉善盟民族关系调查[J].西北民族研究,1995(1).
[3]莱斯特·布朗.环境经济革命[A].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4]刘援朝.历史与现实:阿拉善盟的汉族与蒙古族——阿拉善盟民族关系调查[J].西北民族研究,1995(1).
[5]杨庭硕,吕永锋.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A].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6]刘学敏.西北地区生态移民的效果与问题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2002(4):47-52.
[7]柴海亮,惠小勇.草原何日不再呻吟——内蒙古西部草原生态见闻与反思[J].瞭望新闻周刊,2002(2).
お[责任编辑:罗康智]
Control of Desertification: A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Policy in Alashan Area
XIA Xun-xia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u Yat-sen University, Zhongshan,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sever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of Alashan, Inner Mongolia, is due to various reasons, among which macro-regulation dysfunction and immoderate exploitation by the market econom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e local government, not fully accounting for these reasons in the current migration policy, introduces farming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nomadic mode. Such substitution cannot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ultimately but will bring worse ecological crises instead: the continental climate of extreme drought cannot sustain water resource necessary for irrigation farming far beyond the nomadic style; the excessive exploitation of groundwater can lead to rapid decline of groundwater level, causing irreparable absolute drought, saliniz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It will be the most effective, though most difficult as well, to redistribute the water resources of the Heihe River Basin in a rational way under macro-regulation control so as to make best use of the limited water. A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restor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Alashan, the ecological views and ethics in Mongolian nomadic civilizations as well a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traditional nomadic lifestyle are most suitable to rebalance and renew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for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 of the area.
Key words:
ecological migration; control of desertification; Alas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