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幕府到书院看乾嘉汉学大吏阮元的尴尬与无奈
刁美林 邵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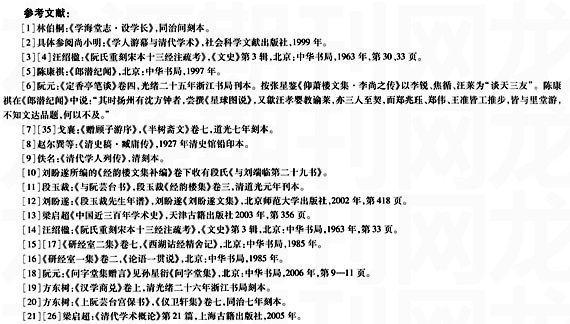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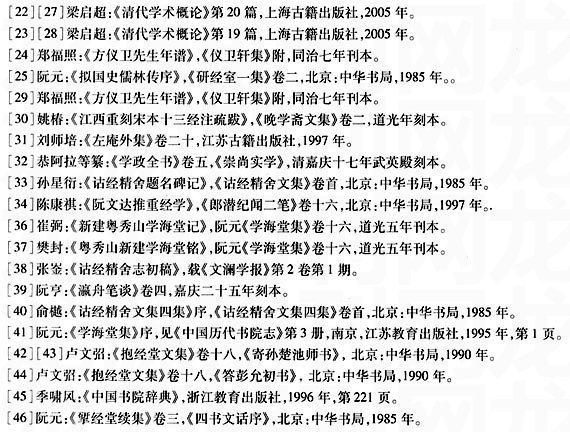
内容提要:阮元是乾嘉汉学的领袖人物。他组织起清代最大的学术幕府,创办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开展声势浩大的学术活动,成绩卓著。然而在与幕宾相处、主持学术研究、领导学术流向、创办书院进行教育改革及实践的过程当中,阮元也有着鲜为人知的尴尬与无奈。这是整个清代学术及士人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阮元幕府诂经精舍学海堂汉学宋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1-65-70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曾任山东、浙江学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嘉庆四年会试的主考官,浙江、江西、河南三省巡抚,漕运、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晚年拜体仁阁大学士,晋太傅衔,是清乾、嘉、道“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他不仅在仕途上为自己赢得了显赫的地位,而且在和扬州学派的汪中、焦循及皖派戴震的嫡传弟子王念孙、任大椿等人的交往中,逐渐成为一位经学大师。他延揽名儒,建立起清代最大的学术幕府,研讨学术,编纂典籍,成就斐然。他还利用自身的地位和名望,通过创办研习汉学的专门机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以期通过“专勉实学”达到“以励品学”和尊经崇汉的宗旨,成为中国书院史上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学术领袖和仕途一帆风顺的封疆大吏,也有其鲜为人注意的学术尴尬与无奈的一面。这些尴尬与无奈,不止阮元本人所独有。作为乾嘉汉学的殿军,阮元的学术困境正是那个時期绝大多数学人状态的流露和表白,也是乾嘉学术逶迤前进的真实写照。
一、礼贤下士然难免有隙
阮元是有清一代赞助奖掖学者而享誉后世的学者型官员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这既表现在阮元幕府规模空前,又表现在阮元及其幕宾的学术活动带有极宏大的气象,是清代其他以赞助学术而闻名的学者型官员所无法比拟的。阮元学术幕府中学人幕宾达到120多位。这些学人幕宾有从事编书、校书一类工作的汉学家;有诗人类的幕宾,他们主要与阮元及其他幕宾进行诗歌唱和,调剂幕府生活;有协助阮元处理政事的幕宾,使幕府的学术活动能够正常进行。这三类幕宾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然而,阮元虽然身为幕主,在整个幕府的学术活动当中处于中心位置,却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事。最能反映阮元身处尴尬境地的例子当属《十三经注疏》的校勘了。顾广圻于嘉庆六年应阮元之邀至杭州“十三经局”,不久便与主定《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段玉裁发生争执,酿成轩然大波。段玉裁认为注疏合刻于北宋之季,顾广圻则认为始于南宋。两人辩驳,“自此二氏交恶,终身不解。”作为发起人的阮元很为难,“从顾则茂堂实为前辈,袒段则义有未安。是以迟至二十年段氏殁后,始行肇工。”嘉庆二十二年南昌学堂重刊《宋本十三经》始成。晚了整整十四年。本属学术范围的争论,结果导致二人关系破裂。这一结果反过来影响到《十三经注疏》的重刊。需要强调的是,阮元早已于嘉庆十九年来到江西巡抚任上,若非当時江西盐运道胡稷、贡生卢宣旬及前给事中黄中杰等人支持以及南昌知府张敦仁和九江、广信二府知府,南昌、新建、都阳、浮梁、广丰、会昌等县知县及一些绅士出资相助,重刊《宋本十三经》今天能否见到都是问题。
不仅是幕宾之间的分歧,主宾之间的矛盾也让阮元感到很为难。段玉裁是雍正十三年乙卯生人,年长阮元二十九岁,阮元对其非常尊重。《十三经注疏》实行分任纂辑,是一项多人合作而成的学术成果。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之《阮刻十三经校勘记》中记载:“《易》、《榖梁》、《孟子》属元和李锐,《书》、《仪礼》属德清徐养原,《诗》属元和顾广圻,《周礼》、《公羊》、《尔雅》属武进臧庸,《礼记》属临海洪震煊,《春秋左传》、《孝经》属钱唐严杰,《论语》属仁和孙同元。”李锐,精通历算学,阮元说他“深于天文算数,江以南第一人也”,与焦循、凌廷堪号称“谈天三友”。徐养原,自幼从师于名流学者,探究学术源流,对经学、小学、历算、舆地、氏族、音律均有研究。顾广圻,《清史稿》说他“天资过人,经、史、训诂、天算、舆地靡不贯通,至于目录之学,尤为专门”,他是乾嘉年间惟一能与卢文弨相提并论的校雠名家,他的好友戈襄云其“性刚果,故出语恒忤触人”。臧庸“沉默朴厚,学术精审”。洪震煊被阮元称之日:“齐侍郎后,不图复见洪生也!”这么多学富五车之士,阮元唯独任命段玉裁“主其事”,也就是相当于现在说的“执行主编”,足见阮元对他的倚重和信任。
可段玉裁对阮元还是有意见。嘉庆九年,段氏致函王念孙云:“弟七十余耳,乃昏如八九十者,不能读书。惟恨前此之年,为人作嫁衣,而不自作,致此時拙著不能成矣。所谓一个错也。”书信中所谓“为人作嫁衣”之事,当指他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过程中,承担了实际负责人的工作,为主纂阮元“作嫁衣”,而“拙著”是指《说文解字注》。他曾提到:“弟衰迈之至。《说文》(即《说文解字注》)尚缺十卷。去年春病甚,作书请王伯申踵完。伯申杳无回书。今年一年,《说文》仅成三页。故虽阮公盛意而辞不敷文。初心欲看完《注疏考证》,自顾精力万万不能。近日亦荐顾千里、徐心田养原两君而辞之。”由此可见,段氏之所以对阮元流露出不满之意,应当是因为主持《十三经校勘记》而耽误了《说文解字注》的撰写。这确实也是事实。
问题不仅止于此。段氏自身的品行和秉性也是两人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段氏在音韵、训诂、经学、小学等多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自视甚高。他曾言:“玉裁昔年深究古文辞之旨,为端临知我耳。”还在《与刘端临第十七书》中狂言:“弟于学问深有所见……吾辈数人死后,将来虽有刻《十三经》者,恐不能精矣。”自负之情,溢于言表。他认为,阮元的水平不如自己,重刊《十三经》的“总纂”一职理应由自己来担当,仅为一“主其事”,实在是委屈自己。
段氏还非常顽固。最著名的例子是《直隶河渠书》的作者署名问题,这是历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段的恩师戴震曾客于直隶总督方观承幕,继赵一清、余萧客之后参与撰写《直隶河渠书》。稿未成而方殁。后为“无赖子”,即吴江捐纳通判王履泰所得,删改之后易名,也就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畿辅安澜志》。关于此书的真实作者,后来发生了争论。由于赵一清先于戴震人幕,且在幕時间比戴长,成稿是戴的一倍还多,所以有戴窃赵之议。段玉裁为文辩之,在《经韵楼集》中定此书系“赵为草创而戴为删定”。其意在夸大其师编撰之功,难以服人。为尊者讳且不惜为之曲的学术诟病暴露无遗。
由是观之,段玉裁是一个恃才傲物且秉性顽固之人。阮元虽对段玉裁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和信任,对他的学问也给予高度的评价,但他们之间还是免不了有罅隙存在。这让阮元很为难。因为,在清代幕府中,宾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所谓“合则留,不合则去”,是主宾之间相处的原则。如果幕宾一旦因不合而拂袖离去,对幕主来说是相当难堪的事,往往会影响其在士林中的地位和形象。上面所提戴震曾客方观承幕,方殁后,杨廷璋继任直隶总督,戴由于杨不礼贤下士,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杨在士林中的威望受到不小影响。因此,对于段氏对自己的怨愤,阮元只能隐忍之。上述《宋本十三经注疏》“迟至(嘉庆)二十年段氏殁后,始
行肇工”便是有力证明。
需要说明的是,阮元和段玉裁之间也并不是积怨甚深。两人交往的过程中,恩是主要的,怨是次要的。段与阮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否则,段也没有必要非得留在阮幕那么多年。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時实际担任主编的重要功绩,但也不能因而否认阮元在其中“总纂”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组织之功。
二、从扬汉抑宋到调和汉宋
所谓“汉学”、“宋学”,是清代学者习用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概念和学术取向。前者在理论上崇尚东汉的古文经学,治学方式提倡“实事求是”取证,特重汉儒经注。作为学术流派,它萌于明清之际,盛于乾、嘉,衰于道、成。后者奉程朱为宗,尤其是朱熹个人的学说,其最大特点是以主观意愿诠释儒家经典,使经学理学化,专主空谈心性,轻考证。
阮元从一开始是主张扬汉抑宋的,他是继惠栋、戴震之后出现的扬州学派的重要学者、乾嘉学派的殿军。作为清代汉学的代表人物,阮元大力推阐汉学治学宗旨:“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有志于圣贤之经,惟汉人之诂多得其实,去古近也。汉许(许慎)、郑(郑玄)集汉诂之成者也。……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经诂,况圣贤之道乎?”并特别强调:“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也。就圣贤之言而训之,或有误焉,圣贤之道亦误矣”,所谓“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经诂,况圣贤之道乎”?是说要寻求圣贤之道和经书义理,就必须通过文字、音韵、训诂,舍此别无他径。他走的是戴震一派以古训求义理的路子。
阮元的汉学立场時有表露。比如《问字堂集》序中,阮元即尊崇汉儒而贬低宋人,“以元鄙见,兄所作骈俪文,并当刊入,勿使后人谓贾、许无文章,庾、徐无实学也……《原性篇》言性本天道阴阳五行,此实周、汉以来之确论,而非太极图之阴阳五行也。引证一切,精确之极,足持韩、孟之平。宋人最鄙气质之性,若无气质血气,则是鬼非人矣,此性何所附丽?汉人言性与五常,皆分合五藏,极确,似宜加阐明之”,“惟是求仙采药,致坏封禅二字名目尔,光武尚可,唐玄宗、宋真宗等,仍是汉武故智,以致宋、元以来,目光如豆之儒,启口即詈封禅,是岂知司马子长、司马相如之学者哉”。阮元不仅自己坚持汉学立场,而且积极推广这种学术:“以经注经,此为汉学之先河,六艺指归”。曾入阮府作为幕僚的方东树就批评阮元“徒以门户之私与宋儒为难”。
然而,自嘉、道時起,汉学由鼎盛走向衰落。这是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考据学家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国家景运昌明,通儒辈出。自群经诸史外,天文、历算、舆地、小学,靡不该综,载籍钩索微沉,既博且精,超越前古,至矣,盛矣,蔑以加矣。”到嘉、道之际,汉学研究已无多大的发展余地,“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的汉学一统局面,已难以再现。正如梁启超云:“考证学之研究方法虽甚精善,其研究范围却甚拘迂。就中成绩最高者,惟训诂一科;然经数大师发明略尽,所余者不过糟粕。”换句话说,嘉、道時期已经到了对百余年来的汉学研究进行全面清理、总结的時期。而当時能够担当此项重任的非阮元莫属。最能体现阮元此時学术观点有所变化的是他在幕宾江藩与方东树之争中所持的态度。
江藩与方东树,历来被视为嘉、道之际汉、宋之争的代表人物。江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系统地总结了清代汉学发展的历史及研究成果,对宋学的贬抑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方所著《汉学商兑》则“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耐人寻味的是,江、方都久客汉学家的领袖阮元幕下,而且他们之间的争论,就发生在他们客阮元幕府期间,这就使争论更加引人瞩目。
作为幕主,阮元在这场争论中的态度很值得注意。方东树上书于他,他并没有给予答复。方东树的弟子郑福照说:“阮文达公初与先生论学不合,晚年乃致书称先生经术文章信今传后。”其实,阮元在结交方东树之前,其学术思想中已有折中汉、宋的趋势,主张“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所谓阮元初与方东树“论学不合”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方东树对汉学的攻击既然有合理的因素,这就不能不引起论学主张实事求是的阮元的注意。但是,由于方东树对汉学的攻击过于猛烈,以至于《汉学商兑》“意气排轧之处固甚多,而切中当時流弊者抑亦不少;然正统派诸贤莫之能受”。而汉、宋兼采在当時还“只是一种强有力的潜流”,并未形成风气,这就使作为汉学家领袖的阮元很难对方东树的观点公开表示赞同,因为“在本派中有异军突起,而本派之命运,遂根本摇动。”事实上,阮元虽没有对《汉学商兑》公开表示看法,但他将江藩与方东树二人长期留居幕下,直至道光六年他调任云贵总督,二人方才辞别,这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说明嘉、道之际汉、宋合流的趋势已开始出现。
阮元晚年,汉、宋兼采形成风气,阮元不必再有所顾忌,所以他著《性命古训》,“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并“致书称先生(方东树)经术文章信今传后。”当然,阮元毕竟来自汉学家阵营,即使主张汉、宋折中,也免不了对汉学有所偏袒:“稍欲调和两家说,然其意护前总不能自克,凡载诸文字者略可考见”。他还资助江藩刻印了《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三种著作。阮元的这种态度与来自宋学家阵营的方东树主张汉、宋兼采,却又免不了对宋学有所袒护,是同样的道理。
以科举正途入仕的阮元不满于汉学家的门户之见,主张调和汉、宋之争。一方面,是因为清廷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哲学;另一方面,汉学末流日益脱离现实而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最重要的是,终身致力于学术研究的阮元发现,门户之见对学术的交流与发展极为不利。强调门户,拘守一隅,自设藩篱,甚至党同伐异,这严重影响了学术的交流与发展。而阮元则主张“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正是汉、宋学兼宗的治学态度,以及与前辈师长及同辈友朋之间的砥砺与切磋,使得阮元的学问具有兼收并蓄、恢弘博大的气象。
实际上,汉学与宋学两者不可偏废,并非阮元首创,早在乾隆初年就已有此提法。乾隆五年上谕说“今之说经者,间或援引汉唐笺疏之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因不可废,而经术之精微,必得以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而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就个人的学术倾向而言,阮元无疑是扬汉抑宋的。其调和汉、宋的学术主张将自己推到了清代两个最大学术流派之间的争端当中。我们在同情其学术境遇的同時,也不得不慨叹,阮元作为一位讲求实事求是治学态度的乾嘉学术大师的确当之无愧。后来的事实证明,阮元的这一做法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主张兼采汉、宋学的思想,对晚清学术界特别是以林伯桐、陈澧等为代表的岭南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虽“不弋科举”却“渐染俗学不能变”
清代的书院,经历了由禁止到控制的文化政策,加上朝廷大兴文字狱的影响,迫使书院改变了学术追
求,一种与现实政治较远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考究经典的学风终于形成,即乾嘉考据之学。而当時清代的书院仍以理学为尊,以朱子为宗,以科举为业,讲求心性之学,不研究或传授汉学。因此,创办新式书院,给腐朽的教育注入新鲜活力,成为乾嘉学者的共同愿望。以阮元为代表的乾嘉汉学中坚创办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专课经史训诂之学,崇扬乾嘉汉学,成为乾嘉汉学研究、人才培养和传播的基地。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创建的目的是以经史实学去挽救书院坠落为科举附庸的流弊,意在返回传统,推古求新,重振书院事业。它们不仅使江浙及岭南地区形成了重汉学的学风,而且成为各地书院改革过程中仿效的楷模。
阮元于嘉庆二年任浙江学政時,在杭州孤山南麓构筑了五十间房舍,组织文人学子辑成了《经籍纂诂》这一规模宏大的古汉语训诂资料汇编。嘉庆六年,阮元奉调抚浙,遂将昔年纂籍之屋辟为书院,选拔两浙诸生好古嗜学者读书其中,颜其额日“诂经精舍”。同時又在西偏修建了第一楼,作为生徒游息之所。精舍地处风景秀美的西湖孤山之麓,它聘孙星衍、王昶等主讲,授“以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于是汉学大行。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说:
萧山毛西河、德清胡朏明所著书,初時鲜过问者。自阮文达来督浙学,为作序推重之,坊间遂多流传。時苏州书贾语人:“许氏《说文》贩脱,皆向浙江去矣。”文达闻之,谓幕中友人曰:“此好消息也。”
天文、算学、地理等长期居于传统学术视野边缘的科技内容,在这里得到了少有的重视,其中甚至还有一些西学内容,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罕见的,在当時大多数书院热衷于八股時艺的环境下显得尤为难得。它开启了清代书院培养真才实学之士、讲求经世致用之学的良好风气。
实际上,在办书院之前,阮元一直就重视西学。前述他的幕府当中的李锐,精通历算之学。阮元说他“深于天文算数,江以南第一人也”,与焦循、凌廷堪号称”谈天三友”。他做了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就是为《地球图说》补画地图和天文图。《地球图说》是钱大昕根据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献给乾隆皇帝的《坤舆全图》上的说明文字润色而成。首次在中国正确地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以及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天文学发现。
阮元任浙江学政、巡抚十余年,提倡汉学、奖掖人才。阮元幕府和诂经精舍培养了大批汉学家,洪震煊、洪颐煊、徐养源、严杰、周中孚、朱为弼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道光以后,汉学开始向广东等边远地区传播。阮元及其幕府对岭南学风的影响又是最大。学海堂的创立,成为阮元督粤時推广汉学的前沿阵地。
嘉庆末道光初,阮元总督两广,目睹“边省少所师承,制举之外,求其淹通诸经注疏及诸史传者,屈指可数”。于是仿诂经精舍之例,在广州城北粤秀山麓建立学海堂,“欲粤士无忘初志,学于古训而有获”。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突出“专勉实学”、崇尚汉学的宗旨,将科举之学完全排除在教学内容之外,“月率一课,只课经解史策、古今体诗,不八比文、八韵诗。”阮元之弟阮亨称诂经精舍“以励品学,非以弋科名”。孙星衍也称诂经精舍“不课举业,许各搜讨书传条对,不用扃试糊名法”。所谓“非以弋科名”、“不课举业”,并不是反对求取功名,而是认为学问和功名并不冲突,在治学中求取功名,顺理成章。不仅如此,诂经精舍还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程朱理学,孙星衍说:“(阮元)使学者知为学之要,在乎研求经义,而不在乎明心见性之空谈,月露风云之浮藻,期精舍之旧章,文达之雅意也。”学海堂的教学内容也是以经史考据为主。阮元要求生徒“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教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
阮元的书院改革获得了一些学者和官员的认同。之后的两广总督卢坤沿袭了他以经史考据课士的传统,将《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等书作为书院授课的主要教材。
然而,宋代以来书院与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的一体化的历史惯性使崇尚汉学的书院很难完全与理学绝缘。更何况在当時科举制度几乎是士人出仕的唯一途径,大多数士人已经从潜意识就信仰通过科举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他们亦不可能不潜心科举之学,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科举制度。况且,乾嘉汉学大师一般也是通过科举之学获得功名以后才专汉学的。因此,从书院发展的传统、科举取士制度所形成的社会背景都注定了反对科举制度、专门研习汉学书院的数量会相当少,并不能成为清代书院的主流。有些宣扬研习经史考据之学为主的书院亦不得不采取变通措施,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卢文招在主讲钟山书院時,愿意跟随他研习汉学的学生是寥寥无几,“在钟山几五载,幸有一二同志信而从焉”,这足能透露出跟随者少的窘境,他也不得不承认“渐染俗学已深者,始终不能变也”。出于教授这些“染俗学”者科举之学的需要,有時也“不得已而看時文,讲時文”。如湘水校经堂创办以后就对教学内容实行变通,即汉、宋并举,与诂经精舍、学海堂创办時反对程朱理学,要“奥衍总期探许郑,精微应并守朱张”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其实阮元对书院生徒从事举业也是有清醒认识和心理准备的,即在科举是士人仕进的主要途径的社会氛围下,根本无法让大多数士人抛弃八股文而完全沉醉于汉学之中去,他说:“上等之人,无论为何艺,皆归于正,下等之人,无论为何艺,亦归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书》文囿之,则聪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习,惟程朱之说,少壮所揣摩,皆道理之文,所以笃谨自守,潜移默化,有补于世道人心者甚多,胜于诗赋远矣。”这可能是阮元对书院讲求宋明理学、开展科举教育的清醒的认识,也是无可奈何的心理表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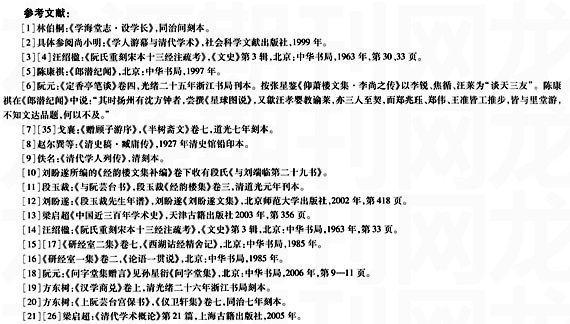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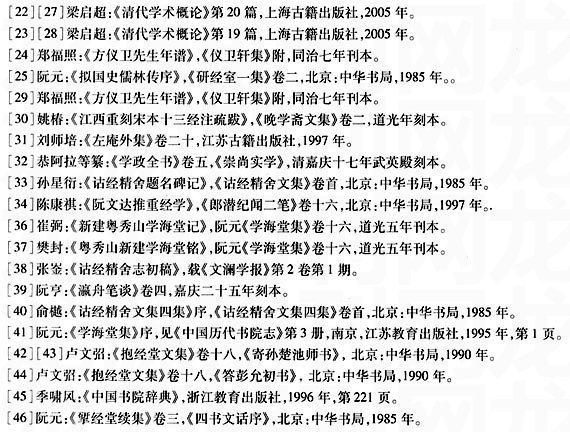
责任编辑林建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