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研究
林永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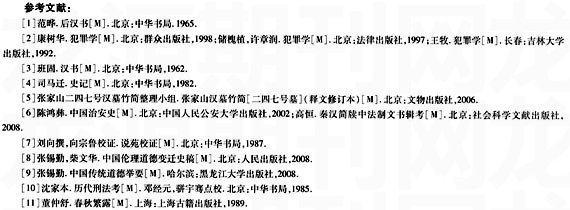
内容提要:道德与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倍受汉代统治阶级重视。在汉代道德与法律两者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其中在汉代道德观念中体现着深刻的法律思想,而在汉代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中同样体现着厚重的道德观念,而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汉代社会之中。而本文通过对汉代“劫质”案的考察就集中体现了笔者对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的一种诠释。
关键词:汉代劫质道德法律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1-9-13
就汉代“劫质”而言,其于政治、军事和刑事犯罪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然而发生在汉代政治、军事领域的“劫质”事件虽间或涉及汉代伦理道德评价之问题,但尚未发现依法制裁的成案记载,当然也存在不完全属于法律制裁范畴的因素。汉代刑事犯罪领域之“劫质”案件的行政处理却不乏其例,汉代“劫质”即今天所说的“劫持人质”,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是严重危害社会应受制裁(或应受处罚)的行为。笔者认为,仅凭汉代“劫质法”来看,汉代依“劫质法”处理“劫质”案不仅渗透着深刻的伦理道德因素,也深深蕴含着时代的法律思想,况且实际案例之内容一定也会更加丰富。因此,本文仅以刑事犯罪领域之“劫质”案件作为主要考察、论证之中心,并藉此以深入探讨汉代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道德与法律二者之关系。
笔者经过统计,在所有汉代的“劫持人质”的刑事犯罪案件中有的记载并不十分详细。内容不够具体是突出问题,既未明言是否以此勒索钱财,也未言明是否以此让官府投鼠忌器,以逃避官府的追捕。如《后汉书》载汉顺帝阳嘉三年“三月庚戌,益州盗贼劫质令长,杀列侯”。但是以下尚有二例“劫质”事件,可以说是颇具典型意义的“劫持人质”方面案例。其不仅属于汉代社会治安中的刑事犯罪案例,而且分属于汉代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笔者试逐次考察并以汉代道德和法律视角加以分析之。案例一源自《汉书》:
富人苏回为郎,二人劫之。有顷,广汉(京兆尹赵广汉)将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长安丞龚奢叩堂户晓贼,曰:“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二人惊愕,又素闻广汉名,即开户出,下堂叩头,广汉跪谢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狱,敕吏谨遏,给酒食。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给敛葬具,告语之,皆曰:“死无所恨!”
通过赵广汉的事迹考察可以知道,这个案件发生在汉宣帝时期。在此案发生前京兆尹赵广汉已处理过有史料记载的一起未遂类似案件,即“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舍谋共劫人,坐语未讫,广汉使吏捕治具服”。因此,就汉代刑事犯罪治安案件来讲,并根据现有史料来看,可初步得出,至迟在汉宣帝时期“劫质”案件已出现,而且汉宣帝时期发生的这个“劫质”案是汉代已知“劫质”类刑事犯罪案中最早的历史记录。就是说,笔者也并没有完全排除“劫质”刑事案件在此前汉代实际社会生活中还有存在的可能。
理由一、秦汉时期在政治军事领域早就出现过“劫质”事件。这些发生过的“劫质”事件源自于当时的社会实践生活之中,因此在汉代现实生活中犯罪分子为劫掠他人的钱财等目的必定会想方设法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不可能无闻于“劫质”之胁迫手段。
理由二、引文中赵广汉所言“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中的“释质”显然是当时久已熟识的司法用语。这为此前汉代出现过“劫质”案件又增加了一种可能。
理由三、西汉法律专门的“劫质”律令虽至今尚无发现,但西汉相关“劫人法”在反映汉初法律内容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中就有体现,即“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J69)”以及从此案件的终审判决为“至冬当出死”的结果来看,此“劫人法”也可适用于“劫质”案件。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劫质”与“劫人”在刑事犯罪行为中的主要犯罪目的和犯罪处罚上有相同之处,但是无论是从犯罪名称,还是在“求钱财”犯罪手段上看,两种犯罪行为显然并不相同。况且但就犯罪目的而言“劫质”行为也不会仅限于“求钱财”一种,挟持人质同行以保证安全逃窜也是一种目的。这就是说“劫质”与“劫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行为。
从道德和法律视角讲,此“劫质”案的处置不仅体现了赵广汉作为执法者的业务素质,也体现了他作为执法者的职业操守,乃至其道德水准。这是西汉时期处理比较好的一宗解救人质的典型案例,其比较充分体现出了人格魅力以及道德教化的力量和法律的震慑力及其严肃性二者的统一。
第一,“劫质”案发生后,负有社会治安责任的部门行政长官亲自出现场,且比较迅速,即“有顷,广汉将吏到家”。就本案讲,这与京兆尹赵广汉干练果断,特别是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有密切关系,即“广汉(汉宣帝时京兆尹赵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这也和赵广汉勤于研究、善于研究社会治安学并及时总结实践经验的职业才能不无关系,所以在关键重大社会治安案件发生后能够作出快速而有力的处置方案。为此,陈鸿彝先生、高恒先生对汉代地方官吏的诸多破案措施已有所总结。更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是赵广汉的职业操守。古人有所谓“食人食者死其事,受其禄者毕其能”之观念。张锡勤先生和柴文华先生认为:“在汉代,更多的人所以忠君,是出于‘食人食者死其事(《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第4192页)的传统观念(这也是中国古代臣子所以忠君的重要出发点之一)”。赵广汉坚决依法行政并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忠于君主的实际行动。正如有学者认为,即所谓“在帝制时代,居官尽心尽职乃是忠的表现”。
第二,京兆尹赵广汉做到了及时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具体处置方法也比较得当。在得知“劫质”犯罪嫌疑人有两名之后,赵广汉马上派长安丞向犯罪嫌疑人喊话,这最能体现赵广汉精明干练之处。为了不激化现场的矛盾,可谓是晓之以法理,动之以真情。首先是用平和而有礼节的语气向犯罪嫌疑人提出了“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的条件。另外,引文中有所交待之情况,即“富人苏回”之内容,据此初步推断本案的犯罪目的基本是为了钱财而非杀人,但由于犯罪分子被包围就使得杀害人质的可能性增加了。因此这个条件是得以继续谈判的基本前提。否则,如果杀害人质,况且人质还是“宿卫臣”,那犯罪嫌疑人肯定会被处死,而赵广汉等人的一切努力也将前功尽弃。于是赵广汉稳住了局面并避免了情况进一步恶化,这突出了法律的震慑力,也体现了法律本身的严肃性。接着赵广汉进一步提出“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对犯罪分子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笔者认为,这其中含义包括了一个承诺、两个结果。其中一个承诺:如果释放人质,犯罪嫌疑人起码会有“得善相遇”的照顾。两个结果:其一,劫持人质所构成的罪行是死罪,时人尽知,而文中隐去而未明言;其二,“幸逢赦令,或时解脱”,这对于生命来说毕竟是一线曙光,而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无疑也是一条可能的最好出路。在汉代得遇赦免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犯罪嫌疑人如果不是亡命之徒,见大势已去,一般是不会放弃这种侥幸逢生的机会。况且“又素闻广汉名”,就是说,
犯罪分子一向了解赵广汉的威名,并对他们一直产生着震撼性的力量。那么这个“名”到底是指什么呢?
《汉书》载,在昭帝时期,赵广汉“少为郡吏、州从事,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举茂材,平准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而在宣帝时,又“迁颍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广汉既至数月,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栗。”以致形成“一切治理,威名流闻,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闻广汉。”及“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唯广汉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已广为流传。
由此观之,赵广汉自进入仕途为吏以来,在治绩上可以说是治行优异,而其本人可以说是德才兼备,并且还体现出了他有着嫉恶如仇、忠于职守这样鲜明的道德观念。作为劫匪而言,深深震撼他们的恐怕不仅仅是赵广汉吏职之精,广汉忠勇的社会伦理道德之影响可能更具震撼力。就古代的教化手段而言,有礼乐之教、诗书之教以及所谓“神道设教”,充其量这仅属于道德教化的范畴。而赵广汉以法为教进行现场说法,法律的震慑作用在此时此地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道德教化的作用也仅仅是辅助。在生与死的对决、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在此法律最终成为阻遏犯罪行为发生的最后一道堤防,但这并非否认道德教化所具有的普遍而持久的影响力。在此“劫质”案的处理过程中,赵广汉一直坚持不懈地对劫匪进行说服教育,他几乎是以其京兆尹的人格担保,并许以“善相遇”的诺言。这些内容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这就是作为人际间的基本准则或规范的“诚”与“信”。正是由于赵广汉的诚恳劝说,才赢得了劫匪的信任,而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在进一步诠释着广汉本人曾许下的充满诚信的诺言,“送狱,敕吏谨遇,给酒食。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给敛葬具”即是明证,而被判死刑劫匪的“死无所恨”一语也似乎证明“信”这一传统伦理道德以此形式实现了它道德教化的完美社会作用。案例二源自《后汉书》:
(汉灵帝时)玄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玄不与。有顷,司隶校尉阳球率河南尹、洛阳令围守玄家。球等恐并杀其子,未欲迫之。玄嗔目呼曰:“奸人无状,玄岂以一予之命而纵国贼乎!”促令兵进。于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诣阙谢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诏书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这个“劫质”社会治安案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在这个资料中没有明确时间标志,但是根据桥玄在“光和元年,迁太尉。数月,复以疾罢,拜太中大夫,就医里舍”。又因为出“劫质”案现场的司隶校尉、河南尹、洛阳令等京官中有司隶校尉阳球,而阳球在光和二年为司隶校尉,而且在任司隶校尉当年便转任卫尉,冬十月甲申下狱死了,所以这既排除了阳球其他时间再任司隶校尉的可能,同时又无疑确立了此案件发生的时间在汉灵帝光和二年。至于是汉灵帝时期的什么具体时间?笔者认为应该在汉灵帝光和二年三月乙丑——五月。其中将光和二年五月作为下限是根据《后汉书》:
(光和二年)五月,卫尉刘宽为太尉。……冬十月甲申,司徒刘合永乐少府陈球、卫尉阳球、步兵校尉刘纳谋诛宦者,事泄,皆下狱死。
这就是说,汉灵帝光和二年5月卫尉刘宽官升太尉之后,基本可以断定司隶校尉阳球才得以升任卫尉。所以说此案一定发生在阳球升任卫尉的时间之前,即光和二年五月(包含五月若干日)之前。而以光和二年三月乙丑之后作为此“劫质”案发时间上限的根据有两点。其一、在汉灵帝光和元年十二月丁巳至光和二年三月乙丑期间,桥玄一直担任“掌四方兵事功课”的太尉。其工作和起居之地理应有较多军吏、卒担任较为严格的保卫工作,因此笔者认为此时不大可能发生“劫质”这样的事件。而光和二年三月乙丑之后桥玄又担任了太中大夫,他于是便有“就医里舍”之举。这对一个级别较高官员来说,其在缺乏足够警力保护的情况下到普通里舍居住肯定不会太安全。其二、从“玄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人舍登楼”来分析,基本断定桥玄住在居民区的里舍。于是这就可以断定“劫质”案发的地点就在居民里区中,而案发时间上限为光和二年三月乙丑之后。为此,笔者认为此汉代“劫质”案一定发生在汉灵帝光和二年3月乙丑——5月(包含五月若干日)之间的某个时段。
其次,从法律和道德两个角度综合分析,这确实是一宗极为不同寻常的‘劫质案。其特殊之处在于:其一,“劫质”案发生后,被劫质人的监护人的态度很特殊。当三个劫匪劫持桥玄的十岁小儿子向桥玄“求货”时,而“玄不与”,甚至放弃解救儿子的生命。这有悖于常人常理。其二,“劫质”案发生后,现场治安官员司隶校尉阳球的处理方法也比较耐人寻味。阳球在开始围捕劫匪时“恐并杀其(桥玄)子”,这是阳球最初的心理活动,但阳球最后为何又不顾桥玄小儿子的生死而果断下令进攻劫匪、以致造成“玄子亦死”的结果。那如何理解这种前后看似矛盾的行为?而阳球当时又是如何跨过这道心理和道德门槛的呢?
就前者而言,笔者认为,桥玄在幼子被劫持时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特殊的态度,是有一定历史和思想道德方面背景。《后汉书》载:
玄少为县功曹。时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国,玄谒景,因伏地言陈相羊昌罪恶,乞为部陈从事,穷案其奸。景壮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宾客,具考臧罪。昌素为大将军冀所厚,冀为驰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还檄不发,案之益急。昌坐槛车征,玄由是著名。……灵帝初,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迁司空,转司徒。……自度力无所用,乃称疾上疏,引众灾以自劾。
由此可知,桥玄年轻时就开始从政且屡受重用、屡蒙圣恩、一生为官。桥玄为官一方,他忠心报国、忠于职守,并且也是一位嫉恶如仇的官吏,直到晚年他仍然流露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拳拳报国之心。桥玄忠君忧国,处处以国事为重。应该说,桥玄是一个中国古代有着浓厚忠君思想的封建士大夫,是一个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忠实卫道士。因此,桥玄才会有“奸人无状,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之豪言壮语,也才会有请求下诏“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之慷慨陈词。同样是在汉灵帝时期,赵苞(辽西太守)曾极其痛苦地对其母亲说:“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为此有学者认为:“忠在东汉进一步强化,一个更重要的表现是,当忠孝不能两全、兼顾时,东汉人往往服从于忠。”这确实是东汉时期的一个现象。更何况“一子之命”又根本不可能与“其义不可以加”的最高德行“忠”和“孝”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因此其也就无从凌驾于代表君主或国家意志的法律之上。即使桥玄怜爱其幼子,但他在思想上也无法逾越当时“忠孝”高于一切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也就是说,忠君爱国之思想观念是与坚决支持并模范遵守或执行国家法律相一致,也是与破坏和践踏国家法律的犯罪分子和犯罪行为势不两立的一种态度。而本案中劫持桥玄之子为人质的劫匪被称为“国贼”已超出了家仇方面的表述,而分明是将其犯罪行为上升为危害国家、危害社会的高度。事实表明,就某个时代和社会而言,道德与法律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是一
致的,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因此法律体现着社会道德观念和思想,也守护着最低的道德底线,二者相辅相成。不过即使主流道德所体现或维护的观念也并非能置于当时法律完全保护之下,而法律最终或真正维护的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核心道德或价值观念。
就后者而言,司隶校尉阳球虽然最终选择了进攻劫匪之举,但在阳球处理此案过程中理智显然与情感存在过较量,而且在法律与道德层面的纠结对阳球的冲击显然也在所难免。分析如下:
一、司隶校尉阳球比较迅速地到达并包围‘劫质现场,处置得当。之后准备解救人质而没有马上实施断然抓捕,即“球等恐并杀其子,未欲迫之”。毫无疑问,这个举措属于情感和道德居于主导地位的阶段。然而“劫质”案情并未因此向有利方向发展,这对阳球来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作为京畿地区的最高专职治安官,阳球当然不会轻易被情感和道德观念所左右,他毕竟是法律的守护者和执行者。在此矛盾情形刚一发生之际,桥玄一席大义弃亲的慷慨之辞却使问题趋于简单化了,于是司隶校尉阳球也就不会因为不顾人质生命安全这一道德问题而进退失据了。此时此刻理智和法律观念开始处于主导地位。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如让劫匪走脱或劫匪目的得逞的话,阳球势必会被弹劾,甚至因失职以致罪。这是司隶校尉阳球不得不很好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引言中可以了解到,至少在东汉安帝之前的几朝期间曾颁布过“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之类的社会治安法令,否则,不会又有“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之说。而且据案例分析表明“劫质”的对象自安帝之后已经扩大到权贵阶层,“赎质”现象越来越普遍,从而直接导致京师社会治安法禁松弛的结果。即所谓“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从而说明安帝之前已明确‘劫质案属大案,而对“劫质”者可以攻杀之。而要想改变京师社会治安法禁松弛的局面,针对“劫质”案而言,就是拒绝“赎质”,拒绝与“劫质”者妥协而坚决依法办案。适用本案的汉代法律就是“凡有劫质,皆并杀之”,忠实地践行法律就是忠于职守,而忠于职守就是忠于汉朝的天子。表面上看,汉代法律在与汉代道德的抉择中取得了优势,但归根结底还是汉代道德领域中的终极问题,即“忠”之德在汉代整个统治思想中的核心地位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以汉代城乡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劫质”案件为中心进行相关历史学考证,同时对汉代典型“劫质”案例进行法律、道德层面的分析。宗旨在于,通过考察“劫质”案本身、相关的法律和当事人的言行从而深入探讨其中法律与道德两者的关系问题。汉代是我国法制建设承前启后的重要时代,同时也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基本确立的历史时期。毋庸置疑,汉代基本施行了德法相结合的治国理念与实践。也就是所谓“以霸王道杂之”。所探讨的汉代两个“劫质”案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因此某些特点值得关注。其一,西汉与东汉时期在处理“劫质”问题时主管官员均能依法办案,但是西汉的赵广汉在处理“劫质”案时的特点是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法治和德治的宣传和教化,而东汉的阳球在处理“劫质”案时缺失此教化环节。其二,西汉和东汉的法律针对劫持人质的劫匪的惩罚虽然均是处以死刑,但西汉时期经常进行的大赦也适用于劫匪,所以劫匪“释质”、“束手”之后还侥幸存在一线生机,这为道德教化留有一定余地,而东汉时期严厉的“劫质”法渐遭破坏,出现“赎质”现象。其三,在西汉和东汉时期的两个“劫质”案处理过程中,前者体现出较为朴素的“信义”之德,而后者则体现出“忠君”、“节义”等三纲思想的强化。总而言之,通过继续仔细深入考察,就一定会有值得期待的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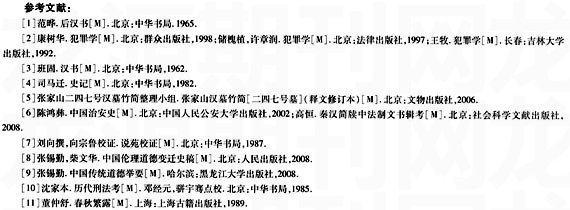
责任编辑林建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