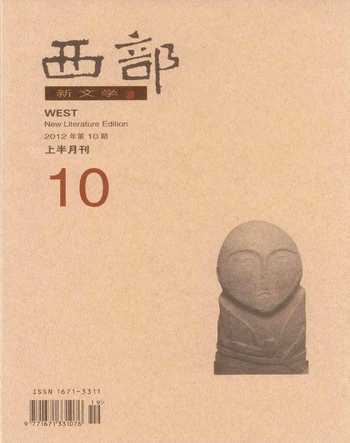“梭子之声”:集体创伤与个人化修辞
李海英
“创伤”经验或事件从精神分析学上来讲,是特指经历某些灾难性事件而使心灵和精神遭受强烈伤害和刺激,这种伤害和刺激能够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甚至是心理发展过程中驱赶不散的阴影。弗洛伊德就是如此定义的。他说:“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 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 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 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 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从二十世纪开始,弗洛伊德的科学研究像是一道谶语,不断地验证这一定义,创伤性事件从各个领域冲击过来,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环境、卫生、教育每一领域都不再给人安全感: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大屠杀、核爆炸、“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人体炸弹、Sars、大地震、海啸、金融危机……这些巨大的灾难如今几乎成为现代人不得不承领的“日常”经验。
但如何把一代人的集体创伤与个人创伤和历史事件恰当地连接起来,使其完成挤开历史门缝的作用,则需要作者根据写作的目标制定一个适当的叙事策略。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讲述的是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的一个角隅(甘肃省夹边沟农场)所发生的故事。边远省份中三千名的右派分子在全国五十多万名的右派分子作分母的比照下,其命运与人生的悲剧似乎很容易被局外人随手抹去,但杨显惠却通过让文本中的“他们”在回顾或讲述相同的创伤经验“饥饿”的无数次重复中,让我们的心灵与身体不停地受到击打。击打的力量既来自于叙述内容对伦理与人性底线的撕裂,也来自于作者看似无心实则精心安置的叙述人与话语方式的推动。下面我们就对此书中的说话人、说话方式与说的内容略作分析,希望能透过杨显惠先生所奋力挤开的“历史的门缝”,逼近历史的真相与人性的秘密。
一、谁在说:“我”还是“他”?
作者在选择叙述人时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夹边沟记事》一书由十九个独立的文本联袂而成,每个文本中都有一个讲述故事的主要人物,这些人物是作者千辛万苦从我们生活的不同角落里“挖掘”出来的。杨显惠说他采访了一百多个从夹边沟农场出来的右派才写成此书。“他们”看似和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在不大不小的地方有着不好不坏的工作,过着或艰辛或自足或安静的生活,所不同的是他们都有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曾经从夹边沟农场死里逃生。夹边沟的右派劳改农场的存活率大约是1:5 ,也就是送到夹边沟农场去的右派,五个里才有一个可以活着出来。因此可以说,这些今天能够讲述故事的人每一个都必须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出色的生存本领,才有机会对着作家讲述那并不遥远的往事。
故事中人物的叙述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第一人称的讲述方法,这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我”找一个替身,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别人的故事,如《上海女人》中是借一个名叫李文汉的右派来讲述一个来自上海的女人的故事;《邹永泉》中是“我”讲述同室的右派难友邹永泉不愿拿自己的浪琴手表与劳改队的管教干部交换馒头,后来因饥饿去吃蜥蜴,结果中毒而死的故事。《在列车上》也应属于此类叙述方式,只是这个故事比较复杂,是故事中套故事的多重人物参与的转述:“我”(文本当下的故事讲述者)与同事李科长一同出差,在列车上巧遇李科长曾经的夹边沟农场的右派难友魏长海(此时为列车长),于是李科长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他们(李科长与魏长海)在夹边沟农场经历的吃死人的事件,“我”又把这些转述给作者。另一种是让文本中的主体“我”讲述右派们“自身”的经历,如《李祥年的爱情故事》、《驿站长》、《憎恨月亮》、《夹农》、《这就好了》、《医生的回忆》。这些故事由当事人讲述自己被打成右派的经历,以及打成右派后身心的遭遇,在夹边沟劳改农场经受的或目睹的磨难与悲惨现实。这两种叙述虽然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在讲述,但不同的是前者是置身事外的冷静叙述(尽管叙述的事情无法让人冷静),后者从自身的记忆和经验出发重构的是对某一段历史的特定的解读和认识,掺和着叙述人记忆的修正与剪裁。
二是传统小说中的正统模式,即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如《走进夹边沟》、《贼骨头》、《坚持到底》、《探望王景超》、《自由的嘉峪关》、《一号病房》、《许霞山放羊》、《告别夹边沟》。这些故事中叙述者不出场,“我”隐退到幕后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文本中故事、人物、环境的主体性被突出出来,这些故事更像小说文本,看不到“我”指手划脚的影子。这种文本中,作者“我”的直接干预看起来最少,但由于叙述的内容是作者选定的,作者的价值判断反而会体现得更加充分。
三是仿访谈录。在《饱食一顿》、《逃亡》两个文本中,作者“我”与故事讲述者发生对话,并对其进行适时的引导和启发,但并不是真正的访谈录,因为及时的引导之后,“我”便从讲述者的话语中退出,并不实际干预故事的发展,其实还是“他”在讲述自己或他人的经历。
从上面简单的归类可以看出,“谁在说话”,其实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文本主体有时替自己发言有时是代他人说话,而作家也是这样,一会儿发出的是自己的评议,一会儿找个替代者让集体意识去说话。让“我”说还是让“他”说?或是让说话的声音时而替换时而交叉时而共响?选择是针对行文的需要,比如《李祥年的爱情故事》讲的是爱情故事,就让“李祥年”亲自出场,《在列车上》讲的是吃死人的事件,出于人之本性,当事人是讳莫如深的,那就让别人来转述,要让转述的东西可信,就让转述者以在场的身份来出场。
杨显惠选取说话人时的态度,类似于贝雷尔·兰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那种超过任何伦理和道德的事件所采取的态度,其反对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添加文学化的修辞来干扰叙述的可靠性。作者在《纳粹种族屠杀的行为和思想》说:“对一个在历史上具备非人性特征及挑战道德极限的主题来说, 任何个人化表述——或给它添加点什么——都显得既没有根据也缺少一致性: 没有根据是因为对象具有团体性质而它却使之个人化;缺少一致性是因为表述的对象否认了极限而它却设置了限度。” 这是提倡一种没有距离的直接表达,即让书写者处于事件中直接书写自己,而不是超然于所讲述的事件之外来讲述。他们强调的都是真实的力量,杨显惠曾说:“我的作品是用诚实的态度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但真实的故事是除了个别的故事写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虚构, 这十之八九又都隐约晃动着真人真事的影子, 虚构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实的细节。”
二、怎么说:“梭子之声”
和“谁在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怎么说”,说话的目的是为让人相信,讨论“怎样说”的时候则必然又要关联对谁说?在什么时间、地点说?从哪一个角度说话?保持一种什么距离和基调说话?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所以“怎么说”,首要之点是选择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说。针对相同的历史事件,就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同作家们会有着各自不同的叙述方式,有的会以亲历者的身份去思考人性在特殊的历史时刻所彰显出的诸多问题与样态,有的则会以非亲历者的身份通过右派们对苦难的集体记忆以及这些记忆对他们余生的影响来反思个人与历史与政治的关系,不同的关注点决定作家选择的语言方式的差异。比如《寻找家园》选择了一种零度的语言说,反思中国文人的深层的人格文化心理。《中国一九五七》选择了一个具有软弱和妥协性格的中间人物“周文祥”作为叙事和回忆的主体,并根据周的四个服刑地点采用四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强调的是个人在时代语境中的无助且无主的飘荡事实。《乌泥湖年谱》以年谱的形式展现了知识分子在1956—1966 年十年间的变化,探讨的是一代人从对生活充满激情到心灵委琐的心路历程。
而杨显惠,他要做的是把“一段惨烈的历史”记录下来,于是他采用“非虚构”的方式。配合这种方式的具体方法就是“采访”,采访除了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对话,还就是被采访者的思绪与情感被进入采访者所设定的某一历史语境中走向回忆的长廊,叙说回忆与往事。讲故事当然是一种“最便捷”也最实际的方式,比如《上海女人》的开头:“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讲故事的人叫李文汉,高中毕业,曾是解放军和志愿军,后来因为大资本家的出身被安排在甘肃省公安部作生产干事,1957年被定为右派。他讲述的是一个上海女人的故事,这个上海女人来到夹边沟是为了看望自己的丈夫董建义。董建义是李文汉所见到的唯一一个不吃脏东西的人。脏东西,是右派们从农场的草滩上搞到的黄茅草草籽、老鼠、蚯蚓、蜥蜴之类的用来充饥的东西。右派们基本上是能弄到什么吃什么,活命要紧,但作为医生的董建义认为那不是人吃的东西,坚决不吃,而只靠他的女人送来的一些食品和营养品维持生命,最后被饿死。董建义的行为已经足够让李文汉吃惊,而董建义妻子的行为对他的震动则更为强烈,她坚持着每两个月千里迢迢从上海来给丈夫送食物,但丈夫还是饿死了。女人在哭得死去活来之后,央求丈夫的室友(李文汉等人)带她去看坟。李文汉最初执意不去,并劝解上海女人也不要去,因为他清楚董建义是怎样被胡乱地埋掉的,但拗不过上海女人最终还是去了。找到的董建义的尸骨不仅暴露在黄土外,并且屁股蛋上的肉也被人偷挖走吃了。女人看过之后,坚持要把董建义带回上海,这无疑是更出人意料,从甘肃的夹边沟到上海要周转数次的汽车与火车,一个瘦小虚弱又极度悲伤的小女子怎么能把一个被禁运的尸体带走呢?但她却用她带去的所有“财产”换取“他人”(包括丈夫的室友与附近的农民)的帮助,把丈夫烧化和没烧化的骨头用毯子包着带走了。
这样一个凄惨的故事采用的却是一个冷静的开场白,这样的开头有如下特点:第一,说话者平静而淡然,人物本来是置身其内,但表述出来的是别人的事情,所以会有一种相对冷静的态度,由于创伤者对过去创伤性情景的强迫性回忆中常常充斥着记忆的变形与扭曲,有时还会以伪装的形式出现,局外人的叙述使文本具有更大的采信度。第二,说话人的平静和与己无关的态度,把作者和说话人的社会性评论隐藏起来,这种说话没有述评,没有描写,他的价值倾向与感情倾向渗透在他复述故事的过程之中。第三,局外人的身份可以把一段过于惨烈的人生经历和事件曲折地说出来。因为对于当事人来说,若要他们直接传达创伤(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期间的经验,而那些具有极大伤害性的往事(如上海女人所经历的丈夫曝骨于野的真相)在回顾中有可能会因为过多的痛苦而无法言说,但选择李文汉作为叙述人则可以在无法言说的条件之下发出 “梭子之声”。“梭子之声”这个短语来自以古希腊“阿特柔斯一家”的故事为基础的少女菲罗美拉被强奸后又被割掉舌头的故事。她遭受了双重创伤而无法向人们诉说,就织一条毯子来描写她的强奸,这样,“梭子”成了她代言的工具,“梭子之声”就是她的声音,毯子就是她的证词。哈特曼教授把这个形象看做“一种补救性的变形”,用它来隐喻创伤及表达创伤陷入无可言说境地时所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直接性的陈述会在一种极端的情绪爆裂中再次伤害自己,甚至“会再次受伤的,并不只是受害者、或是一个不愿被提醒的社会,还有我们这个种属的形象,以及我们的人性概念本身。”(谢琼:《从解构主义到创伤研究——杰弗里·哈特曼教授访谈》)
那些过于严酷的事实(如吃死人、吃呕吐物),那些当事人无法去回顾和言说的事实,就让“梭子”来代言。而那些没有冲破人的情感承受底线的行为(如偷东西),就让故事中的“我”来叙说回忆。在《夹边沟记事》中,不同的事件是被不同的说话方式说出来的,虽然表面看起来都是讲故事的形式,没有什么技巧,但略一琢磨,就会发现,其实配合故事细节的人物以及讲述的方式都是被精心设置的。
三、 说什么:饥饿合唱曲
接下来该是“说什么”。《夹边沟记事》说的主要内容是“饥饿”。但对饥饿的叙说,《夹边沟记事》不同于传统文学中由饥饿引发对制度的愤怒和仇恨。饥饿在杨显惠的小说中不是反抗或革命的理由或导火索,也不是红色经典小说里革命者用以磨炼意志的工具和手段。此外,饥饿也没有被升华为一种饥饿的美学或饥饿的艺术(像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或勒克莱齐奥的《饥饿间奏曲》)。
饥饿,在《夹边沟记事》里是作为本体意义上的由于食物的极度匮乏带来的生理体验来描写的。至于那些可能会与嘴和肚子的饥饿相伴随而产生的性饥饿、感情饥饿、爱情饥饿、知识饥饿、对于未来追寻的饥饿、精神的饥饿等等,通通都被简化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吃”的欲望,“吃”/“吃饱”成为所有欲望之首,也是唯一的欲望。饥饿,成为叙述的动力。在饮食欲的推动之下,一群人(被限定为知识分子的一群人)为了吃,不惜干出诸如监守自盗式的偷窃,杀猪偷羊烤肉吃、甚至是吃死人等一系列行为来。总之,能够吃,要不遗余力,因为吃是保证生存的基本条件。也因此让我们看到,在一个不宜居住与生活的戈壁滩上,一群知识分子是如何展开自己的奇思谋想施展寻找食物的“智慧”的: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就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没有营养,但是没有毒,吃它就能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有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
——《上海女人》
这或许是世界上绝地求生的代表,吃的过程要如此“精细”才能以免把自己“吃死”。但饥饿不仅教会了人特殊的求生意志与本领,也把人的饮食欲望扩张到了极端,偶尔有了一次饱食的机会,人们会把自己给“吃死”:
长期挨下饿的人,可有一顿吃饱的机会了,吃的时候连嚼都来不及,人人都是嚼两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咽呀,囫囵吞枣。吃呀吃呀,肚子吃饱了,但还是接着吃。……我们都吃得洋芋顶着嗓子眼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饱食一顿》
“长期”的挨饿,让人在有食物吃的时候就会丧失理智,还不止是像这里举的例子中几个人去拉土豆就把自己吃得胃痛呕吐,如《驿站长》中的右派王玉峰被一个旧交的县委书记“救”走以后,三天就把自己吃死了,因为他塞下了太多的牛肉和鸡蛋把肠子给挣断了。饥饿的创伤扭变为饕餮之欲望,即使没有了饥饿的威胁,他们也无法控制住自己对食物的“热爱”,如《贼骨头》中的俞兆远回到家中,每天晚上偷自己家的生面粉吃,不偷吃就睡不着觉。
饥饿,在“右派”们回忆的生活中,成为所有事情中唯一的事情,而导致饥饿的灾难性根源却被暂时性地遮蔽,没人去关注更没有人去追问导发事件的原因,最根本的东西在叙述人的叙述那里被搁置、不予追究,外在的后果成为要克服的核心——活下去,成为生命的最高目标。至于身体饥饿之外的屈辱、尊严、自由和情爱,也几乎全部由被饮食极端的缺乏而带来的极端的饮食欲望的膨胀所压倒。《夹边沟记事》十九个故事中,除了在《李祥年的爱情故事》与《夹农》两个故事中有描述男女情爱的追求之外,其他故事中,即使是很久没见的女人来看望自己,丈夫们关心的也多是女人胳膊上挎的篮筐,而不是女人。
这样选择叙述内容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作者选择的东西均是有代表性的,他通过具体的人与事布置出一个特定时空中普通人的现实命运之具体样态,通过故意不写某些东西或故意强化描写某些东西,使其具有隐喻意义,意图在于通过缺席去强化某些不便于说出的东西。这在《自由的嘉峪关》、《贼骨头》等故事中有很突出的表现。《自由的嘉峪关》中一帮右派被派往嘉峪关拾粪,他们依然吃不饱,干的也不是体面活,但是嘉峪关比起夹边沟农场则是一个自由幸福的天堂,他们不愿意回去。《贼骨头》中在惟妙惟肖地刻画做了贼的右派俞兆远诡计多端的偷盗技术的同时,还在不停地强化他的饥饿感与偷盗的欲望。但许多的事情被有意地遮掩了起来,夹边沟是怎样的一种不自由和痛苦,叙述人和作者都没有特意去交代,自由似乎也不重要,吃才是第一要事,不被饿死是他们最关心的。至于农场的仓廪是实或是空,并没有人去指证,叙述者告诉你的是,只要愿意偷,就能偷到,就能不被饿死。因此,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实际内涵,需要我们自己从平静的湖面下去探测。此外,作者依靠讲故事的方式试图让一个事件在许多人的勾画与言说中产生持之不断的力量,一种重复的力量。虽然每一个文本的叙述都是有选择的,但各个文本之间是互文的,它们既是一个微观的小社会,又构成一个并不微观的小社群,你想要发现的社会结构中的一切,都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缝隙中。
除了《夹边沟记事》,杨显惠的其他作品(如《定西孤儿院》)也在自觉地通过对个人记忆和经验的表述去思考我们民族所遭受到的一些集体创伤,在显现历史真实与政治事件的努力中探讨人性、人心的变化与坚守之秘密,这种自觉使我们在与创伤日益频繁接触以及对它进行理解的过程中,对历史也有了一种更多侧面的了解。这样的理解或许并不能帮助我们有效地减少创伤和创伤后遗症,但无论如何会逐渐培养一种相对坚定的态度,去抵御暴力对人类心灵或身体实施的奴役。或许这应当看做是杨显惠等作家们写作的另一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