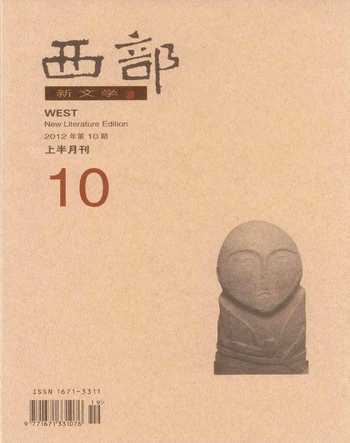写诗是我的天职
田原:回顾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准确地说,您步入诗坛是出于被动式的“被人劝诱”所致,而不是来自自我原始冲动的“自发性”。从现象学上看这是“被动式”的出发,但恰恰是这种偶然的诱发,使您走上写作的道路。从您受北川幸比古等诗人的影响开始写作,到您在丰多摩中学的校友会杂志《丰多摩》(1948年4月)复刊第二期上发表处女作《青蛙》,以及接着在同仁杂志《金平糖》(1948年11月)上发表两首均为八行的诗歌《钥匙》和《从白到黑》时为止,作为您还不满十七岁,那时,您是否已立志将来做一位诗人?或靠写诗鬻文为生?能简要地谈谈您当时的处境、理想和心境吗?
谷川:回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梦想和心境,我想对于谁都是比较困难的吧。在我有限的记忆中,我当时的梦想是:用自己制作的短波收音机收听欧洲的广播节目和有一天买一辆汽车开。至于心境,因为当时无论如何不想上学,所以,一想到将来如何不上大学还能生活下去,就会有些不安。
田原:从您作品的整体特点来看,您诗歌中饱满的音乐气质和洋溢着的哲理情思,都无不使人联想起您的家庭背景——父亲是出身于京都大学的著名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母亲是众议院议员长田桃藏的女儿,且又是谙熟乐谱会弹钢琴的大家闺秀(她也是您儿童时代钢琴的启蒙老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比起与您同时代一起在战争废墟上成长起来的、尤其是那些饱受过饥饿与严寒、居无定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诗人,您可以说是时代的幸运儿。尽管在1945年的东京大空袭之前您与母亲一起疏散到京都外婆家,之后返回东京时目睹了美国大空袭后的惨景,可是作为有过战争体验和在唯一的原子弹被害国成长起来的诗人,您似乎并没有刻意直接用自己的诗篇去抨击战争、讴歌和平。战后的日本现代诗人当中,有不少诗人的写作几乎是停留在战争痛苦的体验上,即战争的创伤成了他(她)们写作的宿命。我曾在论文里分析过您的这种现象,与其说这是对经验的逃避或“经验的转嫁”,莫如说是您把更大意义的思考——即对人性、生命、生存、环境和未来等等的思索投入到了自己的写作中,这既是对自我经验的一种超越,更是一种新的挑战,不知您是否认同我的观点?
谷川:我经历过1945年5月东京大空袭,疏散到京都是在其后。大空袭的翌晨,跟友人一起骑车到我家附近,在空袭后烧毁的废墟里,看到了横滚竖躺烧焦的尸体。尽管当时半带凑趣的心情,但那种体验肯定残留在我的意识之中。可是,与其说我不能用历史性和社会性的逻辑去思考这种体验(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不具备这种天赋),莫如说我接纳了人类这种生物身上实际存在的自古至今从未停止的互相争斗、互相残杀的一面。在这层意义上,你的观点也许是对的。但在我的内心并没有将其语言化为“既是对自我经验的一种超越,更是一种新的挑战”,这跟我个人缺乏历史感觉有直接关系。不过,顺便加一句,最近,我在报纸上偶然读到齐藤野(据说是高山樗牛的弟弟)以拉斯金、左拉、易卜生为例进行的阐述,“在他们面前不存在国家、社会和阶级,只有人生和人生的尊严”,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
田原:在您的写作生涯中,一位诗人的名字对于您应该永远是记忆犹新的。他就是把您的作品推荐到《文学界》(1950年12月号)发表的三好达治。这五首诗的发表,不仅使您一举成名,而且奠定了您在诗坛的地位。三好在您的处女诗集《二十亿光年的孤独》的序言里,称您是意外地来自远方的青年,他所说的“意外”和“远方的青年”即使在今天我相信不少读者对此仍有同感。“意外”无外乎是他没有预料到在战后的日本会有您这样的诗人诞生,“远方的青年”应是他对您诗歌文本的新鲜和陌生所发出的感慨。与中国诗人的成长环境不同的是,不但在战后,即使是现在,大多数日本诗人几乎都是团结在自己所属的同仁杂志的周围,他们的发表渠道也几乎都是通过自己的同仁杂志与仅有的读者见面。我曾查阅过1950年代以后创刊的同仁杂志,洋洋千余种,令人目不暇接。单是1950年一年内有记载的就有三十余种。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日本现代诗的文艺复兴期,产生了不少有分量的诗人。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时代为他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声音提供了机遇。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下,您的处女诗集在父亲的资助下以半自费的形式在创元社出版,请问当时看到自己新出版的诗集时,您是否已明确了自己以后的写作目标和野心?对于刚刚涉足诗坛的您来说,是否存在您无法超越的诗人?若有,他们是谁?
谷川:“写作目标”对于我是不存在的,是否有称得上“野心”的强烈希求也值得怀疑。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到了靠写作维生,因为除此之外我没别的才能。而且那时对诗坛这一概念也没有当真相信过,虽说也有敬畏的诗人,但我从没有过超越他们的想法。当时,我曾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独来独往的狼。因为那时对于我来说,比起诗歌写作,实际的生活才是我最为关心的事。例如,我曾把没有固定工作、靠写诗和写歌词、又翻译歌词和创作剧本维生的野上彰的生存方式,作为了一种人生理想。
田原:1953年7月,您成为刚创刊的同仁诗刊《■》的成员之一。这本同仁诗刊也是日本战后诗坛的重要支流之一,它的重要性完全可以跟崛起于战后日本诗坛的“荒地”和“列岛”两大诗歌流派相媲美。您作为这两大诗歌流派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三期”诗人群中的重要代表,迅速从战争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确立了自己独特的都市型诗风。当然,这跟那时日本社会受美国式的都市型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有关,生存的悲喜和不安以及伴随着它的精神龟裂是你们抒写的主题。我曾在您的书房翻阅过出版于不同年代的这本杂志,从每期不难看出,《■》是同仁轮流编辑出版的。但在翻阅中我发现,《■》好像停刊过很长时间,其原因是什么?另外,与其他形成了统一的创作理念、近似于意识形态化的同仁诗刊相比,《■》的存在更引人注目,它朴素、活泼、自由,而又富有活力。茨木则子的深沉,大冈信的睿知,川崎洋的幽默,吉野弘的智性,还有岸田衿子、中江俊夫、友竹辰等。您能否在此简要地谈谈《■》的各位同仁的诗歌特点,以及它在日本战后诗坛里的存在意义。
谷川:停刊是因为同仁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发表园地。再就是,我们同仁之间的关系因为比较散漫,不仅没有团结一致朝向相同的写作目标,而且还把各自意见的分歧作为了乐趣。至于各位同仁的诗歌特征和《■》在日本战后诗坛的存在意义,还是交给批评家们评说吧。
田原:1950年代,您先后出版了《二十亿光年的孤独》、《六十二首十四行诗》、《关于爱》、《绘本》、《爱的思想》等诗文集。这些诗文集里有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它们代表着您起步的一个高度。诗人中好像有两类:一类年少有为,一起步就会上升到须仰视才见的高度;另一类是大器晚成,起初的作品不足挂齿,但经过长久的磨练,诗越写越出色。很显然,您属于前者。我个人总是愿意执拗地认为,划时代性的大诗人多产生于前者,而且我还比较在意作为诗人出发时的早期作品,因为早期作品往往会向我们暗示出一位诗人在未来是否能够成为大器的可能性,或者说诗人的初期作品会反照出他以后的作品光泽。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天赋吧,天赋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神性,如果把这个词汇拆开也可理解为“上天的赋予”。一位诗人为诗天赋的优劣会决定他文本的质量和作为诗人的地位以及影响。当然,光凭先天的聪慧,缺乏积极的进取、体悟、阅读、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等都是很难抵达真正的诗歌殿堂的。但反过来,如果缺乏为诗的天分,只靠努力是否能成为大器也很值得怀疑。其实我们周围的大部分诗人多产生于后者,我不知道您是否也迷信“天赋”这一概念,若只思考该词本身,它的意义显得空洞乏味,不知道您是怎样理解天赋与诗人之间的关系的?
谷川:虽说我不清楚是来自于DNA(遗传基因)还是成长经历,抑或是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所致,但我认为是有适合诗歌写作的天分的。我创作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恍惚觉得诗歌写作说不定是我的“天职”,但同时,这种“天职”也促使我觉悟到作为适合诗歌写作者的其他缺陷。
田原:您从少年时代就跟着美国家教学英语,您也是我交往的日本诗人中英语说得最为流利和标准的一位,而且还翻译出版了三百多部图书。谙熟英语,是否对您的写作有直接影响?或者是否可以说英语拓宽了您母语的表现空间?活跃在当今国际诗坛上的希尼、加里·斯奈德,甚至作家米兰·昆德拉等,都是与您交往已久的朋友,您对他们的阅读是通过别人的翻译还是直接读他们的原文?另外,在与您交往的当代各国诗人当中,谁的作品给您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谷川:我英语并不熟练,口语也没那么流畅,所以我从未过分相信过自己的英语。我的英语翻译大都局限在平易的童谣和绘本。但是,亲近英语拓宽了我母语的表现空间确是事实(比如,通过翻译《英国古代童谣集》,我受到启发,创造了用假名表记的日语童谣的新形式)。我几乎没有阅读过原版的外国现代诗,交往的比较熟悉的外国诗人中,我多少受到了加里·斯奈德为诗为人的影响。
田原:您曾在随笔里称,1950年代的《六十二首十四行诗》是从您创作的百余首十四行诗中挑选出来的。1960年代初您接着又出版了另一部十四行诗集《旅》,这两部诗集在您的创作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十四行诗据说最初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之后流行于英、法、德等国。以格律严谨著称的抒情诗体对亚洲诗人而言永远都是舶来品。从您的十四行诗作来看,采用的大都是由两节四行诗和两节三行诗组成的形式,这应该是彼特拉克体的十四行,而不是以由三节四行和两行对句组成的莎士比亚体。但由于日语存在难以在韵脚上与十四行诗的要求达成一致的局限性,日语诗的十四行不得不放弃格律和韵脚,成了日本式的自由十四行。战前的福永武彦、立原道造等,战后的中村稔等诗人都有过此类诗的写作。诗人、批评家大冈信在为这本诗集的第六十二首撰写的解读文中称,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您都有着惊人的成果,他还把您的十四行比喻成“世界或者宇宙是保护和包容万物的庞大母胎,是将‘世界、‘我、‘人类介于同一化的幸福过程简洁地构图化的青春赞美和青春遗言” 。《旅》这本诗集分《旅》、《鸟羽》和《anonym》三个部分,我所掌握的资料中,这本诗集的论客似乎更多,吉增刚造、北川透、安水稔和、三浦雅士、法国图卢兹第二大学的Yves-Marie Allioux教授等都给予了很高评价,连小说家大江健三郎也曾在他的评论集《小说的方法》及小说里论述和引用过《鸟羽》里的诗句。《鸟羽》这组诗的写作应该是在1967年您结束了国内旅行回到东京的四月以后,因为我曾询问过这组诗的写作背景,您的回答是,把偕全家去三重县东部志摩半岛的鸟羽市旅行时的印象带回东京,在家完成了这组诗的写作。《旅》出版于1968年11月,在时间上完全吻合。请问,您当时写下大量十四行诗的动机是什么?这些系列的十四行诗的写作难道是您与青春的告别?
谷川:记得组诗《鸟羽》写于1966年到1967年我第一次在欧洲旅行八个月之前;《旅》是以旅行体验为素材写下的;组诗《anonym》的写作则在其后。就是说诗集《旅》是把长时间写下的作品归为一起,在1968年出版的。至于我选择十四行这种形式的动机,可以说是当时我的内心需要一种什么形式——即诗歌容器的缘故吧。我虽然写了很长时间的自由现代诗,但另一方面,“自由”也确有不好对付的一面。进行诗歌写作时,为自己定下暂时的形式能让自己写得更顺利。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审美意识。还有,在我写作十四行诗时脑子里并没有与自己“青春的告别”这样的念头。因为我是一个为脱离青春这一人生阶段而感到高兴的人。
田原:我在一本日文版的与中国文学有关的教科书里偶然发现过令尊与周作人、岛崎藤村、志贺直哉、菊池宽、佐藤春夫等人的合影照,后来也听您谈到过令尊与周作人、郁达夫等中国文人交往的逸事,而且令尊生前酷爱中国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数次访问过中国,并收藏了许多中国古代文物,尤其是唐宋陶瓷和古币等,不知您是否间接地受到过这方面的影响?我在翻译中发现,您的诗里多次出现“陶俑”这个意象,读后总觉得它是令尊收藏的那些中国古代“陶俑”的形象。这一点在您为第二本汉语版《谷川俊太郎诗选》撰写的前言《致中国读者》里有所言及,即您是从令尊在战前从中国购买来的微笑的宋代彩瓷娃娃感受中国的。中日在世界上是很有趣的两个国家,虽文化同源,又共同使用着汉字,但使用的语言在发音和词序以及语法等方面却完全不同。公元804年赴大唐长安留学的弘法大师把汉字和佛教带回了日本,他在《文镜秘府论》等著作中,对中国语文学和音韵学都有精辟记载。之后,《论语》、唐诗和大量的历史文献被大批遣唐使带回日本。直到明治维新,可以说汉文化一直在绝对支配着日本。明治维新前,精通汉文始终是贵族阶级的一个标志,老一辈作家、诗人中像夏目漱石、森鸥外、北原白秋等都写有一手漂亮的汉诗,可见汉文化对日本作家不仅影响至深,而且已化作了他们的血肉和灵魂。可是,由于维新之后的日本打开了封锁千年的国门,随着大量欧美文化的涌入,汉文化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华。对于您及更多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诗人来说,汉文化已不再是主要的写作资源,那么,您写作的主要资源是来自本土还是域外?
谷川:我父亲因为喜欢古董,收藏过一些唐代陶俑,尽管没有古币,但收藏过殷、周时代的玉。我诗歌中出现的“陶俑”不是出自中国,而是来自日本古代。现在手头上虽说没有这些陶俑了,但父亲生前收藏过的那些“陶俑”造型在不同方面给予过我影响。另外,我还属于是在中学学习汉文的一代人,所以,尽管发音不同,但中国古诗已经化作了我的血肉。我想,汉语语境与日语语境齐驱并进,在内心深处形成了我的精神。既然日语的平假名和片假名脱胎于汉语,既然我们如今仍然将汉字作为重要的表记方式,并还在用汉字表达许多抽象概念,那么中国文化乃日本文化的根源之一这种事实便谁也无法否认。
田原:诗歌的定义自古有之,我想每个诗人心目中对诗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概念。柏拉图曾把诗定义为“诗是天才恰遇灵机精神惝恍时的吐属,是心灵不朽之声,是良心之声”。白居易则在《与元九书》里称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庞德把诗歌说成是“半人半马的怪物”。郭沫若干脆把诗歌的概念公式化:“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如果用一段话来概括诗歌的话,您的诗歌定义是什么呢?
谷川:正因为对用简单的语言来定义诗歌不感兴趣,我才用各种方法创作诗歌。不是用简单的语言,而是通过编辑具体作品(主要对象是青少年)的诗选集《诗为何物》来尝试回答诗究竟为何物——即让诗歌自身来回答诗歌是什么。
田原:我总觉得一个诗人童年的生长环境和成长经验非常重要,会影响到他以后的创作。从您的随笔和创作年谱不难看到,童年的夏天您几乎是在父亲的别墅——周围有火山和湖泊的北轻井泽的森林里度过的。而且您在东京杉并区的宅第,也是被绿树和花草簇拥着的。您曾在随笔《树与诗》里谈到过,单是诗集《六十二首十四行诗》里,与树木有关的作品就有十六首之多,您笔下的树木没有具体的名称,而是作为“一种观念的树木”存在的。在这篇随笔里,您“觉得人类比树木更卑劣地生存着”。对于您,“树木的存在是永远持续着的一个启示”。我理解您对树木抱有的敬畏感。1970至1990年代,您还有过不少直接抒写树木的诗篇,大概有七八首之多吧,它们给我的印象大都是枝叶繁茂,有着顽强生命力和不畏惧强风暴雨的树木。有时从树木中反观人性,有时又从人类的生命中衬托出树木的本质。诗题有时使用汉字,有时使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这种对树木的钟爱一直未泯的创作激情,我想与您童年的成长背景密切相关。记得本世纪初在北京大学召开的《谷川俊太郎诗选》的首发式上,诗人西川在发言中曾谈到您的诗有一种“植物的味道”。他的嗅觉和敏感引起了我的注意。过后,我又翻看了一遍诗选,发现与树木有关的诗篇真的还占不小的比例,这是一个偶然的实例。这里,想请您回答的是:童年做为一个永恒的过去,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谷川:对于我来说,树木的意义超出了语言,它们可以说是作为超越了人们所想到的意义的“真”和“美”而存在的。我并不在意将其归纳为散文的形式。每天的生活中,我因为树木的存在而受到慰藉和鼓励,至于用诗歌的形式表现树木则是次要的。
田原:青春对于任何人都是宝贵的,它的宝贵在于其短暂。您第一次的婚姻生活始于1954年,结束于1955年,总共还不到一年时间。您这段短暂的情感经历我个人觉得在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的作品里打上了一定的烙印。之后,您又经历了两次婚变,三起三落的婚姻失败是否跟您是诗人的身份有关呢?
谷川:三次离婚各有其因。如果确切地将其语言化,理由当然在作为当事者的我这里。理由的一端不消说与我的个性有关。无法否认,这也与我作为诗人的“身份”(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表达)有关。这些是我一生在思考的问题。
田原:在您创作的两千余首诗歌中,请您列举出十首最能代表您创作水平的作品。
谷川:我不太理解代表“自己水平”这种说法,只举出我能一下子想到的吧:《二十亿光年的孤独》、《六十二首十四行诗》中的第六十二首、《河童》、《对苹果的执着》、《草坪》、《何处》、《去卖母亲》、《黄昏》、《再见》、《父亲的死》、《什么都不如女阴》等。
田原:在您出版的五十余部诗集里,您最满意的是哪些?您觉得哪几部诗集在您的创作风格上变化较为明显?
谷川:我虽然自我肯定,但并不自我满足。变化较为明显的应该是《语言游戏之歌》、《定义》、《日语目录》、《无聊之歌》、《裸体》等。
田原:您从年轻时代就写下了不少很有分量的散文体诗论,除出版有评论集《以语言为中心》外,还与批评家、诗人大冈信合著有《诗的诞生》、《批评的生理》、《在诗和世界之间》等理论和对话集,对现代诗直面的诗与语言、诗与传统、诗与批评、诗与思想以及诗歌翻译等问题都有涉及。这些深入诗歌本质的理论集在日本战后现代诗坛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这几部书中,您对现代诗独到的见解令人折服。尽管如此,您虽然跟那些“理论空白”的诗人不同,但我觉得还是没有写出系统性的诗歌理论,这是否跟您所说的不擅长写长文章有关呢?
谷川:的确跟我不擅长写长文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我对系统性的理论毫无兴趣。与其说去写理论,不如说我更想创作诗篇。这是我一贯的愿望。
田原:跨文体写作的诗人、小说家古今中外皆有,如荷尔德林、哈代、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博尔赫斯、卡佛等。若单说日本,我们首先会想到战前的岛崎藤村,以及战后的清冈卓行、富冈多惠子、高桥睦郎、松浦寿辉、小池昌代、平田俊子等。他们都是从诗歌创作出发,之后开始了小说创作,而且成就斐然。您年轻时尽管说过自己不写小说,实际上,您也写过一些中短篇。最为典型的是跟小说家高桥源一郎、平田俊子合著的《活着的日语》。这本书由你们仨每人创作的一首诗、一个剧本和一个短篇构成,既新鲜,又有趣。我想问您的是:不写小说是对自己的记忆力没有自信呢,还是诗歌更适合表达自己的生存经验?
谷川:刚才我已经回答我缺乏历史感,而且不擅长以“物语”的形式活着。在我看来,小说是讲故事的,故事属于历史的艺术,而诗歌则属于瞬间的艺术。就是说诗歌不是沿着时间展开的,而是把时间切成圆片。也许这种说法并不适合世界上所有的现代诗,而只适合拥有俳句和短歌传统、至今仍深藏“物哀”情结的日语诗歌,但至少我是写不出叙事诗的,而且,不是我选择不写小说,而是从生理上说我写不了。
田原:我一直顽固地认为真正的现代诗歌语言不是喧哗,而是沉默。我想起您年轻时写的随笔《沉默的周围》,“先是沉默,之后语言不期而遇”。我相信灵感型写作的诗人都会首肯这句话。“沉默”在您的初期作品中是频繁登场的一个词汇。正如诗人佐佐木干郎所指出的:“在意识到巨大的沉默时,诗仿佛用语言测试周围。”这种尖锐的解读让人深铭肺腑。现代诗和沉默看起来既像母子关系,又仿佛毫无干系。您认为现代诗中“沉默”的本质是什么?
谷川:沉默的本质可说是与信息、饶舌泛滥的这个喧嚣的时代相抗衡的、沉静且微妙的、经过洗炼的一种力量。我想,无论在任何时代,沉默,都是即使远离语言也有可能存在的广义上的诗意之源。也许亦可将之喻为禅宗中的“无”之境地。语言属于人类,而沉默属于宇宙。沉默中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田原:我曾把您和与您同年出生的大冈信称为日本战后诗坛的一对“孪生”。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的日本战后现代诗坛,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是你们俩在推动着1950至1980年代日本现代诗的发展。而且,某种意义上,是你们俩的作品,让世界广泛接纳了日本现代诗。您是怎么看待我所说的“孪生”呢?
谷川:诗坛是一个假想的概念,实际上每个诗人都是独立存在的。我想我与大冈信有许多共同点,但是我们完全相异的地方也不少。说我们是“孪生”可能有点牵强附会,以前我们俩并没有“推动诗坛发展”那样的政治构想,将来也不会有。我想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共通之处吧。
田原:数年前,关于您1980年出版的诗集《可口可乐教程》,我曾向被称为是日本现代诗“活着的历史”的思潮社社长小田久郎征询过意见,如我所料,他给予了很高评价。之后又看到北川透在他的新著《谷川俊太郎的诗世界》中盛赞其是“最优秀的诗集”。当然,还有不少学者发表和出版的学术论文。这本诗集确实是用与众不同的写法创作的,它发出了日本现代诗坛从未发出过的“声音”,也是您典型的具有尝试性的超现实主义写作。这本诗集跟您其他语言平易的诗歌作品相比,简直难以让人相信是出自同一诗人之手。在我看来,这仍是您一贯追求“变化”的结果。您自己是否认为这本诗集已经抵达了变化的顶点?
谷川:变化是相对的,也没有所谓顶点之类的东西。在写作上,我是很容易喜新厌旧的人,喜欢尝试各种不同的写法,《可口可乐教程》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田原:发表于1991年3月号的《鸽子哟!》文艺杂志中的《给谷川俊太郎的九十三个提问》里,有一个把自己比喻为何种动物的提问,您的回答十分精彩,说自己是“吃纸的羊”。我想这也许跟您的写作以及您出生于羊年有关吧。我想知道的是:您是在陡峭的岩石上活蹦乱跳的羊,还是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温顺吃草的羊?理由又是什么?
谷川:我觉得两者都是,因为温顺和活泼都是自己的属性。
田原:音乐和诗歌的关系若用一句很诗意的话来表达,您如何表达?点到为止也可。作为一个现代诗写作者,您认为优秀诗歌的标准是什么?
谷川:音乐和诗歌,可说是……同母异父的两个孩子吧。我只能说优秀现代诗的标准在于:我读了或听过后,是否觉得它有趣。
田原: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觉得日本现代诗的整体印象是较为封闭的,而且想象力趋于贫困。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套在中国当下的现代诗上。沉溺和拘泥于“小我”的写法比比皆是,要不就是仅仅停留在对身体器官和日常经验以及狭隘的个人恩怨的陈述,琐碎、浅薄、乏味,缺乏暗示和文本的力度。一首诗在思想情感上没有对文本经验的展开是很难给人以开放感的,而且也很难让人感动。当然这跟一位诗人的世界观、语言感觉等综合能力有直接关系。您认为诗人必须作出何种努力才可以突破现代诗的封闭状态?
谷川:努力去发现自己心灵深处的他者。
田原:意大利诗人好像说过翻译是对诗歌的背叛,我亦有同感。严格说,现代诗的翻译是近乎不可能的。在我看来,在把一首现代诗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的同时,就已经构成了误译。理由是诗歌原文中的节奏、语感、韵律和只有读原文才能感受到的那种艺术气氛都丧失殆尽。生硬的直译,或者一味的教条式的译法,也是不足取的。这也是我始终强调的现代诗的译者必须在翻译过程中保持一定灵活性的原因所在,在忠于原著的前提下,同时在不犯忌和僭越原文文本意义的范围内,凭借自己的翻译伦理和价值判断来进行翻译是十分重要的。我个人一贯认为,把一首外国现代诗翻译成自己的母语时,准确的语言置换尽管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须让它在自己的母语中作为一首完美的现代诗成立。中国的翻译界,至今好像仍约定俗成地墨守着“神、形、韵”这样的诗歌翻译理念,还有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等,这些固然不错,但却很少有人强调在翻译过程中注入一些灵活性。“神”就是栩栩如生,“形”即形式,“韵”则是韵律和节奏。在一首诗的翻译中,天衣无缝地做到这三个要素也并非易事。在日本翻译界,您认为谁是最优秀的现代诗译者?
谷川:普列维尔的译者小笠原丰树,现代希腊诗的译者中井久夫。若不限于现代诗,我认为,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吉田健一也其中。
田原:“只有诗人才是母语的宠儿”,这是我最近写下的一句话。对于诗人而言,母语毋庸置疑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当然也有以母语以外的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家和诗人,但是以第二语言创作的作品大体上没受到好评亦属事实。四十五岁移居法国的昆德拉以法文创作的小说《慢》和《身份》好像也不太受人瞩目。西胁顺三郎也曾用英语写诗,但是那些英文诗并不如他的日文诗那样广受好评。里尔克和布罗茨基也是如此。甚至通晓几种语言的策兰也曾这么说过:“诗人只有用母语才能说出真理,用外语都是在撒谎。”还有刚过世的、在苏联长大、曾做过前苏联总统叶利钦翻译的随笔作家米原万里叶也表示:“外语学得再好,也不会超过母语。”策兰流露出了他对诗人冒犯母语行为所持的否定态度。最近我在用日语写作,常常感受到深陷于日语和母语之间的“对峙”之中,那种“冲撞”和“水火不容”的感觉有时候十分强烈,真切体会到诗人终究无法超越母语这一事实。您通晓英语,是否也想过用英语写作呢?
谷川:我虽然从没想过用日语以外的语言进行诗歌写作,但对视母语为绝对的母语主义者也持有怀疑态度。我们不可轻视利比英雄、多和田叶子、亚瑟·比纳多等人为何不以母语写作的理由。
田原:如果可以自己比喻为草原、沙漠、河流、大海、荒原、森林或天空,您认为自己是什么?为什么呢?
谷川:打个比方说,一切都存在于我自身之中。
田原:请告诉我您对外星人持有何种印象?如果能够宇宙旅行,您想到哪个星球看看?或者想在哪个星球上居住?
谷川:因为我觉得地球以外的生物有可能是以多种形态存在的,所以无法归纳为一种印象。还有,我也没有想到宇宙旅行的心情。
田原:我总觉得您创作的源泉之一来自女性。在您半个多世纪创作的五十多部诗集中,与女性有关的作品为数不少。单是诗集就有1991年出版的《致女人》和1996年的《温柔并不是爱》。纵观您的初期作品,1955年的《关于爱》、1960年的《绘本》、1962年的《给你》、1984年的《信》和《日语目录》、1988年的《忧郁顺流而下》、1991年的《关于赠诗》、1995年的《与其说雪白》等诗集中都有与女性有关的作品。其中《缓慢的视线》和《我的女性论》这两首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诗中的登场者有母亲、妻子、女儿、恋人、少女等。这样看来,也许可以说女性是贯穿您作品主题的元素之一。以前,我曾半开玩笑地问过您:“‘名誉、权力、金钱、女人、诗歌当中,对您最重要的是什么?”您的回答让我深感意外,因为您选择的第一和第二都是“女人”,之后的第三才是“诗歌”。在此,我要重新问您,“女性”对于您是什么样的存在?是否没有了女性就无法活下去?您这么看重女性,能否告诉我您现在沦为“独身老人”的心境?
谷川:女性对我来说是生命的源泉,是给予我生存力量的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我最不好对付的他者。我凭依女性而不断地发现自我,更新自我。没有女性的生活于我是无法想象的。但我不认为婚姻制度中与女性一起生活下去是唯一的选择。也许正因为我重视女性,才选择了现在的独身老人生活吧。
田原:在世界的伟大诗人当中创作长诗的为数不少,至今您创作的作品中,最长的诗歌大概有五百多行吧。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在日本就有■川信夫未完成的《美国》、入泽康夫的《我的出云 我的镇魂》、■井乔的《海神三部曲》、野村喜和夫的《街上一件衣服下面的彩虹是蛇》等长诗。您为何没创作长诗?是写不出,还是出于别的原因?
谷川:也许跟我认为日语基本上不适合用来写长诗有关,实际上也可能跟我不擅长叙述故事更适合诗歌写作的倾向有关。有人说“诗集不但要易读,而且须耐读”,我赞成这种说法。
田原:从您的整体作品来看,围绕“生存”这一主题的作品颇多。您在日本读者所熟悉的《给世界》一文里写道:“对我而言最根本的问题是活着与语言的关系。”这确实是现代诗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正像不少诗人无法从日常经验成功地转换到文本经验一样,过于倾向日常,很可能无法超越生活本身;反之,又容易沦落为知识先行的精英主义写作。您能否具体阐释一下“活着与语言的关系”?
谷川:在日常生活中,对家人和朋友说的语言和作为诗歌写出的语言的根源是相同的,但在表现上不得不把它们区分开来。现实生活中的语言尽可能表现出真实,我认为诗的语言基本上是虚构的。一首诗里的第一人称,不一定指的就是作者本人。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作者完全没把自己投射到作品当中。作者的人性隐藏在诗歌的“文体”之中。“文体”是一个很难被定义的词,它不仅包含着语言的意义,形象、音调、色彩、作者对语言的态度等,所有的要素都融为一体。在现实生活里,人与人的交流不只是特定的伙伴之间的语言,他们的动作、表情等非语言的东西也是非常具体地进行着的。至于化为文字、化为声音的诗,是一个作者与不特定的、复数的读者或听众之间更为抽象的交流。可是,作者本身的现实人际关系也投影到他下意识的领域。虽然“活着与语言的关系”在诗歌里极为复杂,可是,作者无法完全意识到它的复杂性。因为让诗歌诞生的不只是理性。这样想来,对文体进行探究进而牵连到作者这样的分析,其范围有限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想,可以这么说,以不完整的语言把无法完全被语言化的生之全部指示出来的就是诗歌。
田原:在您的全部创作中,《语言游戏之歌》系列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您本人也曾写过:“为探索并领悟到隐藏于日语音韵里的魅力而感到自负。”能够写出这一系列作品,我想大概是因为日语中包含有平假名、片假名、汉字和罗马字这四种表记文字——即日语文字有表记上的便利性。从肯定的角度想,这些作品拓宽了日本现代诗的表现空间,或许正因为此,使这类作品拥了不同年龄层的读者,这一创举可以说对日本现代诗作出了莫大的贡献。我想,这也许跟您“意识着读者去写作”的创作理念有关。可是,若从否定的角度看,您主张的“不重意义,只重韵律”的创作立场,是一种诗歌写作的“犯规”,或者说是分裂语言与意义的行为。一首意义空白的诗歌,再美丽的词藻和语句都是徒劳的,因为它是一个无内涵的艺术空壳。况且,您的这类作品因为“只重韵律”可以说完全无法被翻译成别的语言。关于这一点,您有何看法?
谷川:《语言游戏之歌》只不过是我创作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诗歌作品之一。在尝试写这些作品时,我所思考的主要是探索日语现代诗音韵复活的可能性,结果便产生了看似无聊的顺口溜、诙谐的童谣这类作品。有趣的是,反而是这类作品让我获得了更多的读者,但同时,我也知道了很明显这类作品在主题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它无法开创现代诗崭新的可能性。若以现代诗的价值标准来审视《语言游戏之歌》是有些难度的。可是我并不在乎,对以日语为母语的我而言,“无法被翻译”并非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因为我也写了许多其他可以被翻译的诗歌作品。
田原:自然性、洗炼、隐喻、抒情、韵律、直喻、晦涩、叙事性、节奏、感性、直觉、比喻、思想、想象力、象征、技术、暗示、无意识、文字、纯粹、力度、理性、透明、意识、讽刺、知识、哲学、逻辑、神秘性、平衡、对照、抽象这些词汇当中,请您依次选出对现代诗最为重要的五个词汇。
谷川:我想应该是无意识、直觉、意识、技术、平衡吧。但我不认为回答这样的问题会管用。
田原:迄今为止,您参加过无数次的“连诗”创作活动。这一活动始于大冈信,四五位诗人聚到一起,有事先命题的,也有自由随意的。“连诗”一般以十行以内的短诗为限,第一首写出后,接下来的诗人必须承继上一首中的一个词,然后在意义的表现上重新展开。这是是一种带有娱乐性的创作活动。 “连诗”活动对平时交流不多的日本现代诗人而言,是一个有趣和值得尝试的交流。另一方面,我觉得这种活动对诗歌写作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现代诗写作与集体行为无缘。对此您有什么想法?
谷川:诗歌是一个人写的,这个原则不会改变。可是,脱离与他者的联系,跟语言所持有的本质是矛盾的。大冈信一部名著的书名——《宴会与孤心》可谓一语中的。另外,对我来说“连诗”不单单停留在它所带来的乐趣上,它也有助于激发我的创作。举个例子,我自己比较偏爱的《去卖母亲》一诗,如果不是因为有“连诗”的伙伴、诗人正津勉的存在,恐怕是写不出来的。从他者得到的刺激会唤起意想不到的诗情。
田原:您是怎么处理现代诗的抒情与叙述、口语化与通俗化的?
谷川:我想在自己内心拥有这一切。
田原:贝多芬是音乐天才,毕加索是绘画天才,若说您是现代诗的天才,您会如何回答?
谷川:若是恋人那么说,我会把它看作是闺房私话而感到开心;若是媒体那么说,我觉得自己被贴上了标签,会感到不快;若是批评家那么说,我就想对他们说:“请给予我更热情的评论!”
田原:您在第二本汉语版《谷川俊太郎诗选》的前言《致中国读者》中写道:“……我从十七岁开始写诗,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是,时至今日,我仍然每每要为写下诗的第一行而束手无策。我常常不知道诗歌该如何开始,于是就什么也不去思考地让自己空空如也,然后直愣愣地静候缪斯的驾临。”这段话让我再一次确认到您是“灵感型诗人”,并为对您的这种命名而感到自负。实际上,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诗人几乎都出自这种类型。那么,我想问的是:灵感对于诗人为什么重要?
谷川:因为灵感在超越了理性的地方把诗人与世界、人类和宇宙连接在了一起。
田原:中国和日本常常举办一些诗歌朗诵活动,我也参加过不少次。但我总觉得现代诗更多的时候是在拒绝朗诵,其理由之一,我想应该跟诗歌忌讳声音破坏它的神秘感有关,尽管相对的有时候诗歌也渴望着被阅读。1996年,您曾透露想远离现代诗坛的心境,从此便开始积极进行诗歌朗诵活动。当然,并非您所有的作品都适合朗诵,基本上诗歌是从口传开始的,或者说它最初是从人类的嘴唇诞生的。这么看来,所有的现代诗都应该适合朗诵。但是,与重视韵律、音节、押韵、字数对等、对仗的古诗相比,现代诗几乎都不大注重外在的节奏和韵律,通常都是顺其自然的内在节奏。按照博尔赫斯的说法,必须在诗歌内部具备“听觉要素与无法估量的要素即各个单词的氛围” 。我觉得这跟诗歌朗诵有关。您认为朗诗歌诵活动是否能够解救现代诗所面临的读者越来越少的困境?为什么?
谷川:我想朗诵活动也许无法解救现代诗的困境。文字媒体和声音媒体是互补的。若没有好的诗歌文本,朗诵就会演变成浅薄无聊的语言娱乐游戏。至于那究竟是不是诗歌也就不再成为问题了。只是,现代诗的“困境”,不仅存在于写不出好诗这个层面,我们也能够从这个时代所谓的全球化文明的状态上找到相关理由。诗与非诗之间的界限日益暧昧,日渐浅薄的诗歌充斥着大街小巷。我们难以避免诗的“流行化”,即使是人数再少,我们也需要有与之抗衡去追求诗歌理想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