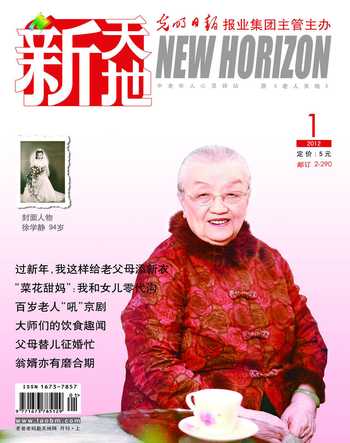父亲曾是民办教师
夏银龙
干惯粗活儿的父亲也曾当过民办教师,说起来那也算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父亲1974年高中毕业,在村里属于为数极少的高才生,因为所谓的成分问题,处处不得志,一直郁郁寡欢。与母亲结婚后,才在母亲娘家人的帮助下,在附近一所村小谋得了一份合同制民办教师的职业。
那时候,我的外公是一所村小的校长,叔伯舅舅也就是母亲的叔伯哥哥是乡里的小教助理。因了这层关系,父亲才谋得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职位。在村里人眼里,能当上教师,无疑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直至现在,乡邻们每每见到父亲,还尊称父亲为“先生”。
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民办教师的工资只有39.5元钱,但也意味着和普通农民不一样了。除了不用再去为种两亩薄田拼命了,还获得了村民们由衷的尊重。我6岁开始读书,没有进幼稚园,直接由父亲带着“升”到了小学一年级,也因此受益不浅。母亲时常绘声绘色讲起父亲带我上学的事儿,说我父亲太大意,大冬天骑自行车带我放学,一直到家都未能发现我脚上的鞋少了一只,害得我小脚冻得通红。
父亲属于生性豪爽之人,喜欢三朋四友,家中时常高朋满座。90年代初,因我家搬迁,父亲从一所小学调动到另一所小学。此后不久,大约是因为民办教师的种种无奈和尴尬,又无望成为公办教师,父亲竟自行脱离了民办教师队伍。为此,曾好意介绍他当民办教师的叔伯舅舅很是生气,一度对他不理不睬。
丢掉了民办教师饭碗后,父亲为供我读书,曾一连几年在县城里拉人力三轮车,一天收入微薄,仅够一家子勉强填饱肚皮,生活的艰辛自不必说。
倘若父亲当年运气好一点,转成了公办教师,或许现在的日子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母亲也常常奥脑地抱怨父亲,假如当年坚持下来,能转成公办教师,现在早已拿上了退休金,哪里还用这么大岁数去给别人打工看大门!我也曾问过父亲,不做民办教师,可曾后悔?父亲只是苦笑,没有作答。
近来我正在读刘醒龙先生所著的《天行者》,被对书中的几位民办教师主人公的际遇所触动,自然联想起父亲也曾经的教师生涯,不禁一阵心痛:在民办教师——这个中国农村的特殊人群中,有多少人像父亲他们一样,曾在育人的神圣感和窘迫的生活之间,经受过内心的苦苦挣扎宁
我懂得鬓发斑白的父亲在心底的懊悔和无奈。当年,父亲缺少的是希望。有希望,才有坚守。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