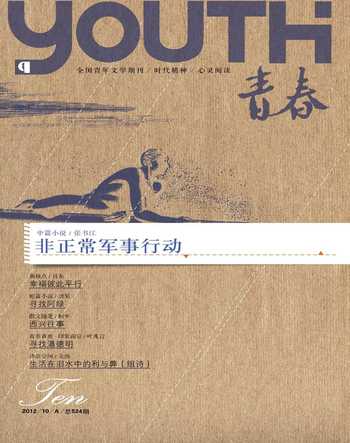男权下的女性宿命
李晓鸥
《妻妾成群》已被评论界无可争议地认定为苏童的代表作,且在当代文学历史化进程中渐成经典。这部小说的广泛影响力与张艺谋以此为蓝本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紧密相关。电影与小说都是自足的作品,它们之间必定存在着认同与疏离。藉此,笔者从《妻妾成群》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之间主题意蕴的疏离之处为切入点,对小说《妻妾成群》做一次文本细读。
一、男权制对女性的迫害——主旨或一个声部
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有一个鲜明的主旨:女性在男权制社会中,世代上演着悲剧命运。男权以利诱和暴力的形式统治着女性。一方面,陈佐千将女性当做玩物,以宠幸带给妻妾们权利和荣耀,使她们为此争斗却无人常胜;另一方面,陈府对企图退出争斗叛逃男权的女人们,用暴力处死。如颂莲所说,女人在陈府“像猫,像狗,像鱼,像老鼠,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除了与其他妻妾争宠,女人别无选择。
为了突出这一主旨,增强戏剧性,电影添加了两个小说中没有的情节。一是颂莲假怀孕的情节。假怀孕使颂莲从最高荣宠摔至妻妾的最底层,显出颂莲在院内斗争中的软弱、无奈,外强中干,并最终宣告颂莲斗法的彻底失败。此外,电影还加入了颂莲酒后失言害死梅珊的情节——一个雁儿不够,还要颂莲参与另一桩谋杀,突出女人在被害的同时也参与害人,这也为颂莲因梅珊之死而精神失常提供了合理解释。
可是细查小说,我们会发现不谙“后宫争斗”法则并非颂莲失宠的原因,男权对女性的迫害也非小说主旨的全部,而只是诸多意蕴和声中的一个声部。事实上,在小说中,颂莲在争宠中并非桀骜不驯、黔驴技穷;而颂莲精神失常也另有其因。小说情节铺展的动力和重点不是妻妾斗法,而是颂莲隐秘的精神世界的微妙变化。小说通过“死人井”的隐喻将这些细微的变化一一展露出来。
二、“死人井”——颂莲精神状态与小说情节的隐喻
总的来说,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以颂莲为一个视窗观察陈家大院,充分展现大院里每一个人,强调情节的戏剧性,外向性强;而小说《妻妾成群》则将颂莲嵌入陈家大院,在陈家的背景下挖掘颂莲本人的精神世界,内向性强。通过电影中“死人屋”与小说中“死人井”的对比,我们能更清晰地觉察出这种差异。
在电影中,“死人屋”好像一块磁铁,吸引着颂莲两次上前。第一次颂莲走近“死人屋”,不得进去;第二次她尾随押梅珊的人,亲自打开死人屋的门,看到梅珊的尸体,发出了疯狂地喊叫。这种对死人屋的“观”将颂莲与整个陈家大院的女人隔离开——放佛在暗示颂莲是这个院中的异类,最终被大院的男权制度压垮。而在小说中,那处死女眷的却是一口“死人井”,就在颂莲的住处附近。颂莲曾四次走到井边,与井有奇异的精神沟通。
事实上,“死人井”是作者透露颂莲精神状态和命运的符号。颂莲每一次靠近“死人井”,精神状态和命运都会出现一次转折。“死人井”是用来处死陈家出轨的女眷的。那么,“死人井”在这里就成为一个隐喻,连接着诱惑(出轨)死亡。小说对颂莲四次靠近“死人井”的情景有细致的描述,在这四次与井的沟通中,诱惑与死亡的力量相依相伏,交替上升,牵动着颂莲的精神与命运。
小说对颂莲第一次走进“死人井”时的情景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她注意到紫藤架下有一口井,而且还有石桌和石凳,一个挺闲适的去处却见不到人。走到井边,井台石壁上长满了青苔,颂莲弯腰朝井中看,井水是蓝黑色的,水面上也浮着陈年的落叶,颂莲看见自己的脸在水中闪烁不定,听见自己的喘息声被吸入井中放大了,沉闷而微弱、一阵风吹过来,把颂莲的裙子吹得如同飞鸟,颂莲这时感到一种坚硬的凉意,像石头一样慢慢敲她的身体。
这次靠近井后,颂莲的命运发生了第一个转折。她先是遇见了陈家英俊的大少爷飞浦,又无意间勘破了梅珊与医生相好的秘密。飞浦是出轨诱惑的人选,而梅珊则为她做了榜样。聪慧的颂莲于此无师自通,猜出那井里死的是出轨的“姨太太”。有意无意间,颂莲觉察到她与井之间的连结,曾半开玩笑地对陈佐千说:“我走到那口井边,一眼就看见两个女人浮在井底里,一个像我,另一个还是像我。”我们可以把颂莲与井的呼应看做一种宿命,或是一种潜意识的外化,井很早地暗示出下文中出轨、死亡与颂莲之间某种必然的联系。
在勘破“死人井”的秘密后,飞浦的箫声飘入了颂莲的耳朵。这箫声让她想起大学拉琴的男生。把飞浦与她的男同学相提并论,显示出颂莲未将飞浦当做晚辈,而是作为同辈男性的想象。为了这箫声,颂莲找自己的箫,从而牵扯出雁儿和卓云用巫蛊术诅咒她、为箫与陈佐千第一次闹僵、剪卓云耳朵等一些列事端。
这些事端都是“后宫争斗”的典型案例,电影通过这些情节,突出陈府的后院生活阴霾的深不可测。而必须注意的是,事端的起因是飞浦的箫声扰了颂莲的心境。颂莲敢于与陈佐千冷战、与卓云为敌的行为都与她之前在陈府如履薄冰的风格相悖。很明显,飞浦的出现和梅珊的秘密使颂莲对生活状态产生了质疑和其他想象。此后,颂莲“脾气越来越大”了。原本春风得意的颂莲情绪开始骚动,命运也在与“死人井”继续加深着呼应。
颂莲在陈左仟生日那天离开宴会,又独自走向了死人井。
在小说里,井像一个魅惑的精灵,向她“呼唤”,甚至“启迪”,又是声音又是手的唤她下去。感到井的“呼唤”,已经是十分严重的精神问题,许多自杀者跳井、跳河,都出于这种“呼唤”。井能启迪、呼唤颂莲做什么呢?前文说过,井是与出轨与死亡相连结的符号。井启迪她出轨,去靠近欲望的诱惑。如果说初次照井时,颂莲出轨是一个预言,此时出轨的欲望已强烈地诱惑、“吸附”着颂莲,让她欲罢不能。
这次照完井,颂莲立刻就在陈佐千的生日宴上闯了祸。小说明确地写道,连下人都“敏感地意识到这将是颂莲在陈府生活的一大转折”。此后,陈佐千开始冷落颂莲。在颂莲受冷落的这段时间,在她身边的是谁呢?是出轨的现成人选飞浦,以及模范先锋梅珊。这给了颂莲出轨更大的空间和推动力。
很久以后,陈佐千来到颂莲屋内,却显露了“暗病”——老夫少妻的困境将诱惑再一次向颂莲推进。
当陈佐千年老力衰,而英俊的飞浦近在眼前,出轨先锋梅珊与其同路时,欲望对颂莲的诱惑便更加强烈。但与欲望如影随形的是死亡,诱惑和欲望越强烈,颂莲对死亡的恐惧也就越深。这一次颂莲并没有照井,却被井吓得逃之夭夭。出轨的欲望与对死亡的恐惧同时达到至高点,故事的结局呼之欲出。
最终,有隐秘出轨念头、犹犹豫豫的颂莲没有走上暗示了几次的投井死路,而早就亮明底牌的梅珊,貌似可以突围成功的梅珊却实践了这宿命。回头看看,便能发现梅珊与死人井的联系。陈府上下都对“死人井”讳莫如深,或不闻不问,而除了颂莲被井吸引外,梅珊也曾和颂莲在井边谈话,并且唱叹井中的是“屈、死、鬼、呐!”很明显,梅珊对“死人井”的隐喻也心知肚明。
明写颂莲的暗藏念头,暗伏的却是敞亮的梅珊的命运。颂莲与梅珊两个人的命运明暗交错,终于水落石出。这是小说最精彩的一笔。苏童没有让颂莲陷入“死人井”的宿命,使故事毫无悬念,也没有使这些暗示成为虚晃的花枪,全无道理。
故事还未完结,颂莲与“死人井”还有第四次交汇。这一次交汇不是提点情绪或情节的转折,而是揭示颂莲的结局:
第二年春天,陈佐千又娶了第五位太太文竹。文竹初进陈府,经常看见一个女人在紫藤架下枯坐,有时候绕着废井一圈一圈地转,对着井中说话。文竹看她长得清秀脱俗,干干净净,不太像疯子,问边上的人说,她是谁?人家就告诉她,那是原先的四太太,脑子有毛病了。文竹说,她好奇怪,她跟井说什么话?人家就复述颂莲的话说,我不跳,我不跳,她说她不跳井。颂莲说她不跳井。
颂莲因目睹了梅珊出轨的下场而精神失常了。这不是因为她曾无意害过梅珊,却是因她与梅珊同病相怜,曾有过出轨的举动。虽然事情未果,但谁能保证飞浦与她颂莲的感情会深于父子情呢?一旦飞浦透露出去,她颂莲便与梅珊是相同的下场。对人来说或,想象可能被处死,和切实地看见与之相同行为的人被处死,带来的恐惧不可同日而语。诱惑幻灭,那井的启迪只剩下了死亡。对死亡的极度恐惧使颂莲成了一具躯壳。
统观小说,“死人井”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隐喻。它牵连、暗示着颂莲的精神状态、命运及整个小说情节的进展。第一次照井,颂莲朦胧地感受了诱惑与死亡同在,逐渐与出轨搭上了边;第二次照井,诱惑的力量开始上升,颂莲在此诱惑下越走越远;第三次,颂莲未曾照井却被死亡恫吓而走,死亡的隐喻取代诱惑成为主旋律,却仍为吓退颂莲,因诱惑仍有可能实现;最后一次,颂莲并不怕井了,反而可以围着井转圈——井丧失了诱惑力后,死亡也不足为惧了。
三、男权暴力的结果——飞浦形象的含蕴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集中呈现妻妾们在陈府中的生存困境。为突出这一主旨,电影舍弃了对飞浦形象的完整塑造。在电影中,飞浦是颂莲幸福的曙光。从外表、年龄上讲,二人郎才女貌,而且颇有灵犀。飞浦的出现好似向观众透露:这严肃、沉重的情节存在着走向通俗小说“英雄救美”模式的可能性,而这点可能性没有践行,是因为理想与现实有悬殊落差。
然而,小说中飞浦的形象远比此丰满得多。他的存在为男权话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语境。让我们看看飞浦的形象是如何在他与颂莲的多次交往中逐渐展现的。
飞浦未出场前,小说就借雁儿之口为他的形象定下了极高的调子:
飞浦一直在外面收账,还做房地产生意。颂莲不经意地向雁儿打听飞浦,雁儿说,我们大少爷是有本事的人。颂莲问,怎么个有本事法?雁儿说,反正有本事,陈家现在都靠他。
这话中的飞浦,貌似是陈家无所不能的顶梁柱。此后,颂莲第一次在饭桌上见到飞浦,觉得他“出于意料地年轻英俊”以及“很有心机”,印象很好。再后来,二人在菊花丛中有以菊为题的交谈——这少爷不仅有本事,还很有文化。再往后,飞浦有四次主动到颂莲房中做客,二人的感情逐步加深。第一次是在颂莲在饭桌上与带太太毓如闹翻后,飞浦上门。二人互道“猜不透你的心”,像一对初恋的男女。第二次飞浦带顾三上门教颂莲吹箫,为此与大太太大吵,全院皆知。第三次,飞蒲上门是来道别。他要到云南处理家族生意,借着“凶多吉少”的由头,颂莲去捂飞浦的嘴,飞浦抓住了颂莲的手。一段若即若离的男女感情,结果呼之欲出。到此为止,飞浦貌似是一个帅气、风流,对颂莲有情有义又在为摇摇欲坠的大家庭撑起一片天的贵公子。
飞浦最后一次上门,形象完全展露,他与颂莲的情感戏也终于落下了帷幕。这一次是在飞浦去云南做生意失败归来后。他对生意原来是一窍不通,俨然一个无能的贵公子,而非拯救陈家的有为少爷。无能不要紧,这不影响颂莲对他的爱,毕竟他还有吹箫青年的风流倜傥。然而当颂莲脚伸向飞浦时,他缩回了他的脚,哭道“老天惩罚我,陈家世代男人都好女色,轮到我不行了,我从小就觉得女人可怕,我怕女人。”“我没法改变了,特别是家里的女人都让我害怕。只有你我不怕,可是我还是不行,你懂吗?”至此,小说才交代清楚,飞浦是一个从能力、心理到生理都孱弱无能的人,与先前的渲染和电影中的呈现绝然相反。
层层揭去面纱的飞浦,不是宝玉,不是两难的觉新,不是勇敢的觉民,也不是稚嫩的觉慧。他不是史上任何一位少爷,他身上承载的,是男权压迫女性给自己带来的反作用力。陈家男人对女人的历代奴役与压迫,最终伤到了男人自己。阴阳相生相克,本是中国道家认定的“天道”,通过飞浦这一形象,“道”这一味料被神不知鬼不觉地融入到小说中,为小说增添了容量。梅珊的话则直接点明了这“道”:“这园子里阴气太旺,损了阳气也是命该如此。”
通过塑造飞浦的形象,小说暴露了男权统治的虚弱本质,揭示了男权暴力另一面的风景。如我们所知,性别话语起于女权主义者,有关性别权利的文学作品也以女性作者居多。作为一个男性作家,苏童为我们提供了与女性不同的视角。他并未如小说中陈佐千那样表达以强刺激维持、更新男权统治的妄图——这正是时下许多男作家乐此不疲的,也没以怜香惜玉的姿态扮演女性之友,而是从客观呈现了阴阳失衡的导致的两败俱伤,重申阴阳相伏相克的“道”。这是苏童作为男性作家对男权的省察,为性别话语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语境。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当代文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维平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