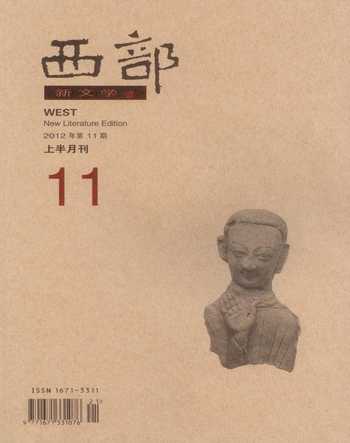明月出天山
阿舍
1
夏天结束之后,大黄山河谷的守林员玉山江爱上了天池景区管委会一个叫燕子的姑娘。消息传开之后,天池景区的工作人员再见玉山江时,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意犹未尽的笑容。事情是玉山江自己传开的。性格爽朗的玉山江并不介意旁人的眼睛与嘴巴,反而是,他有意让景区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爱上了她。玉山江是怎么做的呢?一月一次轮休,出山的玉山江什么都不做,第一件事就是骑着他的枣红色儿马,带着林野之间放旷粗朴的气息犹如天降神兵一般出现在燕子面前。玉山江的意思很明显,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又来看她了。玉山江是这样走在看望燕子的路上的:每当快要接近她的办公室,他会蓦然掉转马头再多绕一段弯路,攀上景区游客中心一旁的一个小山峰,像个将军似地巡视过碧绿的天池水,再回过头望望远处雪白的博格达峰,这才缓缓地往山下走。一段几分钟就能走完的山道,他却尽可能把时间拖得像前往大黄山河谷的路一样长。他胯下的枣红色儿马仿佛也知道他的心思,摇着头,晃着尾巴,故意把蹄子甩得又响又脆,再不时喷出一个响鼻。就这样,人还未到,玉山江心中的爱意已经随着马的蹄音穿过了松林,传进了天池景区管委会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当然,也传进了燕子的耳朵里。景区里有人为此讥笑玉山江,笑他这样兜一个圈子一定是因为心里害怕什么,玉山江听了呵呵一笑,心里说:“你们懂什么!欢喜的泉水让它流得越长才越动人。”
如今,严寒就要来到,才进十二月份,天池已经下了八九场大雪。比起夏日的蓊郁清新,白雪皑皑的天池更有一番韵致。夏日的天池好比一个笑声嘹亮的年轻姑娘,而被积雪覆盖的天池,俨然就是一位经历了荏苒岁月之后心地更加纯净仁厚的老者。
披上银装的天池景区一天比一天显得静谧与圣洁。这一天,山里出了大太阳,十一点刚过,太阳已经越过东山,把金灿灿的阳光洒在了天池景区管委会的院落里。中午两点,玉山江和他的枣红色儿马的身影不紧不慢进了管委会的院子,有力的脚步声把躺在院落里打盹的阳光吵醒了。
“玉山江,你来晚了,燕子刚刚飞走啦!”管委会一位爱开玩笑的大姐站在门前,一边哈气搓手,一边冲着大步走来的玉山江喊。
“呵呵,涂大姐,你这么大的嗓门儿,老鹰都能被你吓跑,更何况燕子!”玉山江已经有三个月没见到燕子了,上一次下山,燕子带人去了博格达峰下的岩画山。现在是冬季,大雪封了山,燕子能去哪儿呢?
涂大姐抓起窗台上的一把积雪,朝玉山江扔过去。雪团捏得不紧,扔出去就散了,飞在金灿灿的光线里,晶莹闪亮,仿佛一位翩翩降落的雪精灵。“玉山江,你别不知好歹,我可是一直在燕子跟前说你的好话呢!”
院子里有一棵上百年的老榆树,因为裹了厚厚的积雪,胖墩墩地站着,慈眉善目,仿佛一位白胡子白眉毛的老爷爷。玉山江把马牵到老榆树下,正要拴绳,涂大姐接着说:“别耽搁了,赶快去吧,说不定还能追上。这丫头,最近奇奇怪怪的。”
“真不在?”玉山江欢喜的面颊露出了疑容。
“不在!谁还骗你!”
“去哪儿了?”
“去东岳庙啦!跟掉了魂似的。”
“去那儿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去问问不就得了。”
玉山江皱皱眉头,健壮的身影定在院子中央,内心泛起一片微暗的波澜,金灿灿的阳光挥照下来,炫目的光芒似乎让每一根波纹都不自禁地微微颤栗。无声无息,玉山江的心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轻轻地揪了一把。
“那,那我去看看,呵呵。”玉山江看了一眼涂大姐,难为情地笑开了。
“嗯,快去,快去吧,别让燕子飞远了。”涂大姐挥挥手,半眯着的眼睛透出隐隐担忧。
2
姑娘们的心思真是难猜啊!玉山江转过身,重新跨上他的枣红色儿马。驱马离开之前,他看了一眼站立在院落中央的老榆树,想起去年冬天第一次见到燕子时的情景。那时候,他还不曾爱上她,但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见燕子,他先是看到了她的背影。也是在这个院落里,他提了两瓶马奶子酒来找涂大姐说话。一个人呆在管护站真是太寂寞了,每次出山,他都憋了一肚子的话。那一天,他是打算美美地说一通话,然后喝醉了要住在管委会的。当年,林校毕业之后,玉山江是有机会留在乌鲁木齐工作的,但是他还是回到了天山脚下,并且主动要求做一位林区管护员。时光匆匆,玉山江已经不小了,寂寞并且不时有些小惊险的管护工作一年年磨练着他,让他越发显得富有男子气概,同时,也让他的性格变得更加粗朴与淳厚。
去年冬日里的一天,玉山江走进管委会的院落,就见到一个长辫子的姑娘仰着头,手里举着一根长木棍,正轻轻地敲打老榆树的枝条,厚墩墩的雪花哗哗啦啦飘下来,转眼之间就在树下堆起了厚厚的一层。那姑娘一边敲一边拨掉落在头上和脸上的雪花。突然,又猛地戳动一根枝条,接着跑开几步,站在一旁,痴迷地凝望着那些飞下树冠扑簌簌扇动翅膀的雪花,傻傻地咧着嘴笑。
“嗨,你干什么呢?”玉山江并不认识这个新来的姑娘,他只是看着好玩,忍不住开口问道。
“啊,你吓了我一跳!雪太厚了,树枝快要压断了。”燕子转过脸,黑灵灵的目光快乐地看着他。
玉山江一眼就记住了这个新来的姑娘,细长的眼睛,鼻子有点塌,因为用力击打树干而被咬红的嘴唇就好像一粒秋天的野草莓。玉山江飞快地转动脑筋,他喜爱并钻研植物,并且善用山林间的草木比对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很快,他找到了能够与这个姑娘相匹配的植物——淡紫色的风铃草。
今年夏天结束之前,玉山江不知采了多少风铃草放在管护站小屋的窗台上!
白茸茸胖墩墩的老榆树站立在院子中央,每天要看见多少次进进出出的燕子呢!打马离开的一刻,玉山江望着慈眉善目却又一言不发的老榆树,真心希望它能够大发慈悲,告诉他一些关于燕子的心事。
燕子徒步去了东岳庙,玉山江骑着马却始终没能追上。什么事让燕子的心劲儿鼓动得这么大?夏天,玉山江和燕子都是科考队的成员,一趟走下来,大家都夸燕子是个懂事心细的好姑娘。玉山江就是从那时候爱上燕子的。
出了太阳,山里并不冷,天空仿佛一块巨大的蓝水晶,光芒炫亮,刺得人睁不开眼睛。白雪覆盖的山峦连绵不绝,空气清爽冰甜;高耸的云杉全都披上了厚厚的雪毯,身形顿然庞大,也更加威严;山谷里的溪水还未结冰,在落满积雪的山石间缓缓流淌,袅袅水雾仿佛仙子一般,■然飘行于水面。
冬天,天池景区游人稀少,最常见的,就是那些前来拍摄婚纱照的幸福情侣,爱情让他们的身心炽热如火,他们也就不畏惧寒冷。经过天池的时候,骑在马上的玉山江勒住马缰绳,特意看了看那位坐在栈道一旁裸露着肩臂的新娘,心下再三比较,觉得不施脂粉的燕子真得要比她好看许多。很快,玉山江走上灯杆山的山腰,东岳庙就要到了。下马之前,玉山江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今天,为了赶来看望燕子,他可是起了一个大早。
燕子果然在这里。燕子身穿一件紫红色的羽绒服,低着头,孤身一人呆坐在空落落的四合围院当中,光洁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漫无边际的沉迷之色,再仔细看,这沉迷之中又含着忧伤。东岳庙是古人祭祀博格达山神的地方,如今虽然只剩下一些零落的残砖旧瓦,但时光的旷远与沉默,以及地势的殊异都使这里的气氛非同寻常。按照常理,燕子这个年龄的姑娘,并不适合这样枯寂远僻的景观,她单薄的身体,也似乎并不能承受这景象里所蕴含的那些人类古老而蛮荒的记忆,她应该和那些拍摄婚纱照的新娘一样,坐在碧波万顷的天池水边,让自己的青春随着荡漾的波纹在阳光下欢唱。可是,她完全都不顾这些,单纯却又专注地坐在台阶上,低着头,一只手托着腮,一只手握着一双大红色的棉手套,目光遥深地落在绵绵不绝的心事里。
踏进围院的一刻,玉山江内心的欢喜已经呼之欲出。坐在石阶上发呆的燕子也看见了玉山江,原本俯在膝上的身体幽幽地发出一声叹息,很快直起了腰。阳光晃眼,燕子微蹙眉头,笑眯眯地看着玉山江,没说话。
“燕子,你不冷吗?”玉山江随便找了句话。单独面对燕子,他有些不好意思,他感到自己脸红了,好在他的皮肤黑,什么也看不出来。事实上,他是想问她为什么要一个人躲在这里,但直接打探一个姑娘的心思,这是多么不礼貌的一件事啊!更何况,玉山江根本没有把握,燕子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他。他听自己的奶奶说过,姑娘家的心思就好像一碗热腾腾的苞谷面糊糊,要想喝了这碗面糊糊,你得转着碗边一小口一小口地溜边儿喝,倘若傻乎乎张嘴就来一大口,不是把你的心烫死就是把你的嘴烫烂。
“不冷,太阳这么大,晒着暖和呢!”燕子声音又轻又脆,好像身后松林间传来的一声鸟鸣。从绵密的心事里回到眼前不断向她表达爱意的玉山江的身上,燕子仍有些迷迷糊糊。玉山江的话刚落下,她的耳边蓦地又响起了另一个声音:“石头上凉,别坐久了。”这声音不是玉山江的,清越明亮,伴随着一个颀长的身形,一句能顶一万句。也是这一刻,燕子突然醒来了,今天,恰好玉山江在,她真是要跟他好好说一说呢。
玉山江听到燕子的回话,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他健壮的身躯立在豁亮又空荡的围院中央,心中七上八落,手脚都找不到的合适的地方来放,只好进退两难地踱起方步,又故意走到院内的一块石碑跟前,抬起头背着手,魂不守舍地看起了石碑。事实上,不管他上上下下看了多少遍石碑上的花纹与图案,他的眼中也好比电视机的花屏,什么也没有看到。
围院里的寂静在等待着他们。燕子仍旧坐在石阶上,一只手托着腮,一只手握着那双鲜红的棉手套,隔着五六米的距离,笑嘻嘻地看着玉山江。她一直把他当做一个敦厚朴实的大哥哥,见到他,她的心从来没有扑腾扑腾地跳过,反而是更加地平静与自如了。即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喜欢她,她也觉得这只是一个跟她无关的善意的传言,也就既不上前阻止,也从不应合。
玉山江被燕子看得六神无主,也就放弃了对自己无措的掩饰,侧过头,迎上燕子的目光,咧开嘴,憨憨地笑了两声。燕子也忍不住了,噗哧一下笑出声来。
3
“玉山江,你知道吗?以前,这里除了祭祀山神,还建过一个气象站,是一个德国专家建的,他在这里观测博格达峰的气象,写了五十多本气象观测资料——这也是一个看风景的好地方,这里真静啊!”
夏天,科考结束后,燕子一直在协助科考队整理考察成果,科考队的主将华老师病重,他的学生林陪着他前去北京看病,大量考察记录都留给燕子来补充誊写。所以,这些日子,燕子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总是绕不开与此相关的人与事。
“博格达是神山,神山的脚下总是有数不清的故事,神山也总是让人看不够。”玉山江是天山脚下长大的孩子,他的心里装着比科考队的科考记录更多更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已经变成他的身体与心灵,已经让他和天山的雪峰、天池的水融成了一体。融成一体的东西就是自己的,是自己的就用不着长吁短叹喋喋不休了。
“燕子,你的考察记录整理完了吗?”玉山江终于找到了话题。
“快了,有一些岩画拓片太模糊,华老师他们恐怕不满意,下雪之前,我又去了一次岩画山,还是没办法把它们画得更清楚一些,石面不平整,岩画又刻得浅。”燕子摇摇头,一边说一边抚摸手中的红手套。
“新买的?”玉山江走近燕子,看着她手中的红手套。
燕子轻轻嗯了一声,突然低下头抿嘴笑了,像是心底里突然涌上来一股暖流,那暖流猛烈地激荡着她,实在是让她无法抑制。
笑意还留在嘴边,燕子抬眼迎向玉山江的目光。玉山江被燕子嘴边的笑意感染了,也跟着笑。然而他又吃了一惊,他突然发现,燕子此时此刻的脸跟记忆中的她是多么地不同啊!这张脸比天池的水更明媚更柔美,这张脸明明白白多了什么内容!是什么呢?玉山江用凝视一朵新疆风铃草的目光敏锐地体察着燕子的脸颊。霎时,脑间甩过一道闪电,他猛然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因为燕子眼中多出的一缕羞涩。
玉山江的目光回到了燕子手中的红手套上,他的心咯噔掉下半截,接着又仿佛碰着了一个尖锐的东西,一丝厉痛猝然穿过他的胸腔。
“颜色……这么红!”
“好看吗?”燕子眼中的羞涩越来越浓稠,话音刚刚落下,那缕羞涩便冲出眼眶,洇上了她的双颊。
“好看,在……在哪里买的?”玉山江有些紧张,但还是问出来了。这一刻,他感到当自己端着枪面对偷猎者时也没这么害怕过。
“……今天收到的,他寄来的。”燕子眼中的羞涩没有了,微笑也收回去了,直视着玉山江的眼睛布满了诚恳。
玉山江呆呆地看着燕子,半天说不出话。
“……哦,他,他是谁啊?”
“……你认识他……夏天的时候,吃过晚饭,他常常坐在这里看书。嗯……就在这里,我坐的地方……”沉默了一阵,燕子断断续续把话说完,话音落下,几滴晶莹的泪花已经挂在了睫毛上。
晶莹的泪花阻止了玉山江仿佛坠下山崖般的失重感,原本隐隐作痛的心艰难地爬回到一个能够使他站稳身体的平地。很快,那泪花又让玉山江的失落与心痛变成了怜惜。又一次,他想起了奶奶的话:姑娘家的眼泪好比无价的宝石,一个姑娘若是肯为一个男人掉眼泪,就等于她把命都送给他啦!
幸好燕子又低下头去,才让玉山江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他抬起双手揉了揉脸,勉强把苦涩、失望、慌乱、晕眩撂在了一旁。望着低头不语的燕子,玉山江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内心。虽然还没有搞清楚那个让燕子掉眼泪的男人到底是谁,但是想到燕子孤身一人走在冰雪重重的寒天,坐在一个枯寂的围院里,脸上挂着委屈又痴心的泪花,他的心比得知那个朦朦胧胧的坏消息摔得更碎。
一切来得太过突然,玉山江毫无防备。今天,他原本是打算告诉她他在管护站为她养了两只小山羊,如今正好到了宰杀吃肉的季节,他是想让她带回给她的家人的,但是眼前,他却变成了一个第三者,一个和她的眼泪无关的人。
又一次,玉山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他把揣在大衣兜里的皮手套拽出来一只,握在手里烦乱地拧了两把,突然间就希望燕子大声地哭出来,让眼泪痛痛快快地流出来,就好像此时此刻他也希望自己躲在一个无人的地方发泄一通一样。
燕子垂下眼眸,咬住嘴唇,花费了一番力气,终于止住了内心的脆弱与冲动,没有让泪花变成挂满脸颊的小溪。好一阵儿,她固执地不肯抬起头来,她一边等待心中的委屈渐渐平息下来,一边动情地想:终于说出口了!
几个月来,燕子的爱无人知晓,甚至连她爱着的那个人也不知道。她爱得幸福又彷徨,强烈又无计可施。从夏天到冬天,多少个日日夜夜,她的爱毫无出口,只能紧紧地压在心底,一天又一天,没白没黑,终于在一个夜晚变成了锥骨的疼痛。接着,这幸福又彷徨的疼痛也开始不止不息,跟着爱一起,一天天地堆积,一天天地剧增,一天比一天更深地钻进她的心里。天热的时候,它们随着雨水流遍她的血脉;天冷刮起了大风,它们又在她的心里掀起了风暴;天下雪了,它们又像压断云杉枝条的积雪一样几乎绷断了她的胸骨!而现在,因为这双寄自远方的红手套,她终于能够说出口了!她的爱终于像阻塞的泉溪找到了出口,可以没日没夜地奔流了!
想到这里,止住泪水的燕子又高兴起来,她抬起头,想对玉山江再说些什么,却在看到玉山江的一刻,内心又让玉山江惘然若失的神情重重地挥击了一下。“哦!玉山江!为什么是你呢?为什么是你听到了你最不该听到的事!”燕子愧疚地想。但是她放远目光遍寻脑海,管委会里可以诉说的人,能够让她信赖的人,除了玉山江还有谁呢?“是不是因为玉山江喜欢我,我才这样心狠又放肆呢?”燕子仿佛在替玉山江责怪自己。
燕子看着玉山江,目光中有一种求救般的信任。玉山江回视着燕子,刹时就明白了自己无可挽回的境遇,这一次,被揪起的心再一次重重摔碎在东岳庙空荡冰冷的平地上。但是玉山江的身体没跟着摔下去,反而是,随着心的坠落,燕子信赖的目光又让他稳稳地站直了。
“我认识他?”带着一缕困惑的微笑,玉山江问道,语气有些无力。
“嗯……他也在科考队。”燕子小心翼翼地回答,努力不让自己的话语和神情更深地刺伤玉山江。
还能有谁呢?那个眼睛明亮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他缄默少语,却始终给人以信赖;他骑在马上入神地端详前方的云雾,一不小心被树枝挂烂了额头;他攀在岩壁上,为了描摹一幅岩画,两个小时不动身子;他已经是研究生了,在导师面前还像旧时代的学生一样恭敬有序;他斯文又害羞,打出的呼噜却能吵翻天……玉山江的脑海里闪过一个颀长的身形。
4
夏天,燕子和玉山江都参加了科考队,他们从天池出发,一路考察了大黄山河谷、西沟河谷、鄂博梁、四工河谷的文化遗迹,一直来到了博格达峰下的岩画山。燕子就是在科考队里结识了华老师的得意弟子林。
其实燕子不记得她的爱是怎样开始的,但是她怎么也不相信,她的爱会没有怦然心动的一刻就轰隆隆地发生了。她一遍遍地问自己:总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或者,一个细致入微的细节吧?譬如一个回头的笑,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或者四眸相对天降灵犀。她苦恼地思来想去,真的没有,记忆里空空一片。她这么年轻!她的爱那么强烈那么特殊!她怎么可能不记得呢?但事实就是这样。她只记得,突然一天,她的爱已经涨成了天池的水,碧波荡漾,绵绵不尽,就好像春天的鄂博梁草甸,谁能说得清楚哪一棵青草第一个拱出地面呢?而博格达峰下突降的大雨,哪一滴是第一滴?天池上空的雪花,哪一片又是第一片呢?
她只记得一些后来的片断,那些已经和她长成一体永远也甩不掉的片断。
她记得大家坐在那块黑色岩壁的对面吃午餐,博格达峰就在前方,她的内心飘摇又沉醉,因此坐开在一边,秘密地嗅闻周身甜蜜的空气。忽然,他从她的身后走过,回过头看她的眼睛,微笑着说:“石头上凉,别坐久了。”
她记得大家在半月湖前留影,拍完合影,众人说说笑笑就散开了,她转身也要走,却见他仍然站在原地。他们四眸相对,淡淡地笑了笑,就听身后的摄影师喊了一声:“来,来,你们俩再拍一张,多美啊,这样的景色,一生只有一次!”后来,她把这张照片传在了他的邮箱里,他回了信,说:“我们的笑容多么相似!”
她记得科考结束后,她的爱已经随着雨季的到来,与天池的水一起骤然上涨。她无法确定他的内心,更没能对他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她又害怕又焦急,虽然他们在一起整理科考队的科考成果,但是她知道,他的离去在一天天临近。而他始终平静又自然,亲切地微笑,简单地问候,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直到有一天,吃过晚饭,她从管委会办公室往宿舍区走去,在管委会的院门前,她遇见了他。看见她,他挺了挺颀长的身体,轻轻地问:“东岳庙远吗?”她慌乱地告诉他不远,其实也不近,然后又晕头晕脑地告诉他路怎么走。她绕来绕去说了许多,最终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哪条路可以更近,哪座山在前,哪座山在右,她全都混乱了。怦怦怦的心跳声终于迫使她不得不把话停下来,她定定神,这才看清楚他的表情,他抿着嘴,正轻轻地笑着,明亮又温柔的目光刺痛了她的心。从那天起,一直到他带着华老师离开天池景区,他每天傍晚都要去东岳庙独坐。她知道他天天去那里,却从不敢也让自己去那里。唯一一次看见他只身坐在东岳庙残旧的石阶上,还是她作为陪同带领几位客人不得不去了那里。那一刻,她站在人群里,又一次与他默默地四目相接,她感到自己早已了解了他的一生一世。
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漫长又寂静的正午,办公室里,大家都在做自己手中的工作,他没有征兆地忽然就走了进来。站在办公室门口,他迟疑地看了看大家,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两秒,很快又移开,接着,她听见他轻轻地说:“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华老师病了。”他的声音轻得好像一声叹息,她看见自己的心像一只落难的飞鸟冲向地面。
这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也不再与他有过任何联系,只是间或在有关华老师病重的消息里猛的听见他的名字。而仅有的两次,每一次都如同巨大的钟鸣,震得她头晕眼花,阵阵心悸如同突遇可怕的惊吓。
他走了以后,她的时光变成了浩浩荡荡的大水,她梦见水不停地上涨,淹上她的脚踝,淹上她的双膝,每一天都逼着她往后退。她不知道大水要把她逼退到哪里,就开始每天黄昏代替他去了东岳庙。她一天又一天地在黄昏疾步快走,如果不是工作外出,她从不间断。她的脚步越走越快,她的目光越走越湿润,她的嘴越走抿得越紧,像是满心迫切,仿佛他在那里等候着她。每一次,她都把自己走得满身是汗,每一次,她都把自己走得魂飞魄散。似乎只有这样,她不得喘息的心才能够稍稍缓释。而每一天,只有站在东岳庙空荡的围院里,让密林间的清风吹吹心中的思念,让天池上空的霞光照照心中的爱意,这一天才能够平稳度过。
那些日子,除了天池的山水草木,没有谁知道她的心思。当然,最切近地听见了她的心跳的,还是那些护送她一路走上东岳庙的云杉树,它们一棵棵伫立在山路两旁,安静地看着她从它们身边走过,一次次看着她来,又一次次望着她去,然后轻声交谈这个姑娘的痴心,又在晚风到来的时候把这个故事一遍遍地传送给整个天池的山林。她这样走着,不知不觉就在秋日里的一天体察了他为什么每天都来东岳庙。天池的水这样清澈,天空这样蓝,松林这样安宁,风这样轻,空气这样清甜……高爽的秋意不经意地就打通了她的心神,她突然觉得她的心里长着一个眼前所见的世界,天池在其中,自然万物在其中,她的爱也在其中;这世界明亮,美好,久长,经历了万千时光,又被时光越擦越清晰。那一刻,她明白了,无论她要等多久,等得到或者等不到,她的爱都将是长久的。
有了这个想法,她的痴心就更加坚定了。一次,一个秋末的夜晚,整理完一段科考记录,她突然无法忍受心中的激荡,一口气跑到从前他暂住的小木屋,在漆黑的夜色里,对着漆黑的木屋足足站立了两个小时。那段记录仅仅是为一些文化遗迹打下的数字基点,但是她在每一个数字里都听到了他的声息。看着那些被他写下的数字,有一刻,她简直害怕到了极点,她觉得那些数字组成的他就站在她的面前,离她很近,她害怕极了,生怕那些数字真得变成他的手,一把握住她。她无法忍受心中的激荡,一口气跑了出去,隔着一段十米左右的木栈道,目光灼灼地站在小木屋的对面。气温已经降到零下,黑暗中,寒意随着白霜纷披掉落,松林与群山吃惊地望着她,她一点儿没觉到冷,任由万物凝视她澎湃的内心,她静静地看着对面一团漆黑的小木屋,觉得自己从来不曾这么清晰地看见他。
另一次是她以带朋友穿越博格达峰为由,再次去了岩画山。夏天的科考成果中,一部分岩画拓片做得非常模糊,她知道这些岩画对他很重要,就下定决心帮他做得更好。到达岩画山时正当晚霞披照,朋友们坐在正对博格达峰的草滩上,一边尽享晚餐,一边饱览博格达峰红云缭绕的奇观,每个人嘴里都忍不住大呼小叫。只有她拿着纸与笔,从岩画山的东区走到中区,一一找见了那几幅没能拓清的岩画。第二天,在出发前往博格达峰之前,她又特别花了半天时间,独自趴在冰凉的岩壁上,背对雪白庄严的博格达峰,一幅接一幅,仔仔细细重新拓画。对于那些无法拓清的岩画线条,她又是拍照,又是描画,总算补齐了不足的资料。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她虽然又累又孤单,心里却有无尽的欢乐,仿佛看见了他的笑脸。当画完最后一笔,她回过头看到凝望着她的博格达峰,她又蓦地低下了头,她暗暗地在心里笑,她知道,神山博格达已经看到并见证了她的爱。
她如此痴醉地思念一个人,用尽全部心力,也就无法细加体察玉山江对她的心意。
她抱歉地看着玉山江,紧闭双唇,勉强露出一丝微笑。正午的阳光落在她明净的脸上,浅浅流动。那些光线一落上来就被她心中的爱融化了。
玉山江叹了口气,说:“这么说,燕子,你快嫁人了?”
玉山江的脑海浮现出林的身影。事实上,直到目前,林给他留下的印象依然很好。他一会儿低头想一想,一会儿抬头看一眼燕子,慢慢地,就把林的形象放在了燕子的身边。“他和她,倒是真得很般配啊!光光亮亮的,就像奶奶说的,真是一对好人儿!他比我小好几岁啊!”
“……不是的,玉山江,你想错了,我们……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什么不知道?”
“就是……就是都没有说过。他没说过,我也没有说过。说不定……说不定只是我自己在瞎猜。”燕子又低下了头,最后几个字几乎又让她掉下眼泪。
“他不是给你寄手套了吗?”
“只是手套,什么也没有说。”
“这就够了,还要说什么……你想想,红颜色,还能有别的意思吗?”
“嗯,不管是不是,我想好了,等他来了,我要让他知道。”
“他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华老师的病很重。但是他肯定会来的,为了那些考察资料他也会来的。”
“……对,来了,你就……你就告诉他。”
“……玉山江……我其实……其实不敢说。我怕……”
“怕他不喜欢你?”
“什么都怕,不喜欢会怕,喜欢了会更怕。”
“呵……傻丫头,喜欢了怕什么?那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嗯,是真的怕,要是喜欢了我有多么幸福啊!幸福真让人害怕!我不相信自己会有那么大的幸福!”燕子的话带着颤音。
玉山江呆望着燕子亮晶晶的眼睛,无法相信她的话,便在心里喃喃地说:“这是什么奇怪的想法!谁会害怕幸福呢!唉,姑娘家的心思,真是太难猜了!”
5
他们走出东岳庙的围院,准备下山。燕子在前面走,玉山江去解马绳。
看见他走过来,玉山江的枣红色儿马甩了甩一只前蹄,又噗噗吹出两口白气,然后定住身体,静静地凝望着他。枣红色儿马又黑又湿的大眼睛惹得玉山江十分难过,他的心倏然抽动了几下。
玉山江不想多看枣红色儿马的眼睛,也不想让心中的阴云更多地浮上面庞,靠近马身时,他快速跨出两步,躲过了枣红色儿马满是关切的目光。解开马绳,玉山江回过身,就见枣红色儿马还在望着他,目光中的关切又多了一些悲戚。玉山江的心忽然乱了,猛地伸出手掌抚了抚枣红色儿马的脸颊,然后把它推向一边,嘴里跟着说道:“好了,别看了,那是人家的姑娘!”玉山江这样一说,枣红色儿马不再固执地盯着他看,便低低地打了一个响鼻,伸直脖颈,注视着身下雪白的山谷。
玉山江顺着枣红色儿马的目光望出去。蓝天下,白雪覆裹的松林与群山明净炫亮,天池在远处露出一角,像块金子熠熠闪动,整个眼底就好像一个圣洁宁静的雪国宫殿,滤尽尘埃,没有喧嚷。玉山江想起燕子说的话,这儿真是个看风景的好地方!是啊,有了那个年轻人,灯杆山山腰的这块台地就成了燕子心中无可替代的福地,映入眼帘的天池风光就成了爱的永恒见证。
枣红色儿马静默的神情触动了玉山江,它似乎比他更深地受到了挫伤。玉山江越看越不忍心,双手抚住枣红色儿马的脸颊,嘴边露出一丝苦笑,亲呢地端详它的眼睛,这才发现枣红色儿马黑褐色的睫毛尖上还结着冰霜。玉山江摊开手掌,像为他心中的姑娘抹擦眼泪一样,轻轻地抚去枣红色儿马睫毛尖上的冰砣。枣红色儿马一直垂着目光,任由玉山江用心中的苦涩安慰它。玉山江一边擦,一边凑近枣红色儿马的眼睛,就看见它黑玛瑙似地眼眸里辉映着整个白雪皑皑的山谷,当然,也浸沥着他内心的忧伤。玉山江叹口气,拍拍它的脸,说:“走吧。”
燕子在前,玉山江牵着马跟在后边,两个人默默无语,各自怀揣心事,很快下了灯杆山。
冬天,天池景区几乎没有游人,滤尽尘埃的天池山水犹如一面凌空的水晶,任何一点声响都会像一道亮光,刺穿时空,在四下里升起。走下灯杆山不久,远远地,燕子和玉山江就听到天池那边传来的争执声。
“都快五点了,你们还占着这里!天池是你们的吗?”
“那么多好风景,你们为什么偏偏要和我们挤?”
“什么话!你知道这里景好,别人就不知道,别人是傻瓜吗?为了让你们,我们把四周走了遍,等了四个多小时,你们倒没完没了了!”
谁都知道,这里是拍摄“明月出天山”雪景的最佳景观。雪峰之下,明镜般的天池还没有结冰,只在背阴的一面断断续续浮起一些又薄又亮的冰层,有阳光的地方,碧波泛动的水面上还飘着一层淡淡的水雾;连绵的雪峰并没有完全被雪覆盖,在靠近天池的雪山阳面,顺着地形,那些高大的云杉林仿佛不怕冷的年轻人,大片大片地钻出披盖在山坡与山崖上的雪毯,倔强地要使深绿色的身体迎着阳光;而稍远处海拔更高的雪山,因为始终沐浴着朝阳与夕照,皓白的雪峰之尖已经渗进了辉煌的金色;明镜般的天池看到了这一切,便将金色的雪顶,白色的山坡,绿到发黑的松林,同时映现在自己明暗相间的身躯之中,再用鳞鳞波光顺次将它们轻轻拂动,这样一来,天池水就变成了一条绵长的黑白相间金光闪亮的艾德莱斯丝绸;如果再遇上晴朗的天气,下午五点左右,夕阳正将金光洒向雪山,还在醉心观赏雪景的人,不觉中一抬头,就能看见皎白的月亮已经升上宝蓝色的天空,一时间,阳光,月亮,蓝天,雪山,松林,碧水……就构成了一幅绝无仅有的人间美景。
两家拍婚纱照的摄影师就是为争夺这幅美景争吵起来的。美景易逝,谁都想抓住机会赶快拍完,把身穿白色婚纱几乎要冻昏倒地的新娘早早送走。燕子和玉山江走到他们近前的时候,一位摄影师正举着长焦相机瞄准站在天池岸边的一对新人。新人站在雪白的山石间,婀娜又亲密地摆着姿势。另一位摄影师拿着一架同样高级的相机站在一旁,一边被寒冷逼得不停跺脚,一边大声嚷嚷。
“再给你十分钟,时间一到,我们就上人!”
玉山江顺着摄影师的镜头看过去,那对婀娜又亲密地摆着姿式的新人的动作越来越僵硬了,而距离他们十步之远的地方,正抖抖索索等着另一对身穿白色礼服的新人。
因为受到连连抗议,正在拍照的摄影师也无法专心了,他一边按着快门,一边大声提醒新人保持姿态,一边不得不抽空凌厉地回顶一句。
“你上上试试看!我看你能上得去!”
双方都很不耐烦,火药味越来越重,两边的工作人员也越来越多地加入了争执,有一两个年轻气盛的,推来搡去,几乎要打起来了。
“唉唉唉,你们别吵了,有吵的时间照片都拍完了。”燕子上前阻止,可是并没有人听她的,两个身形单薄的小伙子已经拧在一起了。
“都住手,都给我住手,再打我叫保安了,谁都别想拍!”玉山江的声音洪亮粗健,小小的骚乱被他的气势给压住了。
“你们拍的是结婚照,结婚是喜事,你们打什么架!你,你,快拍,拍完也让人家拍,没看天气越来越冷了吗!”玉山江说完,回到路边牵马,枣红色儿马跺跺前蹄,噗噗喷了两个响鼻。
两边的人都安静下来了。那个挨了训的摄影师很顺从地举起镜头,瞄准了远处的新人。
玉山江牵着马往新人拍照的方向走去,走到那对正在一旁等候的新人附近,停下了马,对着他们说了几句话。一身雪白的新人听了他的话,忙不迭地跨过山石,快步走到玉山江身前,把身体紧紧地靠在了枣红色儿马的身上。
燕子看到这边相安无事,也跟着往玉山江那边走去。在她的对面,那对站在山石上拍照的新人已经拍完了照片,正小心翼翼穿过积雪覆盖的乱石往路边走。气温突然降了几度,燕子感到脸颊僵硬了许多,但是她的心却突然被那位紧紧靠在枣红色儿马身上的新娘感动了。燕子慢慢走着,恍恍惚惚想着自己的将来,忽听玉山江对着那对拍完照片的新人说:“你们也过来暖和暖和吧。”听到他的邀请,这对刚刚拍完照片的新人疾步跑上马路,仿佛得救似地把身体紧紧靠在枣红色儿马的身上。他们脸色发青,浑身哆嗦说不出话,两个人的眼睫毛上都结了冰霜。
这真是一幅动人的画面!四个新人,穿着雪白的礼服,在冰天雪地之中,紧紧依靠在一匹枣红色儿马的腹部。
燕子走到枣红色儿马跟前,赞许地看了一眼玉山江,然后伸开双手,捧起枣红色儿马热气腾腾的嘴,满含疼惜地凝视着它的眼睛。枣红色儿马也看着她,湿黑的大眼睛像天池的水一样明亮,隔了片刻,枣红色儿马突然轻轻“呃”了一声,把头扭向玉山江一边。
燕子看着枣红色儿马的眼睛,这一次,枣红色儿马的眼睛里映现的不再是她了,而是对面仿佛艾德莱斯丝绸一般的天池水,以及玉山江高大健壮的身影。
两对新人稍稍暖和过来,睫毛上的冰霜渐渐化成了水,滴落在脸颊上,有人一边轻轻擦拭,一边连声向玉山江道谢。玉山江呵呵地笑着,挥挥手,对他们说:“祝福你们啊。”新人们点点头,带着微笑,各自走了。
路边就剩下了玉山江和燕子。燕子望着升在半空里的月亮,一只手还在抚摸枣红色儿马温暖的脸颊,目光却已经魂不守舍地飘到了更远的地方。玉山江看看月亮,又回头看看她冻红的鼻子,咬咬嘴唇,黯然又真切地说:“燕子,也祝福你啊!”
燕子没有想到玉山江会对她说这样的话,吃了一惊,睁大眼睛顿住片刻,接着就害羞地笑了。玉山江接着说:“要是你的结婚照也是这时候在天池拍,我就帮你挡着别人,让他们谁都不敢和你抢!”燕子听了,更加抑止不住心中的欢喜,咬咬嘴唇,甜蜜地低下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