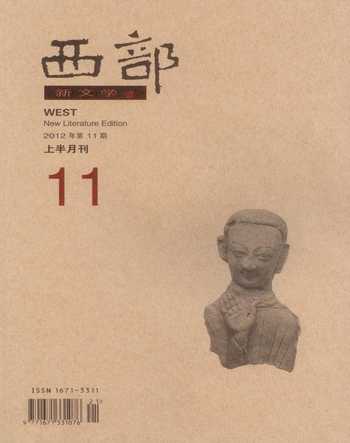龋齿
弋舟
除了一双眼睛,他的脸基本上被白色遮盖住。无影灯下的白色非常耀眼,有种趾高气扬的光芒。躺在那张古怪椅子上的她,很难把这个男人和昨夜联系在一起,因此,她意识到,这个男人终究还是一个陌生人。他们认识一年了。当时,她恰好刚刚离异一年,同事把这个牙医介绍给她,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走到了昨夜。她知道自己并不年轻了,但依旧难以做到坦然。昨夜并不顺利,起码,在她是有种隐含的抵御。牙医不能理解她的态度,也许还觉得那些额外的磨擦有点多余。牙医吮吸她,她突然咝咝地吸起凉气来。她无可遏制,那一瞬间,牙医的舌头纠缠而来时,有尖锐的痛,牵扯了她的某根神经。整个过程伴随着她的吸气声。平静下来后的牙医发现了她的异样。她冲进卫生间,拼命地漱口。牙医免不了产生误解,赤裸着扒在卫生间的门框上,禁不住责问她:“有必要吗?”而她,显然也明白了牙医的不快,嘴里含着一口水,用手指盲目地示意。她在艰难地表达,仿佛急于澄清事实。而她要澄清的事实,无非是——她的某颗牙齿痛。可这有必要吗?当眼前的男人终于露出恍然大悟的样子时,她觉得有股无以复加的委屈淹没了自己。看着她的眼眶涌出泪水,牙医笑了。他果断地决定:第二天就给她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此刻她躺在了这张古怪的椅子上。
来之前她有些犹豫。那个疼痛的根源,似乎已经模棱两可了。其实,昨夜的痛是否真的来自于一颗牙齿,她自己都不能完全确定。她指认着某颗牙齿,无非是需要把虚无的疼痛安放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是牙医,最终敲定了这个位置。昨夜,他打开了卫生间的浴霸,炽热的光照耀着她大张着的口腔。“张大些,再大些。” 牙医用手卡住她的下颌。暴露的口腔,令她倍感羞辱。她觉得自己的疼痛迅速转移了,流窜到某个永远无法确认的部位。颌骨在隐隐作痛,发出细碎的咔嚓咔嚓声。“就是它,一颗龋齿。” 牙医卡着她悲伤的脸说。她怒不可遏地挣脱出自己的脸,长发掩盖了她瞬间的愤怒。牙医没有觉察出她情绪的变化。在这个女人的口腔里,他发现了一颗龋齿,这让他萌生出职业的优越感。这个女人一年来在他心目中所有的矜持于是都瓦解了。因此,牙医以高高在上的口气向她指出了一颗龋齿所能造成的危害:牙髓炎,关节炎,心骨膜炎,乃至慢性肾炎以及全身的其他疾病。“这种细菌性疾病……”牙医用近乎傲慢的口吻说。这种细菌性疾病这样的句子令她难堪,仿佛一语中的地定义了她的生活。同时,那最终波及全身的后果,也令她不寒而栗。那时她的心理几乎崩溃了,不明白自己为何这样,赤身裸体,呆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被检测,并且被诋毁,生活中所有纠结着的哀伤,都凝聚在那颗糟糕的龋齿上。
今天早晨,他们在牙医家门前分手。她钻进出租车里,牙医扒在车窗外,敲打着车窗玻璃,叮咛她准时来医院就诊。她茫然地点了头,然后她赶到了学校。她是一名小学教师。在校门口,她遇到了送儿子来上学的前夫。前夫匆匆向她打了声招呼,一瞬间,那种无以复加的委屈又淹没了她。——她想起了牙医的这句术语。目送着前夫踌躇满志的背影,她怨怼地认为,这个人就是“这种细菌性疾病”的病灶,虽然如今已离她而去,却给她的生活留下了一颗巨大的龋齿。
儿子由前夫抚养,上三年级,正是顽皮的时候,中午和她一同在学校吃饭,该午睡的时候,却吵着要出去买雪糕。她神经质地烦躁起来。“雪糕会弄坏你的牙齿!”她恶狠狠地说,并且伸手卡住儿子的胖脸,把儿子的嘴掰开,检查起儿子的牙齿。儿子粉嫩的口腔令她茫然,她分辨不出那些牙齿的优劣,只是感到失措的慌乱。直到儿子大吼着哭起来,她才落寞地释放了儿子。
怀着这样的情绪,她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一共是四节课,却让她有筋疲力尽之感。放学的时候,前夫并没有来接儿子,他的母亲,她曾经的婆婆,一脸冷漠地从她的手里接走了孙子。儿子向她告别,走出很远了,突然回过头朝她龇牙咧嘴地做了个鬼脸——他在炫耀自己的牙。她也想回敬儿子一下,但嘴角牵动了一下,终究只是露出了一丝苦笑。这时她已经忘记了和牙医的约定。她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昨夜的效应此刻显露出来。她感到了身体的异样,毕竟,她是个离异了一年的女人。她在路边的橱窗里看到了自己,发现自己的衣服折皱很多。这让她一阵不安,仿佛暴露了巨大的破绽。她隐约记起了昨夜那个牙医凶猛的进攻以及自己本能的抵抗。她觉得自己的呼吸有些短促,并且有些轻微的耳鸣。她凝视橱窗里的自己,依稀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她回头张望,看到前夫正捧着一束明媚的黄玫瑰站在马路边仓惶四顾。恰在这时手机响起来,起初她并没有听出对方的声音,直到那个人理直气壮地要求她,她才恍然大悟。
“来治牙!”牙医斩钉截铁地说。
身下的这张椅子令她不安,她很容易就把它和记忆中的损害联系在一起。她曾经躺在这样的椅子上,张开双腿,根除掉自己的第一个孩子。那时,她刚结婚不久,怀上了第一个孩子,但却被诊断出了心脏病。医生说她并不适于生育,那样很危险。于是只有打掉。她躺在妇科诊室,和现在一样,同样需要暴露自己隐秘的洞穴,扩张,照射,将身体无望地呈现着。她身下的那张椅子,高大,冰冷,可以升降,唯一不同的是,有两根支架,用来恶毒地举起她的双腿,这唯一的不同并不能把它和眼下的这张椅子区别开,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强硬,不由分说,充满了机械与医学的暴力,能够迅速剥夺人的尊严。她觉得自己被这张椅子绑架了,被无形地勒索着。
被白色包裹的牙医与昨夜判若两人,甚至他的声音也在口罩后面发生了改变:“张嘴,别紧张。”——有股椅子的味儿。可是她反而更紧张了,双手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椅子的扶手。她的手指苍白、修长,指甲里残留着白色的粉笔末,右手中指的关节上还有一团批改作业时遗留下的红色墨水。牙医观察到了她的紧张,有些正中下怀的愉快,随即做出了令她吃惊的举动。他捧起了她的手,放在掌心,温柔地拍了拍。她感到突兀,心脏一阵抽搐。她似乎厌恶牙医的这个举动,但却用力地握住了对方的手。牙医在口罩后满意地笑了,发出被遮蔽的咯咯声。仿佛得到了许可,他终于肆无忌惮地探究起她来。她觉得,牙医的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自己的口腔。“很糟糕,嗯,很糟糕……”牙医的声音瓮声瓮气地回响在她的口腔里。他开始使用工具了,口镜,探针。一阵难以言喻的酸痛被这些工具激活,猖獗地蹦跳在她的神经上,然后直抵心脏。她不禁发出了呻吟般的呜咽。牙医却因此变得兴味盎然,饶有兴致地越发鼓捣起来。她的口腔里有一个焦点,仿佛是她神经中枢的神秘按钮,一经碰触,就能令她彻底崩塌。牙医持续地敲打这致命的地方,浅尝辄止,锲而不舍。他似乎是在考验着她能忍受多久,也似乎是在检验着自己能坚持多久。
她流泪了,完全是生理性的。每一下敲打都令她痉挛,大张着的嘴咕噜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她突然有了某种不可名状的兴奋,有种恶毒的摒弃一切的亢奋情绪风暴般地席卷了全身。她痛恨,同时也渴望这种施虐般的折磨。她认为生活对于她,就是一个反复施虐的过程。起初是心脏病,莫名其妙地选中了她,她因此被扔在了妇科诊室的椅子上,不得不掏空自己的子宫;她并不甘心,吃了三年的药,把自己弄成了一个浑身散发着苦涩的女人,然后,冒着生命危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她精心将儿子喂养到小学三年级,却被前夫带离了身边,为此她和前夫经历了艰苦的诉讼,但最终的判决依然是——剥夺。她并不是一个前卫的女人,除了前夫,她在昨夜之前没有和任何男人共宿过,她的道德观排斥婚姻之外的床笫之欢,但是她终究被生活强硬地改造了……一切都仿佛丧失殆尽,活着的态度,与生俱来的荣辱观,都呈现出一片狼藉。现在又是龋齿!“这种细菌性疾病”再一次将她扔在了毫无尊严的境地,被窥视,被玩味,被不由分说地侵犯。
牙医终于放弃了他游戏般的诊断,他决定填充那颗牙齿上的龋洞,仿佛是要给她身体的漏洞打上一个补丁。但她却断然拒绝了,粗暴地说:“拔掉!”她是脱口而出的,不假思索。“拔掉?”牙医再一次捉住了她的手。但是她的手挥起来,坚决地说:“拔掉!” “嗯,没有炎症,可以拔——也好,一劳永逸。”牙医执著地捕捉着她扬在空中的手,抓住,握紧,迎合着她。不错,一劳永逸,这正是她此刻的想法。
她被注射了麻药。注射前,牙医询问了她的病史,她隐瞒了自己的心脏病。她并不是有意要隐瞒,她只是感到厌倦,她不愿把自己想象得千疮百孔。麻药让她的知觉空旷。她感到口腔沉重,像是塞进了一颗铅球,仿佛有一个粗鲁的大汉,在她的嘴里伐木。她隐约觉得自己的骨头被撼动了,身体的一部分被连根拔起。
那颗龋齿终于出现在她眼前,带着一缕血丝,当啷一声,掉在一只金属托盘里。看着这颗脱离了自己的牙齿,咬着一团纱布的她,心情在刹那间抑郁起来。“要吗?”牙医的声音仿佛无限遥远。她明白他指的是什么,费力地表示出了她要。于是,拔掉的龋齿连同进入过她口腔的那些器械,被装进了一次性的盒子里。“这只盒子你带走,下次复诊时带上。”牙医突然变得有些冷漠了,恰如一个男人房事后惯常的那样不耐烦,也许是拔牙的过程让他回到了自己的职业角色中。他机械地叮嘱了她一些注意事项:不要做激烈的运动,勿高声谈笑,不要用舌头舐创口,两小时后方可进食,等等。总之,一切都需要暂时地改变,一切都乱了。她依旧躺在那张古怪的椅子里,发现自己已经被汗水浸透,身体像经历了一场肮脏的战争那样无力自拔,所有的洞穴都麻木并且凌乱。牙医还说了一些话,但她完全听不清楚了,耳朵里一片蜂鸣。她的脸色灰白,表情涣散,眼角的细纹在无影灯下浮现出来,似乎还在蛇游着蔓延,这令她的脸看起来仿佛正在不可逆转地龟裂。她可是真的并不年轻啦!牙医在内心感叹着。两人之间特殊的关系,使牙医忽略了眼前这个女病人的异样。
后来,她捧着那只一次性盒子离开了诊室。牙医追出来,塞给她一样东西。那样东西藏在一只装药片的袋子里,因此她很自然地将它当作了药片。她很疲惫,有些迟顿,连礼貌性的告别都没有,就迅速走出了医院。她是走得有些急了,仿佛要立刻摆脱什么,但是她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一阵快步后,只得在医院门前蹲了下来。
此刻已经是黄昏了,天边有一团乌云遮住了夕阳。
她蹲在路边,头垂在怀里,觉得自己像一块被压缩在罐头里的肉。她知道自己的姿势很不雅观。平时她非常讨厌蹲姿,但现在她身心交瘁,心脏的压力迫使她放弃掉内心的好恶。她蹲在那里,很萎顿,很哀伤。稍微缓过些劲儿,她就顽固地站了起来。一阵头晕目眩,她觉得世界有一瞬间是颠倒着的。此刻她愣了一下,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因为她在窒息中又一次看到了前夫的背影。那个熟悉的背影和全世界一同倒立着,在她眼里旋转了一圈,才脚踏实地了,但是依然在左右晃动,世界宛如波涛荡漾的海面。
果然是前夫。她略感惊讶,今天实在是蹊跷,他们居然第二次不期而遇。正当她恍惚的时候,前夫恰好回头了,一眼就看到她。他们距离并不远,也就十来步的样子,但彼此的眼神却仿佛是无尽的眺望。很显然,前夫有些尴尬,他在犹豫,是不是该过来打个招呼。她却异常平静,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前夫胸前的那捧玫瑰上了。那一团很大的黄色,完全充斥在她的视觉里。她想,他就这样捧着这些花在街上乱转吗?他不是这样的人啊,以前鲜花是会令他害羞的,他是一个耻于把自己和华丽联系在一起的男人。她嘴里紧咬着的那团纱布,已经被唾液浸透了,药水的气味混合着血腥,辛辣无比,呛得她咳嗽起来。前夫终于走了过来,不过抢先到达的还是那捧黄玫瑰。他说:“很巧啊?”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该告诉他自己刚刚拔了一颗牙齿,她有这样的愿望,甚至还很迫切。但是她欲言又止。
这时一个年轻女人从她身后冲了上来,几乎是蛮横地插在了他们之间。于是,前夫胸前的那捧花转移到了这个女人的怀里。她立刻就明白了眼前的局面,手捧鲜花的前夫,是在等这个女人。女人对前夫热烈地说着话,不经意地一回头,就让她感到了自卑。她觉得这个女人真年轻啊,完全还是个孩子,你看看,她还穿着那种有卡通图案的裤子!可是这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她却没来由地火了,隔着年轻女人,突然厉声向前夫吼道:“你还有一点责任心没有?你就是这样带儿子的吗?你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你也做得出……”她的情绪不可自控,麻木的口腔让她发出的每一个字都显得像石头一样浑浊有力。她觉得快要上不来气了,只能一边吼一边用力呼吸。结果,那团浸着血的纱布从嘴里飞了出来,居然飞过年轻女人的肩头,跌落在那捧玫瑰花里。年轻女人惊叫了一声。这令她无地自容,同时也加剧了她的冲动。她继续激烈地斥责:“你知道儿子的功课已经有多糟糕了吗?你现在应当呆在他身边,那才是你正确的地方!你不愿为他负责,为什么当初要抢走他?”前夫的脸憋出了紫色。他不能理解她此刻的态度。他从未见到过她如此暴怒的样子,即使在他们关系最恶劣的时候,她也没有这样威风凛凛过。
手捧鲜花的女人吓坏了,试图拉着前夫离开,但刚一抬脚,就被她凶狠地阻挡住。她拦在他们面前,咄咄逼人地迫近年轻女人的脸。当她们近距离对视的一瞬间,她被年轻女人眼里那种不易觉察的轻蔑给激怒了——她轻蔑什么?她懂什么?一个穿着卡通图案裤子的小孩!她将自己所有的愤恨都归咎于这个年轻的女人。虽然残存的理智告诉她,自己并没有任何权利。但是这又如何?即使对方真的无辜,此刻她也需要将自己的愤怒有所针对地倾泻出来。有那么一刻,她似乎平静了下来。其实她是在酝酿。她酝酿着的,是一口含着血的唾沫。她觉得自己的口腔里有一个源泉,那是她身体里的洞,所有的一切都从那里汩汩流出。当她觉得这口唾沫已足够充沛的时候,她对准年轻女人的脸吐了出去。但她没有勇气去看自己这口唾沫达到的效果。她在一瞬间吐空了自己,明白自己做了不可思议的野蛮的事情。她拔脚欲走,刚刚转身,却瘫软在地。她觉得自己的胸腔有种紧缩感,随即一种压榨性的疼痛贯穿了她的肺腑。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心脏病突发了。虽然她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诊断出了这种疾病,但从来都没有发作过。疾病始终只是张着隐形的翅膀威胁和恐吓着她,让她活在阴影里。时隔多年,今天,它终于降临了。她甚至有种千回百转的感慨,禁不住泪流满面。
她发现自己的四周迅速聚拢了一群人。最早贴近她的,是一个老年男人,年纪很大,几乎可以做她的父亲了,还穿着那种竖格条纹的病号服,看来是医院的病人。老头将她的身体搬成侧卧的姿势,用自己的腿担在她的脖子上,以与实际年龄不符的洪亮嗓门大声对围观的人宣布:“我要给她急救。”然后,居然伸手去松她的腰带。她的意识正在逐渐丧失,那只扯在自己腰带上的手却令她骤然复苏了,她神奇地坐直了身子。令她欣慰的是,此刻前夫向她伸出了援手。他从身后抱住了她,双手插在她的腋下,协助她站了起来。那个老头立刻大声疾呼道:“你这样做会要她命的!她必须就地躺着!”老头是在警告前夫。尽管她知道老头言之有理,指出的是一个重要的常识,但却非常反感老头的态度。因为当前夫的手插在她腋下的一刹那,她感到了汹涌的伤心。可是她多么渴望这样的有所依托的伤心。所以她反感老头的干涉,仿佛对方是要驱散自己的希望。她配合着前夫,努力站稳身子,怀着一种优胜者的近乎炫耀的情绪,向围观者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她要表达的立场是——他们,她还有前夫,他们是一个共同体。
一切宛如奇迹。在前夫的搀扶下,她居然缓步向医院走去。好事者尾随着他们。那个老头兴奋地大张着嘴,喋喋不休地说:“看着吧看着吧,她就要死了!她走不了几步啦……”他甚至大声数着她的步子。还有,那个年轻女人,收拾起所有委屈,脸上挂着残留的血沫,手捧着黄色的玫瑰,顺从地跟在身后——她都有些怜惜起这个年轻女人了。以她为中心,一支队伍形成了。在她的意识里,这支队伍有种隐隐的庄重之感,仿佛浩浩荡荡,如同一场肃穆的仪式。她被自己感动了。她觉得自己是用生命为代价进行着一场跋涉,好像童话里的人鱼,每一步,都走在刀刃上。她已经感觉不到心脏的压力,某种玄秘的力量替代了心脏,支撑着她的肉体。她动情地将头依靠在前夫的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原谅了生命中的一切,非常甜蜜。
眼前出现了医生。她有片刻的迷惘,任由医生们把她放在了一张推车上,但是她很快惊醒,急迫地去寻找前夫。当她终于发觉自己已经无法支配自己的身体时,那种巨大的无可转圜的残酷的无能为力铺天盖地而来。
四周都是忙碌的白影,有人在往她的舌下塞药片。她依稀看到了前夫,很模糊,像是映在橱窗里的影子。她看到,有一团朦胧的黄色依偎在前夫的怀里。前夫在抚慰着那团黄色。她都能想象出前夫的神态了,一定是一脸的小心,低声下气。想到这儿,她甚至想笑了,恍惚着在心里嘀咕:“这下,你可是有了大麻烦了……”
依然是除了一双眼睛,他的脸基本上被白色遮盖住。无影灯下的白色非常耀眼,有种趾高气昂的光芒。
看到她苏醒过来,牙医如释重负地捂住自己的脸。
事实是,她连那张古怪的椅子都没有下来,就直接昏厥了过去。心脏病发作得令人措手不及,几乎没有任何先兆。当时牙医完全沉溺在某种违背医学原则的兴致勃勃中,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变化,当那颗龋齿刚刚脱离她的牙槽,她就不省人事了。
牙医被吓坏了,对于自己的轻率追悔莫及,他明白一场置人死亡的事故意味着什么。她被送进了抢救室。整个抢救过程牙医都守在旁边,他在忐忑地祈祷之余,也目睹了一个最奇怪的昏迷者所表现出的症状。她面色苍白,嘴唇发紫,仿佛化了浓艳、奇异的戏妆,而且,丧失了意识的她,居然有着丰富多彩的夸张表情,时而哀伤,时而喜悦,有那么一刻,她还绽露出和煦的微笑,这一切,都令她宛如一个正在表演的演员,而她头顶的无影灯,也恰如舞台上孤独的灯光。其他医生无暇他顾,只有袖手旁观的牙医捕捉到了她的每一个表情。牙医不能理解她的表现,他的医学知识不足以为他解释这其中的奥秘。牙医把这一切当做自己的幻觉了,他想自己一定是被恐惧搞晕头了。
她苏醒过来,仿佛穿越了一条无尽的隧道。这是一条环形的隧道,光滑,紧迫,却又布满粗砺的阻碍,如同母亲的产道,从生到死,周而复始,终点即是起点。她的意识顺畅地与昏迷之前的记忆对接起来。她明白自己经历和臆造了什么。她的心脏一度停止了跳动,在那条死亡的通道上她洞见了自己内心所有的秘密。她的确是被掏空了,就像在谵妄中奋力吐出那口血水、向整个世界唾弃一样,此刻,她变得空空如也。
她继续留在医院里治疗。第二天,她的同事来看她。这个同事正是她和牙医的介绍人。她一眼就看出了这里面的原因,她知道,牙医把同事叫来,是基于一种怎样的逻辑——喏,看看你给我介绍的人吧!牙医很愤懑,他不能原谅,自己结识的这个女人居然有严重的心脏病——他本来是很认真的!他觉得自己被欺骗了,有种蒙受损失后的追究心理。同事带来了一束花,令她吃惊的是,那居然是一束黄玫瑰。由于受到了牙医的埋怨,同事的情绪有些低落,只是简单的慰问了她几句,就匆匆告辞了。临走前,同事对她说起了她的儿子:“你儿子今天没来上学,你通知他们了吗?”她知道,同事所说的“他们”,是包含着她的前夫的。在这座城市,除了“他们”,她再也没有其他的亲人了。如今她出了事情,在所有人看来,最应当被通知的,就是——他们。一念及此,她本来空空如也的心立刻灌满了悲伤。她始终一言不发,像一个真正的病人那样虚弱。
同事走后,牙医来到了她的身边。他依然把自己包裹在白色后面。他这样的装扮,令她根本想不起他真实的面貌了。他很专业地翻了翻她的眼皮,又将手指搭在她脖子的动脉上测了测,俨然一副主治医生的派头,尽管他只是一名牙医。接着牙医又看了看液体瓶上贴着的配方,然后将一只药片袋子塞在她枕边。那里面放着的,是一件礼物吧,也许是一枚宝石戒指。牙医决定用这枚戒指结束他们一年来的交往。结果是,这只袋子和她昏迷中经历的某个细节重叠了,她不由得一阵心悸,有种梦魇走进现实的惊惧。同时,这也令她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它呢?”她说出了苏醒后的第一句话。“什么?”牙医疑惑不解,而且,他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去搞明白。“我的牙,我的——龋齿。”她严肃地说。“牙?”牙医愣了片刻才回过神来,他有些恼火,仿佛听到的是一个不可理喻的问题,所以没好气地质问道:“你还要它干什么?不过是一颗龋齿!”她深深地吸了口气,这一刻,她才充分感觉到了自己口腔里缺失了某样东西。当她开口的时候,那个豁口仿佛刮过了一阵风。她在这阵风的伴随下,空空荡荡地说:“它是我的牙,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尽管,它是一颗龋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