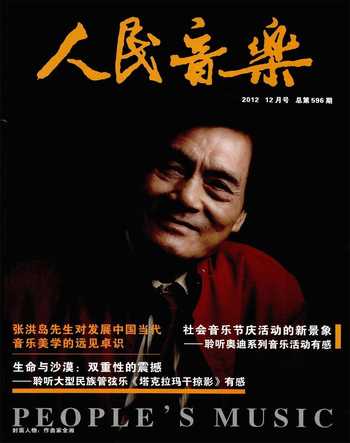刍议音乐的听与看
古今中外音乐理论体系中,对音乐的本质属性形成了一个共识——音乐是诉诸于听觉的艺术。孔子说:“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①荀子也说:“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②这里的“盈耳”与“养耳”都是两位圣贤充耳闻到音乐之美后发出的赞叹!法国哲学家、作家卢梭(J.J.Rousseau,1712—1778)说:“全世界的人听到美的声音都会得到满足,但如果没有旋律的习惯变化赋之以生命,单凭这种满足是引不起喜悦之情的,是不会成为高度的精神享受的。”③卢梭所指的“美的声音”显然不是特指音乐,而是指除音乐以外的所有能够引起人的快感的声音。如婉转的鸟鸣、恋人的笑声、自然界引起人的瞬时美感共鸣的风雨雷电等所有的声音,甚至一些喧闹声或噪声也会被有些精神囿于短暂特殊情境的人认为是“美的声音”;而“旋律的习惯变化”是指由作曲家(包括那些大量的、不知姓名的民间作曲家)的灵感“赋之于生命”的“美的声音”。卢梭认为,只有能称之为音乐作品的“美的声音”,才会引发人们“满足”后的“喜悦之情”,才能使人们得到“高度的精神享受。”而后者,正是音乐诉诸于人的听觉所获得的。奥地利音乐美学家、评论家汉斯立克(E.Hanslick,1825—1904)说:“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对抗,追逐和遇合,飞跃和消逝,——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使我们感到美的愉快。”④汉斯立克作为“自律论”音乐美学流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否认音乐中思想性和情感因素的存在。他所说的音乐“不依附、不需要”的“外来内容”正是指音乐的思想性和情感因素。在他看来,音乐那独特的美,只“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换言之,音乐无需所谓的思想性和情感因素等“外来内容”的干扰,仅依赖于其“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对抗,追逐和遇合,飞跃和消逝”就足以“使我们感到美的愉快”啦!而这愉快的情感体验,是人类被作为审美客体的“乐音的艺术组合”所感染而引发的、仅属于人类情感泛起的涟漪而已,与由“乐音的艺术组合”所构成的音乐毫无关系。无论汉斯里克所鼓吹的“自律论”音乐美学观如何摈弃音乐艺术内涵的思想性和情感因素,但他十分肯定地认为“音乐所特有的美……存在于乐音的艺术组合”这音乐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中,而“乐音的艺术组合”正是触动人类大脑听觉神经而产生“优美悦耳的音响”的音乐。
美国当代作曲家艾伦·科普兰(AaronCopland,1900—1990)说:“在有生气勃勃的听众的情况下,音乐才能真正地生气勃勃。全神贯注地听、有意识地听、用自己全部的智慧听是对我们推进这门人类光辉的艺术的最起码的要求。”⑤科普兰干脆直截了当地要求人们“用自己全部的智慧”去聆听音乐;而且只有“用自己全部的智慧听”,音乐的听众才称得上“生气勃勃的听众”。
请注意,科普兰在这里还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在“生气勃勃的听众”面前,音乐怎样“才能真正地生气勃勃”?音乐作品作为作曲家智慧的结晶,怎样才能“生气勃勃”地展现于“生气勃勃的听众”面前?显然,这就需要另一群音乐家——指挥家、歌唱家与演奏家用“生气勃勃”的表演来展现“生气勃勃”的音乐。于是,此答案便引出了音乐本质属性的另一面——音乐表演。
音乐既然是诉诸于听觉的艺术,那么就必须依赖于指挥家有序地组织起“乐音的艺术组合”、依赖于歌唱家与演奏家以“乐音的艺术组合”为媒介将作曲家脑际中“汨汨流淌”出的美妙乐思(这乐思的物质载体即由复杂的符号体系构成的、默默无声的乐谱)以创造性的表演转化为“真正地生气勃勃”的“乐音的艺术组合”,呈现于“生气勃勃的听众”的耳际,以最终完成音乐的表现功能。音乐的本质属性也由音乐表演的再创作得以体现和确立。
然而,作曲家脑际中的美妙乐思只是他们对世间万象充耳闻之的艺术性再造?指挥家、歌唱家与演奏家在有序地组织创造性表演的过程中难道没有打翻过他们内心中蕴藏着的“酸甜苦辣咸的五味瓶”?“真正地生气勃勃”的音乐只是停留在诉诸于听觉的演绎阶段?听众仅凭“全神贯注地听、有意识地听、用自己全部的智慧听”就会变得“生气勃勃”?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说:“音乐用作内容的是主体的内心生活本身,目的不在于把它外化为外在形象和客观存在的作品,而在于把它作为主体的内心生活而显现出来,所以这种表现必须直接为表达一个活的主体服务,这个主体把他自己的全部内心生活摆到作品里去。人声的歌唱尤其如此;器乐也多少是如此,它只能凭熟练的艺术家以及他的精神方面和技巧方面的本领,才演奏得出来。”⑥黑格尔所说的“主体”应指的是指挥家、歌唱家和演奏家,还包括音乐的鉴赏家——听众。音乐的内容是凭借“主体的内心生活显现出来”的。黑格尔强调,要表现音乐那丰富多彩的内容,“主体”必须“把他自己的全部内心生活摆到作品里去”,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作品的再创作中。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借助熟练而精湛的演唱、演奏或指挥技巧,将作品的内涵表现得更加完美,更加“真正地生气勃勃”。而“主体的内心生活”当然是指“主体”在现实社会活动中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而逐步积累的生活阅历——逐步形成的艺术修养和品位——由生活阅历和艺术修养的融合逐步升华的精神境界。这一切无疑都是“主体”对世间万象的悉心观察和体验的收获,而不是仅凭听觉所能得到的。因此,在作曲家对世间万象艺术性再造时生成的美妙乐思中;在指挥家、歌唱家与演奏家进行再创作时内心打翻的“五味瓶”里,一定内含着丰富多彩的视觉印象。这视觉印象与听觉印象一样,不仅是作曲家创作灵感的源泉,也是音乐表演家们进行二度创作时再现和激发作品思想和情感内涵的依据和动力。
生理学认为,光作用于视觉器官,使其感受细胞兴奋,其信息经视觉神经系统加工后便产生视觉(vision)。通过视觉,人和动物感知外界物体的大小、明暗、颜色、动静,获得对机体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各种信息,至少有80%以上的外界信息经视觉获得,视觉是人和动物最重要的感觉。人们在现实社会活动中都有这样的体会:当嗅觉受到饭菜香味的刺激时,大脑会根据曾经的饮食经验(此时应有味觉的介入)来判断香味的类别,此时,无论你是否看到了饭菜,其香味类别的判断结果总是以曾经的饮食经验的视觉印象加以确定。“盲人摸象”的典故告诉我们,失去了视觉感知的触觉印象,只能是以偏概全的假象。另外,在人们生活中的有意无意间,心理活动中的视觉印象总是“统领”着听觉印象。如,当我们听到幼儿园孩子们的欢笑声时,他们的形象是通过听觉产生的视觉联觉而感知的,这种视觉联觉是借助于我们以往若干次对学龄前儿童的特征及其玩耍形象的视觉记忆而生成的不确定印象;当孩子们进入我们的视线时,由于实时视觉印象的介入,先前由听觉产生的视觉联觉会瞬间消失,不确定印象被立即修正,被孩子们可爱而顽皮的样子所吸引而形成的视觉印象占据知觉的主导地位,听觉悄然退居其次。这一知觉心理反应在音乐审美心理活动中屡见不鲜。如我们聆听某音乐作品的录音时,听觉占据着主导地位;当我们观看同一作品的音乐会录像时,视觉便毫不客气地将听觉推向知觉的边缘而将知觉的主导地位据为己有。在音乐会现场,观众同样会有类似的知觉体验:舞台上,指挥家、演奏家或歌唱家们精湛的技艺和精准的情感演绎自然会使听众一饱耳福。然而这“一饱耳福”仅仅是由听觉感知贡献的吗?不然,“一饱耳福”之中必然包含着使听众“一饱眼福”的音乐家们与其精湛的技艺和精准的情感演绎相辅相成的仪态(包括体态、步态等)、神态乃至由仪态与神态折射的心态表现。否则,听众很难得到“一饱耳福”的满足。听众从来就不是闭着眼睛听音乐会的。特别是在当代,电视、互联网和电影等以视觉表现形式为主体的娱乐媒体,早已将音乐听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打造成了下意识的、以视觉知觉为先导的“音乐观众”。
走上舞台的音乐家们在表演中,不仅要使自己诉诸于音乐观众的听觉的技艺尽可能完美地展现出来,还要倍加注重培养并保持自己居于舞台的美好仪态、神态乃至心态。这是音乐家对自己更是对音乐观众的尊重。某些音乐家因不注重自己自然天成的或经表演修饰的仪态和神态的优美(指美学意义上的优美),或因表演中的失误造成了仪态和神态美的缺失。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缺失必然会干扰“乐音的艺术组合”“洋洋乎,盈耳哉”,“主体的内心生活”的显现也会因这种视觉干扰而难以“真正地生气勃勃”,从而进一步干扰音乐观众获得“高度的精神享受”的诉求。
不能否认的是,音乐表演中的仪态、神态乃至心态,是音乐家们为抒发音乐作品情感、传达音乐作品思想观念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譬如,指挥家对音乐作品内涵的深刻理解不仅必须以其敏锐的听力、无与伦比的记忆力和超强的乐感,也必须以其严谨、缜密、精准的指挥技巧与动作,热情洋溢的外在气度在歌唱家与演奏家们中间建立自己的权威和魅力,从而驾驭乐队并创造性地赋予“乐音的艺术组合”以鲜活的生命力。歌唱家与演奏家完美演绎音乐作品内涵也不仅凭高超的演唱、演奏技巧和充沛的情感储备,其规范的演唱演奏姿态,基于作品情感宣泄的需要而生发的恰如其分的夸张形体和表情(包括适度的舞蹈动作),与所表演的作品内容、风格相适应的化妆与服饰造型(这里包括角色造型与非角色造型)及不同凡响的精神气质等,毋庸置疑地构成音乐表演的两个不可或缺的互补性创作条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观点不仅适于“艺术音乐”概念所涵盖的音乐形式的创作与再创作(指所谓的二、三度创作),也包括“布鲁斯、爵士乐、狐步、探戈、乡谣、新民歌”以及“结合古典音乐、民族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的探索汇聚成的‘世界音乐与‘新世纪(或译新纪元)音乐”⑦等抒情性较强、表演形式接近于“艺术音乐”的一类流行音乐。当然,诉诸于视觉感官的各种元素是否恰当,如何避免过度诠释的“喧宾夺主”,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因此,当代的指挥家、演奏家和歌唱家们在音乐表演这一音乐作品的再创作中,不能仅奉献给当代的音乐观众以“听觉盛宴”,也可以用自己全部的身心奉献给音乐观众以“视听盛宴”。只有这样的音乐表演“才能真正地生气勃勃”,才能对得起“用自己全部的智慧”去聆听音乐“这门人类光辉的艺术”的“生气勃勃的”的音乐观众。
①吉联抗译注《孔子孟子荀子乐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②吉联抗译注《孔子孟子荀子乐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页。
③何乾三选编《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3页。
④?眼奥地利?演汉斯里克《论音乐的美》,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版,第38页。
⑤?眼美?演艾伦·科普兰《怎样欣赏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
⑥同③,第103—104页。
⑦金兆钧《光天化日之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1页。
谢力荣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