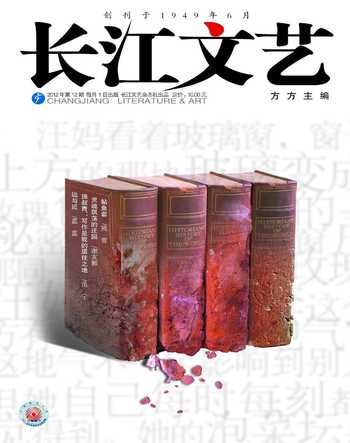远与近(8首)
蓝蓝
废墟
废墟里有着自由那
奇怪的阴影
在徘徊。在咳嗽
清理嗓子
它也迷恋可能的解放
所以,它也赞美。
但是,只赞美高度
在瓦砾和低矮的野草之上
深处的蛇悄悄游动。
盯着无数脚跟的盲目
爬上供品的祭台,花朵枯萎着
这是必然的枯萎。这是
必然的乌鸦驮来了成功者要求的黄昏。
这首诗或许写得太早,但已经太晚。
世界各处都在倒塌
那高大的殿堂。那废墟的主席台
还会重建,因为自由的阴影
在徘徊,咳嗽
在话筒前又开始清理嗓子。
我是谁
我不是一个,
不是三个。
我是你,
或者他。
我是两条线交叉的
那个点
至少。
远与近
人们奔向奇异之处,那指示着
现代生活的路标。
我爱我的老式电脑。我混乱的桌子。
我划着密密麻麻符号的破书。
我爱我失眠的床。那里有一个泵
启动一颗生锈的心脏,当它因为
破碎而差点儿松开抓紧世界的手
它重新擦出电闪——我旋转
再次你来。
带着春天给我的允诺
我爱你老式的爱,你的勇气那沉甸甸的
椅子。坐下——开始第一口呼吸。
语言和思想
有首东蒙民歌唱到:那些树上的叶子
争相落在人们的脚旁。
但有一次我忽然想:
这是为什么?
赫塔·米勒女士在童年的故乡
为她要学城市德语和罗马尼亚语感到迷茫
一棵乳飞廉的名字令她心慌。这小小的植物
或许应该有更正确的名字。
如此这般的例子很多。
语言的篝火需要柴禾。或许还需要
想象力的油。氧气。风,和必需的
寒冷与黑暗。
当它们燃尽——我是说
那些柴禾没有了。
是不是火就要熄灭?
仅靠语言活着的人们
是危险的。
天上会降下火种。的确。
这近似于神话,全靠幸运。
况且柴禾会被淋湿,会烧光。
而赫塔·米勒仍像策兰那样在用某种语言书写。
而树叶仍然在向人们身边飘落
——靠着大自然不慌不忙的信念。
还有:真实的火。
语言,这位苦恼的墨涅拉奥斯
究竟想要的是特洛伊的海伦还是
埃及的海伦?
“语言并不完全覆盖故乡。”她说。
我以为她是对的。
飘落的树叶也是对的。
——先生们,
在伦理学就是美学的法庭上
生活的陪审团会同意这些话。
2010年10月8日纪事
沉默的人们点燃了鞭炮
代替他们的叫喊炸响在北京的夜空
如果你能想到,沉默也曾经浇灭过火种
沉默也是铁栅栏的一根
——正是如此!
有一瞬间你站在窗口
望着烟花四坠的光芒,欢喜和悲伤
无疑在你心中升起一道耀眼的彩虹
有人愤怒,有人欢呼,有人叹息
孩子们在抱怨未写完的作业
而你慢慢回到桌前坐下,想着
明天的早餐吃什么
还有爱情的尖刺和秋日的静默——
你拿过针线,继续缝补
衣服上的破绽正如被炮仗炸裂的
漆黑天空。
无题
我们对温柔的渴求
我们被它粗鲁地统治。
多么猛烈的嘶喊和卡在喉头的窒息
在祈求我们的屈服。
幸福只在这般的顺从里
推开门,走出来。
梦
你上楼,下楼。你停住脚步。
为什么你从众人里回头?
年久的木楼梯嘎吱作响。人们脊背上
可怖的眼睛迟迟不愿意拐弯。但你走过来
俯身,伸出你的手拥抱被角落的孤寂
死死按住的你的女人。可怜的、幸福的女人。
滴落到你手背上的泪水泄露了
上帝那苦恼的破洞。
而你比上帝离她更近。再一次,她低声说:
——亲爱的,别走。
诗
爱。
你说:我爱。
你说:这仅仅是爱情。
你说:云彩。微风。
栅栏和水井。
你说:湖水带来了沉思。
一些词。
一些不同于他人的排列。
你写诗。
别人也用过。那同样的词。
然而:词就是政治。
话语就是。
爱的方式也是。
其中有了恐惧。
有了恐惧的对应物。
这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