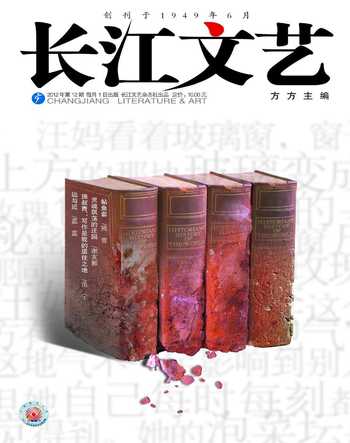家乡的河
叶文福
那时候的自然有人性,人在自然的怀里,如同在母亲怀里。那时候的人有自然性,自然在人的怀里,如同在爱人怀中。
1
你在我记忆里活泼
你在我记忆里沉默
有一个地方,是你歇息的深潭
只有我晓得,那是我心窝
——哦,家乡的河……
你流成我的泪水
你流成我的脉搏
我一生流的泪,其实是你的春水
我一生流的血,其实是你的秋波
——哦,家乡的河……
你只是忙着浇灌
我只是忙着收获
许多该想起你的时候总是忘却了你
待得想起你,已是泪水滂沱,已是血流成河
——哦,家乡的河……
一直想写点关于家乡的河的文字,但每每提起笔来,笔管里流淌的竟也不知是水,是泪,还是血。此情无寄相思苦,痛得三更叹夜长。
我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情感来思念家乡思念家乡的河……
我不知道该以怎样的语言来表述家乡表述家乡的河的美丽、温柔、深情和悲哀……
家乡的河,何等诱人的词汇!
如果说,想起家乡的土地就如同想起母亲的肌肤,想起自己儿时曾经匍匐过的母亲的肌肤,那么,想起家乡的河,就意味着想起母亲的乳汁,想起曾经浇灌过自己的母亲的汗水,想起曾经滋润过自己的母亲的泪水。
多少年来,我不敢思念家乡,不敢思念家乡是因为我不敢直面眼前的家乡,眼前的家乡总是让我一次又一次地目不忍睹。我无法不允自己思念家乡,思念家乡又不敢思念眼前的家乡,于是每每在需要家乡的热土和草木来慰藉浑身的伤痕之时,闭上眼睛,只得把思念的线头抛回儿时,去思念永远也回不来了的记忆中的儿时的家乡。
我总是害怕,害怕后人不知道以前的家乡美丽迷人的样子,以为家乡以前就是如今这般丑陋,这般贫困,这般困顿,这般无奈,这般扭曲和荒凉……
我总是害怕,害怕后人误解,误解我思念家乡时描绘的家乡的迷人景色是现在的风景,以为上了我一个不大不小的当。
几十年身居北国,多少阑夜披霜望月,数雁试风,无数重思念的挤压,如同地层里无数重板块互相挤压,使我终于有了这篇文章。我想借这篇文章对后人说:
后人,你们看见的眼前的我的家乡以前不是这个样子,请你们跟着我的思念一起走进我儿时的家乡,那是真正迷人的家乡……
2
不生于江南,不长于江南,母不在江南,父不在江南,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品味烟雨江南的内在蕴涵的。
烟雨江南的蕴涵到底是什么?景色?滋味?谁也无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但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品出点味儿来。
杜牧有诗名《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因为山西有杏花村酒,于是一直以来就有争论,这个杏花村到底是在山西还是在江南?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实,这并不是个难题,我可以肯定地说,杜牧指的这杏花村是在江南。因为:
1. 只有江南的清明时节才是雨纷纷时节。北方的清明时节正是几乎年年都出现的掐脖子旱时期。北方的农谚说:“春雨贵如油,夏雨遍地流。”既然“贵如油”,当然就没有“雨纷纷”了。
2.清明时节也是江南的牧童放牛的最佳季节。在北方,清明时节还冷着呢,冰天雪地,不可能到野外去放牧。
3.杜牧一生尽在江南转悠,压根儿就没到过山西。
4. 或者干脆说,其实就没有什么具体的杏花村,只不过是泛指,用以点染烟雨凄迷的江南阳春景致而已。
我的家乡可算得上是标准的江南。
所谓标准江南,想来想去,大约也就是——山好,水好,气候好。
山好——有山就有树,就有草,就有水,就有竹,一年四季郁郁葱葱。
山多高,水就多高,燕语莺歌,蜂飞蝶舞,獐麂■,蛇蝎鸣虫,无命不有。
水好——随你在哪里挖一镢头,清粼粼的泉水立时如活泼泼的歌声涌出。那水是清冽得生甜的,是冬暖夏凉的,是从你指缝滴落时你都以为是爱人跌倒而心疼的。
气候好——四季分明,该热则热,该凉则凉,该冷则冷,该爽则爽。嘴里喊热也能忍,阳气生刚;手上搓冷也能受,冻能除病——是人类生存和居住的最理想的地域。
3
从幕阜山的云缝雾罅中流出来两条河,一条从我家村庄东边的村头流过,一条从我家村庄右边一箭之地的田畈上流过。两条河在村后的柳林里汇成一条河,这时才有了一个小孩儿的名字——泗水河。泗水河在柳林里拐一个急弯,把被称之为小汉口的汀泗桥一分为二,擦山而过,径往长江。
我们村就坐落在两条河中间的白羊畈上。
我们村就坐落在两条河汇合处的柳林里。
所谓畈,就是小平原。两条河夹着个小平原,中间有大大小小的山。所谓山,到了平原上的山,也就失去了高度,失去了险峻,变得十分平缓,十分舒展,十分优雅,像一局没下完的残棋。
满畈都是稻田,这是我们村最上等的良田,是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我们对这片良田的熟悉和亲爱就如同指纹。再往南,叶家岭上是松,是竹,是柳,是地。除了从南面叶家岭上可以看到我们村的一色青砖老瓦之外,从其它三面看我们村,都只能看见一片树林,其中最多的是柳树。春天,从远处望我们村,一片柳烟袅袅亲切而动人。
两条河像围巾一样围着我们村,从汀泗桥到我们村,不管是从东边去还是从西边去,你都得过河,你都得过桥。
东边的是石板桥,九礅十孔,桥礅桥面,一色的青石板,桥面是两块大约30 —— 40厘米宽的长条石,桥礅很高,每孔大约有10米长,过桥还很需要一点胆子。只有两孔桥下的河床里有水,其他的桥孔是防洪的。
西边的是石拱桥,三孔,只有两孔河床有水。石拱桥十分精致,小巧玲珑。假如小河是一条琴弦,小拱桥就是一个琴码,在小拱桥上听河水潺潺,那就是在听音乐。小河两岸长满了蒲草,草岸平缓,舒展,小草们像音乐厅里的听众,在静静地听音乐之声。还有小草长长的手臂随碧水流波摇曳,有谁能说,那不是贝多芬的手呢?还有一孔没水的地方,是我们放牛娃夏天放牛时躲着歇凉吃黄瓜的天然帐篷。
我们村在一个长形龟背上,村里栽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有松,有柏,有檀,有栗,都是古树,几乎都有合抱之围,树上有许多苹果大的小洞,都是各类小鸟的窝巢。其中脚板林有两棵枫树,分长在进村的大路两边,两棵树几乎一模一样,三个大人才能抱住。虽隔着一条大路,上面却有许多枝叶交织在一起,雨里风中,仿佛情话呢喃,所以家乡有民歌唱这两棵树:
白羊畈,几十里,
叶家的枫树嘴对嘴。
像兄弟,像姊妹,
过细一看是夫妻。
4
但栽得最多的还是柳。
柳爱水,无水不柳,无柳不水。
我们村世世代代,大人小孩,有事没事,随手就插一枝柳。棒槌落地也生根的土地,柳一插就活。不但活,还活得十分滋润。柳是不进宫的西施,柳最美,美在水边,长丝如纤纤之手,总也在浣纱;柳最美,也最贱。所谓贱,也就是生存能力最强。柳是农家女儿,有一把糠就能熬,没一把糠吃野菜啃观音土也挺得住。不但挺住了,还是最美的。
柳柳柳
江南酒
人间不见天上有
如果盘根问底,我们村或许就是柳的故乡。
我仿佛这才想起来,难怪我们姓叶,原来我们属于大自然,我们是大自然中一个最大的家族,我们插一枝柳就是生下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儿。
西施魂
王嫱手
黛玉春心嫦娥袖
柳最是多情,阳春三月,柳把我们只能感觉无法看见的相思幻化成迷人的柳烟。相思是什么样的呢?柳让我们看见了——哦,相思是这样的多情,这样的柔美,又这样的变幻无常。
远似烟
一抹清淡几许愁
近如梦
万缕相思一茎柔
柳有好多种,有大叶柳,小叶柳,其实杨也是柳的一种。我所说的家乡柳最多的是垂柳,也就是美人柳。
美人柳简直就是天生的美人。不管她是在柳林里,还是在河堤上,不管是几年的新柳,还是几十年上百年的老柳,不管是在雨里,还是在风中,不管是在阳春三月,还是在数九隆冬,她就随意站在那里,那长达几米的柳丝,都要惹得你无尽地眷顾,无尽地留恋,无尽地牵挂,无尽地相思。任随你是哪一路英雄,一到美人柳面前心就醉了,就迷茫了,那长长的柳丝你不知道是美女的长发还是细腰在你眼前款款摆动,打乱了你心里的节奏,你必须随她而摇。
是的,柳是树中的美人,更因为我们珍爱她而美得有了人性,美得成了人中的美人。
两条河从山中迤逦而来,曲曲弯弯几十里,河堤上全是密密的柳树,且大多是合抱的老柳,有不少地方依着河堤就是一片柳林。柳是真的犹如一路美人,将自己的妩媚与多情尽献给爱细腰如细柳的楚王。而河水则果然如同楚王,波心荡柳,巡视和欣赏着每一位美人之袅娜,以自己的碧波,把所有的美人都记在心里,在一路美人浓荫密爱的庇护之下,荡荡然推波而去。而柳却不走,柳以她独特的个性眷顾着这方土地。
最美的柳是河边的柳,就象一袭袭美人,自由自在地或者说是懒懒散散地依在河边,怎么歪着斜着都是美。长长的柳丝拖在河里,随波荡漾,说是美女在濯发,在浣纱,在抚琴,怎么说都有理。
儿时放牛,总也不由得蹲在河堤上,望着河水,望着碧波中的柳影发呆,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现在才想通了,我想那楚王也是不愿离去的,你看那拐弯处,河水静静地依在深潭里,纹丝不动。潭很深,最深处有三人深,藏在这么深的潭里,不是不想走么?但你不走,岁月要走,最终还是走了,只剩了柳——
柳柳柳
江南酒
不知君见否
村前后
溪左右
故乡处处有
江南酒
柳柳柳……
家乡赤壁是个县级市,我前后看了四十年,看了多少届领导。每一届领导上得台来,都有宏图大略,这位喜欢松,全县栽松,那位喜欢桉,全县拔掉松,一律栽桉,再来一位喜欢白杨,全县拔掉桉,一律栽白杨。几十年来,栽来拔去,拔去栽来,路边街边,永远是香肠粗的小树苗苗,下面还涂着白灰,还裹着稻草,一副很受人爱怜的样子,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有一年,一位领导上台,我认真写了一份建议,希望能开发和发展旅游业,远山栽竹,近山栽茶,路边插柳。把柳变成家乡特产,把家乡变成名副其实的江南柳乡。可是人家根本不当回事,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增加GDP,召来一个火力发电厂,就在县城边,就在赤壁水库旁。又建了印染厂,造纸厂。后果如何呢?GDP是上去了,政绩有了,官阶也提了,只是这些年来,每次回家乡,看见每栋楼都在灰溜溜地呻吟,几乎都活不下去了。
当我在山西,在忻州,在黄土高原上,看见当年光秃秃的原野,现在竟有那么多两人才能抱住的美人柳,叫我怎能不落泪?
只有左宗棠这样的卓越人物才识得了柳!
是呵,楚王走了,只有柳,只剩下柳——原来这里的子民才是柳。
柳是最贱的,也是最美的。
是呵,柳,柳,柳,江南酒,人间不见天上有……
5
两条河在我们村后合流,风水先生说这是双龙护珠,是藏龙卧虎之地,上好的风水。我对这些倒不在乎,只是我们村的自然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两条河到了我们村后的柳林子里,已然没有了河堤。天晴时河水在河床里,一下雨——哪怕是下一阵儿雨——河水就漫溢出来,在柳林里变成无数条小菜花蛇样的溪水,大大小小,晶莹剔透,调皮可爱,在草丛里乱窜。这时候如是打着赤脚在柳林子里趟水,那实在是如同在天堂里过日子。柳林里高低不平,深处到小腿肚子,浅的地方连脚背都淹不住。水牛们在浅水里吃草,用不着管。我们则在柳林子里疯狂地玩儿。可惜那时候只是贪玩,在柳林子里打水仗,玩不出质量,品不出江南的无穷韵味。
河边的老柳树蔸半边在岸,半边在水,根底下被河水冲成半人深的潭,一个树蔸里可以藏十来个孩子,因为河床几乎都是沙石,十分干净,成了我们捉迷藏的上佳选择。躲在树蔸里,只把头伸在水面,数不尽的鱼星子在眼皮子底下游来游去,伸手一捧,以为能捧好多,其实不然,鱼星子动作更快,一闪身改变了方向,又悠哉游哉,在你眼皮子底下看你的热闹,捅你的胸脯、下巴。
河里几乎到处都长着鱼草。鱼草有好多种,有的扁扁的,像韭菜,有的像紫藤,几米长。鱼草不但鱼爱吃,猪也爱吃,我们一大半猪草都是在河里捞的。那时候养猪不成规模,大多数家里只养一头猪,鱼草长得比猪吃得快,怎么捞也捞不尽的。
哎,如今回忆起来,到处都是遗憾。像鱼草,我们村的孩子们,几乎人人脱口就能说出好多名字来,我就不能。不是我笨,是母亲管得严,下河的机会比别的孩子少多了。几乎全村的男孩子,一个猛子扎到河里,再出水时,脚下踩水,手里肯定高举一条不小的鱼。我就不行,就我一个人不行。
但我也不是全不行。母亲管不着的时候太多了,尤其是夏日放牛,几乎一上午一下午地泡在水里。我的水性虽不如人,但玩水的能耐足够。
夏日中午,赤日炎炎,路上的土都烫脚。大人们都躲在家里睡午觉,河里、柳林里就是我们孩子们的天下。水牛在河里浴水,不用管。我们或者在河堤的柳荫里,或者在拱桥的桥洞里,铺开骑牛的麻袋,看小人书,打扑克牌,下石子棋,或恣意玩闹。吃着从邻村或从汀泗桥三八妇女生产队里偷来的黄瓜、西红柿、香瓜、菜瓜。谁觉得热了,往河里一蹦,凉透了才湿漉漉地光着屁股爬上岸来。
村东的水码头旁边,是一段细沙平平的河床,简直就是天然的游泳池。三伏天,只要是晴天,一到下午,全村大人孩子,几乎都到这里来玩水,不下水的妇女或老头老太太,也站在码头边的老枫树下,小溪边的青石板上看热闹。码头的青石板铺得很是整齐,一直铺到两边的路上,好多老头老太太把手工活、针线活都搬到枫树下来做,边歇凉边做活,边看孩子们在水里尽情地闹腾。
6
两条河并不算大,但在我们眼里却是大河。我们河里游的可都是长江里的鱼。这不奇怪,北边四十里外就是长江,小河通江,满河形形色色的大鱼小鱼,青草鲢鲤,鳝虾龟鳖,甚至畈上的、田里的鱼都是从长江里上溯而来的。特别是每年春上,春子鱼上水,满河上下黑压压的,清一色的春子鱼,连一只虾也没有,连一只别样的鱼也没有,真叫得上是声势浩大。春子鱼是一种特别小的鱼,最大的也就2厘米长,而且长不大。它味道鲜美,把它晒干,储存起来,凡打汤下面条,放上一撮,那味道就鲜美极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人们并不像现在人们的心态。看见这么多春子鱼到小河里来了,并没有一丝赶尽杀绝的想法。男女壮劳力们都忙春耕去了,只有村里的老太太,每天吃过晚饭之后,坐在河边小板凳子上,在那种作蚊帐的夏布扳罾上撒一把米饭,摇着蒲扇,一会儿拉一下,这一下就有好几斤,个把小时就拎回一小桶回来。每家每年都晒一点春子鱼,够吃就行。
许多时候又觉得两条河很小,不仅小,而且小得如同身边的宠物狗宠物猫什么的,甚至说得上是一个咿咿呀呀学语爬床的婴儿,她活泼可爱,清纯亮丽,是我们中间的一员;她温顺贤良,诚恳无欺,从不伤害任何人。有些年头雨水过多,她也发洪水,但也就淹了岸边的稻田,几天就退去了,从没有过恶行泛滥。一路虽然有不少深潭,但从没听说淹死过人。
河不仅在河里,她还能延伸,延伸到田里。
记得小时候在田塍上放早牛,屁股上总是吊一个鱼篓。牵着牛一面走着,眼睛却在田塍两边的田里顾盼。那时候稻田里的水,都是从河上游的土堰上引来的,所以田里有鳝鱼,有泥鳅,有秧鸡,有鹌鹑,有布谷鸟,有大田螺,有小田螺,都能吃,都好吃。鳝鱼喜欢在田塍边的稀泥里钻一个直直的洞,傻傻地躺在里面。洞有两个明显的口子,一大一小,只需用两手的中指从两头堵住,一下子就可以从洞里拖出来。不过鳝鱼身上滑溜溜的,如果不会抓,它一下子就从你手心溜走了。只是农家孩子都会抓,一抓一个准,鳝鱼一上手就没法溜掉。一个早上回来,鱼篓里要是没有十来条鳝鱼就叫晦气。
当然,不只是有鳝鱼。
因为所有的水田都是连着的,稻子随时需要根据生长的具体情况灌水或排水,所以每一丘田都有进水缺口和出水缺口。因为活水长时间的冲刷,每一个缺口下面大大小小都有一个凹坑。这些凹坑简直就是百宝箱,里面几乎什么鱼都有。小鱼星子当然没人理会,时常就会突地跳出一条比筷子还长甚至两筷子长的大鲤鱼或大乌鱼来。割稻子或割麦子,不定什么时候就碰见一窝秧鸡蛋,鹌鹑蛋,或者刚出窝的小秧鸡,小鹌鹑,都是惹人喜欢的家伙。这些并不难理解,因为小河也在稻田里流淌,或者说稻田也是小河的另一种流淌形式。
7
如果说,有两条河从村边流过便觉得幸福无比,那也太不江南了。江南之所以如同美人,饶有风韵,是因为她不只是让你只能以最低水平维持生存,最重要的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把各种享受不经意地送到你面前,直到你把最惬意最富有风情的享受当成平常日子。
虽然两条河都清澈得不得了,抬手一舀就能喝,但其实我们并不喝河里的水,我们喝的是两条小溪里的水。
假如我的村庄是一个人,其实村东村西两条河只是他的外衣,两条小溪才是内衣,因为两条小溪在两条小河的里面,是从村边流过的。所以从汀泗桥到我们村,除了要过两座大石桥,还要过两座小石桥。
村东的小溪很长,水势也不小,是小河流出幕阜山时,就着山势筑了一个小土堰,把河水引出来一溪,如同美人梳头,将头发分出一绺挂在耳畔那样。这一溪流水则又如同一条长长的藤蔓,在白羊畈上一路蜿蜒而来,两岸结满了村庄。
小溪流到我们村东,在小河码头边的大枫树底下流到村后的田畈上,就算是没了,再从稻田里流进柳林,从柳林里再流进小河。
村西的小溪流的是泉水,泉水是从我们村前畈上的稻田里涌出来的,为了饮用,在几个泉眼旁边,大约有两间厢房大小的稻田就不种了,一年四季,泉边都长满了绿茵茵的青草,十分秀气可人。
这是几个神奇的泉眼,它们并不是固定的,有时三、四个,有时七、八个,越是天旱时泉水就越冒得凶,趵突出来像一个个大南瓜。越是下雨,它们就越小,像小孩儿们吹气泡泡。所以我们村的畈上任何时候也不缺水,旱涝保收。
小溪从村边绕过,村边有青石砌的码头,二十米长,吃水,洗菜,淘米,洗衣,都在这里。水是甜的,越是三伏天越凉,几同井水。因为也是从柳林里流进小河,小溪里也有鱼,而且也有大鱼。儿时没事就到小溪里去,用淘米的筲箕撮鱼,那是我们的最爱——小溪简直就是呵护我们农家孩子长大的幼儿园阿姨。
那时候人口也不多,小溪对于我们很神秘,两岸几乎什么都有,有小毛竹林,有美人柳,有野蔷薇,有桃树、李树等。阳春三月,妖桃艳红,李白素洁,桃李隔溪牵手而恋,一路花明柳暗,岸草萋迷,随水起伏扬抑。我们钻进小溪,就如同钻进地道,里面幽香如麝,只有斑斑点点日脚,即使伏天,也是凉荫袭人。
那时候的自然有人性,人在自然的怀里,如同在母亲怀里。
那时候的人有自然性,自然在人的怀里,如同在爱人怀中。
8
最提心吊胆最盼望最紧张的,就是“闹港”的日子。
“闹港”是我们那里的土话。 我们土话称河叫港,“闹港” 就是闹河。所谓闹河,就是将磨好的巴豆在某一处河滩上一撒,巴豆顺流而下,下面一截河水里的大鱼小鱼就全被药昏了,但是没死,这时赶紧顺流而下,一路大网小网,尽情捕捞,就能捕捞到用别的办法无法捕到的大量的鱼。
夏秋是闹港的最佳季节。闹港一般都很秘密,几个年轻人一商量,定好时间、地点、规模就行了。找个地方偷偷磨好巴豆,到下半夜,再偷偷到既定的河滩,将磨好的巴豆往河里一撒,赶紧点亮马灯、火把之类,顺流而下,一路在各个浅滩上设网拦截捕捞。大约两三里地,药性没了,就迅速撤兵。
这叫头水,就是这几个主事者趁着巴豆的药性的有效时间,将该捕到的大鱼都捕到了。这头水之肥,肥得让人嫉妒。要是鱼情好,就这么一会儿,就这么两三里地,十来几处河滩,就能捕到七、八担鱼,都是大鱼。
许多时候,是一直到河边亮起了马灯、火把,我们才得到情报的。等到我们七手八脚赶到河边,人家头水已经得手,担着鱼回家睡觉去了。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捡鱼的兴致。头水并不能把所有的鱼捞光,一般情况下,最多只能捕到百分之四十或者一半,剩下的鱼就成了附近几个村庄所有捡鱼者的猎物。这时候,那个热闹,简直比过年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小河上下,就那么两三里地,灯笼、火把、马灯、手电,到处乱晃。笑声、吆喝声、尖叫声、骂声、哭声乱成一片。岸上、河滩、深潭边,到处是人,各自拿着无奇不有的家伙,包括锅碗瓢盆,到处捡鱼。这般热闹从下半夜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甚至下午。只要天气不太热,有时过了几天,河里还有鱼可捡,我们放学回家,时常能捡到鱼。
第二天上午,男人们都在睡觉,家家妇女们都在门口收拾鱼,一面收拾一面讲述自己家男人或孩子捡鱼的得失与奇闻。这一天是家家吃鱼,家家晒鱼,家家说鱼。
哎家乡,家乡的河……
哎家乡,家乡的鱼……
9
李泽夫是我小学时的同学,他们麦园李村在我们村西头,就在河边,与我们隔河相望。在村头扯一嗓子,互相都听得见的。
他长我两岁,没想到长大之后,他娶了我一个堂姐的女儿,于是我成了他的舅舅。
有一年秋天,我回家休假,到他家去做客。多年不见,他成了个地道的农民,里里外外,听着我侄女调遣,迟钝得有点木讷的样子,使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从北方回去,算是稀客,他一家人忙里忙外地招待我。没想到李泽夫凑到我身边,神秘兮兮地轻声说:
“呃,想不想下河?”
在黄土高原上钻过来钻过去好多年,身体和感觉都已然没有了家乡水气,一听见这少年伙伴如此亲切的言语,不觉眼泪都来了。一霎间,儿时与家乡河的种种亲昵都涌上了心头,我想都不想就说:
“走,走走,下河。”
亲人们顿时都叫起来:“天都黑了,就要吃饭了,这时刻还下什么河?快,快摆桌子吃饭!”
李泽夫不理睬那些嚷嚷,拉着我出门,在门口提起一个鱼篓,鱼篓里早备好了能装四节电池的长电筒,扛起一个篾做的大鱼罩,就往河边跑去。
他们家就在河边,下几级石板坎儿就到了河岸。
这时候天黑下来了,天上月亮、星星都出来了,但时时有云遮着,四下里时明时暗的。我们不管那些,在河边踢掉鞋袜,顺着小路就下到河里。这时候的李泽夫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屁股上吊着鱼篓,右肩扛着鱼罩,猫着腰,也不跟我说话,左手拧亮长电筒,在水里机警地寻觅。那架势,如同侦察连长在执行任务。
这时候的河,在朦胧月光下,十分迷人。刘方平在唐诗里说:“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我这里不是,我这里是“朦胧月色半床河,柳在河边月在波。”
我紧跟在他身后,看着他屏住呼吸的样子,由不得也紧张起来。我因为从小母亲就管得很严,在伙伴中玩水不算好手。不会玩但我会看,看哪一种架势属哪一等行家。李泽夫从小在这一带就是有名的水上好手,但到底功夫好到什么地步,我还真没见过,现在与他一起下河,我心里充盈着久违的激动。
突然,李泽夫飞快地把鱼罩倒到手上,像一只剽悍的非洲豹,打着手电,在河滩上飞一样地狂奔。我在后面紧跟着,但一下子就拉开了好长一段距离。只见朦胧月光下,他轻捷无比,矫健无比,踏浪如飞,两扇溅起的浪花被月光照得透亮。一气冲出去20多米,干净利索地将鱼罩罩在浅滩的鱼草上。待得我急匆匆跑到他身边,他已经从鱼罩里掏出条足足两斤多重的大鲤鱼来。
“嗨呀,好大!”我激动得语无伦次。我没想到他如此身手,只是高兴得乱说乱笑一气。
李泽夫扬起头,神气十足地笑着,骄傲地说:“你们叶家也有几个好手,但比我……嘿嘿……嘿嘿……”
话未落音,他突地转身,手电光直照在水面,他一声不吭,紧追不舍,只跑了十几步,一罩下去,就伸手到罩里掏鱼。
“罩着了吗?”我边叫边跑过去。
“当然。”他笑着提起一条金色的鲤鱼,往鱼篓里一扔。
我赶到他身边,见那条金色的鲤鱼湿漉漉的,在鱼篓里拼命地跳,十分可爱。
“真好看哪,这条鱼别吃,拿回家养着。”我说。
“不行不行,”李泽夫笑着摇头,“这金鲤鱼性子刚烈,你不晓得吧?你看它,拼命地蹦吧?一直蹦死为止,养不活的。”
说话间,那条金鲤鱼嘴角已经撞得流血了,但它还在舍命地蹦。我眼圈湿了,我把鱼篓从李泽夫腰间解下来,双手捧着,一直看着那条金鲤鱼跳得不能动为止。
大约半小时光景,李泽夫就凭着一个手电筒,一个鱼罩,就大大小小抓了十来条鱼,最小的也有半斤多。那敏捷的身手,让我大饱眼福。
回家的路上,他自豪地说:“我家里都习惯了,这时候葱姜都备好了,就等我的鱼下锅呢!”
我笑着说:“你真是个河神,哎哎,我就封你为河神。”
李泽夫笑起来:“要说,我还真是个河神。你们村,还有上边涂家,还有郭家湾,好多高手都不服气,都跟我比试过,没一个有我这本事。”
“那你这辈子油盐零用钱是不用愁的吧?”
“愁大了!”我一句话没问好,勾起李泽夫的往事。他停下来,指着月光下闪闪的小河波光,“就差没送到嘴边来的鱼,就是不让搞。说鱼是资本主义,搞鱼就是搞资本主义。家里连买油盐的钱都没有,我穷得实在没法子了,偷偷到河里弄了两回鱼,还把我绑到公社去批斗。”
“真的?”
“不真的我哄你干什么?把我吊在公社那堂屋的房梁上,喊着口号斗了小半天,还挨了几扁担,放下来还逼着我到河里去抓鱼给他们吃!”
“真的?”
“狗日的们!两个基干民兵拖着枪押着,我抓了满满一鱼篓鱼,十几斤,一直送到他们公社食堂,才放我回来。”
“那他们不也吃资本主义了?”
“是呀,我也是这么问,你猜他们说什么?说,资本主义被我们吃了,不就只剩下社会主义了吗?”
10
我需要以生命的名义,庄严地感谢1954年那场长江特大洪水。
当洪水以滚滚的巨浪吞没了汀泗桥,整个汀泗桥只能看见波涛上的楼顶时,我们村后河边的稻田也被淹没了。那时候正是八月,稻子已经黄了八、九成,母亲和二哥没日没夜地用竹竿撑着扳桶与洪水赛跑,在洪水淹没稻子之前把稻穗抢割回来。洪水到我们村已然是强弩之末了,涨势不快。那时还没有合作社之说,母亲和二哥终于抢在洪水之前,把稻穗都割回来了。
洪水的最高水位到了我家门槛,没进家。
那年我十岁,母亲怕我出事,在洪水快进村的日子里,把我送到八里地以外二哥的未婚妻家放牛去了。她们家地势高,没有危险。
十来天后,洪水退了,二哥便急急忙忙把我接回家了。
谁也没想到的是,洪水退的时候竟出现了奇观。
原来村里不知道是谁最早发现,村后田畈上,水田里竟有大量的江鱼。这一发现非同小可,全村人几乎家家都到被洪水淹过的自家水田里去淘宝。我家也有不少被洪水淹过的稻田,母亲和二哥忙不过来,赶紧把我接回来帮忙。
那是我这辈子看见鱼最多的一次。
几乎每一丘田里的鱼都成了鱼粥,大的有近一米长。其中有些很长的鳗鱼,平时是看不见的,大人们说是海鱼。洪水在慢慢地退,而鱼不仅不跟着水一起退,反而拼命地争着抢着上水。一丘田里的水退干了,大鱼小鱼就在田里乱蹦乱跳,那情景十分壮观。
我们家在河边有好几丘田,其中有一丘大田叫三斗二,我们娘儿仨,仅在这丘田里就挑回来好几担鱼。有些大鱼力道可足,好多回把我掀翻在田里。
与上半年几乎天天下雨相反,洪水发过之后,老天爷仿佛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几乎天天都是万里无云,毒太阳晒得地皮烫脚。那些日子,既忙着割稻子,晒稻子,又要收拾鱼,晒鱼,家家忙得热火朝天,像过年一样。
那一年,全村家家都晒了数量极可观的干鱼。但绝大部分人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先后把干鱼都卖了。我母亲是个藏得住东西的人,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也舍不得卖鱼。没想到1958年大跃进之后,连续三年大饥荒,这些干鱼救了我们一家人,村里有的人家实在饿得没了法子,母亲就送几条鱼过去救命。
我需要以生命的名义,庄严地感谢1954年那场特大洪水,感谢洪水送来的那么多鱼,那么多帮我们熬过了三年大饥荒的救命鱼。
11
我还需要以诗的名义,庄严地感激1959年那个除夕之夜,感激那个除夕之夜家乡的河送给我永生永世无法忘却的感受。
1959年,“大跃进”进入到了极其艰难的时期。二哥在外面修铁路,嫂子在外面修水库,家中只有母亲带着个一岁的侄女。家家没有隔夜粮,母亲饿得全身浮肿。我上初中,家里拿不出一分钱交学费和伙食费,我只得在县城做小工,勉强维持。放寒假回家,见母亲饿成那个样子,我放声大哭,坚决不上学了,要回家帮母亲一把。可怜母亲以死相拼,非要我继续上学不可,并要我赶紧在寒假中多挣点学费。
母亲把我不想上学的情况请人搭口信,告诉了在几十里外修铁路的二哥,二哥急了,告诉领导,想请几天假,回来帮我挣点学费。可是“大跃进”期间,天天都是“革命”,根本请不动假。眼看到了除夕,二哥横下一条心,与一个堂兄一起,从工地偷跑,到崇阳山里放竹排出山来。母亲知道了,赶紧叫我提一大土罐子野菜粥,到村东水码头去接哥哥。野菜粥里有不少红薯,是我年三十上午,带领全村孩子到麦圆李村一块没有挖过的红薯地里,把人家的红薯偷回来,才有了这顿年饭的。母亲不能去,母亲和侄女还在生产队的仓库排队,领大年初一的口粮。
除夕之夜,我一个人站在水码头上。北风呼呼地从河面席卷奇寒,迎面如狼似虎地扑来。那年冬天特别冷,饥荒岁月,大年三十的年饭,母亲、侄女和我也就喝了几碗野菜粥。我冻得直跺脚,但是不敢轻易离开。大冷天在河里放竹排,那是什么滋味?二哥能受得了么?我又心焦如焚。
除夕之夜,我一个人站在水码头上。那是一个死寂的夜,没有鞭炮,没有笑声,全村人都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排队,等候到大队部去喝酒的生产队长和会计回来分口粮。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等待哥哥,我不敢让人知道我在等待哥哥,因为哥哥是为了我的学费,从“革命”的工地偷跑回来放竹排的,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大祸就要临头。
除夕之夜,我一个人站在水码头上。我不知道站了多久,我已经全然麻木了,肚子里几块红薯敲打着难耐的饥饿,我一会儿禁不住望一望土罐子里的野菜粥,依得我肚子里那饥饿的野兽脾气,我可以把一罐子野菜粥一气喝得精光,那年月,肚子撑破了也饿。可是我不敢,我知道两个哥哥在河上挣扎了大半宿,又冷又饿,就等着我这罐野菜粥接济点力气,才能把竹排连夜放到汀泗桥去。
这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个除夕之夜。
一直到下夜,两个哥哥才驾着竹排,终于在河上出现了。两个哥哥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冻得直打哆嗦,上下牙冻得格格地响,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但是,见到野菜粥,两人就不顾一切,搬起土罐,坐在青石板上,你一口我一口,亡命地喝起来。那粥已经凉透了,但两人依然喝得津津有味。见粥里有红薯,像见到金子似的,就用五指将军,掏出来往嘴里塞,好几次都噎住了。
喝完粥,两个哥哥大约身上有了点热气,摸着肚子喘了几口气,也顾不上说句话,又拿起竹篙,跳上竹排,往下游而去。
我站在水码头上,禁不住呜呜地哭,二哥回过头来,死命地吼一句:
“要——读——书……”
12
几十年过去了,家乡的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变了。
村子里的老树,砍得一棵不剩,说是破除迷信。连那两棵最老最大的像夫妻一样的枫树也砍了。因为村里人一直以来认为那两棵树是我们的祖先,逢年过节,都到树下去祭祀。
叶家岭上一山的树和竹子全没了,大队建起了一座砖瓦厂,大队与生产队利益分割不清,亏本,不干了,只剩下一个大烟囱。
村后那一片迷人的柳林,砍得一棵草也没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被汀泗桥人砍去炼了钢铁。
几十年间不断地修河改道,把两条河都拉直了,河再也不在村边了,村边的那一截河道成了死水湾。最重要的是河水再也不能喝了,河里,连一只虾也没了——全被污染了。
河里是这样,田畈上也如此。一代一代都被视为村里最上等粮仓的田畈,现在竟然荒芜了,田没人种了,好多田都闲在那里,胡乱长满了野草。
畈上的水沟里还是有水,但水被污染了,不能喝的。畈上别说没有泥鳅,没有鳝鱼,没有田螺,没有秧鸡、鹌鹑,怕是连细菌都没了。村民们都在自己家打井,家家吃井水。
有点本事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去了,村里只有老弱病残孕。
说来话长,说来心痛,痛得跟碎片似的。
我们村是标准的江南农村,历史上只要把田种好,就什么都有了。所以我们村世世代代都只会种田,以种田为荣。老辈人插一上午或一下午秧,上田塍时只把手脚在田边或溪边稍微一摆,趿上鞋子,便像作客回来一样干净。我们养成了根深蒂固的种田意识,全村每一代人只有一个残疾人学剃头的,其他什么手艺都不学,不但不学,还以学手艺为耻,认为是不学正经。
一改革,一开放,这地面上的人全傻了。地道的农民,连出去打工的本事都没有,他们一生都没离开过村庄,汀泗桥就是他们的省会,县城就是他们的首都。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怀着一种天生的恐惧,他们只能在这里存活,一离开这方地面,就像鱼离开了水,就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如何生存。
整个村庄像一条脱了水的鱼,暴露在三伏天的毒太阳底下,奄奄一息。
去年回家乡,在河边看到村里岁数最大的一位老人。八十多岁了,他在河堤上搭了一个简陋的窝棚,独自在河里放鸭子。一年四季,就在窝棚里睡,在窝棚里搭锅做饭。我问:
“放了多长时间了?”
“十几年了。”
“时常到村里去吗?”
“不去,懒得去。”
“不想乡亲们吗?”
“不想。不想看见他们,看见就烦。”
“他们来看您吗?”
“想来就来……”
“过年也不回去吗?”
老人嘴角动了一下,想笑,但没笑出来。好大一阵儿,才坚决地摇了摇头,说:“不去!”
老人大约很少与人说话,说起话来舌头都不灵活了。他跟我说话时不时望着村里,村庄就在他眼前,但他望着很漠然,一副要与之抗争到底的架势。
我不敢问为什么,怕触动他的伤心事。我坐在他的草铺上,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紧握着我的手。好半天,他忽然说:
“文福,明年再回来,再不回来,就……看不见了……”
13
我有个习惯,写作感到累感到乏,或者是在构思某个问题的时候,就转过身,在写字台边练练书法。就在写这篇文章的这几天,满脑子都是家乡的河——以前的河,现在的河,不知为什么笔底下竟无意识地写了两幅字:
“还我河山。”
“总想流泪。”
我不知道怎么就写了这么几个字。这时刻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恨我自己,我为什么如此地不会藏私?怎么就不会像那些聪明人一样坚决地将自己包装起来,伪装起来,像郑板桥那样糊涂起来?把流行的假话说得钢钢地,却来说这些左边的耳朵不爱听的鬼话?
岳飞怒发冲冠,是向金人长啸,向金兀术长啸:“还我河山!”我向谁长啸?向化肥?向农药?向时代?向科学?向愚昧?
“总想流泪。”几十年来,我的潜意识里大约就是时时刻刻地、分分秒秒地想让自己的泪水多流一点,多流一点——
流……到……家……乡……河……里……去……
而今,不知是我在哭你
还是你在哭我
你的泪在我身上如此龌龊
我的血在你河床里如此混浊
——哦,家乡的河……
这世界,我只不过是个过客
有没有我,生活每天照样生活
可是,这世界要是没有了你
子子孙孙,这日子,该怎么过
——哦,家乡的河……
我写不下去了……
2009.2.19 —2009.3.5于北京三叶宫
责任编辑 王社平